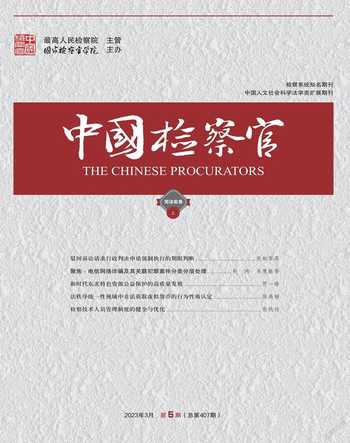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難點與應對
壽志堅 翁音韻 宋珊珊
摘 要:基于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所呈現的犯罪組織形態復雜化、犯罪踞點跨域化及技術手段智能化等趨勢特點,該類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存在“認罪”范圍確定難、“從寬”尺度把握難、量刑要素平衡難等諸多難點。應以“分類”處理還原拆解產業模塊,準確定罪,以“分層”處理厘清犯罪組織、個人層級,為該類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建立體系清晰的底層結構,進而探索建立“認罪”范圍的判斷標準,設置“從寬”減讓梯度以及明晰共同犯罪量刑平衡的具體規則,回應紓解制度適用的現實難點。
關鍵詞:電信網絡詐騙 認罪認罰從寬 分類分層
一、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難點
當前,伴隨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行動的深入推進,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數量快速增長勢頭得到有效遏制,但形勢依然復雜嚴峻,且呈現犯罪組織發展形態復雜化、犯罪踞點跨域化、犯罪技術手段智能化、遠程化等新的趨勢和特點,引發網絡語境下共同犯罪意思聯絡及共同犯罪行為、地位作用認定等特有難題,并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帶來諸多難點。
(一)共同犯罪意思聯絡認定難導致“認罪”范圍確定難
隨著網絡黑灰產業的不斷成熟,完整犯罪過程被精細化拆分,形成大量專注特定領域的犯罪模塊,主要包括資金業務、網絡黑灰產、通訊技術、網絡服務這四大模塊,各模塊兼容性和復用性極強,模塊之間臨時或長期組合成“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的協作關系,但由于各模塊相對松散、獨立,可根據犯罪需求隨意搭建,使得共同犯罪中各模塊之間的意思聯絡與傳統犯罪相比粘連度低。犯罪手段與信息技術的同步迭代更新,使犯罪手段得以裂變式傳播,形成松散的犯罪網絡,共同犯罪行為人達成意思聯絡的方式更加隱蔽。此外,因共同犯罪同案犯到案時間往往不同步,部分先到案行為人的供述完整性、真實性較難印證,且可能會被后到案行為人的供述推翻,行為人系事前幫助、相對獨立還是事后協助行為,其定性難度加大,直接影響到對共同犯罪“認罪”中“如實供述”的范圍和內容的準確把握,如供述內容是否應當含括上下游、平行或關聯犯罪團伙的相關犯罪事實等。
(二)共同犯罪認罪認罰不同步導致“從寬”尺度把握難
1.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跨國式有組織犯罪與產業化特點疊加,在國內外分工協作上,往往犯罪團伙的組織領導者藏身境外,并在境內誘騙招募低學歷、在校大學生等至境外實施詐騙行為,上游售賣提供信息、“兩卡”以及網上引流推廣等團伙以及下游轉款取現等行為人在境內。“引流”、售賣“兩卡”等前端團伙成員往往最先被司法機關抓獲,詐騙犯罪團伙的組織領導者常年不入境,抓獲到案難度大,而其他一般參加者在案發后先行到案,對其中的首要分子、主犯、從犯、脅從犯的認定存在一定難度,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可能致“從寬”尺度把握不準,如本應認定為主犯的未予認定甚至認定為從犯,而給予了不相符的較大幅度的“從寬”。
2.囿于共同犯罪行為人是否認罪認罰以及認罪認罰所處訴訟階段、程度、層次不同步,特別是在數人共犯一罪的類型中,可能會出現共同犯罪行為人之間關于認罪認罰層次上的差異,如其中一人或數人僅“認事實”,或“認事實+認罪”,或“認事實+認罪+認罪名”,以上三種情形都是不完整的認罪認罰形態,未構成“認事實+認罪+認罪名+認量刑”四層次完整形態。[1]在共同犯罪行為人不具備認罪認罰的完整形態,但均在不同程度表明了其對行為的主觀認識和悔罪態度的情況下,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這些行為人的處理也應當體現從寬的精神。但是,不同程度、層次的認罪認罰“從寬”梯度如何科學合理設定,亦是實踐中的難點。
(三)認罪認罰與其它共同犯罪量刑要素交織導致量刑平衡難
共同犯罪案件中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還面臨著僅部分共同犯罪行為人認罪認罰、認罪認罰與坦白、自首等量刑情節交織等復雜情形,一定程度限制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空間。實踐中,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中,僅有部分共同犯罪行為人愿意認罪認罰而其他共同犯罪行為人不認罪不認罰的情形并不鮮見,也是量刑難點所在。一般來說,對于從犯認罪認罰,主犯不認罪認罰的,不存在量刑平衡難以把握的問題,主要是對主犯認罪認罰而從犯不認罪認罰的情形,可能與自首、立功等量刑要素雜糅,致使從寬尺度難以把握。
二、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分類分層處理的價值與方法
(一)分類分層處理的內涵與價值闡釋
本文所稱犯罪分類的旨趣在于解決定罪問題,而犯罪分層則聚焦量刑問題,即“分類”系根據犯罪性質界定不同環節犯罪行為的罪名;“分層”系在分類的基礎上,根據犯罪嚴重程度等實質化標準,區分同一犯罪的不同層次,予以區別處理的一種手段方法。
從價值內涵看,分類分層處理不僅本身蘊含提升司法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的獨立價值,而且對準確厘清網絡語境下共同犯罪的組織結構形態及個人責任認定具有重要的工具價值。具體體現在,分類分層可以作為網絡語境下共同犯罪案件處理的方法策略,去厘清共同犯罪產業模塊、組織關系架構和犯罪個體層級,還原拆解黑灰產業鏈條,對犯罪團伙、犯罪個體的地位作用進行精準定點、畫像,為共同犯罪行為認定、罪責相當、量刑均衡繪制清晰、客觀的底層圖,為進一步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科學、合理、規范適用奠定基礎,從而實現司法辦案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
(二)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分類分層處理的具體應用
1.分類:還原拆解犯罪產業模塊。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除去核心“詐騙”實施環節,“上游”鏈條多形成“信息”“技術”“引流”等服務模塊,“下游”多為通過地下錢莊、非法第四方支付平臺等“洗錢”服務模塊,由于犯罪產業鏈各犯罪模塊參與人的主觀明知狀態和具體參與時間節點不同,根據實踐經驗難以一并認定詐騙犯罪,還可能涉及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因此,需根據不同犯罪環節,判斷犯罪模塊的犯罪性質,準確認定罪名。
2.分層:全景式掃描犯罪組織及個人。基于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組織結構、人員關系的特殊性,可從犯罪組織架構、共同犯罪參與人兩個層面進行分層。
一是厘清組織結構關系。根據共同犯罪故意的聯系緊密程度、共同行為的聯系方式和社會危害程度等共同犯罪者組織結合程度的不同[2],對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組織架構形式予以區分,認定系一般共同犯罪、犯罪團伙還是犯罪集團。實踐中,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多數系以團伙或犯罪集團形式作案。在認定共同犯罪組織形式后,再從縱向、橫向等不同的維度,進一步梳理組織內部結構關系,如系單一縱向型,還是“一對多”縱向與平行混合型,對各犯罪團伙系平行獨立還是交織的關系等作出判定,從而準確界定團伙責任范圍。在集團作案案件中,對集團內部又分立若干時空上獨立的犯罪小組,考慮到互為獨立的犯罪小組在詐騙場地、成員及管理上均相互獨立,客觀上并無相互之間產生協作和促進等客觀事實,對“犯罪集團-犯罪小組”進行分層分組后,將詐騙成功金額區別計算,而不是簡單籠統處之,更加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二是準確定位犯罪個體層級。在劃定團伙框架結構的基礎上,根據各個團伙內部成員的地位、作用、參與程度等進行分級,區分不同對象以及從嚴打擊重點和從寬處理范圍,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其一,以地位作用區分主從犯。根據各個體的地位和作用區分主從犯,對起組織、指揮和管理作用的認定為主犯,對被指示參與到某個具體詐騙環節等起次要作用的認定為從犯。再如認定資金結算團伙中指示他人轉移資金的認定為主犯,對受指示提供本人銀行卡并實施轉賬的認定為從犯。其二,對地位作用區別確實不明顯的,可以不區分主從犯,但應當充分考慮反映其可譴責性、人身危險性等量刑要素,如參與時間長短、非法獲利大小、初犯偶犯、是否為在校學生等,準確界定其個人責任。
由此,“分類”通過準確認定犯意聯絡、犯罪行為等確定犯罪事實,服務于判斷認罪認罰從寬的“認罪”要件,而“分層”的技術構造本質是為了解決量刑均衡問題,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核心問題“量刑優惠”目標上是一致的。通過對犯罪模塊的準確分類以及犯罪組織結構和犯罪人員的分層分級,可有效破解網絡語境下共同犯罪行為人犯意認定難、從寬尺度把握難、量刑要素平衡難等難點,從而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該類犯罪案件中的適用。
三、分類分層處理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難點的回應與紓解
共同犯罪行為人準確的刑罰裁量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價值實現的核心所在,其主要涉及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哪些行為成立共同犯罪,二是共同犯罪行為人身份及責任認定。以分類分層處理為中心,厘清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產業模塊、組織結構、共同犯罪行為人層級,尋找到該類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連接點與契合點,本質還是要落腳到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難點問題的回應解決上。具體而言,需要將目光聚焦到“認罪”范圍的實質把握、“從寬”幅度的合理設置和量刑均衡的路徑設計上。
(一)建立以分類分層為基礎的“認罪”范圍的判斷標準
認罪認罰從寬中的“認罪”范圍除了如實供述其本人的犯罪事實,是否應當包括對同案犯及其犯罪事實的供述[3],關鍵在于對共同犯罪事實的確認。具體到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要落腳到對共同犯罪行為人犯意聯絡的合理區分與界定。通過對該類案件分類分層處理,還原拆解犯罪產業模塊、厘清犯罪組織結構關系,可以有效界定上下游犯罪關聯交織程度,準確認定系共同犯罪、獨立犯罪還是事后協助犯罪,從而判斷供述是否符合“認罪”的實質要件。如對于事前共謀、事中聯絡,上下游產業交織的,以及可以證明行為人應當認識到與他人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且后者有同樣參與認識,或行為人應當概括認識到共同行為的性質和結果,或是行為人應當概括地預見到共同犯罪行為與共同結果的因果關系的[4],則“認罪”范圍應當包含其所知的同案犯及其犯罪事實。但對在案證據無法確認犯意聯絡又或是犯意聯絡粘連度低的,僅供述本人犯罪行為的即可認定符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罪”要件。
(二)探索設置分類分層處理后認罪認罰“從寬”減讓梯度
檢察機關在具體考量“從寬”幅度時,要區分各共同犯罪行為人地位作用,綜合考慮從寬因素,確保罪責刑相適應。其一,準確區分層級對象。由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多呈現組織架構龐雜、參與者眾多、分工細化等趨勢特點,在對“從寬”幅度考量時,應根據共同犯罪組織層級結構,界定各行為人責任邊界及地位作用,從而正確區分主從犯,劃定刑罰檔次。如按照“組織領導者-積極參加者-一般參與者-特殊參與群體”的標準區分各自地位作用,對組織領導者,依法從嚴懲處;對積極參加者,嚴格限制從寬幅度;對一般參加者,綜合考慮從寬因素;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特殊群體,犯罪層級較低,參與時間不長,非法獲利較少的,給予更大幅度的量刑優惠,乃至作出罪處理。其二,在遵循認罪認罰所處訴訟階段越早、越穩定、越徹底則從寬幅度越大這一梯度性從寬政策下,充分考量認罪認罰層次的完整程度,設置差異化從寬優惠幅度,如對“認事實+認罪+認罪名+認量刑”四層次完整的認罪認罰設定減讓幅度上限,其余每缺少一個層次扣減相應從寬幅度。其三,結合全案事實,綜合考慮各種量刑要素,可以“是否具有起訴必要”“是否可能適用緩刑”為標準,在訴前分流及刑罰執行方式上予以分層處理,如對符合不起訴條件的作不起訴處理,對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依法提出適用緩刑的量刑建議。
(三)明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共同犯罪量刑平衡的具體規則
根據我國現行相關法律、司法解釋及指導意見,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運用,主要遵守以下一般原則:如果沒有特殊理由或例外情況,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均應得到從寬處理。而“特殊理由”的內涵,主要是指“犯罪性質和危害后果特別嚴重”“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等情況。[5]因此,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只要共同犯罪行為人滿足認罪認罰的條件,且不存在上述特殊理由,就應對其作從寬處理。但應限制認罪認罰相關情節總體從寬幅度,避免為提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而對同意認罪認罰的共同犯罪行為人片面強調從寬,使打擊犯罪的價值無法真正體現。特別需要關注以下兩點。一是主犯認罪認罰而從犯不認罪不認罰情形的處理規則。對該類情形,若無法定理由,主犯從寬后所承擔的刑罰一般不得輕于從犯。但是,刑罰體現并平衡多重價值,對主犯、從犯刑罰的確定,也需要考慮多種因素。如主犯可能具有重大立功、自首等從寬處罰情節,若按照量刑方法,主犯的宣告刑確實低于從犯的,在量刑上可以采納。但對于該類主從犯刑期倒掛的特殊情形,應當通過建立相應的內部審批機制等進行監督制約,以防止司法量刑的恣意。二是認罪認罰與其它量刑要素的綜合考量。對于不宜區分主從犯的,在確定具體從寬幅度時,仍應當充分考量各種量刑因素,如直接參與詐騙成功金額、非法獲利等,為不予從寬、限制從寬、予以更大幅度從寬的適用提供依據。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第四檢察部副主任、三級高級檢察官[200001]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四檢察部三級高級檢察官[200001]
***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二級檢察官助理[200001]
[1] 參見汪海燕:《共同犯罪案件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問題研究》,《法學》2021年第8期。
[2] 參見林文肯、茅彭年著:《共同犯罪理論與司法實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 58 頁。
[3] 參見劉亦峰、周云:《論共犯認罪認罰案件中的被告人供述:界定、范圍與性質》,《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
[4] 參見劉守芬、丁鵬:《網絡共同犯罪之我見》,《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5] 同前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