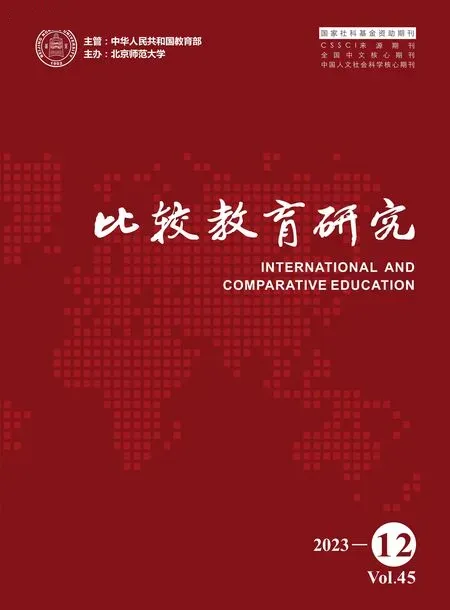把學還給教:比斯塔的教學觀意蘊
熊華軍,楊旭
(1.西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甘肅蘭州 730070;2.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廣州廣東 510665)
格特·比斯塔(Gert Biesta)被認為是當今歐洲教育哲學界一位富有遠見的思想家。他敏銳地發現,當前學校的學習變得更具有“交易性”特質,被打上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經濟交易的烙印,以滿足學習市場的需求。他認為,完全用“學”替代“教”的教學理念是一種非教育性思維方式,其副作用是弱化教師的作用,也動搖教學的根基,勢必造成“教學的消失和隨之而來的教師的消失”[1]。德里克·福特(Derek Ford)認為,比斯塔提出的“教育”和“學習”之間區別的觀點是非常有價值的。[2]比斯塔深刻地分析學習異化現象在教學中產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提出“把學還給教”的教學觀,希望恢復教學應有的重要性,重新認識教師的不可或缺性,將教學權力交回教師手中,從而將學生引入真理的世界。
一、教的祛魅:學的異化
這是一個終身學習的社會,學習已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強音。信息技術構筑起環繞現代教育的學習幕墻,改變傳統的教學理念和方式,從以教為主轉變為以學為主,將全民和全時的學習異化為學習化(learnification)。
(一)異在何處
在比斯塔看來,由于國家政策、社會需求、技術發展等原因,學的異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學生同自己的學習成果相異化。學生通過認知、掌握、理解和應用學習內容,逐漸積累并形成自己的知識體系,其學習成果往往呈現差異性和多樣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無法以學習階段為節點精確衡量。而在當下的教育中,學習結果已經被徹底量化,以數字、表格、區間分布的方式呈現。學校在量化或循證的教育評價體系之下視學生為產品,好的產品合格出廠,有瑕疵的產品被放棄。將學生所有學習中的過程、變化、發展轉化為0~9的數字組合方式來展示全部的學習成果。 冷冰冰的數字體現出的是去“人”的殘酷表象,掩蓋學生的差異性,增加由這些評價結果給家庭帶來的心理焦慮和社會壓力。
第二,學生同自己的學習相異化。亞里士多德在談到學習時說,“求知是人的本性”[3]。學習應是學生自主超越自身發展的需要,自為把握世界真諦的需要,是他們主動地和外界交換信息,不斷成為更好的自己的行動。而學習異化首先表現為一種規定性的學習,學習內容是被加工的,學習目標是被預設的,學習過程是被監管的。其后果是學生的學習意志被政策驅使,而不是由興趣、動機激發與引導。其次,學生未來的可能性被剝奪,其主體性生成被壓制,成為受控客體,讓渡自身的學習權利。在此情形中,學生不會自主履行學習義務,而只是機械式按部就班地學習。所以,學習異化讓學生學習不自由。
第三,學生同自己類本質相異化。馬克斯·舍勒(Мaх Scheler)認為,完整的人就是在生命精神化和精神生命化的過程中向世界無限伸展與開放,即“人之為人的本性不是給予的和前定的,而是在人的生成過程中自己創生的”[4],是生命和精神的相互結合“無限生成小宇宙”而存在于世界中。但學習化卻將學生視為可物化的消費者,將學習看作可消費的商品。學習和學生是經濟交易關系,學生從教育市場購買高度商品化的學習產品,從而陷入封閉的交易行為中。人和知識成為對立面,成為馬克思所說的人與自身的創造物的對立,所以學習化將學生在世界上發展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第四,學生同教師關系相異化。學生與教師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教學中是獨立的兩個主體,學生需要在教師的“教”中從不成熟狀態逐漸變為成熟的主體。但學習異化打破兩者之間的應然關系,學生成了教學的唯一中心。“教育被解釋為教學和學習,學生被解釋為學習者,教師被解釋為學習的幫助者,學校被解釋為學習環境。”[5]這種嚴重的學習概念泛化現象,稀釋了教育、教學和教師的重要性,將學生盲目地推向客體位置,與教師、世界相對。被異化的教師變為知識的儲存器,被動地由學生索取,逐漸失去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為何異化
學習化讓學生學習過程被控制,學習結果量化,學生自身被同質化,學生和教師關系對立。學的異化導致“教”讓渡給“學”,“學”成為教學中的主旋律,由此“教”被“學”所規訓,教育語言也完全被學習語言所取代。在比斯塔看來,造成學的異化有如下深層次原因。
第一,后現代主義的洗禮。后現代主義認為不存在客觀的自然現實,邏輯和理性僅僅是概念性的建構,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篤信“根據知識和實踐的辯證關系,只有當學校的知識建立在學生已經擁有的文化資源所產生的隱性知識之上時,課程才能最好地激發學習”[6]。后現代主義倡議學生要掙脫教師權力,爭取教育解放以便獲得知識自由。“教育解放”消解教師和學生的緊密聯系,使教師在教學中的作用日益減弱,教學讓位給學習,學習成為教育的中心。比斯塔認為,學生的解放并不能導致教學的消亡,他們所獲得的自由其實是一種舒適的不自由,是被控制失去積極自我的假自由。而學生也無法將這種解放轉化為自主的學習驅動力,他們將在盲目無序的學習中一無所獲。
第二,福利主義的推動。20世紀后半葉,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和能源危機導致許多歐洲國家的社會政策轉向福利主義,其核心是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教育作為其中一項重要的社會資源被要求關注每位社會成員的教育福利。福利國家把教育作為社會成員必須接受的資源推向市場,看似人人享有社會資源的權利,享有受教育的機會,但這種資源是以被動接受的方式分配給社會成員,其實公民并未真正獲得教育的自由,而只是得到一種社會政策的妥協。真正的教育自由應該是個人所需的自由教育,可以享有拒絕被供給的教育的自由。
第三,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盛行。建構主義提倡知識由學生自我建構,其核心是一種關于學習的理論,基于此的教育實踐也是以學習為中心的。但在實際的教學中,許多教師奉行知識自我建構的理念。凱瑟琳·福斯諾特(Catherine Fosnot)指出:“從建構主義中得出的一般原則可能會對學習有幫助,而不是教學。”[7]比斯塔認為,建構學習理論稀釋教師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分裂師生關系。教師淪為配角,成為學習的支持者、學習資源的提供者,學生占據課堂,教師只是學生學習的輔助,似乎學生只需在“腳手架”的幫助下自主學習就可以獲得知識,而無需教師的存在。
第四,成人學習的熱潮。學習語言的興盛不僅在教育理論領域造就許多擁躉,而且在全民教育的背景下使社會出現成人學習熱潮。成人投入大量時間、金錢去學習,隨之產生一種充滿交易味道的學習市場。比斯塔指出,這暴露出的是經濟行為,而非教育行為,“那么,對于這樣的消費者而言,還有哪個名字比學習者更合適呢?”[8]教育是培養人的過程,不是簡單的買賣雙方交易過程,成人通過付出的時間或金錢不可能換回期望的等價學習成果。而且成人學習都以個人為中心,學習的內容是由學習市場提供的,是一種被動的選擇,追求的只是個人認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現,學習變為能夠滿足個人急功近利目的的利器
無論是建構主義對學習中心論的理論支持,還是全民學習對教育權利的熱情追隨,以及教育市場化、經濟化行為都深刻地影響著現在的教育。加之現代技術和網絡時代的裹挾,學習化恰恰試圖遮蔽教育中“不確定性”特質,在標準化指導下“同一”學生,否定教師和學生的主體性。以學習代替教學的大部分作用,異化學習在教與學中的關系本質。
二、教的返魅:回返“教”的本源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是教育關注和意向的中心。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讓學生從不成熟走向成熟。教學是學生作為主體生成和成熟,喚起主體存在的不二途徑,教師必須在教學的權威性中回歸應有的位置。
(一)教學的回歸
傳統的教學被新自由主義批判是對教育和學生的控制,理應被解放。教學在“進步”教育思潮的影響下,只能發揮協助學習的功能。學生以教育自由的姿態站到講臺之上自我建構,成為教學活動的中心。比斯塔認為,這其實是一種解放的假象,無論是教學和學習,還是教師和學生的關系都是平等的,教育中沒有所謂一方對另一方的解放。雙方都應保持積極對話和主動交流的關系。
第一,擺正教學和學習的關系。在現代教育環境中,對教學的評價以 “學習結果”的形式體現,而學習結果是用一套既定、細致和完備的考核與評價指標體系來衡量和比較的。比斯塔否定教學與學習之間的因果關系,即“教”不是“學”的導因。他認為,“學習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會產生持續性的永久變化,是個體與環境互動后產生的結果,這個個體就是學生,即學生的學習,是‘做’,是學生從教學中獲得的內容”[9]。教學不會生產學習結果,不是教學計劃的產物,而是去“影響”學習。這個過程首先具備動態性,在教學和學習兩者之間變化,沒有固定的模式;其次,具備互動性,學習結果的產生是基于學習和教學的雙向作用,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指揮或強制關系;最后,具備開放性,教學與學習是一種生成,有可能有結果,也有可能無結果,但只要保持兩者的關系應然存在,就能由不可能走向可能。
第二,擺正教學和知識的關系。學習化社會將人的知識獲得全部歸為己有,認為只要不停地學習就能獲得普遍必然性的知識,完全忽視人的經驗性和先天心靈認知的可能性。知識是教學存在的價值所在,教師通過教學活動將知識作為信息呈現給學生,學生才會以感性直觀方式和理性抽象思維進行加工處理,以形成自己所能認知的知識,同時知識的積累又會為新信息轉換提供基礎。知識的獲得必須是由教學“給予”時才會發生,繼而轉化為知識的學習。
第三,擺正教師和學生的關系。學習化吞噬教師與學生應有的關系,將教師變得可有可無,剝奪教育賦予教師的特殊責任。比斯塔認為,“教育的任務關涉的是被教育者喚起‘在’這個世界且‘與’這個世界以成熟的方式而存在的欲望”[10]。學生“是一種能被教和能接受教的動物”[11],“能被教”是因為學生對經驗性知識的吸收能力是無可預估的,他們在知識不斷增長、消化和建構的過程后,最終形成自主的意識、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接受教”是因為學生先天心靈呈現出開放的狀態,他們愿意接受世界的新知識、新思想,一個新的自我就會不斷生成和涌現。我們永遠不知道學生在被教和接受教之后會產生什么樣的短期與長期結果,在極端情況下也許沒有結果。盡管教學可能帶來一些不可避免的風險,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控的,但這種“不確定性”或者風險恰恰保證學生主體自由的教育。
教學與學習的非因果關系、教學與知識的價值關系、教師對學生的責任關系都反映出教學的重要性。上述三種關乎教學關系的必然存在,打破任何破壞教學本位的不良企圖。
(二)教師的回歸
由于社會建構主義學習和教育心理學在教育領域提倡學生中心論,強調學生的自我組織學習,導致教師在教學中的退出。教師從講臺的“圣人”降格為一旁的向導,甚至被置于幕后。比斯塔提出,必須將教學的權力還給教師,原因只有一個,“真理是從教師那里獲得的”[12]。
第一,教師是學生獲取真理的啟蒙者。啟蒙即開發蒙昧,明白事理。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性無能為力。[13]人類的理性是追求真理的必備之物。人類從不缺乏理性,卻由于沒有勇氣去運用理性,而呈現出一種“不成熟”的狀態。教學的本質是為了他者,是一種強制的無法逃避的責任。教師就是幫助學生從不成熟的狀態轉變為成熟狀態,幫助他們運用理性獲得真理。一方面,知曉什么是被遮蔽的真理,如何被遮蔽的;另一方面,進一步知曉如何去解蔽和去蔽。這樣學生就可以不依靠任何權威,自由自主地運用理性去判斷。
第二,教師是學生獲取真理的開端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Аrendt)認為,“開端不是某物的,而是某人的,人自身就是一個開端者”[14],一切事物的開端是在人自由、自為、自有的思維中形成的原初認知。它既能為人引入新的世界,也能給世界引入新的事物。真理為人類打開認識世界的大門,為我們敞開一片真理存在之地并引入其中。教育是人類不斷探索實踐真理的重要途徑,是知者對不知者的帶動。教師作為知者,首要責任就是讓學生意識到真理的存在,這種存在不以個人意志和認知而有任何改變。教師不是真理的擁有者,而是讓學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學習與認知真理,他們是學生獲得的真理的開端,是已有的出發。教師還是知識的開發者、創新者和生產者。教師在對既有知識批判和繼承的基礎上,還會以新的研究方法、工具和手段,建構新的認識體系和價值體系,對知識分析、批判后進行新的整合、創造和提升,來促進學生更新知識的獲得。
第三,教師是學生獲取真理的領航者。教師不僅將真理教授給學生,而且還要成為“獲取真理的條件的授予者”[15]。真理的獲得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沒有既定的真理,也沒有想當然的真理。人類尋求真理的路程是鋪滿荊棘的,人類認知世界的歷程也是從確定到不確定、再到確定的循環往復。學生在獲得真理的同時,還需要掌握獲得真理的條件,換言之,學生需要具備辨別真理為真理的條件,才可以無限接近真理。所以教師還要提供一切可能性條件讓學生自主向前獲得真理。教師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下,幫助學生能夠“打開自我以獲得教學禮物”[16]。 這是學生向世界的敞開,與世界為他們敞開一樣,是一種雙向的敞開。在此開放環境中,學生以自我解放的姿態主動接受教育,揭示出他們主觀地接觸世界的積極意義。學習不是一種內部環境的索取,不應是“學生是保管人,教師是儲戶”[17]。 學生不能只會從有限存儲的知識中簡單復制和重復,從而失去批判意識,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教”應是由教師將一個新事物不斷出現的世界、一個與他者共存的世界帶給學生,讓他們向往一個有無限可能的世界。
比斯塔認為,將教學的權力還給教師,使學習被設想為一種更廣泛、存在性的經驗,在這種經驗中,學生在學習中體驗事物、自己和他人。
三、教的復魅:重新發現教學
比斯塔提出重新發現教學的倡議,以恢復其原有的魅力。他將教學視為一種相遇,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為學生創生更多的機會,賦予教學和學習更大的可能性,最終為教學創造超越的有利條件。
(一)空間的創生
比斯塔認為,“今日教育之責任在于創生,一個多元與差異的空間,一個自由得以顯現、獨一的個體得以進入世界的空間”[18]。如何進入世界的空間?他認為個體在教育中存在于兩個相異的“社群”之中,一是由共同語言和概念體系所構成的理性社群;二是以“異”構成的他者社群。教育就是從中構建肩負雙重責任,共在共生的教育空間。
一是理性社群的空間。[19]理性社群最顯著的特點是由一種共同的語言構成,可作為社群成員相互識別的符號系統。如教育中相同課程的內容、統一遵守的學校規章、標準化的教育檢查報告等。通過這種共同的語言,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相互理解。理性社群賦予成員可以說話的權利,相互之間可以溝通交流。在社群內,大家使用規范性的語言,成員的語言也可以互換和復制。理性社區可以為它的“發言者”提供一個有代表性的聲音,無論任何一個社群成員都可以被代言。教育負責每位理性社群個體的“同”,學校課程教會學生符合社群中的話語內容,學校實踐活動教會學生如何發出共同的話語。在此空間中,學生首先作為主體通過教育獲得在世界存在的資格,具備生存與生活的知識、能力和技能,獲得在社群中工作生產的條件,即資格化;其次在共同的文化、政治、信仰規則中,學生作為主體通過教育能被自己所生活的社會和世界承認,以共同語言相互認同,可嵌入共同的理性社群中,即社會化。
二是他者社群的空間。[20]比斯塔在理性社群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教育不應該僅僅從文化再生產,即理性社群的角度來理解,還應該作為一個非生產性的過程,重視安排與未知、陌生和他人的相遇,搭建一個他者社群。在他者社群,每位成員都可以在與他者相遇時發出自己的聲音,并期待他者不同的回應。[20]他者的回應是以其自身的言說激起主體的回應。正是在主體和他者的交流回應之間,主體與他者得以共同顯現。換言之,任何一個主體的顯現都是來自他者的相遇,只有在面對迎接他者的挑戰時,一個人的獨特聲音才可能出現。教育就是為學生創造相遇的機會,只有讓他們面對他者的挑戰,才能將主體主體化。教學為學生創立“可能性”空間,產生相遇的可能。這種“可能性”是學生多元性在他者社群中的充分展現,是學生差異性在他者社群的豐富表現。
在理性社群中,主體是以其代表來言說和行動的,帶有強烈的共性,而他者社群是主體與他者區分的空間,是個性身份的界定之處。比斯塔認為,人類有能力接受他者,人要“放開”理性的聲音,有勇氣去回答陌生人,正是這種回答構成他者社群。教育本質的可能性和生成性將兩個社群緊緊勾連,在兩者之間教育生成更大的空間。學生既需要在前者中完成共同話語的建構,又要在后者中保證主體話語獨一性的顯現。學生在理性社群中獲得知識、價值觀或技能,是嵌入共同社會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同時,學生還需擔負主體的責任面對他者,以不可替代的方式回應,成為主體存在不可或缺的條件。
(二)時間的生成
比斯塔批評傳統教育中從變化、發展、進步等概念構建出的單一的線性時間觀念,他認為那是典型的以目的論為指導的時間概念。在這種時間觀念中,如果開始是確定的,過程也是限定的,那么結果也就是可預測的。將學生以線性時間維度來衡量和控制,實質上是預設他們所有和所缺的能力,使其無法擺脫被設計的軌跡。線性時間觀念是學生主體的缺失,一切所謂的發展變化都不是主體自由的選擇。
教育繼發過去存在,即教育在原有基礎上不斷發展。教師作為教育者所被賦予的對學生的先天責任,即承擔起“已知”世界認知內容的傳播和教授職責。“已知”并不意味著讓學生接受過去的知識、陳舊的事物和經驗。學生作為被教育者、世界的新來者,所謂的已知對其而言是未知、新知。教育需要尊重歷史和經驗,它代表著人類認知的結晶,是人類發展的進步之梯。學生的學習必然要回顧和總結過去,挑選經驗之物轉化為自有之知,是從未知到已知的過程。
教育面向可能性未來。教育一定是由“面向”①教育要面向教育的對象,不能閉門造車,只有在此姿態中才能真正知道教育的實際需求和發展方向。面向是一種開放的、充滿可能的姿態。而生,由生而可能,教師面向學生召喚學生進入世界,學生面向世界而發生認知過程,不斷地以可能性籌劃自身。未來在學生主體存在中不斷突破,沖破現存狀態,拒絕“我不能”的判斷,主體積極籌劃“我能做什么、我可能是什么”。教師賦予學生無限的信任,不為學生設定未來的必然性,讓學生自由地做可能的事,也能完成不可能的事情。
比斯塔提出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生成的教育時間。學生既可以在歷史中徘徊,也可在當下充實。教育時間是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生成,學生可以跳躍、回望、前進,在教育時間中有機會體驗不同的可能。如果教育對學生的判斷只是基于既往,那實際上意味著一種對學生不平等的假定,是對他們先見的預設。教育要打破對學生的固有認知,不加限定地讓學生的主體以開放的姿態展現自我。教育也不為學生設定未來的界限,任何時間的規劃都是減弱他們未來可能性的紅線。教育時間無法為學生的未來劃定刻度,但保證他們向未來前進的新鮮度,不斷地為他們更新可能的起點。
(三)世界的開啟
比斯塔認為,教師肩負著雙重責任,即“一”的獨顯和“異”的多顯。教師在教學中為學生創設一種開放性、生成性的情境。在此,允許學生主體的存在并以主體成熟為目標,教師有責任將學生召喚到新的世界中,并與世界的他者相遇。這種責任就是教與學關系存在的意義,也是教師與學生關系存在的意義。
“一”的獨顯。教育情境的創生將每一位學生引入其中,使其具備自我的誕生性②阿倫特將“誕生”視為開端啟新的能力 ,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在教育的空間中,不斷突破自身,生成新的能力。,激發自身天賦和潛力,成為世界上的異者。在此,教育引起學生向往的火苗,去滿足學生主體對世界的向往,讓他們去好奇、探尋自身的未知。讓他們在世界與他者的對話中,以此發現自己獨特于他者的存在,使學生意識到自己與他者的相異性,凸顯自身的唯一,是無法被替代的“一”,是獨立于任何他者的“獨一性”。
“異”的多顯。教育情境不僅是自我理性的成熟,而且還讓學生知道與他者世界的共存是主體無法脫離的責任。學生作為主體進入世界與他者相遇,用言說回應他者,而不是自說自話。學生在與他者面對面中,學會認識自己是誰,自己與他者的差異,自己應持有的立場。自身是在他者的“異”中顯現出來的,沒有他者,主體只是孤立于世界的獨思者。比斯塔認為,“責任是教育關系的構成要素,而且教育借此成為可能”[21]。與他者相遇激發出為回應他者而產生的責任,為兩者建立天然的倫理關系。主體與他者相呼應,積極參與彼此的言說和行動中,以責任的強制性將學生主體與他者聯系起來。這種責任關系促使兩者不斷生異而具備存在價值,“生”就是新,就是教育的可能。
在自我和他者所形成的張力之間,教育為雙方留存“中間地帶”[22]。自我以其異于他者而具備獨一性,成為理性自主之人。自我不以自己沉默之思反省自身,而以自身理性思考表達獨立自由之聲,具備自我行動和判斷之力。他者以多元性共存于世界,用差異的言說表達自身,不限于任何既有話語。自我理解和接受他者之異,但不盲從于他者的意志和判斷。中間地帶可提供自身理性成熟的養分,以便使他們按照自己的愿望成長。教師為自我和他者搭建聚集之地,將兩者與世界聯系在一起,在自我和他者的各自顯現中開啟世界新的未來。
四、結語
“學的異化”現象的盛行,一方面讓學生在學習化中被控制和限定,無法主動積極發揮其擁有的理性之力,來獲得真正的教育自由;另一方面,讓教師在學習化中逐漸喪失教學權力,無法掌握教學的主動性,丟失自由教育。比斯塔以自由、解放和民主為主線,關注學生的主體性存在。一方面,批判當代教育中的學習化,并提出以存在主義為特征的教育理論;另一方面,積極回應現代技術、循證管理模式以及問責現象給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達到超越學習,超越學生作為主體的本真教育,即把學還給教。比斯塔希望擺正教學與學習、教學與知識的關系,恢復教師原有的教學權威,為學生與世界的共存創造必要的可能條件。比斯塔提出,教師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為學生提供成長的條件,在理性社群和他者社群的交融中完成學生資格化、社會化和主體化的空間創生,以超越線性教育時間將學生帶入多元性、差異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