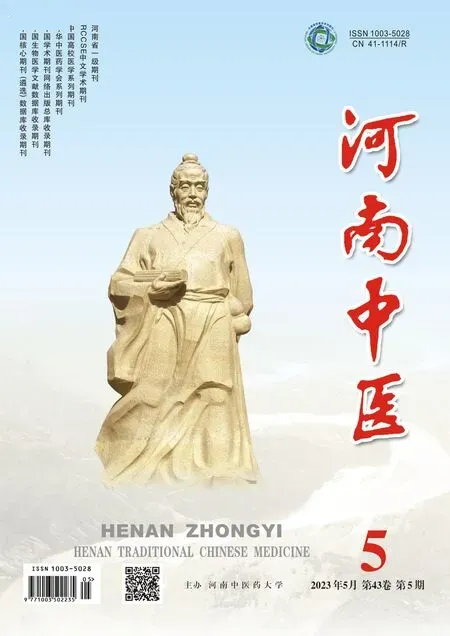濕疹2號方治療亞急性期濕熱蘊膚證濕疹臨床研究*
孫曉庭,戈雪婧,陳曉暉,楊耀忠
上海市寶山區吳淞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上海 200940
濕疹是發生于皮膚真皮淺層的炎癥,發病機制尚不清楚,一般認為可能與變態反應有關[1]。濕疹發病人群廣,我國濕疹患病率約為 7.5%,且呈逐年上升趨勢[2]。現代醫學認為,濕疹發病可能與機體慢性炎癥、內分泌代謝失衡、血液循環障礙等因素有關,也可由于攝入異體蛋白、吸入敏感性蛋白、外在生活環境刺激、接觸動物皮毛等外部因素誘發或者加重,急性期臨床表現以液體滲出、皰疹為主;慢性期表現以浸潤、肥厚、苔蘚樣病變為主[3-4]。
濕疹屬中醫學“濕瘡”范疇,多由先天稟賦不足,或因風、濕、熱之邪內侵所致。濕疹的典型特征是皮損對稱,多形損害,瘙癢劇烈,反復發作,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因此,尋求簡便、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尤為重要[5-7]。濕疹2號方是上海市基層名中醫楊耀忠主任醫師的經驗方,臨床應用此方治療濕疹等皮膚病均取得較好療效。筆者采用濕疹2號方治療濕熱蘊膚型濕疹,取得滿意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上海市吳淞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診治的102例濕疹患者為研究對象,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各51例。對照組男22例,女29例;年齡(48.9±12.3)歲;病程(40.6±17.2) d。觀察組男21例,女30例;年齡(49.6±13.7)歲;病程(37.9±19.7) d。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符合《中國臨床皮膚病學》[8]中亞急性期濕疹的診斷標準:炎癥性丘疹、鱗屑、結痂為主,有暗紅或淡紅色斑塊,僅伴有少數丘皰疹和糜爛,或輕度浸潤,基地潮紅,自覺瘙癢;由于搔抓,可能會有點狀滲出及糜爛,有漿液滲出,且病變中心癥狀較重,逐漸向周圍蔓延。
1.2.2 中醫診斷標準符合《中醫外科學》[9]中濕熱蘊膚證的診斷標準:急性濕疹炎癥減輕之后或者急性期未及時處理,拖延較久而發生的亞急性濕疹,皮損以丘皰疹、鱗屑、結痂為主,僅有少數丘皰疹或小水泡或糜爛,亦可出現輕度浸潤,自覺仍有劇烈瘙癢,心煩、口渴,身熱,大便干結,小便短赤;舌質偏紅,苔黃,脈以滑、數為多。
1.3 病例納入標準①符合上述中西醫診斷標準;②年齡18~70周歲;③患者及其家屬對該項研究知情并同意,并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④依從性高并可積極配合復診及隨訪者。
1.4 病例排除標準①治療前2周服用過激素治療者,有藥物配伍禁忌者,或者與治療藥物過敏者,或者不適宜采用本治療方案所使用藥物者;②伴有心、肝、腎及神經系統損害者;③妊娠及哺乳期婦女;④病例資料不完善、依從性較差者。
1.5 病例脫落及剔除標準①依從性差,不能嚴格按照醫囑用藥者;②資料不全者;③試驗過程中有相關不良反應,致使患者不能繼續接受治療者;④自動脫落失訪,無治療記錄者。
1.6 治療方法兩組患者均外涂復方倍氯米松樟腦乳膏(上海延安藥業有限公司,批號:國藥準字:H42021866),局部適量外涂,每日3次,治療2周。對照組給予防風通圣顆粒(山東潤中藥業有限公司,批號:國藥準字Z20174069),每日2次,每次1袋,口服,連續治療4周。
治療組給予濕疹2號方口服,具體藥物組成:荊芥9 g,連翹15 g,生薏苡仁30 g,蒼術9 g,苦參 10 g,當歸9 g,浮萍15 g,焦梔子9 g,白鮮皮15 g,徐長卿15 g。若瘙癢甚者加地膚子15 g,百部9 g,烏梢蛇9 g;若滲出明顯者改蒼術為18 g,加滑石20 g。由上海市寶山區吳淞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藥房統一代煎,每次1袋,每日2次,溫服,共治療4周。
通過利用虛擬化的技術構建計算池、網絡池、存儲池和桌面池,最終形成一個可以共享和處理信息的統一的資源池。這是一種由服務器、存儲和網絡等設備構成的數據資源。正常辦公人員、教學人員可以享受到應用層提供的體育教學系統和辦公OA系統的應用程序。學生可以享受到用戶層對于數據中心的訪問權限和服務支持。移動教學桌面云和資源層的管理構成了管理層,最終形成管理體系。
1.7 療效判定標準痊愈:患者瘙癢體征及癥狀均消失;顯效:瘙癢程度改善明顯,相關體征改善程度顯著;有效:瘙癢癥狀有所緩解,皮損部分消退;無效:瘙癢癥狀改善程度不明顯,甚至有加重跡象。
有效率=(痊愈+顯效+有效)/n×100%
1.8 觀察指標
1.8.1 瘙癢程度評分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療效性觀測評分標準:無瘙癢計0分;偶發,不用使用藥物治療,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計 1~3分;陣發性瘙癢,輕重情況不一,對學習、生活等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需要藥物介入治療計4~6分;瘙癢劇烈,必須要使用藥物干預治療計7~10分。
1.8.2 瘙癢消退時間比較記錄兩組患者皮膚瘙癢消退的時間,采用微信或者電話隨訪的形式進行詢問,對瘙癢情況進行視頻、拍照形式留存。
1.8.3 臨床癥狀評分根據患者皮損情況分為紅斑、丘疹、鱗屑、抓痕等、浸潤、肥厚、苔蘚化。根據每一項臨床表現的無、輕度、中度、重度分別計0分、1分、2分、3分。
1.8.4 濕疹面積及嚴重指數評分采用改良濕疹面積及嚴重度指數(eczema area and severity index,EASI)評分法對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皮損面積及嚴重指數進行評分,使用燒傷手掌測量面積法,即患者五指并攏時,其單手掌面積占總體表面積的1%,無皮損計0分,皮損面積為1%~5%計1分,皮損面積為6%~10%計2分,皮損面積為11%~15%計3分,皮損面積為16%~20%計4分。
1.9 統計學方法統計學分析采用SPSS 21.0軟件,根據數據的特點進行分類統計,即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以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濕疹患者臨床療效比較對照組有效率為74.5%,觀察組有效率為94.1%,兩組患者有效率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濕疹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2.2 兩組濕疹患者瘙癢消退時間比較觀察組瘙癢消退時間短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濕疹患者瘙癢消退時間比較
2.3 兩組濕疹患者治療前后瘙癢程度評分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后皮膚瘙癢程度評低于本組治療前,且治療后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濕疹患者治療前后瘙癢程度評分比較 分)
2.4 兩組濕疹患者治療前后臨床癥狀評分及EASI評分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后臨床癥狀評分及EASI評分低于本組治療前,且治療后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濕疹患者治療前后臨床癥狀評分及EASI評分比較 分)
2.5 兩組濕疹患者治療前后血清EOS、IgE水平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后血清EOS、IgE低于本組治療前,且治療后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濕疹患者治療前后血清EOS、IgE水平比較
3 討論
濕疹在中醫典籍上記載較多,如《類經·疾病類一》云:“熱甚則瘡痛,熱微則瘡癢……”《醫宗金鑒·血風瘡》云:“此證由肝、脾二經濕熱,外受風邪,襲于皮膚,郁于肺經,致遍身生瘡。形如粟米,瘙癢無度,抓破時,津脂水浸淫成片,令人煩躁、口渴、瘙癢,日輕夜甚。”濕熱蘊膚證濕疹患者常因濕邪致病,濕久化熱,濕熱久羈,耗傷陰血,血虛化燥生風而致肌膚失養[10]。病機以濕熱為主,此階段濕熱為盛,郁滯氣血,則皮膚表面多呈現潮紅、丘疹、水泡易糜爛等表現,以清熱、除濕、祛風、潤燥為主要治療原則[11]。濕疹2號方為楊耀忠主任醫師的臨床經驗方,根據多年臨證思考,擷取古代醫家對濕疹的診療經驗,以《萬病回春》中荊芥連翹湯化裁而來,荊芥連翹湯具有散風理氣、瀉火解毒之功效,常用于頭面部紅、腫、熱、痛之病證及熱性體質的調理。濕疹2號方中荊芥、連翹散風解毒,為君藥;生薏苡仁、蒼術、苦參、白鮮皮為臣藥,以協助君藥發揮解毒、祛風、止癢之效;當歸、浮萍、焦梔子、徐長卿為佐使藥,以清、散作用為主,發揮協同增效作用。諸藥合用,共奏清熱、解毒、散風之效。本方用藥由始至終貫穿風、濕、熱三邪的特點進行治療,同時根據病情的變化隨證加減,取得良效。
現代醫學治療濕疹主要以抗組胺類藥物、類固醇皮質激素等為主,急性期可有效控制癥狀,但病情容易反復發作,且會演變為亞急性或慢性濕疹[12-13]。復方倍氯米松樟腦乳膏為中西藥復方制劑,又名“無極膏”,具有抗感染、鎮痛、止癢、抗菌、局部麻醉等作用,臨床上常用于蟲咬皮炎、蕁麻疹、接觸性皮炎、皮膚瘙癢等癥[14-15]。復方倍氯米松樟腦乳膏藥性清涼,可增加局部涂抹的舒適感,臨床應用時患者接受度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患者有皮膚糜爛破損嚴重時應禁止使用,以防止藥物通過破潰組織侵入過多,導致不良反應發生[16-17]。
現代醫學研究顯示[18-20],機體在受到外界過敏原經皮膚或黏膜刺激進入機體后,可活化B細胞等抗原發揮信號傳遞作用,活化的B細胞對過敏原進行識別、處理后,產生白細胞介素類等炎癥誘導因子[21],如白細胞介素-4、白細胞介素-13等,此類細胞因子在受到激發后,可刺激免疫球蛋白E重鏈恒定區的基因轉錄,并進一步誘導IgE的合成,白細胞介素-5可刺激骨髓釋放EOS的生成,進而引起血清IgE、EOS的表達量異常升高,提示血清IgE、EOS的變化在過敏性皮膚性炎癥疾病中有重要作用,為臨床皮膚病炎癥變化及綜合診斷治療提供了參考依據[22-24],因此,本研究選取該IgE、EOS作為濕疹療效的實驗室評價指標。
綜上所述,濕疹2號方治療亞急性濕熱蘊膚型濕疹,可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縮小濕疹面積,加速皮疹消退,緩解皮疹瘙癢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