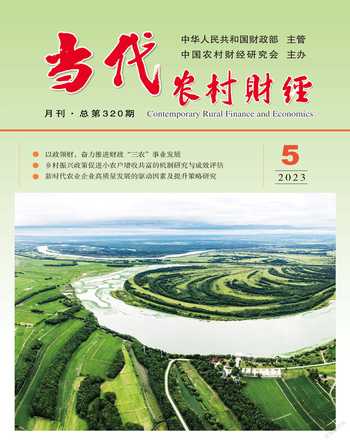農業擔保的風險來自哪里?
尹迎欣 孟光輝 孫越
摘要: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建立,有效緩解了農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但隨著農擔業務的快速發展,農擔機構代償率逐漸攀升,擔保業務風險問題突出。本文選取具有代表性的100個典型案例來進行深度研究,發現出險的原因主要由農擔公司內部、借貸主體自身以及外部環境三方面因素造成。以期通過提升農擔機構內部建設、加強對經營主體的管理監控、設立農業保險等風險分流措施,做好農業信貸擔保業務的風險防控、完善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建設。
關鍵詞:農業信貸 擔保機構 業務風險 案例分析
一、引言
農業天然的弱質性制約著農村金融的發展,多年來農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一直未有效緩解。2015年7月,財政部、農業農村部、銀保監會聯合下文,明確提出構建覆蓋全國的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利用國家信用為農村金融助力。截止2021年底,國家農擔體系累計擔保項目217萬個,金額達到6892億元,個別地方農村金融超過60%的業務依靠農業擔保增信完成,國家農業擔保體系的政策效能初步顯現。但與此同時,農擔體系累計發生代償項目10994個,代償金額達到58億元,累計代償率為1.53%,其中2021年代償6021個,代償23.2億元。可以預見,隨著擔保項目還款周期的陸續到來,代償率有攀升的趨勢。毫無疑問,農擔業務發展的同時其風險因素不容小覷,農業擔保相關的問題也成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喬樸等(2019)認為我國的農業擔保體系發展較晚,很多公司的業務發展還處于摸索期,擔保機構內部管理制度滯后,擔保體系不完善,存在內部風險。陳旭紅(2022)認為由于政策環境以及市場環境復雜多變,擔保公司的經營很容易受到影響,不能及時做出風險處理,導致擔保業務經營風險增加。曹木子(2021)對我國融資擔保公司的風險管理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通過建立與政府、銀行等金融機構要建立風險分擔機制以降低擔保公司的風險。孫同全等(2022)認為我國農擔公司正面臨“去擔保化”的挑戰,應加強對農擔體系代償損失的補償,可以通過建立各級財政共擔的風險補償資金池,保證擔保資金規模不減少、農擔機構資信不降低、擔保能力不弱化。通過研究發現國內對于農業擔保業務風險的研究較少,現有的對農業擔保業務風險的研究中,大多為宏觀研究,鮮有學者以大量真實的擔保案例為依據,進行擔保風險的微觀研究。本文通過對全國省級農業擔保機構的典型代償風險案例進行考察和系統分析,寄希望于研究成果對農擔體系的健康發展提供有益幫助。
二、研究樣本來源
全國農擔體系共有33家省級擔保機構。研究伊始,課題組在對國家農擔體系進行了調研,并針對農業擔保的整體風險情況,最終選取在全國最具有代表性的省級農擔公司進行專項代償案例調查。考慮到農業擔保項目風險不僅產生于信貸客戶的自身因素,也產生于項目的操作的內部過程,貫穿項目審批、盡調、監控的全流程,涉及因素方方面面,為了保證案例分析的準確性和代表性且不流于形式,在大量隨機粗選的前提下,最終精準確定100個典型案例來進行深度研究。其中,90份選自某最具典型代表的省級農擔公司,輔以10份全國農擔體系典型通報案例,據此展開政策性農擔體系業務風險特征的綜合研究。
(一)機構樣本選擇
通過對國家農擔體系多家機構進行對比分析,最終選擇某省級農擔公司為調查對象進行案例研究,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改革開放40年以來,該機構所在省份的農業生產始終處于全國前列,農業經濟穩定發展,對農業資金的需求日益增加,農業擔保業務需求量擴大。第二,自國家農擔體系建立以來,該省級農擔公司發展迅速,其業務量趨于全國首位,目前擔保余額占全國近20%,極具代表性。第三,該農擔公司大力推進擔保機構數字化轉型,利用大數據進行精準全面的資格審查,將風險前置,能有效規避因前期項目審查不當而導致的業務風險,是農擔機構未來發展模式。最后,該農擔在國家農擔公司對全國33家省級農擔公司進行的風險管理評估評價中,該農擔機構在保、累保及風控水平均居于全國首位。綜合來看,該省級農擔機構在業務風險管控方面采取的措施效果明顯,但仍然出現了一定的業務風險,以此機構的風險案例為研究調查對象更具有說明力,也能夠展示未來農擔風險的發展趨勢。
(二)案例樣本選擇
對該省級農擔公司近幾年實際發生的風險案例進行研究,并對其風險成因總結歸納,最終選取具有代表性的100份風險案例作為研究對象。該樣本案例覆蓋全省15個地市,分布均衡,范圍全面,且樣本案例的出險因素具有典型特征,其風險成因分布集中,具有代表性。所選100份案例中,包含各類農業生產擔保業務,其中種植類33個,養殖類30個,購銷類17個,加工類10個,投訴及其他類10個,涵蓋了所有新型經營主體類型、多種農業生產經營范圍。

三、實證分析
通過查詢業務檔案和搜索關聯數據信息,與相關業務人員深度交流,課題組對100份代償案例做了深度分析,對所涉風險因素做了提煉并加以統計分析,分別從農擔機構因素、農業經營主體因素和外部環境三個角度展開風險成因的研究。
(一)農擔業務風險成因情況綜合統計分析
通過對案例情況進行梳理,共統計出20類核心風險因素,各風險因素發生次數總計450次*,對其風險成因進行匯總并分類分析如表1所示。
總體看,在三類風險因素種類中,農業經營主體自身原因種類因素占比最多,超過一半達到56%。在20項細分風險成因中,自然災害、疫情等不可抗力影響居于首位,占比達到9.78%,生產主體的經營能力不足、收入下滑等因素的影響占比達到9.56%,位居第二位。
(二)擔保業務風險成因分布分析
1.農擔機構關聯因素
從農擔機構內部5類因素分析,反擔保措施單一或無反擔保措施原因占比最多,高達41.03%,占總體因素的7.11%。這是農業項目的普遍性情況。由于農業項目擔保物匱乏是客觀情況,雖然這是擔保出險的重大因素,但現實中基本上不可能彌補。農業擔保項目依靠增加擔保措施來減少風險因素的思路在現實中不可取,不應過于苛求。保后管理不及時也是重要的分險因素,占本類因素的26.92%。占總體的4.67%,側面印證了有效的保后管理對避免項目風險的重要意義。保后發現信息與申保材料矛盾和明知風險較大但仍然審批兩類因素,占本類因素的37.18%,這主要是業務人員不盡職或盲目追求業績而違規審批造成,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擔保機構自身業務人員素質和風險監控的必要性。內部人員與借款人過于密切或隱瞞重大材料明顯是業務人員的道德風險原因。道德風險是擔保機構應極力避免的重大風險,考慮到該項因素的隱蔽性和內外勾結的巨大危害,雖然道德風險因素僅占比5.13%,但其最不容易預防,引起的風險往往具有更大的破壞性,更應當重視。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
2.農業經營主體自身因素


從本類風險因素分析看(見圖2),農業經營主體自身的因素仍是擔保業務風險的主要風險,56%的風險與經營主體自身相關。在本類因素范圍內,農戶經營不善導致收入下滑占比最多達17.13%,占總體的9.56%,是所有統計因素中占比次高的。顯然,經營能力才是項目安全的最大保障,統計數據誠不我欺。與經營能力相對應當直接影響還款能力的是負債因素,其中顯性負債因素(保前負債嚴重,資金鏈斷裂)占比12.75%,隱形負債因素(民間借貸爆發)占比12.35%。出乎預料的是,農業經營主體的隱性負債尤其是民間借貸因素與顯性負債因素幾乎并駕齊驅,負債因素合計占比本范圍因素的25%以上,占總體比例也超過14%,已是農業擔保中的最大風險因素。這充分說明過度負債是任何經營主體應當避免的情況,也是擔保風險審查的重中之重。而在具體經營過程中的錯誤決策性因素占比較高,貸款資金挪為他用和盲目擴張,二者合計占總體比例接近10%。這也說明農業經營主體的盲目求大和業務隨意轉型具有較大的風險性,在擔保業務中應重點防范。而與還款意愿相關的兩類因素“借貸人信用意識弱、信譽低”“貸款人及保證人還款意愿差”合計總體占比達到12%,占到本大類的21.5%,充分說明體現借款人、保證人信用意識的還款意愿確實是影響擔保項目風險的第二大類因素。現實業務中抓還款能力、關注還款意愿兩大主要因素是正確的。統計顯示,日常生活當中的意外很可能就是擔保項目中的常態風險。經營者或實際控制人意外事故發生(身故、羈押,重病)是項目風險因素中的顯性因素,占總體因素的4%,占經營主體相關因素的7.17%,顯然這些也不能忽視。至于純粹的惡意欺詐、逃債因素也是風險原因,但是占比并不高,綜合占比3.11%。事實上在相對完備的大數據反欺詐技術幫助下,純粹以欺詐為目的的信貸業務會逐漸減少,但在當下仍然需要仔細防范。
3.從外部因素分析
統計因素顯示,風險產生的外部原因主要是雨雪、洪澇等自然災害與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市場價格波動、宏觀政策調整以及合作銀行轉移風險等而導致項目代償。該四項因素基本上屬于擔保機構自身不可預見、不能控制的外部因素,雖然僅有四項,但出險的頻次高達121次,占比27%。大約三分之一的農業擔保風險因素是農擔機構自身難以控制或預見的,從側面說明農擔業務本身帶有強烈的公益性,具備準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這其實契合了政策性擔保機構的天然使命。仔細分析看,自然災害因素總體占比達到9.78%,占全部外部因素的36.36%,是所有統計因素當中占比最高的。農業擔保業務的最突出風險因素是自然因素,在本研究的統計結論中再次得到了證實。農產品價格波動作為不可控制的因素,總體占比也達到全部的6%,占到本類因素的29%。這說明,農產品市場的價格因素是決定擔保項目安全的重要因素。一直以來糧食價格相對穩定,意味著種植類農業遇到此類風險概率較低,但由于養殖類項目近年來價格“過山車”現象并不少見,此類項目風險率相對較高。通過比對案例實際情況,也印證了該結論。研究樣本中,養雞戶、養豬戶貢獻了該類影響因素的絕大部分。細分之下,銀行向擔保機構轉嫁風險因素占到總體比例的3.33%。雖然比例看似不高,但按該比例推算,該類項目在全國范圍內也約有350個,并非少數。各類風險占比如圖3所示。
四、政策建議

100個典型案例反映出來的風險因素特征,為農業信貸擔保業務發展和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建設提供了完善的思路和可行性方向。研究結論顯示,統計數據和日常經驗感覺有一致性,如經營能力、負債情況對項目風險的影響較為明顯。但同時也會發現,部分研究結論還是超出一定的經驗范圍,如自然災害因素對擔保項目風險的影響頻次10%,竟然超過了經營能力因素,而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波動對項目風險影響的頻次甚至比農戶還款意愿、貸款資金挪用、盲目發展擴張等因素更多。要強調的是,案例統計雖然比較直觀地反映了各類風險因素的相對影響頻次,但不同因素之間會產生交互影響,并且不同因素之間的影響程度在不同的案例環境下未必完全一致,并不意味著這些因素對項目風險影響就是各類影響因素的簡單相加。根據研究結論,可以對擔保業務實踐中的各種做法做出進一步的優化。
(一)創新反擔保措施
采取靈活多樣的反擔保措施,合理進行評估,并建立有效的風險評審機制。各省級農擔公司可采取生產資料與設施抵押、糧食及特色農產品抵押、訂單倉單質押、產業化龍頭企業保證擔保、農民專業合作社保證擔保、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聯保與互保等新型擔保方式;也可將農業經營生產中的各類用益物權等資產納入農擔項目的反擔保措施中,可以結合地理位置、購置成本、市場變現價綜合考慮,凡經公司專業評估具有一定價值,能夠辦理抵(質)押手續,并有變現渠道的,均可作為反擔保措施。這些權利包括:生物資產、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經營工具、經濟林林權、土地生產經營權等,以上述各種用益物權提升農業生產戶履約動機,增強違約反制手段的威懾性,有效將提升反擔保措施的覆蓋范圍,掃清反擔保業務的運作盲區,降低農業擔保業務風險。
(二)推進農業擔保機構數字化轉型
擔保業務開展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的審批紕漏現象,獲取借貸人的實際借款用途及還款能力等信息有偏差。在數字經濟時代,提高農業擔保的數字化技術水平,推動農擔公司的數字化轉型成為擔保行業發展的“必修課”,可以有效降低農擔公司的運營成本,推動農擔業務的高效、高質發展。國家大力推進農擔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在對農戶主體信息收集渠道上,發揮互聯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的優勢,多渠道利用各類信息平臺,整合信息優勢并通過交叉印證的方式確保數據信息的準確性與可靠性,規避資格審查的失誤。政府部門可以成立專業的農業征信公司,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針對借貸人發生隱瞞負債等道德風險的情況,擔保公司可以利用大數據平臺建立或完善農戶及企業信用檔案系統,或利用大數據反詐技術進行規避,全面運用政府、銀行以及大數據庫等對客戶進行風險排查,加強對有不良行為記錄客戶的識別,建立優質客戶“白名單”與失信客戶“黑名單”,降低潛在風險。
(三)加強對農業經營主體的考察
通過標準化、連續性、可追溯的農業經營主體的信息記錄,在初審、報送、審查、保后管理以及追償等業務的各個階段加強對農業經營主體的考察。加強“政銀擔”之間的聯合,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構建全方位、一體化的數字平臺,由政府為主導結合金融機構的信貸數據建立統一的農業經營主體基礎數據信息系統。主要考察內容分為三個方面,一是經營主體自身的經營情況,除了盈利能力外的過度擴張和盲目轉行情況;二是仍然要關注經營主體的負債,尤其是隱性負債的情況。深度挖掘負債情況,是小微金融業務永遠的難點和重點,應積極利用大數據技術,多角度搜集該類信息;三是重視小微項目中個人意外因素,經營者或實際控制人意外事故發生(身故、羈押,重病)已經是項目風險因素中的顯性因素,因此多采用人壽保險分流的方式是比較可行的方法。
(四)提升擔保機構內部管理水平
在農業擔保機構內部,仍然要重視內部員工的道德風險的防范,適度調整業績壓力與風險防控之間的平衡點,加強機構內部控制制度建設,完善內部制衡和監督機制,重點以機制來防范員工舞弊。基層擔保機構在發展的過程中,應提升擔保人員的專業能力。一方面,可以高薪聘請專業人才,帶動非專業人才,提升員工專業能力,高效地為擔保機構服務。另一方面,加強基層業務人員風控水平,強化內部人員風控意識,制定擔保業務風險管理的培訓課程,提高內部信用評價團隊的專業素養。除此之外,構建在線經營管理體系,形成獨有的動態經營追蹤機制,實現對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及時發現、分析與解決。及早監測擔保農戶的管理情況,對其出現的異常狀況和可能出現的風險因素進行及時地觀察,并對其采取針對性的行動,做好風險辨識,對風險進行及時的控制,減少擔保業務中出現的風險。
(五)有效防控自然風險
要客觀認識到自然風險因素是擔保項目風險的最重要部分,既不能無視該客觀規律盲目設定過低的代償率,也不能過度夸張自然風險移速的作用而裹足不前。在實地調研過程中發現農民的防災抗災意識仍然比較薄弱,風險的防控體系的建設相對滯后,可以在風險的預防、控制、處理三個環節進行干預。首先,完善風險防控體系建設,可以利用大數據網絡建立起完善農業災害測報預警體系,提升農業災害監測預報水平;第二,建議加強高標準糧田建設及配套設施的改造,構成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格局,提高農業生產抵御旱澇災害的能力;第三,制定自然災害的處理預案,擔保機構可以聯合政府加強對農戶的技術指導與服務,提高其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除此之外,農業保險是種植業最重要的政策性風險分流措施,擔保機構應當加以利用,比如可以把是否加入農業保險作為是否為糧食類產業的擔保服務條件之一,同時應當積極利用價格指數保險對沖農產品價格波動的不利因素。
參考文獻:
[1]Wu Kai,Jin Zejun,Xu Maobin.Thirst for money: External guarantees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J].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22,2(10): 101-105.
[2]Jarrow RA, Turmbull SM. The intersection of market and credit risk[J]. JournalofBanking&Finance2000(27): 271-299.
[3]陳旭紅.擔保公司擔保業務風險管理研究[J].中國市場,2022(05): 63-64.
[4]張萌.論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風險預警體系的構建[J].法治與經濟,2016(05):180-181.
[5]張大明.農擔聯盟的風險控制與風險管理實踐及啟示[J].財務與會計,2018(05):39-41.
[6]喬樸常,禮軍趙,文張臻.政策性農業擔保風險化解方式研究——基于陜西農擔的實證分析[J].財經界,2019(32):52-54.
[7]李萬鏑.財政支持農業擔保機構的效應分析與對策研究[J].地方財政研究,2013(01):60-64.
[8]李鐵寧,羅建華,胡建國.分類分級的政策性融資擔保業務費率體系構建[J].金融發展研究,2016(10):20- 25. DOI:10.19647/j.cnki.37-1462/ f.2016.10.003.
[9]林毅.擔保圈風險成因探析及防范對策[J].吉林金融研究,2014(10): 21-26.
[10]劉波.新冠肺炎疫情下融資擔保行業如何擺脫自身發展困境并助力中小微企業與民營經濟發展[J].吉林金融研究,2020(08):1-3.
[11]張超,王振宇.政府干預、管理者道德風險與農業信貸擔保風險防范策略[J].地方財政研究,2021(12):76-86.
[12]孫國民.金融擔保鏈問題的辯證分析及風險化解機制[J].現代經濟探討,2019(07):59-64.
[13]曹敏.擔保公司風險成因及應對措施[J].財會學習,2017(20):224-226.
[14]王靜.融資擔保公司經營風險控制和管理研究[J].中國中小企業, 2020(05):179-180.
[15]王壽辰.新冠肺炎疫情下發展農業經濟的思考[J].西部財會,2020(03): 59-61.
[16]牛彤.X融資性擔保公司與商業銀行合作的風險控制[J].經濟師, 2021(10):124-125+128.
[17]曹木子.融資擔保公司風險管理優化探討[J].征信,2021(10):86-92.
[18]孫同全,田雅群,馮興元,董翀.“去擔保化”與農業信貸擔保的未來[J].銀行家,2022(5).
[19]譚智佳,張啟路,朱武祥,李浩然.從金融向實體:流動性風險的微觀傳染機制與防范手段——基于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行業的多案例研究.管理世界[J]. 2022,38(03):35-59.
[20]杜群陽,周方興,戰明華.信息不對稱、資源配置效率與經濟周期波動[J].中國工業經濟,2022(04):61-79.
(作者單位:山東農業大學)
責任編輯: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