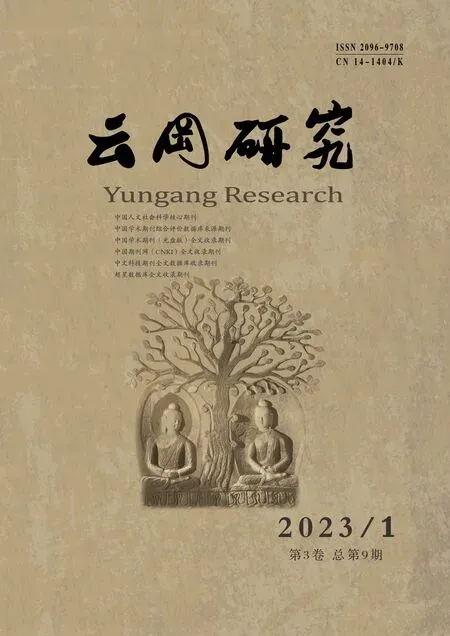龜茲石窟壁畫中菩薩信仰及其流行
殷弘承,王 斌
(1.新疆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2.烏魯木齊職業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龜茲石窟中的菩薩形象,是在釋迦牟尼成道前的生平經歷展開的,龜茲佛教很長一個階段盛行小乘說一切有部,而在古龜茲菩薩信仰是一切有部佛教信仰的重要構成元素,龜茲石窟的壁畫內容,始終貫穿以釋迦牟尼為中心的“唯禮釋迦”信仰展開的。其壁畫題材主要以宣揚釋迦菩薩在過去世的行善功德以及種種光輝事跡,尤其是以大量的故事畫的來表現釋迦菩薩在三阿僧祇耶階段對過去諸佛的供養并多次獲得授記的事跡來展開的。
一、以本生、因緣為主的故事畫表現輪回時代的釋迦菩薩
菩薩信仰的形成,應該與釋迦過去生中的修行活動有關,釋迦的修行,各部派都稱之為波羅蜜多。在三阿僧祇劫中,釋迦菩薩供養過無數佛,是成佛過程中的“累世修行”,這在龜茲石窟中大多是以“本生故事”(Jātaka)加以表現并被大量繪制在石窟主室頂部的兩券腹上(圖1),主要表現三阿僧祇劫階段的“四度”行為,本生包括佛與弟子過去世中的事跡,如木生譚所說,佛陀在其前生,時而變為馬,乃至變為象、鳥、國王、商人等,一切皆是凡夫形。石窟中大量的本生、因緣故事畫,宣揚輪回轉世。釋迦牟尼成佛前也只是一個菩薩,仍然跳不出輪回,必須經過無數次的轉生,積累大量功德,才最終覺悟。表現釋迦菩薩在行菩薩道時的形象以及宣揚釋迦菩薩的供養事跡,流行最廣的是“儒童供養”本生,該本生講述了釋迦牟尼前世為——梵志儒童,因向燃燈佛供養七朵蓮花、布發掩泥而獲得授記成佛。

圖1 克孜爾第17窟右券腹菱格本生故事畫
另外,龜茲石窟壁畫中還有以“誓愿畫”的形式表現釋迦的本生故事,最重要的是燃燈佛(Dīpa?kara)授記和陶師供養。克孜爾第100 窟主室兩側壁的方形格說法圖中也有誓愿畫,右側壁可釋讀的有陶師供養、婆羅門獻精舍;左側壁有婆羅門獻精舍、摩頂授記等題材。[1]描繪了釋迦菩薩往昔供奉過去佛,成道后被大眾供養的故事。庫木吐喇第34、50 窟有很多表現釋迦前世供養過去諸佛的畫面。如庫木吐喇第50 窟主室正壁佛龕側壁(含中脊部份)現存42 幅小型方格壁畫,每幅繪有一位供養者及一位佛陀,其供養人很可能都是千佛之中某位過去佛的前世,以此描繪歷代過去佛在往昔善心供養的功德或者發心向初佛果的誓愿。[2][3]第50 窟千佛名的釋讀,為壁畫中禮敬、供養大量的過去佛提供了有力證據,這是用壁畫與文字形式印證了從菩薩到成佛必須供養大量過去佛的佛經記載。
二、最后身菩薩——以釋迦菩薩的傳記為中心
“最后身”菩薩,是指釋迦菩薩結束萬劫輪回,從兜率天最后一次降生人間開始,到覺悟成佛、說法教化至最后涅槃之身。關于最后身的菩薩,當其從兜率天下生時,大眾部主張“一切菩薩入母胎時為白象形”。但是早期記載釋迦牟尼傳記的經典《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記載:“菩薩初下,化乘白象……因母晝寢,而示夢焉,從右脅入。”[4](P437b)釋迦菩薩從兜率天下降人間的投胎方式,部派佛教各派別有不同的看法,說一切有部認為化為白象入胎只是一種向征。菩薩追求無上菩提的同時,也要考慮下化眾生,向大眾宣揚佛法。龜茲石窟中的“最后身”菩薩,是以釋迦牟尼的傳記形式加以表現的。這些傳記題材大多見于《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普曜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等經典中。龜茲石窟中的佛傳壁畫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描述釋迦從誕生到涅槃前后一生的事跡,為本行圖,主要在方形石窟四壁中繪制,如克孜爾第76、110、206等窟;二是描述釋迦成道后的因緣佛傳或說法圖,主要在中心柱石窟主室的兩側壁的方形格或券頂的菱形格中繪制,如第38、34、163、171等窟。克孜爾第76、110窟作為反映釋迦菩薩“最后身菩薩”事跡最為集中的2 個石窟,第76窟主室左右側壁與正壁中上部各繪三欄佛傳故事畫,繪畫大面積被德國探險隊切割。[5](P88)第110窟為方形窟,頂部券頂繪菩薩、佛陀、坐禪比丘,券頂與側壁連接處繪本生故事。此外,主室正壁及左、右側壁各繪三欄佛傳故事畫,共計60幅,主室北壁上部繪大型降魔變,若加上正壁上方的降魔變,則佛傳圖達到61 幅。佛傳故事基本按照時間先后順序有序繪制,反映了釋迦牟尼從兜率天下降人間直到涅槃的平生事跡,勾勒出連續而完整的釋迦牟尼傳記畫面。德國學者施密特(Klaus T. Schmidt)釋讀了克孜爾第110 窟的龜茲語題記,釋迦牟尼在成道前后的稱呼發生了改變,在第34幅畫之前稱釋迦牟尼被稱為為“菩薩”,而在第34 幅畫成道之后,則被尊稱為“全知的人、導師”。[6]小乘佛教講究輪回轉世,成道之前的釋迦牟尼是一位菩薩,經過無數次的輪回轉世,積累功德(Pu?ya)和修行,最終成道后,將佛陀視作是一個偉大的導師。 克孜爾第110 窟有摩耶夫人(Mahāmāyā)夢見六牙白象入胎的壁畫題材。然后是逾城出家,第110窟“逾城出家”則繪制表現了在梵天、帝釋天協助釋迦實現“逾城出家”的事跡,畫面有夜叉用梯子接太子出禁宮,四天王共托馬足騰空逾過城墻畫面(圖2)。此為釋迦菩薩舍去“煩惱”步入“解脫”(vimok?a)的第一步,是“最后身菩薩”的關鍵環節階段。

圖2 克孜爾第110窟釋迦王子逾城出家
其它如克孜爾第118窟壁畫也是反映“最后身信仰”的石窟,主室正壁大幅反映宮中生活的畫面也屬于最后身的范疇,釋迦菩薩在成道之前,其信仰活動仍然有不完善之處,這也是說一切有部將成道之前的釋迦牟尼的最后身菩薩看作是凡夫的主要觀點。
三、菩薩信仰在龜茲的流行
龜茲石窟壁畫內容主要體現說一切有部的基本佛教信仰,宣揚菩薩信仰的壁畫內容在石窟中被作為重點來加以表現。是時在龜茲當地僧人們的修行過程中,菩薩道信仰的流行也可見一斑,如克孜爾第58窟出土的龜茲文木牘中提到一段殘文:“他們也有很多弟子們、菩薩們”,[7]該木簡的發現為龜茲地區菩薩道的信仰提供了有力佐證。
克孜爾石窟出土的佛教文獻中有一本《瑜伽禪經》(Yogalehrbuch),是一本修行手冊。《瑜伽禪經》用婆羅迷文A 型文字進行書寫的,據經書文字特點,書寫時間可定為7-9 世紀。德國學者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教授認為此文獻是屬于說一切有部。經書中屢次提出要以無上菩提為修行終極目標,規定修行者在普度眾生使命完成前,不得入涅槃,并將修行者直接稱為菩薩,《瑜伽禪經》的禪法內容與《阿毗達磨俱舍論》關系密切,接受了新有部的信仰體系,該經具有明顯的菩薩道信仰。菩薩們的所發誓愿是修行僧人在禪修實踐過程中冥想的對象,冥想中的僧人將自己比作具有“三十二妙相”的未來釋迦牟尼佛。該文獻還記載有關于“摩頂授記”的禪法,修行者在想象中受到釋迦牟尼的摩頂并得到了未來成佛的預言。涉及此經殘片有數片還在北道的其他佛教遺址中發現,說明該經在本區域的廣泛流行。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在龜茲自始至終都占據主流地位,而以追求阿羅漢為最高果位,是小乘佛教的修行者們的畢生追求。
季羨林先生曾引用了幾段在克孜爾石窟出土的有關彌勒菩薩的梵文文獻:“為以彌勒為首的諸大士菩薩們啟請,使他們迅速獲得等正覺”,“由于布施了食物及其他生活用品,祈愿以彌勒為首的各個菩薩們快速得到神通力”,“由于布施了虔誠的物品,愿一切走上了菩提之路的以彌勒為首的菩薩們迅速得到神通力”。[8]這些發愿文顯示菩薩有很多,以彌勒為首,表達了信眾由于對寺院的僧伽進行了布施,其功德猶如修行中的菩薩,希望他們能盡快地獲得具有佛陀一樣的神通力。彌勒圖像經常被繪在龜茲中心柱石窟主室前壁入口處的位置(也是禮拜者最后的出口)上方,呈交腳坐姿,有時手提凈瓶,是作為僅次于釋迦牟尼佛而被崇拜的。德國學者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最早將龜茲中心柱石窟主室前壁門道上部繪制的菩薩坐像都釋讀為彌勒菩薩(Maitreya)。[9](P103)克孜爾石窟第17、38、171(圖3)、224等窟彌勒說法圖保存較好,而克孜爾第77 窟彌勒則被繪在了甬道內側壁上。[5](P90)龜茲石窟壁畫中還有表現“七佛一菩薩”的畫面。①庫木吐喇第33窟將彌勒繪制在了主室穹窿頂上,在克孜爾第135、123窟,以及森木塞姆第46窟主室穹隆頂部梯形8個條幅內,各繪一身立佛,從殘存的壁畫看,可能是七佛及彌勒菩薩侍奉的畫面。克孜爾第80、97窟主室正壁“降伏六師外道”畫面上部出現“七佛一菩薩”,其對面,即主室前壁上方繪制“彌勒兜率天說法”圖。第114 窟則將主尊彌勒像繪在主室正壁的龕內,而其對面前壁門道上部的“降伏六師外道”畫面中出現七佛一菩薩(彌勒菩薩),反映了彌勒與“七佛”是一種繼承關系。將彌勒置于入口上方,顯然與彌勒菩薩將繼承釋迦成佛的信仰有關,具體地說,與小乘說一切有部“三世實有、法體恒有”的“三世”觀念有關。“三世實有,法體恒有”是說一切有部的信仰基石,也是說一切有部與其他派別有所區別的重要特征。

圖3 克孜爾第171窟主室前壁門道上部呈交腳坐姿的彌勒
說一切有部的“三世”觀念認為過去、未來和現在都有法的存在,三世之間具有密切的因果聯系。《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76 記載:“復有三法,……無出家受具。”[10](P393a-b)如果不承認過去法,也就否定過去佛的存在,否定過去佛的存在,就等同否認佛教的存在,那么也就沒有了出家受戒的佛教僧團。小乘只承認三世佛(過去、現在、未來),而不認可“十方佛”的存在。
龜茲誓愿畫的出現,除了頌揚釋迦菩薩的圣跡之外,也應與僧侶追求無上菩提的愿望與實踐活動有關,如《勸發菩提心文》載:“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不可緩也。[11](P449)供養過去諸佛,普度眾生是成為圣者的重要條件,這是菱形格故事畫在龜茲石窟中大量繪制的原因。克孜爾第8、34、38、80等窟主室券頂菱形格故事種類眾多,釋迦成道后對大眾的說法、教化以及對他人的授記,具有很強的宣傳與教育意義。通過描繪釋迦菩薩前世供養諸佛的事跡,可以教導人們去發菩提心,追求菩薩道,是龜茲小乘佛教信徒的最終目標。
說一切有部在成佛的實踐上,卻又與大乘佛教有根本的區別。認為菩薩供養諸佛的事跡除了宣揚菩薩的偉大之外,還給大眾樹立了榜樣,教化眾生發菩提心,追求無上正覺。供養過去佛并且獲得佛的授記是菩薩信仰的重要步驟,吐魯番柏孜克里克與龜茲的誓愿畫與《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的內容可以一一對應,說明公元7、8 世紀時誓愿、授記信仰在龜茲地區一帶長期流行,進而有力地證明了菩薩信仰在當地的上升趨勢。
結語
說一切有部以敘述有關釋迦菩薩的事為主,菩薩“逢事諸佛”、修妙相業、修四波羅蜜、“超越九劫”等內容,這些都是菩薩信仰的基礎。龜茲石窟壁畫中有的很多壁畫內容是表現釋迦菩薩的,畫面中的佛陀形象不一定是釋迦牟尼,而是釋迦菩薩在行菩薩道時供養的過去佛,以宣揚釋迦菩薩的功績。
修“菩薩道”要通過“波羅蜜”的修持,這在龜茲石窟常常以本生故事的形式加以表現,“本生故事”是釋迦牟尼過去無數劫中行“菩薩道”階段的種種犧牲、供養過去佛的事跡。石窟壁畫中的誓愿畫大量出現反映了菩薩信仰在當地的流行,實際上,龜茲本生故事與誓愿畫反映的是小乘說一切有部的佛教信仰。
龜茲石窟中有大量的有關釋迦牟尼的傳記題材,這是關于“最后身菩薩”信仰的具體反映。最后身菩薩是菩薩的最高階位,經過此位,來生在人間成佛。說一切有部將釋迦菩薩成道前“最后身菩薩”仍然視為“凡夫”,僅僅是眾生的偉大導師,而不是神。
從菩薩到成佛要供養很多過去佛,對釋迦菩薩在三阿僧祇劫中供養過去佛的功德進行贊頌,目的是為了襯托釋迦牟尼的偉大。龜茲梵文經典的發現證明了當地存在修行菩薩道的僧侶以及菩薩信仰在當地流行,而龜茲的菩薩信仰應該屬于北傳小乘佛教菩薩體系,從說一切有部的角度體現了菩薩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