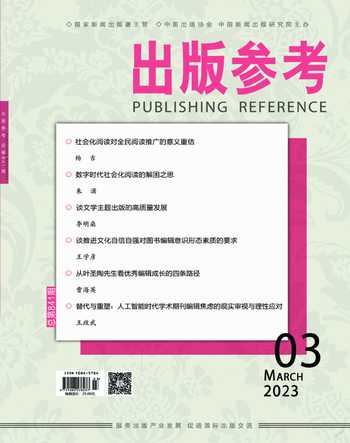紙書(shū)閱讀的破繭之道
張文彥 袁繼慧
摘 要:從社會(huì)知識(shí)史的視角看,信息繭房其實(shí)始終伴隨著知識(shí)傳承與傳播的過(guò)程——面對(duì)知識(shí)生產(chǎn)廣泛分散,人類便有了聚合的訴求,同質(zhì)化、淺層次、機(jī)械化聚合的結(jié)果便是信息的繭房化。從讀者角度看,閱讀繭房是人類在閱讀超載壓力下的應(yīng)激反應(yīng),是從現(xiàn)代社會(huì)到信息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程中一種越來(lái)越突出的閱讀癥候。紙書(shū)閱讀的精神特征與物質(zhì)特征使其蘊(yùn)藏著其他媒介閱讀尚不具備的破繭力量,有著催化新媒介產(chǎn)品的元閱讀價(jià)值。展望未來(lái),紙書(shū)閱讀或許會(huì)作為一種文化技藝長(zhǎng)存,為置身信息宇宙的我們提供沉思的綠洲。
關(guān)鍵詞:書(shū)籍 信息繭房 閱讀繭房 信息聚合 全民閱讀
信息繭房概念被廣泛應(yīng)用,展示了人們對(duì)數(shù)字化時(shí)代信息選擇的憂思:對(duì)信息的偏好會(huì)導(dǎo)致個(gè)體、群體乃至整個(gè)社會(huì)被同質(zhì)化的信息系統(tǒng)所包裹,雖然繭房能持續(xù)提供愉悅、溫暖且友好的感受,但這舒適的代價(jià)有可能是重大的錯(cuò)誤、可怕的夢(mèng)魘。[1]從社會(huì)知識(shí)史的視角看,信息的繭房化其實(shí)始終伴隨著知識(shí)傳承與傳播的過(guò)程——漫長(zhǎng)歲月中,知識(shí)生產(chǎn)廣泛分散,人類便有了聚合的訴求。聚合同質(zhì)化、淺層次、機(jī)械化的結(jié)果便是信息的繭房化;而具有開(kāi)放、協(xié)商和糾錯(cuò)機(jī)制的聚合,則促進(jìn)知識(shí)健康秩序的形成,以及創(chuàng)造性積累的可能。從讀者角度看,要具備“破繭”的意識(shí)和能力,需要通過(guò)復(fù)雜持久的閱讀訓(xùn)練。紙書(shū)作為文明的產(chǎn)物,在漫長(zhǎng)歲月中一直是人類提升閱讀能力的可靠工具。如今,信息云海瞬息萬(wàn)變,新技術(shù)和新載體更加助長(zhǎng)了繭房化效應(yīng),我們是否仍然能通過(guò)紙書(shū)閱讀這項(xiàng)古老又現(xiàn)代的技藝去陶冶閱讀審美,提高閱讀素養(yǎng),讓信息以飽滿、豐富、多元化的方式實(shí)現(xiàn)智慧聚合?
一、信息繭房與閱讀繭房
近年來(lái),我國(guó)學(xué)界對(duì)“信息繭房”概念開(kāi)展了許多富有啟發(fā)性的實(shí)證或理論研究,這些研究大部分著眼于數(shù)字化社會(huì),從信息生產(chǎn)傳播角度審視信息繭房的生成邏輯、具體構(gòu)造以及用戶影響,并從技術(shù)或機(jī)制改進(jìn)、受眾信息素養(yǎng)提升角度提出一些“破繭”建議。受眾是否具備防止“繭房化”的警覺(jué)和“破繭”的能動(dòng)性,在具體行動(dòng)層面是由閱讀決定的。如上文所述,信息繭房并非數(shù)字化社會(huì)獨(dú)有現(xiàn)象,只不過(guò)技術(shù)和載體讓這種現(xiàn)象成為當(dāng)代社會(huì)突出的閱讀癥候。大量高速生成的信息帶來(lái)了閱讀超載的壓力,個(gè)體或群體由此產(chǎn)生各種應(yīng)激反應(yīng),直覺(jué)和感性主導(dǎo)下的反應(yīng)會(huì)日積月累形成信息繭房,而直覺(jué)和感性主要源于生活的環(huán)境和質(zhì)量,并由日常閱讀習(xí)慣和能力所支配,是信息裹挾中的被動(dòng)追隨。
我們需要將研究起點(diǎn)前移至現(xiàn)代社會(huì)剛剛崛起的時(shí)刻,書(shū)報(bào)刊的數(shù)量和品種開(kāi)始激增,讀物從精英走向大眾,閱讀從少數(shù)人的專屬技藝融入大多數(shù)人的日常生活,卻在世界各地表現(xiàn)出一種降維普及的狀態(tài)。伯明翰學(xué)派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在《識(shí)字的用途》一書(shū)中以深刻細(xì)膩的筆觸,剖析了20世紀(jì)上半葉英國(guó)工人階級(jí)文化生活所發(fā)生的變革與延續(xù):物質(zhì)環(huán)境進(jìn)步巨大,而文化觀念的變化卻相對(duì)遲緩,一些滋生于工人工作、生活、社交中的古老因素仍然在工人的家庭閱讀中發(fā)揮著隱形作用,左右著成為新興讀書(shū)群體的工人讀者的興趣與品味。商業(yè)出版巨頭極力逢迎,旗下的眾多新興雜志“就像是坐在一位多情、迷信、老派的母親身邊那個(gè)腦筋轉(zhuǎn)得快、手中有一大堆新式選項(xiàng)的年輕聰明兒子”[2]。傳統(tǒng)與商業(yè)的合流,造成了品質(zhì)低下的社會(huì)閱讀特征:如果作家沒(méi)有立刻吸引住那種一目十行的初次閱讀,那么他就犯了錯(cuò),讀者從來(lái)不犯錯(cuò);好的作品無(wú)法走紅,大眾作品無(wú)法真正去探討經(jīng)驗(yàn),因?yàn)樽x者欠缺“通過(guò)文字的復(fù)雜性尋求一種理解”的能力,就像一個(gè)“小男人”卻被(大眾出版物)“塑造成像個(gè)巨人似的,因?yàn)橐磺袞|西都按照他的尺寸縮小了比例”。[3]所謂縮小了比例,就是以個(gè)性化、碎片化、提供大量樂(lè)趣的閱讀導(dǎo)向?qū)⒆x者拉攏到“假裝親密”的團(tuán)體中;為了讓讀者流連忘返,還要以更直觀的事物取代傳統(tǒng)文字讀物,比如讀連環(huán)漫畫(huà)。[4]出生于工人家庭的霍加特在書(shū)中以大量犀利的文字批判這種不斷“向下滑行”閱讀風(fēng)氣的后果:“對(duì)一個(gè)時(shí)代影響最大的并不是原創(chuàng)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在這些觀點(diǎn)被簡(jiǎn)單地、扭曲地篩濾之后從中得出的東西。”[5]他悲觀地指出,雖然工人階層擁有了閱讀的能力,卻仍然是出版物之車上載著的“野蠻人”,“在仙境中義無(wú)反顧地朝前走……單單為了向前而向前”[6]。這里提到的“仙境”,與信息繭房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更側(cè)重于讀者體驗(yàn),或許我們可以藉此提出一個(gè)仿造的概念:閱讀繭房。
信息繭房著眼于信息的生成機(jī)制,閱讀繭房則指向了讀者自身的閱讀素養(yǎng)。《信息烏托邦》將維基百科等協(xié)商、眾創(chuàng)的知識(shí)生產(chǎn)方式作為前者的破解之道,而對(duì)于“仙境”中后者的警示與解放,則需要已經(jīng)掌握更高級(jí)閱讀技藝的同類來(lái)幫助促進(jìn)改善,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閱讀整體素養(yǎng)的提高,這種人類閱讀共同體意識(shí),開(kāi)啟了二戰(zhàn)后尤其是冷戰(zhàn)結(jié)束以來(lái)西方國(guó)家促進(jìn)全民閱讀的歷史。在《國(guó)外全民閱讀法律政策譯介》[7]的編撰過(guò)程中,筆者發(fā)現(xiàn)西歐諸國(guó),美、日、韓等國(guó)家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均遭遇到如霍加特所描述的閱讀資料日益豐富與大量新識(shí)字人口閱讀素養(yǎng)不足的社會(huì)性矛盾,這成為各種國(guó)家閱讀推廣政策、法規(guī)、研究報(bào)告和大型項(xiàng)目落地的原因。其中,紙書(shū)閱讀一直扮演著主角,這主要由三方面原因決定:一是紙書(shū)歷史悠久,隨著印刷技術(shù)的發(fā)達(dá),教育、圖書(shū)館、出版發(fā)行等行業(yè)建立起了成熟完備的紙書(shū)生產(chǎn)、傳播和評(píng)價(jià)體系,為閱讀推廣者提供了穩(wěn)定可靠、源源不斷的物質(zhì)工具。二是人類閱讀的方法體系和鑒賞標(biāo)準(zhǔn),也主要是在紙書(shū)的大量長(zhǎng)久閱讀實(shí)踐中積累凝結(jié)而來(lái),為閱讀推廣的專業(yè)化提供了保證。三是兒童是閱讀推廣的重心,無(wú)論從生理機(jī)能還是心理認(rèn)知規(guī)律看,紙書(shū)仍然是該群體最適合的讀物。
對(duì)紙書(shū)的倚重,逐漸形成了各國(guó)閱讀推廣實(shí)踐中的一些共識(shí),例如:越早讀書(shū)越好,美國(guó)的《卓越閱讀法案》、日本的《少年兒童讀書(shū)活動(dòng)推進(jìn)法》、英國(guó)的“閱讀起跑線計(jì)劃”等都是著力促進(jìn)兒童早期閱讀;要大量讀書(shū),如全美圖書(shū)館廣泛開(kāi)展的“1000 Books Before Kindergarden”(上幼兒園前讀夠一千本書(shū))項(xiàng)目,致力于為廣大家庭的孩子提供足夠的繪本;倡導(dǎo)經(jīng)典閱讀、精讀、批判性閱讀、培養(yǎng)讀書(shū)持久力等閱讀素養(yǎng)方面的理念,在大量項(xiàng)目中得以落地推廣。以紙書(shū)閱讀為軸心的世界閱讀推廣實(shí)踐,期待以這種載體所塑造的閱讀能力,可以阻斷精神上的代際貧困,增進(jìn)閱讀文化的多樣性,實(shí)現(xiàn)文化的創(chuàng)造力,這可以視為一個(gè)民族、一個(gè)國(guó)家合力進(jìn)行的閱讀破繭之策。然而,數(shù)字技術(shù)所引發(fā)的紙書(shū)閱讀危機(jī),對(duì)閱讀推廣帶來(lái)了更多的壓力和不確定性。日本2005年專設(shè)了《文字及印刷品文化振興法》,旨在應(yīng)對(duì)危機(jī),重振閱讀傳統(tǒng)。數(shù)字化媒介產(chǎn)品在短期內(nèi)的大量涌入,似乎在整體性地瓦解著人類閱讀長(zhǎng)久秉持的觀念和特質(zhì)。
二、紙書(shū)的物質(zhì)特征與精神特征
筆者提出閱讀繭房的概念,是希望藉此揭開(kāi)數(shù)字化所帶來(lái)的時(shí)代性遮蔽,進(jìn)而去體察閱讀行為本有的內(nèi)在矛盾。如上文所述,在工業(yè)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程中,大多數(shù)人雖然擁有了閱讀機(jī)會(huì),卻也陷入到大眾閱讀的夢(mèng)幻漩渦中。閱讀的繭房化既是傳統(tǒng)生活慣性的延續(xù),又是物質(zhì)生活在精神世界中的延伸——現(xiàn)代國(guó)家的崛起,首先表現(xiàn)為物的豐富多樣。越來(lái)越琳瑯滿目的物品,讓我們養(yǎng)成依賴品牌、包裝、廣告這些直觀要素進(jìn)行節(jié)時(shí)省神選擇的習(xí)慣,發(fā)達(dá)的物流快遞系統(tǒng)不斷縮短我們等待收貨的時(shí)間,物的世界以我們的需求為指針配比在縮小的時(shí)空中,一切立等可取、垂手可得,這種物質(zhì)生活的方式影響著我們的信息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類千百年來(lái)贊頌的“踏破鐵鞋無(wú)覓處”的求學(xué)精神,削弱了那種因求書(shū)艱難而倍加珍重的閱讀體驗(yàn),也因此影響著社會(huì)閱讀能力的整體發(fā)育。
閱讀世界自身構(gòu)造也在發(fā)生劇變,現(xiàn)代性的加速邏輯改變了我們的閱讀時(shí)間分配——時(shí)間總量沒(méi)有變化,單位時(shí)間里的閱讀量卻大幅增加。有越來(lái)越多的工作、社交和娛樂(lè)都需要通過(guò)閱讀進(jìn)行,不斷擠壓著為知識(shí)和信息而讀的專有閱讀時(shí)間;數(shù)據(jù)海洋為我們提供了太多選項(xiàng),于是我們?cè)跓o(wú)意和有意之間開(kāi)啟了與數(shù)字技術(shù)新的合謀——以“10+”“+訂閱”、朋友圈、算法推薦為助手,把浩瀚信息宇宙縮小到我們喜聞樂(lè)見(jiàn)的格局,以獲得一種更為輕松溫暖和親密牢固的閱讀體驗(yàn)。這看似綿密的繭房其實(shí)由大量不連貫的信息聚合而成,沒(méi)有知識(shí)系統(tǒng),只是同類的語(yǔ)言、觀點(diǎn)周而復(fù)始。這種閱讀風(fēng)潮是社會(huì)加速發(fā)展所導(dǎo)致的新異化[8]的表征之一。在其主導(dǎo)下的海量閱讀、長(zhǎng)時(shí)間閱讀不再有靈感火花的耀目綻放,不再有浮士德般上下求索的尋覓精神,而更像是一種身體導(dǎo)向的饕餮追求。
在這種閱讀風(fēng)潮里,紙書(shū)閱讀是否還持有培養(yǎng)閱讀素養(yǎng)的力量?紙書(shū)閱讀的優(yōu)勢(shì)是由其載體形態(tài)和內(nèi)容邏輯共同塑造的,我們需要將紙書(shū)與數(shù)字化媒介進(jìn)行比照觀察。
首先,從物質(zhì)屬性看,讀者能夠獲得紙書(shū)所具有的物的專屬性能。紙張發(fā)明后,各民族的知識(shí)開(kāi)始陸續(xù)從皮、石、木、金等多介質(zhì)向紙書(shū)整體轉(zhuǎn)移,紙書(shū)成為全人類共有的知識(shí)載體,逐漸形成由印張、封皮、書(shū)頁(yè)、書(shū)脊等具體構(gòu)件組合而成的穩(wěn)定物理形態(tài),塑造出翻書(shū)、批注、讀書(shū)摘要、筆記、曬書(shū)等特定動(dòng)作行為,衍生出藏書(shū)印、書(shū)簽、書(shū)衣、書(shū)包、書(shū)架、書(shū)房、書(shū)店、圖書(shū)館、出版社、書(shū)展及書(shū)市等具有美學(xué)和文化象征意義的物質(zhì)體系,紙書(shū)由此成為人類精神得以聚集的“家園”“避難所”或“詩(shī)意棲居”之地。換句話說(shuō),紙書(shū)閱讀是人類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dòng)形式,與其他精神活動(dòng)和身體活動(dòng)有著鮮明的區(qū)別。這不同于壽命短暫、體量有限的新聞紙、雜志,亦不同于手機(jī)、電腦或可穿戴設(shè)備——閱讀這些媒介的方式更輕松隨意,所受時(shí)空條件限制更少,但與其他娛樂(lè)、社交行為的界線也不明顯,對(duì)閱讀技藝的專業(yè)程度要求不高。人類用手指或鼠標(biāo)控制界面,數(shù)字化內(nèi)容以整齊劃一的步調(diào)和樣式供我們調(diào)遣,人類憑借紙書(shū)這種物質(zhì)形態(tài)所建構(gòu)起的閱讀觀念、能力、審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數(shù)字化閱讀素養(yǎng)尚未明確與普及之時(shí),閱讀繭房會(huì)給我們?cè)炀蜔o(wú)數(shù)個(gè)性化、多元化、彼此分隔的空間,我們只去探訪我們的“親朋好友”,用鍵盤(pán)對(duì)不順眼的信息口誅筆伐,紙書(shū)世界中所形成的強(qiáng)有力的認(rèn)同與價(jià)值判斷,也就此瓦解。
其次,紙書(shū)時(shí)代所形成的創(chuàng)作、翻譯、編輯、校對(duì)、裝幀、倉(cāng)儲(chǔ)、發(fā)行、陳列、保藏、評(píng)論、推薦、二手售賣等一系列知識(shí)生產(chǎn)與傳播的模式,建構(gòu)了紙書(shū)閱讀的技藝、規(guī)則與速度,并使之成為需要指導(dǎo)與訓(xùn)練才能實(shí)現(xiàn)的高難度復(fù)雜性精神活動(dòng)。數(shù)字化時(shí)代內(nèi)容的生產(chǎn)與傳播,有著更為明顯的降低閱讀門(mén)檻的趨勢(shì),從積極角度看,這幫助人類逾越了生理構(gòu)造導(dǎo)致的多種閱讀障礙,提高了閱讀效率,比如通過(guò)虛擬仿真技術(shù),可以更加直觀地掌握幾何圖形、人體解剖、抽象科學(xué)概念等知識(shí)。但需要警醒的是,紙書(shū)時(shí)代所積淀的豐富閱讀技藝和創(chuàng)造性閱讀精神,正陷入被降維和簡(jiǎn)化境遇中。閱讀的專注力、長(zhǎng)篇閱讀持久力、精讀以及經(jīng)典閱讀力在普遍下降,不僅因?yàn)槊媾R多元媒介的競(jìng)爭(zhēng),也因?yàn)楦鞣N以降低文本難度與長(zhǎng)度為招牌的知識(shí)產(chǎn)品在大量出現(xiàn)。這種代價(jià)是閱讀的扁平化,我們用輕松占有知識(shí)的快感替代了經(jīng)大腦艱苦勞作而“一覽眾山小”的暢快,挑戰(zhàn)艱澀文本的銳氣被日漸消磨,也就喪失了突破閱讀繭房的信念與力量。
最后,紙書(shū)所承載的是以文字符號(hào)為主的信息形式,大部分書(shū)籍以色彩單調(diào)、文字密集、版式單一的二維面貌出現(xiàn),裝幀和插圖并非紙書(shū)世界的主角,讀者需要憑借以看為主的視覺(jué)活動(dòng),激發(fā)理解、領(lǐng)悟、想象、判斷、推理等具有復(fù)雜耗時(shí)的精神活動(dòng),以足夠的精神能量超越枯燥的符號(hào)矩陣,才能游弋于思想的精巧雄奇之中,建立心靈的秩序。而影視、游戲、網(wǎng)頁(yè)、AR或VR等數(shù)字化產(chǎn)品卻能運(yùn)用色彩、光線、聲音、質(zhì)感、氣味甚至冷熱等元素給人以多元感官刺激,甚至造就任人行動(dòng)的虛擬世界。紙書(shū)和數(shù)字化產(chǎn)品所帶來(lái)的體驗(yàn)是否有高下之分?積極心理學(xué)奠基人契克森米哈賴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礎(chǔ)上撰寫(xiě)的《心流:最優(yōu)體驗(yàn)心理學(xué)》一書(shū),讓我們看到,只有高水平閱讀才能獲得心流體驗(yàn)。所謂心流,是指專注于實(shí)際目標(biāo)并全身心投入,讓回憶、思考、意志力都充分發(fā)揮作用,當(dāng)感官變得井然有序時(shí),心靈體驗(yàn)就能到達(dá)最優(yōu)狀態(tài)。[9]無(wú)法掌控注意力,就不能對(duì)目標(biāo)注入足夠的精神能量,也就無(wú)法達(dá)到澄瑩如練般超我的高級(jí)狀態(tài)。書(shū)中常常以書(shū)籍閱讀來(lái)印證這種心流體驗(yàn)的實(shí)現(xiàn),同時(shí)也多次提到電視或報(bào)刊、社交等不需耗費(fèi)太多精神能量,自然也無(wú)法出現(xiàn)心流體驗(yàn)。這部作品出版于20世紀(jì)90年代,尚不涉及數(shù)字化媒介,但書(shū)中提到,注意力可以像探照燈那樣集成一道光束,也可能毫無(wú)章法地散開(kāi),經(jīng)訓(xùn)練由我們控制的注意力,能夠改變體驗(yàn)的品質(zhì)。[10]據(jù)此我們可以判斷,數(shù)字化媒介所催生出的大量產(chǎn)品,恰恰如電玩大廳那樣躁動(dòng)、喧囂、絢麗、令人目不暇接,分散著我們的注意力。沉湎于這種外在感官刺激,不斷期待虛擬的豐盈獎(jiǎng)賞,無(wú)法掌控意志力的人將樂(lè)而忘歸。
三、作為元閱讀的紙書(shū)閱讀未來(lái)發(fā)展
筆者批判當(dāng)下社會(huì)閱讀的普遍無(wú)力,并不是說(shuō)唯有退回紙書(shū)時(shí)代才能得到救贖,而是要更好地運(yùn)用紙書(shū)閱讀的潛能,將紙書(shū)閱讀嵌回到數(shù)字化世界之中,試著厘清它與各種新媒介、新閱讀行為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才能更為客觀平衡地探尋這種古老技藝的未來(lái)。
首先,紙書(shū)閱讀與新媒介閱讀不僅只有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也在不斷生發(fā)著彼此促進(jìn)的合作關(guān)系。相關(guān)實(shí)證研究已有許多,尤其是針對(duì)青少年這些數(shù)字時(shí)代“原住民”的研究。筆者想以自身日常的大量觀察作為例證:在開(kāi)設(shè)《閱讀推廣》課程的幾年教學(xué)經(jīng)歷中,常常發(fā)現(xiàn)學(xué)生們會(huì)在新媒介的使用中激發(fā)起讀書(shū)的興趣。尋找到讀書(shū)的軌道,英劇迷去讀英國(guó)的歷史,音樂(lè)劇迷去看西方音樂(lè)史;有聲書(shū)、嗶哩嗶哩視頻被廣泛用于輔助學(xué)習(xí)、理解學(xué)術(shù)著作;有位學(xué)生玩了以希臘神話為主題的電子游戲Hades后,意外解決了《荷馬史詩(shī)》諸神姓名難記、關(guān)系難解的閱讀障礙。最近筆者為《青島大學(xué)報(bào)》主持了一個(gè)實(shí)驗(yàn)性專版《在世界讀書(shū)日,聚焦新媒體閱讀》[11],學(xué)生們從有聲閱讀、路牌、電子游戲、電影、推理游戲、短視頻等方面觀察人類閱讀行為與需求的多元發(fā)展,分析這些閱讀行為對(duì)社會(huì)或個(gè)體的新價(jià)值。具有積極意義的新閱讀行為往往可以憑借數(shù)字技術(shù)繼承,甚至加強(qiáng)紙書(shū)閱讀的某一種功能,豐富人和紙書(shū)之間的閱讀層次。而閱讀的疊加效果更大限度地開(kāi)發(fā)了紙書(shū)中的思想世界。鐘愛(ài)某些書(shū)籍的讀者如今可以擁有由該書(shū)而再造的有聲書(shū)、影視、游戲等多種選擇,實(shí)現(xiàn)由平面到立體、多維的閱讀鑒賞。而以紙書(shū)為根系的多元媒介產(chǎn)品,往往是群體閱讀體驗(yàn)交匯碰撞的有機(jī)產(chǎn)物。從這種意義而言,信息繭房經(jīng)由閱讀者的智慧性能動(dòng),有了改造成“信息皮膚”的可能,并幫助閱讀者更為積極主動(dòng)地在數(shù)字化世界開(kāi)拓。紙書(shū)閱讀對(duì)于信息皮膚的生成,起著原始基因式的作用。
其次,紙書(shū)閱讀是閱讀新生態(tài)體系中水和營(yíng)養(yǎng)的輸送管道,其他媒介的繁茂健康成長(zhǎng),無(wú)法脫離積累了上千年的人類紙書(shū)文明。電影《沙丘》的拍攝史就是一個(gè)典型案例。紀(jì)錄片《佐杜洛夫斯基的沙丘》(2013)回顧了著名導(dǎo)演佐杜洛夫斯基為《沙丘》付出了巨大努力卻未成功的拍攝歷路,其中關(guān)鍵性的努力來(lái)自于導(dǎo)演及主創(chuàng)人員對(duì)小說(shuō)《沙丘》的閱讀。《沙丘》的拍攝史就是由導(dǎo)演組織發(fā)起的一場(chǎng)大型讀書(shū)會(huì):佐杜洛夫斯基為了將這部美國(guó)科幻小說(shuō)的里程碑式著作拍攝成電影,租了法國(guó)一座古堡潛心研讀,但前100頁(yè)幾乎看不懂。《沙丘》的閱讀難度是眾所周知的,人物眾多,充滿線索性的暗示,夾雜大段大段意識(shí)流式的人物內(nèi)心獨(dú)白;既有古希臘式的古典戲劇結(jié)構(gòu),又以浩瀚宇宙為背景,蘊(yùn)藏著作者在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外交、民族、宗教、生態(tài)、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深邃思考。佐杜洛夫斯基需要仔細(xì)斟酌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尋找文字改編成畫(huà)面的可能。為此,他傾注心血做了小說(shuō)的“閱讀筆記”——將小說(shuō)改編成劇本后,他找到法國(guó)漫畫(huà)家再改編成3000幅速寫(xiě)畫(huà)。導(dǎo)演閱讀理解的精神結(jié)晶成為與其他制作人員溝通的工具,找當(dāng)紅的搖滾樂(lè)隊(duì)配樂(lè),找藝術(shù)家設(shè)計(jì)造型,甚至找到畫(huà)家達(dá)利出演皇帝這個(gè)反派角色……陣容強(qiáng)大的制作參與者都可謂佐杜洛夫斯基《沙丘》讀書(shū)會(huì)的參與者。雖然這部構(gòu)思超前的電影最后以流產(chǎn)告終,但卻被稱為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失敗——因?yàn)閷?dǎo)演對(duì)《沙丘》的閱讀理解與表達(dá),在后來(lái)的歲月中持續(xù)激發(fā)著制作團(tuán)隊(duì)成員的靈感,使《沙丘》的精神財(cái)富在《星球大戰(zhàn)》《異形》《普羅米修斯》等電影中分享。佐杜洛夫斯基未竟的電影夢(mèng)想于2021年由知名導(dǎo)演丹尼斯·維倫紐瓦實(shí)現(xiàn),這位導(dǎo)演正是這部小說(shuō)的忠實(shí)讀者。質(zhì)言之,在數(shù)字媒介的運(yùn)作中,經(jīng)由集體閱讀的方式被跨媒介再造,紙書(shū)閱讀也由此獲得了數(shù)字化時(shí)代元閱讀的地位:掌握精湛閱讀技藝的人是元閱讀的實(shí)施者,通過(guò)閱讀實(shí)現(xiàn)對(duì)文本的再造和分發(fā),由此創(chuàng)造出的媒介新產(chǎn)品,經(jīng)由用戶的使用派生出元閱讀之后的次級(jí)閱讀、三級(jí)閱讀……紙書(shū)在群體分層閱讀中顯示了更多創(chuàng)造性價(jià)值,并具備了開(kāi)放性、協(xié)商性、交互性的新機(jī)遇。紙書(shū)閱讀得以成為新媒體閱讀的“巨人的肩膀”。
最后,在人工智能、元宇宙、腦機(jī)交互等技術(shù)的潮涌之中,紙書(shū)或許終將成為小眾讀物,紙書(shū)閱讀也或?qū)⒊蔀橐环N小眾化的文化技藝,供有興趣、有天賦的少數(shù)人掌握和傳承。但在紙書(shū)作為商品大行流通的今天,在人類文明還未從紙載體向硅載體整體搬遷的今天,紙書(shū)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jià)值。在商業(yè)邏輯和計(jì)算機(jī)邏輯的雙重作用下,人類的信息世界越來(lái)越呈現(xiàn)出無(wú)限度、無(wú)結(jié)構(gòu)的特征,[12]可供任何閱讀口味和能力的人長(zhǎng)驅(qū)直入,于是新聞、觀點(diǎn)會(huì)以病毒式的速度傳播擴(kuò)散,最簡(jiǎn)單的閱讀功能造就了包容人類的巨大閱讀繭房,個(gè)體或群體分據(jù)其內(nèi)部空間,生命時(shí)間被大量消耗。唯有紙質(zhì)圖書(shū)的不可直接聯(lián)網(wǎng)性,使其保留了“閱讀綠洲”的意義,紙書(shū)閱讀給予讀者主動(dòng)斷網(wǎng)的體驗(yàn),減慢閱讀的速度,延長(zhǎng)沉浸的時(shí)間,訓(xùn)練形成體系、結(jié)構(gòu)和邊界的閱讀,以此濯洗我們的感官,建立心靈和知識(shí)的秩序。
(作者單位系青島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