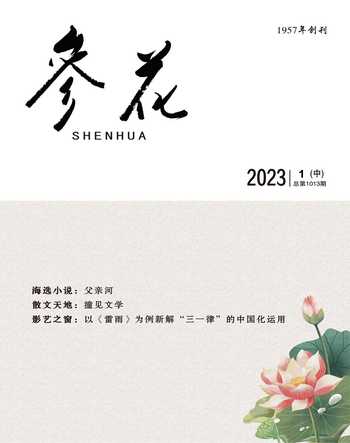異化理論視角下《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中的異化研究
1960年,愛德華·阿爾比憑借獨幕劇《動物園的故事》名聲大噪,在美國戲劇界引起轟動,成為美國戲劇界的大師。《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這部劇一炮而紅,獲得了紐約劇評獎,并被評為當季最佳戲劇。該劇講述了兩對夫婦之間的情感沖突,以及他們與來訪的尼克夫婦之間有趣的“游戲”。他們四個人不停地爭吵,瘋狂地跳舞、做游戲,直到天亮才漸漸清醒過來。在戲劇的結尾,瑪莎和喬治的幻想破滅了,他們選擇了和解,破除了異化,開啟新的生活。
一、弗洛姆的異化研究
艾里希·弗洛姆是著名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代表作有《愛的藝術》《健全的社會》等。弗洛姆在吸收了勞動異化理論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后,對異化理論進行了更廣泛的解釋。首先,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中解釋了異化與心理健康的關系。他認為,異化會導致精神上的罪惡感,人們會缺乏愛別人的能力。其次,弗洛姆認為現代的人普遍會因為大眾傳媒的影響而感到孤獨,異化等同于孤獨。他認為只有持續的愛才能消除孤獨,實現平衡和諧的生活方式。最后,他認為個體在家庭中的經歷也會形成疏離感,這種疏離感形成了孤獨感。本文通過分析弗洛姆的異化理論,不僅可以為讀者理解該劇的異化主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而且對探索如何通過情感來消除日常生活中的異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中人物的異化癥狀
弗洛姆曾在《健全的社會》中提出,被異化的人并不體驗到自己是權力的中心,而是依賴于外部的權力(弗洛姆,2008),劇中的人物陷入了不正常的異化的愛情,然而,在這種愛情中,他們內心的孤獨和無力被暴露在公眾面前,他們的愛人成為他們感受自己存在的對象。根據弗洛姆的理論,他們失去了以自己為中心的體驗能力。相反,他們傾向于尋找一種外部力量——他們的愛人來幫助他們感受自己的存在,實現自己的身份認同。
(一)自我異化——自我幻覺的產物
自我異化是弗洛姆人的異化理論的核心,它會導致人的身心分離,從而失去了對世界之美的追求和探索。《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中的人們想要逃離現實,所以他們生活在幻想中。
1.喬治的自我異化
喬治對歷史的研究、對兒子的捏造,以及與妻子之間傷人而激烈的文字游戲,都象征著喬治的幻覺。他埋頭研究歷史,厭惡無用的社交活動,討厭一味地追逐物質。他厭惡瑪莎和她父親對金錢和權力的渴望,然而,諷刺的是,他是為了物質才接近瑪莎的,這正是喬治一直無法與自己和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瑪莎和她的父親對喬治事業的遏制,使喬治無法實現他成為作家的理想。可見,他不僅與外界的物質世界有沖突,與內心理想的自我也有明顯的沖突和隔閡。于是他逃離了現實生活,使自己沉浸于幻想中,逐漸異化。
2.瑪莎的自我異化
瑪莎和喬治幻想有一個孩子,但他們彼此深知兒子只是一個幻影,是他們無情婚姻中的慰藉。在戲劇的結尾,喬治為了打破幻境,聲稱他們的兒子“死”了,瑪莎無法面對兒子的死亡,因為在她的內心深處,她深知現實的殘酷,只是不想從美好的幻想轉入實際的牢籠。瑪莎在他們的生活中似乎占據著家庭的主導地位,而事實上,她一直在父親的庇護下生活。她沒有逃離世俗的視野,也不愿意依靠自己來改變命運。她覺得自己的生活毫無意義,感到無比空虛,這使她與自身發生了異化。
(二)自我與他人的疏離——缺乏愛與溝通
在弗洛姆看來,只有和諧共存才能促進共同融合。弗洛姆還認為,人類的互動具有交際性,充滿愛和創造力。然而,異化也來自人際關系的扭曲。這一部分通過分析主人公的婚姻和家庭關系來闡述人與人之間的異化。
1.夫妻關系的異化
劇中的喬治和瑪莎是一對中年教師夫婦。瑪莎想獲得未來校長夫人的頭銜和榮譽,而喬治接近瑪莎,則希望自己能在學校獲得更高的職位。 因此,瑪莎和喬治的婚姻不是建立在愛情上的,而是建立在物質上,他們都帶著各自的目的接近對方。瑪莎討厭喬治缺乏野心,無法給她帶來至高無上的尊嚴,而喬治討厭瑪莎酗酒和輕率的舉止。他們互相仇恨,互相疏遠,甚至想把彼此的虛偽暴露于大庭廣眾之下。毫無疑問,他們的婚姻是失敗的。
另一對夫婦,尼克和哈尼的婚姻也不幸福。尼克把他們的婚姻看作是攫取錢財的手段。他語言粗俗,行為放蕩,尼克一直在努力為自己鋪平道路,甚至用不正當的手段來獲得成功,所以哈尼是他成功的墊腳石。然而哈尼也有她自己的秘密。她懦弱的性格使她對丈夫的背叛無動于衷。她害怕分娩的痛苦,于是選擇放棄肚中的嬰兒。他們的婚姻也充滿了欺騙、懷疑和疏遠,導致彼此陷入婚姻的泥淖之中。在文中,這兩對精英夫妻違背了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倫理,扭曲了他們的婚姻關系,使他們的婚姻形成一種不統一的狀態。婚姻關系的異化不僅使他們喪失了愛人的能力,還使他們失去了人性。
2.父母與孩子關系的異化
在當時,不僅夫妻關系變得疏遠,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也變得異常。孝順和關愛子女的美德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關系的扭曲和異化。劇中也體現出了父母與孩子之間的異化關系,如瑪莎與父親的異化關系、喬治與養父母的異化關系,以及兩對夫婦與未出生的孩子之間的異化關系,都以一種異化狀態表現了出來。
喬治和養父母的關系是極端異化的。喬治是被收養的孩子,他從沒有對養父母敞開過心扉,反而與他們產生了隔閡。此外,喬治對養父母的疏離也影響到了他對瑪莎的行為態度。瑪莎任性自私,經常虐待喬治,當喬治不開心的時候,她會像“媽媽”一樣安慰喬治,像對待“孩子”一樣對待喬治。喬治并不覺得奇怪,反而喜歡這種行為,樂此不疲。由此可見,婚姻悲劇的產生,很大一部分是受非正常家庭關系的影響。
瑪莎和她父親的關系也不尋常。瑪莎從小就非常喜歡她的父親。他們相依為命,所以在瑪莎的心里,她非常崇拜父親。在瑪莎看來,她的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才,盡職盡責,散發著成熟男性的魅力。因此,瑪莎對父親的愛與日俱增。瑪莎選擇了在她父親的大學工作的喬治,她希望這個人將來能繼承他父親的事業,成為校長的繼承人。這樣,她就可以一直待在父親身邊,不時地看到父親。瑪莎像是個逃避長大的孩童,對自己的父親過分依賴,事事都以父親為中心,大事小事全由父親做主。可見,瑪莎的父親是他們婚姻中的破壞者,而他們婚姻中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與瑪莎對父親不正常的感情密切相關。
兩對夫婦和他們不存在的孩子之間的關系也很奇怪。 阿爾比專注于主角無法生育和沒有孩子的事實。作者通過描寫無法生育的殘酷事實來象征生活中的荒謬等。劇中,兩對夫妻被剝奪了生育的權利,他們生活在幻想與現實的鴻溝中,唯有用荒誕的行為來獲得精神上的救贖。最終,這兩對夫妻的謊言被無情戳破,自我的權利訴求形成了與現實的沖突和對抗。他們在荒誕中“殺”了自己的孩子,陷入了無兒無女的實際中。
三、《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中異化的原因
在《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中,不難發現其中的異化現象。因此,本章將討論產生異化的深層次原因。
(一)自我認同的喪失
在這部戲劇中,人物經歷了自我異化。他們都陷入了孤獨、無力和分離之中,無法找到真實的自己,被虛假的自己所折磨,他們失去了自我認同。自我認同是個體自我意識的標志。只有建立了相對充分的自我認同感,才能有效地建立自信和自尊。失去自我認同的個體無法在內心世界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他們必須依靠別人來獲得價值感。瑪莎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相反,她把自己埋在幻想中,幻想她有一個兒子,幻想有一個美好的生活,她整天都很困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喬治為了升職,選擇了瑪莎,違背了自己的理想,成了別人眼中的懦夫和落伍者;尼克看似努力地拼命往上爬,實則野心勃勃,他缺乏靈魂的實質,與真實的自我分離。
仔細觀察劇中這些人物的行為,會發現他們的對話語無倫次、不合時宜、自言自語。對話的不合邏輯,削弱了語言的溝通功能,表達了人們無法溝通的滑稽感。人不再擁有獨立的個性和人格,成了一種無意義的存在。人很難與自己和諧相處,這是異化的表現。所以,失去自我認同的個體,往往會與真實的自我疏離。為了從他人身上尋求價值感,他們會改變對人對事的態度。個人不能保持自己的真實本性,因為他們必須按照別人的方式生活。
(二)愛的缺失
弗洛姆非常強調愛在心理革命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情感異化理論。在弗洛姆看來,愛是一種消除孤獨,把人從孤立和疏離的世界中拯救出來的有效方法。相反,如果人們不關心他們的真愛,繼續生活在物質世界中,對生活沒有任何同情和耐心,那么他就會破壞與他人的關系,甚至與自己的關系。沒有相互的愛、尊重和支持,就沒有人能享受生活。當異化發生時,人對一切事物、所有人都變得冷漠。他們不再愛自己,形成了一種自我憎恨的感覺。更重要的是,他們也停止愛或幫助別人,對世界沒有同情心。他們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不能成功地追求愛情,他們生活在一個所有人都冷漠和不真誠的世界里,這使他們成為世界的局外人。他們內心愛的喪失導致了他們的孤獨和愛與外界的分離。最終,他們的心理和精神都被扭曲了。愛的孤立和扭曲導致了人在環境中的異化和生存困境。在異化的影響下,人群中的所有人都充滿了冷漠和敵意。于是,溫暖的社會被取代。
在戲劇結尾,喬治和瑪莎都驅除了內心的惡魔,在荒誕中找到了一條通往真理的道路。阿爾比在劇終所表現的,不僅是喬治和瑪莎之間的妥協,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接納也充分體現了愛的力量。在這場游戲的過程中,不同的個體之間不斷重復著難以忍受的回憶和諷刺的話語,這給他們造成了創傷,但這種狀態不會持續太久,因為他們最終會在愛中找到生存的意義。身體的“敲打”和靈魂的“折磨”,讓家庭成員開始面對彼此,實現了真正的溝通。喬治親手“殺死”了這個孩子,把瑪莎從脫離現實的異化狀態中解救出來。當他們共同面對現實世界時,也完成了從異化空間到理性空間的過渡,實現了家庭意義上的救贖。同時,也預示著他們最終將實現對真實家庭空間的占有,重新獲得個人身份。可見,人類與社會主要是通過情感聯系在一起的,其中,愛是最重要的元素。換言之,人類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感受著包括異化在內的所有情感的存在。人類有各種各樣的情感,無論是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人類世世代代的活動中,愛都是最永恒、最富有活力的主題。
四、結語
人的異化是西方近代哲學所關注的問題,也是西方現代文學的主題之一。愛德華·阿爾比通過對兩對夫妻言語和行為的描寫,生動地向人們描述了家庭中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關系的復雜而刻板的特征。作者從弗洛姆的異化理論出發,分析了社會家庭倫理問題導致的家庭成員之間的異化,尤其是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異化。他們沒有愛和寬容,只帶來無限的冷漠和敵意,最親近的人變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本文通過分析喬治、瑪莎、尼克和哈尼四個主人公在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下,經歷了起起伏伏,展現了他們的生存境遇,同時,在該劇的結尾,主人公克服了異化,這也為讀者提供了全新的態度去面對生活和認識世界。
參考文獻:
[1][美]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會[M].孫愷祥,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
[2]霍然.《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芙》與荒誕派戲劇[J].時代文學(上),2010(03):138-139.
[3]邵春發.論《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中男主人公的戀母情結[J].名作欣賞,2013(11):139-140.
[4]左進,俞東明.荒誕與解構——《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中的二元對立[J].外語教學,2009,30(05):82-85.
(作者簡介:甄旺,女,碩士研究生在讀,遼寧大學,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