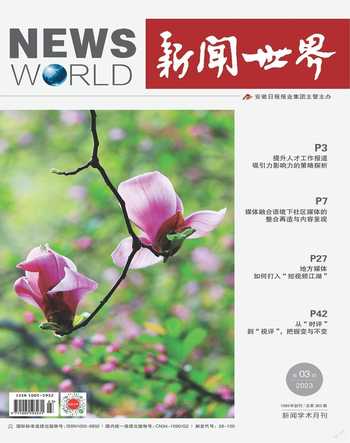新媒體場域下“非虛構”新聞實踐的嬗變
陳海軍 趙穎 鄒君波
【摘? ? 要】“非虛構寫作”一直是受眾關注的重要寫作方式,其起源于西方但在本土化的新聞實踐過程中不斷呈現出新變化。就現階段而言,在新媒體場域中新聞實踐面向的“非虛構寫作”呈現出偽議性、引導性、情感傾向性等特征,其中對于突破行業原則性的問題需要檢視,同時從客觀性原則、憂患意識、建設性方面規避問題并破解其未來發展面向。
【關鍵詞】非虛構;新聞業;建設性新聞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數字時代多元融合傳媒人才跨界培養研究”(項目編號:20YBJ23)、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基于LDA主題建模的‘非虛構寫作新聞文本分類與情感動員傾向性分析”(項目編號:CX2021117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伴隨著互聯網作為第四媒體啟幕了新媒體時代,各類新聞實踐在移動平臺開拓出豐富的內容版塊,“非虛構寫作”因聚焦現實、視角多元、題材邊緣,于新媒體場域獲取了“對現實的公共解釋權”。“非虛構”起源于文學場域,目前已延拓出文學創作、學術寫作和新聞實踐三種基本的面向[1]。進入新聞領域的“非虛構”伴隨實踐應用,其意涵已經逐漸發生了改變,常指一種敘事文體,被稱之為特稿(featurestory),這種參與社會公共事件的“非虛構”新聞實踐必須在“真實性”與“時效性”的基礎上運用文學寫作的技法,實現對事件的深度刻畫。
如今新媒體以迅猛的勢頭發展,媒介的更新催化了媒體的數字化轉型,2012年微信公眾號的誕生掀起了自媒體的發展風暴,“非虛構”實踐也在新媒體平臺遍地開花,其中有轉型融入互聯網的傳統媒體平臺,如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新京報的“剝洋蔥people”、GQ智族的“GQ報道”;有互聯網公司的媒體平臺,如網易的“人間theLivings”、騰訊的“谷雨實驗室”;以及原生于網絡的媒體平臺,如“真實故事計劃”“故事硬核”等等[2],構建了“非虛構”實踐的新媒體矩陣。在此紛繁的背景下,現代“非虛構”新聞實踐在與新媒體場域交織的進程中漸次嬗變,有必要警惕其對新聞實踐原則的異化,思考如何破解“非虛構”新聞實踐未來的發展面向。
一、新媒體場域中“非虛構”新聞實踐的嬗變
(一)向壁虛構的偽議性
1980年9月《華盛頓郵報》刊登了27歲女記者珍妮特·庫科的特稿《吉米的世界》,這篇文章讓她在1981年獲得了普利策的特稿寫作獎,但僅三天后公眾就發現它完全是篇“純虛構”作品。這件在美國新聞界轟動一時的丑聞使普利策獎金委員會遭遇尷尬境地,《華盛頓郵報》也自此結束自水門事件報道獲獎以來的輝煌時期,這也讓人們開始第一次審視“非虛構”的真實性問題。
近些年在媒介泛化的影響下,雜化的寫作圈層使得宏觀新聞場的整體真實愈發難以抵達,涌現出許多“半虛構”甚至是向壁虛構的作品,它們以“非虛構”之名參與或挑起社會公共事件,輿論場中反復出現對“假事實”的高言偽議,使公眾的注意力不斷被消耗。2019年1月29日,一篇杜撰之文《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在微信平臺發布并獲得10萬+的閱讀量,文章多處細節與現實的出入引發網絡爭議,創作團隊卻回應此文“不是新聞報道,這是一篇非虛構寫作”,這樣的推諉之詞讓公眾對“非虛構”的文學界限性再次變得模糊不清。正因為“非虛構”報道具有引發社會事件的能力,使得未遵循客觀報道原則的“非虛構”作品蘊含更大殺傷力,除了“后真相”的扭曲事實可能會對被報道者造成二次傷害,被牽制注意力的受眾也會在反復的輿論中開始麻木,“失真”的報道讓新聞專業主義面臨危機的同時,也降低了媒體公信力。
(二)情感動員的傾向性
在“非虛構”新聞實踐中,通感是常見的寫作技巧,往往也是能夠在情感上“說服”受眾的核心機制,這種由文字符號觸發的心理聯想甚至還會引起生理層面的聯覺,使受眾感官上與作者同頻共振。
在《生死巴丹吉林》《飛躍十三號室》等眾多“非虛構”作品中便可見一斑,它們通過描寫感官對世界本真的體驗,讓讀者由認知域投射到感官域,在閱讀時感到身心俱在而產生同理心,通過移情實現情感水平上的角色轉換[3]。當文字真正能讓受眾感受到作者描繪的故事,并接受了這些信息時,就會擴大化地對作者想要表達的情感或立場產生認同感。不可否認,通過情感動員能夠激發解決社會問題的推動力,但同時或許會以煽情主義模糊了事件的性質,如《盛世中的螻蟻》所激起的“悲憤”情緒會讓受眾在非理性狀態下接受作者在文章最后所傳達的“社會有罪論”,認同作者將底層的悲慘個案片面地歸結于社會體制的極端觀點。非理性的情感傾向性不僅會增加網絡社會風險的交叉感染,還會使受眾產生不安心理或用緊張情緒取代理智分析,極易利用輿論干預事件,成為媒介審判的誘導劑。
(三)“春秋筆法”的引導性
2018年1月30日澎湃新聞發表《尋找湯蘭蘭:少女稱遭親友性侵,11人入獄多年本人“失聯”》一文,以對事實細節描述的不同側重,暗示受眾“人肉”已在公安局保護下改名遷戶的受害人,錯誤的指向與文學性的表達已經影響了受眾解讀的方向與重心,并引起巨大的輿論反彈。該文章的表達誤導大眾對受害人進行尋索與追問,也反映出“非虛構”在嚴肅新聞報道中引用“春秋筆法”可能存在的隱患:創造刺激條件而引發網絡中非理性、非常態的集合行為。
文章學家周振甫在《春秋筆法》一文中提出,“春秋筆法”主要指通過對人物或事實的敘述來表示褒貶[4]。“春秋筆法”并不意味著弄虛作假,而是在行文中通過對事實細節的取舍引導受眾以預謀的方式解讀事實,從新聞實踐的角度出發,這顯然違背帶有一定理想色彩的“新聞專業主義”。伴隨自媒體快速迭代的高度機動性,片面敘事的現象愈演愈烈。2020年4月9日《南風窗》發表“非虛構”報道《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兒三年,揭開這位父親的“畫皮”》,僅三天之隔,《財新》針對同一事件發表了一篇“反轉”特稿《高管性侵養女案疑云》,兩篇文章從對立信源取證呈現了不同的版本,引發公眾對媒體有失規范性的譴責。網絡平臺非專業的門檻激勵了創作主體的下沉,而差異化背景下形形色色個體間的碰撞是迸激創新的溫床,但“非虛構”不是超驗的理想化的作品形式的范式,尤其是在新聞實踐這一面向中,每一篇作品都應在多方取證的前提下盡量避免采用“春秋筆法”,而是要以追求客觀、理性、準確的態度,避免違背新聞實踐原則。
二、“非虛構”新聞實踐的未來面向
(一)敘事理念:以客觀性原則糾偏補弊
由于“去專業化”的“非虛構”作品相較于“程式化”的傳統新聞報道帶來的疲倦感往往更容易收割流量,因此具有較強情節沖突的案件資源或社會事件經常成為“非虛構”報道的對象,也凸顯出“非虛構寫作”對推動社會病灶防治的能力,這種能力正存在于網絡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的新媒體環境中。要實現“非虛構”實踐的新聞價值,首先需要檢視的是其敘事理念的底線原則。赫伯特·甘斯在《什么在決定新聞》一書中將新聞中存在的價值界定為“檢視那些有關國家與社會以及主要的國家與社會有關議題的偏向性陳述”。誠然,新聞從業者的思維與行文方式難以脫離自身的框架,在敘事理念上所追求的是“客觀性報道原則”,即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理想型”:通過結合多樣性的觀察來分析某一社會現象[5]。
在對于多樣性的思考上,媒介的融合發展已經賦予新聞報道更多的可能性,數據技術對新聞業的滲透已催生更多元的報道形態。對于“非虛構”的新聞實踐而言,以文本為核心敘事符號與以數據為細節補充事實并不沖突,新聞從業者可以考慮將“文學性手段”與“以數據為支撐對事實的深度解析”相融合并作為切入點革新新聞生產理念,在價值理性的前提下實現對工具最大化的利用,這不僅能夠彌補數據新聞在微觀層面上質化分析的缺位,把人文關懷融入冰冷的數據分析中,也能夠利用數據的價值矯正過多文本寫作的主觀性,在敘事理念上接近“客觀性原則”,實現對“非虛構”新聞報道的糾偏補弊。
(二)社會功能:以憂患意識關照邊緣角落
由于社會地位、經濟能力、宗教文化等差異,社會邊緣群體的發聲常被埋沒于大眾化的傳播格局中,而他們同樣需要通過媒介去表達自身的價值訴求。《歲月不饒羊》就是反映山西蒲縣因“限羊政策”執行不當造成農民損失的“非虛構”作品,但諸如此類的底層困境能夠被書寫的只是冰山一角,在公共領域之外的角落,往往隱藏著更多影響社會穩定的逆向因素。新媒體場域使得文化資本取代商業或經濟力量進而轉換為權利的可能性大大提升[6],現實社會的公民權利在相對弱勢的局面中仍需要合適的機會來突破,“非虛構”的新聞實踐則是提供這種機會非常允洽的選項。
新媒體時代,信息終端的多樣化讓個體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容易接觸新聞信息,但現代社會仍然存在著由“新聞回避”帶來的社會溝通機制上的阻礙。2020年發布在《公眾意見季刊》的一項研究表明,“軟新聞”偏好與新聞回避呈正相關[7],盡管“新聞回避者”會有意無意地減少對“硬新聞”的接觸,但仍然會通過更加有人情味、趣聞性、知識性的軟新聞關心公共事務或獲得一定的信息量。凸顯人情色彩與社會性的“非虛構”作品顯然是“軟新聞”的典型,是在“彌散式”新聞環境中更能夠規避“新聞回避”現象的文本類型,也更適合發揮新聞實踐的社會功能。當代受眾普遍對高臺教化較為反感,這就需要“軟新聞”來呈現各個利益群體的復雜性,且“非虛構”作為具有強大實證功能的田野調查性文本類型[8],能夠在龐雜事件的縫隙中發現真正的痛點,從而最大限度地囊括多元群體的聲音,以憂患意識關照社會的角落。
(三)價值捍衛:以建設性診愈現實痼疾
盡管“非虛構”作品依托網絡平臺并以此為主要陣地,但在信息市場中始終面臨商業化的壓力,在被“機器生產新聞”“中央廚房”“算法推薦”等科技產物填充的融媒體時代,“非虛構”新聞實踐中文學手段的滲入反而使其成為科技革命難以企及的領域,無法實現流水化作業,也意味著經濟效益的大打折扣。若要使得文本的功能達到最大程度的拓展與實現,捍衛“非虛構”新聞的實踐價值,就要以社會效益作為“非虛構”實踐奔赴的方向,那么將“建設性新聞”理念融入到“非虛構”新聞實踐中則與這種目標不謀而合。
“建設性新聞”倡導新聞報道要保持某種平衡,如將體現社會苦難的死亡和破壞的新聞比重減輕,增加具有建設新要素的相關報道[9]。“非虛構”新聞實踐可以在“建設性新聞”的四個關鍵要素中分別發揮作用,一是方案,“非虛構”新聞的深度與篇幅均有利于記者發揮知識權力分配的能力,將具有實踐性意見的解決方案作為信息資源融入文章;二是讀者,利用“非虛構”的議程設置能力喚起受眾參與事件問題解決或積極建設的能動性;三是積極情緒,通過獨特的文學性寫作手段有意識創造共情基礎,關注公眾的情感需求并提供積極的心理影響;四是全球幸福導向,“非虛構寫作”與“建設性新聞”均起源于西方,最終在世界范圍內對新聞行業產生重要影響,也理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對全球新聞業展開積極的社會建構活動[10]。通過積極姿態融入“非虛構”新聞創作來參與“建設性新聞”的實踐熱潮,并通過議程設置在網絡輿情事件、社會公共事件中發揮作用,進一步借助民眾之力診愈現實社會的沉疴痼疾。
結語
“非虛構”新聞實踐的嬗變顯示出這一文體在自反性的調適發展策略,但在進化的過程中仍需要彈性修正。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要求傳媒展現并促進時代的進步與發展,如何持續性跟隨時代發揮這一文體的價值仍需要更多從業者的思考與論證。毋庸置疑,“非虛構”文學性的寫作手段使其有能力也有義務去傳達社會事實中的人民性、思考性、思辨性。未來,新聞場域仍然需要“非虛構”作品幫助社會糾偏補弊,用擲地有聲的作品重建公共性、重建時代與個體的親密聯系。
注釋:
[1]李文學,曹艷.非虛構寫作新聞實踐的內涵、特點與基本原則[J].新聞論壇,2019(04):42-44.
[2]倪丹燕.非虛構在中國新聞界的興起[D].南京大學,2020.
[3]高志明.通感研究[D].福建師范大學,2010.
[4]振甫.春秋筆法(上) [J].新聞業務,1961(10):41-43.
[5]洪長暉.何以“認”真:自媒體時代的非虛構寫作[J].中國記者,2021(04):81-84.
[6]王冬冬.新媒體時代網絡輿論對社會權利結構的影響研究[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01):116-124.
[7]Benjamin T. & Antonis K.,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Ignor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No.S1, p.S1.
[8]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的反自律性及其局限[J].文藝理論研究,2020(05):112-118.
[9]史安斌,王沛楠.建設性新聞:歷史溯源、理念演進與全球實踐[J].新聞記者,2019(09):32-39.
[10]楊家寧.建設性新聞的知識屬性探究[J].新聞研究導刊,2020(19):79-80.
(作者單位:湖南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