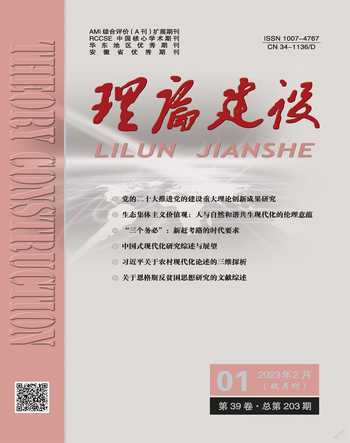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的倫理意蘊
摘 要:隨著人類文明進入工業(yè)文明與生態(tài)文明疊加的嶄新時代,集體主義也需要適應生態(tài)文明發(fā)展的要求而發(fā)展出適應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和人類文明形態(tài)的新集體主義,即生態(tài)集體主義。作為生態(tài)文明時代集體主義價值觀的一種新的歷史形態(tài),生態(tài)集體主義既承續(xù)了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精髓,又適應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新的倫理訴求,不斷增強人民認同和踐行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歷史自覺與歷史主動精神。新時代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培育與踐行,需要從馬克思主義自然觀、馬克思主義人本觀和馬克思主義發(fā)展觀這三個維度進行。
關鍵詞:生態(tài)集體主義;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4767(2023)01-0014-09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diào)新時代必須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教育,“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1]44。這意味著,集體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重要價值理念、道德原則和倫理基石,始終得到堅持和弘揚。被稱為“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集體主義,是人類社會由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文明、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發(fā)展到當代后工業(yè)文明時代(工業(yè)文明與生態(tài)文明疊加的新型文明)的歷史性產(chǎn)物,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致力于中國式現(xiàn)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歷史自覺意識和歷史主動精神在價值觀上的革命與呈現(xiàn),是人類社會進入生態(tài)文明時代一種新的集體主義的發(fā)展形態(tài)[2],能夠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踐行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建設,促進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豐富和發(fā)展。
一、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內(nèi)涵與要求
在“集體主義”價值觀構(gòu)建的問題層面,無論是國內(nèi)還是國外,一直以來人們看到的還只是人與人的關系(包括人與社會、人與國家的關系),沒有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視野。生態(tài)集體主義不僅強調(diào)調(diào)節(jié)和維護人與人的關系,而且調(diào)節(jié)和維護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從“集體主義”價值觀到“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轉(zhuǎn)變,是人類社會對于自身秉承的價值觀的一次非常深刻的自我革命,能夠更好地適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建設。
(一)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概念生成
伴隨著以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為內(nèi)在動力的工業(yè)文明的興起和發(fā)展,西方社會的生態(tài)問題日趨嚴重,并由此催生著西方生態(tài)學的孕育、發(fā)展。美國思想家、文學家亨利·梭羅在《瓦爾登湖》(1854年)中認為,一切動植物都不過是寄住在地球“這個偉大的中心生命”[3]287上的存在,必須認識到人類在這個“中心生命”上對自然的絕對依賴,從而擺脫愛默生狹隘的人類中心論,這為反思人與自然關系和構(gòu)建“生態(tài)集體主義”這一新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概念提供了借鑒。德國哲學家、生物學家海克爾曾在其《生物體普通形態(tài)學》(1886年)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旨在揭示有機體與周圍環(huán)境關系的“生態(tài)”概念,強調(diào)要想正確理解和真正把握人與人的關系就必須認真審視和領會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就為在生態(tài)文明語境下提出“生態(tài)集體主義”概念提供了生態(tài)學依據(jù)。美國環(huán)境保護主義先驅(qū)利奧波德在其《沙鄉(xiāng)年鑒》(1949年)中提出了蘊含從關愛生命個體權(quán)利到關愛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生態(tài)整體主義思想,指出“一個孤立的以經(jīng)濟的個人利益為基礎的資源保護主義體系,是絕對片面的”[4]246,因為它會導致雖缺乏商業(yè)價值但能讓“土地共同體”健康運轉(zhuǎn)的生物的滅絕,從而給人類生存帶來嚴重威脅,這為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語境下構(gòu)建“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提供了環(huán)境倫理學參考。
在我國,最早使用“生態(tài)集體主義”這一詞語的是甘紹平先生。他認為,在以效益至上為原則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統(tǒng)攝下,“單純的生態(tài)集體主義缺乏受到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的現(xiàn)實基礎”[5]175。隨著我們絕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6]532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和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設生態(tài)文明”[7]628戰(zhàn)略的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學者雖然未使用“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語詞,但開始有意識地將生態(tài)倫理、生態(tài)主義與集體主義統(tǒng)一起來,進行人與社會、自然間價值關系的整體構(gòu)筑[8],從而為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概念生成奠定了學理基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之后,生態(tài)文明建設成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總布局“四梁八柱”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僅注重社會關系和諧,而且注重自然內(nèi)部和諧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不僅注重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gòu)建,而且注重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構(gòu)建,至此,“生態(tài)集體主義”有了研究和踐行的現(xiàn)實條件和客觀基礎。
從生態(tài)集體主義概念的邏輯生成來說,早在黨的十八大之前,筆者就意識到,在生態(tài)文明視野下應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調(diào)整范圍,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內(nèi)涵[9]。繼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diào)“把生態(tài)文明建設融入經(jīng)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10]11之后,經(jīng)過多年思考,筆者正式提出“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概念:生態(tài)集體主義是指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tài)文明觀為指導,視人、自然、社會于一體,著力處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矛盾與沖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保證社會的全面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和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原則[11]。
(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基本內(nèi)涵
生態(tài)集體主義本質(zhì)上仍是集體主義,是與超越“黑色”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的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相適應的集體主義新形態(tài),既承續(xù)了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精髓,又適應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新的倫理訴求,能夠更好地促進美麗中國和人類地球美好家園的建設。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基本內(nèi)涵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堅持屬于生命共同體的集體利益(或稱整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特別是相對于由個人組成的社會有機體來說,要想實現(xiàn)社會有機體的穩(wěn)定健康有序、和諧共生發(fā)展,就必須要求個人讓渡部分權(quán)益,并與自然公共利益一起,組成事關每個人利益的公共集體利益。在此前提下,我們講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分以下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正常狀態(tài)(即非緊急狀態(tài))下,要求作為個體的人不得損害生命共同體的公共集體利益,既包括不損害他人和社會有機體利益,也包括事關人類生存發(fā)展的自然生態(tài)整體利益;第二種情況是非正常狀態(tài)(即緊急狀態(tài),如自然災害、國家受到外來侵略等)下,要求作為個體的人必須自覺服從并服務于生命共同體的公共集體利益,甚至不向公共集體計較因維護公共集體利益而做出的個人利益犧牲或遭受的個人利益損失。第二,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保護屬于同一生命共同體這一集體內(nèi)的所有有利于人的現(xiàn)時、長遠生存和發(fā)展權(quán)益的個體合法利益。作為維護生命共同體這一生態(tài)集體利益的公權(quán)力者,在要求作為社會有機體個體的人必須維護社會有機體利益和自然生態(tài)整體利益的同時,按照權(quán)利義務雙向?qū)ΨQ原則,要求作為社會有機體的集體同樣不損害社會有機體個人的合法權(quán)益,當生命共同體的公共集體利益與作為社會有機體的個人的合法權(quán)益出現(xiàn)矛盾與沖突而需要個人做出某種權(quán)益上的讓步或犧牲時,作為社會有機體的集體必須對做出某種合法權(quán)益讓步或犧牲的個人進行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合理補償。第三,以追求生命共同體中的“人與社會”(包括人與人)和“人與自然”兩大權(quán)益關系的最大和諧發(fā)展為終極目標,以更好地旨在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的實現(xiàn)。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既強調(diào)社會有機體這一集體與組成社會有機體的個人的雙向?qū)ΨQ義務,也重視和秉承人對屬于同一生命共同體的自然的單向道德責任。這就是說,生態(tài)集體主義作為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新的歷史形態(tài),要求生命共同體這一生態(tài)集體中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正視自然規(guī)律、尊重自然價值,辯證揚棄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各自不合理的內(nèi)容,合理開發(fā)利用好自然資源和像對待自己生命一樣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促進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解與和諧。
(三)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基本要求
按照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我們每個人都不應該自私自利,而應該通過對生命共同體中社會生產(chǎn)資料共同占有實現(xiàn)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合,并通過這種聯(lián)合達到人類對自然關系的集體控制,最終克服人和自然環(huán)境之間關系的異化。這正如美國學者戴維·佩珀所指出的,人類絕不應該以超出自然維護自身生態(tài)平衡所能承受的極限的方式肆意掠奪和揮霍自然,“為了集體的利益,我們應該集體地支配(即計劃和控制)我們與自然的關系”[12]282。這里他所表達的意思與馬克思提出的聯(lián)合起來的人類“將合理地調(diào)節(jié)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13]928是基本一致的。據(jù)此,應該從更高的角度來審視處于生命共同體中的人類對自然的態(tài)度,作為自然界唯一擁有主體覺醒意識并富有創(chuàng)造能力的人類,可以根據(jù)人類自身的合理需要去改造自然,但這種改造不能對自然形成破壞從而使環(huán)境變得越來越糟糕,必須通過建設性改造,在保證大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平衡穩(wěn)定、健康運轉(zhuǎn)的前提下,使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越來越美好,從而使人類更有安全感、滿足感和幸福感。作為維護全人類公共利益的政府和社會組織,應努力用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來規(guī)范、引領、指導人們的生態(tài)行為,在改造惡劣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以及創(chuàng)造美好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下功夫,既要努力引導全社會重視對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有效利用和保護,防止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受污染和惡化,也要努力實現(xiàn)人人都能享有綠水青山的自然生態(tài)治理現(xiàn)代化目標。
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時代價值
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與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建設相適應,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其調(diào)整范圍,克服傳統(tǒng)集體主義只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弊端,從而為認同踐行生命共同體理念、建設美麗中國和清潔美麗世界、彰顯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并最終實現(xiàn)“兩大和解”的理想社會奠定重要的價值觀基礎。
(一)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為踐行生命共同體理念、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奠定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生命共同體理念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特別是綠色“一帶一路”倡議、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和綠色金融等,為全世界描繪了共同構(gòu)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共同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共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的規(guī)劃藍圖。但如何才能使生命共同體理念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理念得到全世界最廣大人民的認同和踐行呢?筆者認為需要將生態(tài)集體主義作為生命共同體理念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理念的價值基礎。到目前為止,圍繞“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主要提出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一定意義上說也屬于生命共同體。因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本身就包含著三類關系,即自然內(nèi)部關系、人與人之間關系、人與自然之間關系,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要構(gòu)建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就蘊含了生命共同體所包含的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中所說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本質(zhì)是人與人的和諧共生。這就是說,無論是生命共同體理念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都需要在新時代繼續(xù)致力于促進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兩大和解”或“兩大矛盾的真正解決”。生態(tài)集體主義無疑為其提供了重要的價值觀基礎。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從哲學層面來說,“生態(tài)集體主義”所主張的價值主體依然是人類,但這里的人類絕對不是指稱某個具體的人,而是指稱全人類,它以追求事關長遠并以“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雙重和諧的共同利益為價值目標,而生命共同體理念所要追求的也正是這樣的價值目標。因此,要想使世界人民認同和踐行生命共同體理念,更好地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建設,就需要以生態(tài)集體主義為價值基礎。
(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能夠彰顯生命共同體理念自信
生態(tài)集體主義最大的價值優(yōu)勢就是將“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這兩類關系同時納入其價值觀視野,有效克服了以往價值觀因建立在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哲學方法論基礎上而存在的無法改變的缺陷。在以往的東方社會的集體主義和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那里,“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這兩類關系是分離的,而且主要局限于人與人的關系這一價值層面,人與自然的關系如同自然外在于人一樣被人所忽視了。“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這兩類關系的分離,也體現(xiàn)在:以往基于人類中心論的社會共同體只關注人與人的關系,而以往基于非人類中心論的自然共同體又只關注人(被降格為一般動物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換言之,以往的社會共同體只關注“人”而不關注“自然”,自然共同體又只關注“自然”而不關注“人”。這使得兩者都不夠全面,在社會共同體那里“自然”不見了,而在自然共同體那里“人”不見了,直接導致了兩者在價值觀層面的殘缺,因而也就都不夠自信。
生命共同體理念將“人與人”“人與自然”這兩類關系有機統(tǒng)一起來,并通過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形塑和整合,從而獲得了廣泛的價值認同和實踐遵循。生態(tài)集體主義也因高度契合生命共同體理念而獲得更為廣泛的社會認同,從而展現(xiàn)出生態(tài)集體主義這一集體主義新的歷史形態(tài)的價值觀自信。第一,生態(tài)集體主義既承繼了我國現(xiàn)代社會的“集體主義”思想(主要規(guī)范調(diào)整各種人倫關系),也承繼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規(guī)范調(diào)整人與自然關系),使生命共同體理念獲得了價值觀的文化基礎。第二,生態(tài)集體主義更能實現(xiàn)外來的生態(tài)哲學、生態(tài)倫理主義、生態(tài)社會主義等生態(tài)文化價值觀念本土化,使得這些生態(tài)文化價值觀一傳入我國,便融合在我國優(yōu)秀且堅韌的傳統(tǒng)文化語境和現(xiàn)當代文化語境中,使生命共同體理念獲得了價值觀的獨特民族魅力。第三,“生態(tài)集體主義”是對西方把人淹沒在自然之中、把人降格為一般動物的“生態(tài)共同體主義”的辯證否定,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及其所蘊含的共同體思想的中國化話語表達,能夠更好地使以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為內(nèi)核的生命共同體理念得到世界人民的廣泛接受和普遍認同,從而更好地提升我國在生態(tài)文明建設方面的世界話語權(quán)。
(三)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建設中的獨到價值魅力
生態(tài)文明建設最主要的就是協(xié)調(diào)處理好“人與自然”看似不可調(diào)和的關系,使“人”與“外在于人”的“自然”在生命共同體的這一有機體內(nèi)獲得最大限度的和諧共生發(fā)展,而在以往的集體主義的視野中只有“人”沒有“自然”,因而不能勝任生態(tài)文明建設場域內(nèi)的價值觀需要,造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建設在價值觀上的空場。當然,盡管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對象目標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和諧,但價值主體仍然是人,沒有了“人”,自然再美也沒有任何意義。誠如馬克思所說的,自然界一旦被高度抽象為“自為的”與人相分離的存在,“對人來說也是無”[14]220,而人又是絕不可能離開自然界而獨立存在。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重要基石的生命共同體理念,盡管關注人,但并沒有把人當作自然的主宰;反對人對自然的為所欲為,但沒有把人降格為一般的動物;反對人在自然面前的消極無為,強調(diào)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從而引領我們擁抱美好生態(tài)環(huán)境、創(chuàng)造人民幸福生活、一起走向生態(tài)文明建設新時代[15]。從這個意義上說,以生命共同體理念為基石的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其重要價值觀基礎是旨在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xiàn)代化倫理追求的生態(tài)集體主義。由于生態(tài)集體主義統(tǒng)合兼蓄了以傳統(tǒng)人類中心論為理論根基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和以非人類中心論為理論根基的生態(tài)整體主義價值觀,因而更符合以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為特點的自由人聯(lián)合體思想,并由此彰顯生態(tài)集體主義在生態(tài)文明建設和促進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中的獨到價值魅力。
這種獨到的價值魅力體現(xiàn)在:第一,能有效克服傳統(tǒng)集體主義價值觀不關注“自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特別是,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因沒有意識到個人也是自然的存在,而生態(tài)集體主義既關注每個人命運相連的自然環(huán)境利益,也關注每個人的自然物質(zhì)需要和個性自由需要,因而更容易被人們認同和踐行。第二,能夠促使人們廣泛接受和認同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理念、推進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建設、“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新時代”[16]393、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生態(tài)集體主義將現(xiàn)有的生態(tài)倫理學(或稱環(huán)境倫理學)與社會倫理學有機結(jié)合,克服了生態(tài)倫理學與社會倫理學在調(diào)整“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兩類關系上的片面性、狹隘性,從而使人真正地通過社會將“人”“自然”有機統(tǒng)一起來,既顧及自然系統(tǒng)內(nèi)部的關系和人類內(nèi)部的關系,也顧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使倫理學真正獲得了自身完美的統(tǒng)一,從而促使每個人都能參與生態(tài)文明理念的實踐,把建設富裕中國、美麗中國、幸福中國的實踐“轉(zhuǎn)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17]366。第三,能夠進一步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發(fā)展。我國創(chuàng)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匯集人類文明一切優(yōu)秀成果于一體,符合馬克思主義所向往的、實現(xiàn)了“兩大和解”“社會全面進步”“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理想境界的文明形態(tài)。其中,生態(tài)文明對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形成與發(fā)展起著關鍵性作用,因為雖然生態(tài)文明并不完全等同于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但是少了生態(tài)文明或者沒有生態(tài)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相互協(xié)調(diào)、健康有序的發(fā)展,就不可能有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形成發(fā)展。這也說明,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蘊含著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基因,是建立在生態(tài)價值主義價值觀基礎上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而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重要價值觀基礎的生態(tài)集體主義必將能夠更好地推進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從而為實現(xiàn)“自由人聯(lián)合體”奠定良好的社會條件。
三、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路徑
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有利于全社會更好地認同和踐行生命共同體理念、更好地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但如何培育和踐行,同樣需要人們進行認真探討和研究。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可以從馬克思主義自然觀、馬克思主義人本觀、馬克思主義發(fā)展觀三個維度進行。
(一)從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高度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
馬克思主義自然觀蘊含了“人”“自然”兩大范疇,科學闡述了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指出全部的人類歷史其實也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14]196,抑或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的過程”[18]208,從而彰顯由“人”與“自然”所組成的“有機體”的兩個方面,即“自然生態(tài)”和“社會生態(tài)”。從這個意義上說,人不僅僅是社會生態(tài)中的人,同時也是自然生態(tài)中的人,構(gòu)建內(nèi)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命共同體、實現(xiàn)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必須從自然生態(tài)、社會生態(tài)兩個維度,進行人與社會、自然間價值關系的整體構(gòu)筑[8]。這就是說,原先我國傳統(tǒng)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西方生態(tài)整體主義都不能科學勝任同時蘊含人、自然、社會在內(nèi)的整體價值觀構(gòu)筑需要,而生態(tài)集體主義無論從哪一個方面進行分析都非常好地適應了這樣的需要,能夠成為生命共同體理念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的重要價值基礎。事實上,從黨的十五大提出在現(xiàn)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并強調(diào)要正確處理好經(jīng)濟發(fā)展同人口、資源、環(huán)境的關系起,就開始有學者將生態(tài)倫理與集體主義價值觀結(jié)合進行研究。黨的十七大召開前后,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將研究視角延伸至以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對集體主義與生態(tài)主義進行價值觀整體構(gòu)筑啟示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gòu)建生命共同體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的理念,以及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指出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1]23,在進一步豐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同時,也為從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高度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提供了學理支撐和實踐依據(jù)。
(二)從馬克思主義人本觀的高度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
馬克思主義自然觀本質(zhì)上也是馬克思主義人本自然觀,“人本觀”構(gòu)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質(zhì)。馬克思、恩格斯盡管反對“把人對自然界的關系從歷史中排除出去”[14]545,但也強調(diào)“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19]9“歷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4]211,甚至基于離開人談自然毫無意義這一點,批判“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14]499都不是從人這一主體方面去理解。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彰顯人的價值主體,但也非常重視人對自然的道德責任和善良行為,提出要重建人與社會、自然的精神關系和精神秩序[20],這與馬克思主義人本觀或馬克思主義人本自然觀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能夠為從馬克思主義人本觀的高度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提供學理依據(jù)和實踐引領。當然,從馬克思主義人本觀的高度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需要重建人與社會、自然的精神關系和精神秩序,只是采取什么樣的方法論和本著什么樣的價值目標追求來構(gòu)建人、自然和社會的合理價值關系顯得特別重要。值得欣慰的是,隨著習近平總書記“5·17”講話精神的落地和以往僵化保守的學術觀念被打破,越來越多的學者基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觀認識到能夠在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意義上再建人、社會和自然的合理關系[21],從而為認同和踐行生命共同體理念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奠定重要的價值觀基礎。在新時代,必須深入挖掘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反生態(tài)性和反人性的資本邏輯的哲學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從唯物史觀立場準確理解人的價值主體性與自然價值優(yōu)先性的辯證關系,將人與人的經(jīng)濟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關系統(tǒng)一起來[22],構(gòu)建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物質(zhì)變換理論和可循環(huán)可持續(xù)的生態(tài)經(jīng)濟理論,從而促進經(jīng)濟社會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生態(tài)集體主義。總之,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必須堅持和理解馬克思主義人本觀,并從馬克思主義人本觀的高度進一步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
(三)從馬克思主義發(fā)展觀的高度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
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還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發(fā)展觀的高度來進行。從馬克思主義發(fā)展觀的高度培育和踐行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能夠更好地推動新發(fā)展理念在踐行生命共同體理念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的偉大實踐中落細落小落實,從而使新發(fā)展理念在彰顯生態(tài)集體主義思想光芒的同時更好地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建設。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fā)展觀的重大創(chuàng)新主要體現(xiàn)為以創(chuàng)新、協(xié)調(diào)、綠色、開放、共享為內(nèi)容的新發(fā)展理念。新發(fā)展理念與生態(tài)集體主義具有內(nèi)在關聯(lián)性:①創(chuàng)新是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價值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不斷闡述和強調(diào)的生命共同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生態(tài)集體主義中的“生態(tài)集體”,在“生命共同體”這一“生態(tài)集體”中,必然存在諸多阻礙生命共同體發(fā)展甚至破壞生命共同體發(fā)展的消極因素,有些消極因素來自于技術層面的不完善,也有些消極因素屬于體制機制層面的僵化保守與落后,當然說到底還是思想文化觀點層面存在問題導致的理論上的不完善。消除這些消極因素并努力使之轉(zhuǎn)化為積極的因素,要靠持續(xù)不斷的觀念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②協(xié)調(diào)、開放是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價值手段。地球本身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在這樣的生命共同體中,“生態(tài)集體”既要努力協(xié)調(diào)處理好不同國家內(nèi)部這一生態(tài)集體子系統(tǒng)的若干關系,也要處理好不同國家外部生態(tài)集體子系統(tǒng)之間的若干關系,這就需要堅持運用協(xié)調(diào)、開放的發(fā)展理念化解“生態(tài)集體”各子系統(tǒng)內(nèi)部或之間出現(xiàn)的諸多不穩(wěn)定因素、潛在的矛盾和風險。一方面堅持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理念,在打破既得利益固化藩籬的基礎上不斷追求社會公平正義,與此同時破解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性矛盾和不平衡發(fā)展難題,在補齊“內(nèi)輪差”基礎上促進全社會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堅持開放理念,不斷學習和借鑒一切先進技術、發(fā)展理念與管理經(jīng)驗,在擴大視野的同時謀勢借力,最終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大做強自身。③綠色、共享是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價值目標。一方面,“綠色”是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底色,其目的就是要有效平衡人類發(fā)展無限需求和資源環(huán)境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有效化解自然資源短缺和自然生態(tài)惡化所造成的阻礙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卡脖子病”;另一方面,“共享”生態(tài)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本質(zhì),其目的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1]46,扎實推進全社會共同富裕,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完善符合公平和促進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覆蓋全民、統(tǒng)籌城鄉(xiāng)、公平統(tǒng)一、安全規(guī)范、可持續(xù)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1]48。
總之,生態(tài)集體主義價值觀絕不是為了所謂的學術創(chuàng)新而創(chuàng)設的一種抽象和脫離實際的價值觀,它契合了生命共同體理念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理念,并能夠成為認同和踐行生命共同體理念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理念的重要價值觀基礎,能夠引領人們在不斷實現(xiàn)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兩大和解”的過程中,推進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生成、豐富和發(fā)展。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團結(jié)奮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耿步健,段然.生態(tài)集體主義:《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原典釋義及其現(xiàn)實意義[J].寧夏社會科學,2020(2):27-33.
[3] 亨利·梭羅.瓦爾登湖[M].徐遲,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 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xiāng)年鑒[M].侯文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5] 甘紹平.應用倫理學前沿問題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6]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胡錦濤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 周峰.人與社會和自然間價值關系的整體構(gòu)筑——唯物史觀對人道主義歷史觀的超越[J].學術研究,2005(7):50-55.
[9] 耿步健.生態(tài)文明視野下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完善[J].求索,2010(12):106-108.
[10]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1] 耿步健.正確認識生態(tài)環(huán)境也是生產(chǎn)力[N].新華日報,2015-05-26(16).
[12] 戴維·佩珀.生態(tài)社會主義:從深生態(tài)學到社會正義[M].劉穎,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2.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耿步健,高雨童.論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的原創(chuàng)性貢獻——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學習綱要》[J].理論建設,2022,38(5):43-52.
[16]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7]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胡惠林.文化產(chǎn)業(yè)規(guī)劃:重建人與社會和自然精神關系和精神秩序[J].東岳論叢,2015,36(2):49-54.
[21] 耿步健,沈丹丹.論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及其價值基礎[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1):13-18,27.
[22] 耿步健,許陽.《資本論》中的綠色發(fā)展思想及其當代價值[J].財經(jīng)問題研究,2017(9):11-16.
Abstract: As human civilization enters a new era of superposition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llectivism also needs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develop a new collectivism that adapt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namely ecological collectivism. As a new historical form of collectivism values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ollectivism not only inherit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ollectivism values, but also adapts to the new ethical demands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an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people to identify and practice Xi Jinping's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life. The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ollectivism in the new era need to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rxist view of nature, Marxist view of humanism, and Marxist view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collectivism;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責任編輯:倪大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