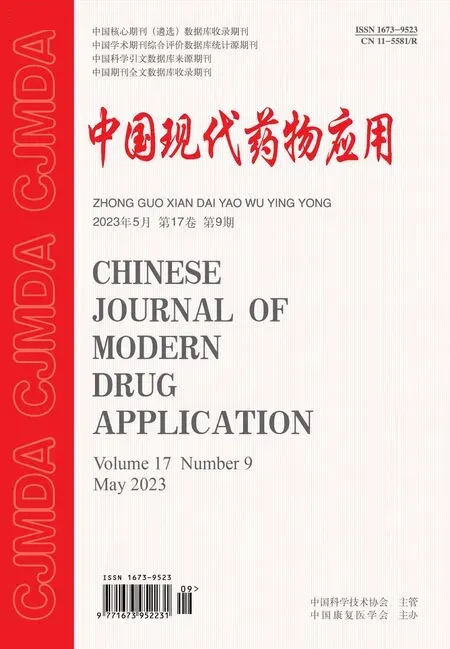腔內激光消融術治療原發性大隱靜脈曲張的手術效果、安全性及術后康復質量分析
王為華
大隱靜脈曲張是臨床常見下肢靜脈曲張類型,以長期站立、重體力勞動所致大隱靜脈瓣膜功能障礙后血液倒流至遠端靜脈瘀滯為主要病因[1],可見患肢淺表靜脈擴張、疼痛、水腫等癥狀表現,生活質量、下肢功能負面影響顯著[2],臨床建議如出現踝周水腫或(和)下肢皮膚改變等癥狀需行外科治療[3]。血管外科治療技術的應用,以高位結扎術為主要術式類型,通過對曲張大隱靜脈的結扎及局部剝脫治療實現對病癥的治療緩解[4],但此類手術全身麻醉要求及術后疼痛明顯對患者治療耐受要求較高,且存在一定的并發癥風險,臨床應用局限較多,故靜脈腔內閉合治療技術的應用或可成為疾病患者未來治療新選擇[5]。因此,為分析原發性大隱靜脈曲張行腔內激光消融術治療的手術效果、手術安全性及術后康復質量,特行臨床研究,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20 年9 月~2021 年8 月血管外科接診行手術治療的73 例原發性大隱靜脈曲張患者作為研究對象,術前采用中心隨機系統分組法分為對照組(37 例)和研究組(36 例)。對照組中男18 例(48.65%),女19 例(51.35%);平均年齡(55.68±5.37)歲;CEAP分級中C3 級 12 例、C4 級 16 例、C5 級 9 例;單左下肢發病20 例、單右下肢發病17 例;大隱靜脈內徑:隱股靜脈交接(SFJ)處(7.38±1.72)mm、膝關節處(5.81±0.65)mm。研究組中男17 例(47.22%),女19 例(52.78%);平均年齡(55.74±5.45)歲;CEAP 分級中C3 級11 例、C4 級15 例、C5 級10 例;單左下肢發病21 例、單右下肢發病15 例;大隱靜脈內徑:SFJ 處(7.35±1.78)mm、膝關節處(5.84±0.62)mm。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n,±s)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n,±s)
注:兩組比較,P>0.05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單側下肢原發性大隱靜脈曲張確診患者[6],年齡≥18 歲;②臨床慢性靜脈疾病CEAP 分級均為C3~C5 級;③思維健全,治療配合度良好,確認手術。排除標準:①年齡>80 歲;②CEAP分級<C3級或>C5級;③合并患肢深靜脈血栓;④確診繼發性大隱靜脈曲張;⑤血壓、血糖控制效果不佳。
1.3 方法 兩組患者術前均行下肢大隱靜脈超聲檢查或CT 造影,確認靜脈曲張范圍涉及靜脈主干類型,于站立位下標記大隱靜脈曲張范圍。
1.3.1 對照組 患者行大隱靜脈高位結扎術治療。全身麻醉后,選擇患側腹股溝沿皮紋走行做橫切口,經切口分離皮下組織至暴露大隱靜脈及分支,選擇大隱靜脈主干近心端、分支結扎處理,將遠心端送入剝脫器內至膝下,做切口引出,完成大隱靜脈剝離處理后,對小腿靜脈曲張血管行點狀剝脫治療,血管治療后注射泡沫硬化劑,閉合靜脈,對手術切口行加壓包扎處理,術后住院治療至康復后出院。
1.3.2 研究組 患者行腔內激光消融術治療。行超聲檢查于膝關節大隱靜脈處選擇穿刺點,經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后,行超聲引導賽丁格爾技術穿刺,穿刺后置入5F 血管鞘,送入安全導絲后,沿導絲將激光光纖置入隱股連接處遠心端2 cm 位置,其后取腫脹液(2%利多卡因25 ml+腎上腺素0.5 ml+碳酸氫鈉475 ml+氯化鈉注射液500 ml)自大隱靜脈遠端至近端足量注射后,行局部腫脹麻醉。麻醉后抬高患側下肢與床面呈30°夾角,開啟激光光纖連續模式后(10 W),以1 cm/s 速度勻速退出光纖,同期配合沿大隱靜脈走行壓迫患肢。激光光纖完全退出后,行超聲引導下膝關節大隱靜脈、交通靜脈穿刺后,于靜脈內注射泡沫硬化劑0.5~3.0 ml,充分閉塞殘余靜脈曲張血管;如治療中發現團狀靜脈曲張組織,需行點狀剝脫治療。治療完畢后復查超聲檢查,確認曲張靜脈閉塞效果,行穿刺點偏心性加壓包扎處理,留觀2 h,無異常后于手術當日指導出院。
兩組患者術后均接受抗凝、促微循環藥物治療,配合彈力襪穿戴及術后康復訓練。
1.4 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 比較兩組患者治療有效率、大隱靜脈閉合率、靜脈曲張復發率,靜脈曲張殘留指標,術后疼痛評分、疼痛持續時間、恢復時間,手術并發癥發生率,手術前后患肢血流速度、VCSS 評分。
1.4.1 治療有效率、大隱靜脈閉合率、靜脈曲張復發率 術后12 個月時超聲檢查患者無靜脈曲張,下肢疼痛癥狀改善明顯或消失,閉合大隱靜脈內無血流,為有效[7]。靜脈曲張復發率統計患者術后6 個月內疾病復發情況。
1.4.2 靜脈曲張殘留指標 于術后6 個月,超聲檢查患肢有無殘留靜脈曲張,統計殘留靜脈曲張血管數量、殘留靜脈曲張血管長度及直徑[8]。
1.4.3 疼痛評分 于術后次日采用VAS 評估患肢的疼痛程度,評分越高則疼痛越嚴重。
1.4.4 手術并發癥發生率 統計患者術后6 個月內皮下血腫、感染、神經損傷、深靜脈血栓形成(DVT)、局部硬結等發生情況。
1.4.5 血流速度 于患者術前1 d 及術后第7 天行超聲檢查,確認患肢髂外靜脈、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
1.4.6 VCSS 評分 采用VCSS 評分評估靜脈臨床嚴重程度,對患者術前1 d 及術后1 個月時患肢疼痛、靜脈曲張、水腫等癥狀評分,各項評分為0~3 分,評分越高則癥狀越嚴重[9]。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4.0 統計學軟件對研究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N<40,行Fisher 精確檢驗。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治療有效率、大隱靜脈閉合率、靜脈曲張復發率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有效率、大隱靜脈閉合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患者術后6 個月內靜脈曲張復發率為2.78%,低于對照組的21.62%,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治療有效率、大隱靜脈閉合率、靜脈曲張復發率比較[n(%)]
2.2 兩組患者靜脈曲張殘留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術后殘留靜脈曲張血管數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術后殘留靜脈曲張血管共106 條,對照組共115 條。研究組患者殘留靜脈曲張血管直徑(1.55±0.21)mm、殘留靜脈曲張血管長度(3.64±1.24)cm均短于對照組的(2.34±0.32)mm、(4.75±2.45)cm,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靜脈曲張殘留指標比較(±s)

表3 兩組患者靜脈曲張殘留指標比較(±s)
注:與對照組比較,aP<0.05
2.3 兩組患者術后疼痛評分、疼痛持續時間、恢復時間比較 研究組患者術后VAS 評分(2.16±0.94)分低于對照組的(3.65±1.34)分,術后疼痛持續時間(1.05±0.34)d、術后恢復時間(3.02±1.41)d 短于對照組的(3.75±1.48)、(7.21±2.37)d,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術后疼痛評分、疼痛持續時間、恢復時間比較(±s)

表4 兩組患者術后疼痛評分、疼痛持續時間、恢復時間比較(±s)
注:與對照組比較,aP<0.05
2.4 兩組患者手術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兩組患者手術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患者手術并發癥發生率比較[n(%),%]
2.5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患肢血流速度、VCSS 評分比較 術前1 d,兩組患者患肢髂外靜脈、股靜脈、腘靜脈血流速度及VSCC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第7 d,研究組患者患肢髂外靜脈血流速度(25.14±1.86)cm/s、股靜脈血流速度(26.87±1.57)cm/s、腘靜脈血流速度(18.25±1.22)cm/s 高于對照組的(24.25±1.73)、(25.11±1.08)、(15.92±0.93)cm/s,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1 個月,研究組患者VSCC 評分(3.17±0.87)分低于對照組的(4.45±1.56)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6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患肢血流速度、VCSS 評分比較(±s)

表6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患肢血流速度、VCSS 評分比較(±s)
注:與對照組比較,aP<0.05
3 討論
大隱靜脈瓣膜功能的病理性變化為大隱靜脈曲張的主要誘因,可由靜脈內血管反流至下端靜脈后血管瘀滯,誘發淺表靜脈團狀曲張、色素沉積、水腫及疼痛癥狀,影響患者生活質量[10],部分患者可由靜脈內栓塞進入循環系統后誘發肺栓塞,威脅生命安全,故及時對有癥狀大隱靜脈曲張患者開展治療對癥狀緩解、預后改善具有積極意義[11]。
大隱靜脈曲張傳統治療中高位結扎術的實施,可經手術剝離大隱靜脈及分支后,有效切除曲張部分靜脈阻斷血液回流路徑,減少下肢靜脈內淤血,改善水腫、疼痛癥狀[12]。但受手術方式、治療路徑等因素影響,對患肢腓腸神經、隱神經存在損傷風險[13],且術后疼痛感明顯,或可由疼痛生理應激增加皮下血腫、DVT 風險,手術效果有限,而全身麻醉治療對高齡患者手術耐受要求較高[14]。腔內激光消融術是近年來利用激光光纖所形成的微創治療技術,經患肢大隱靜脈穿刺后置入激光光纖,在激光熱能作用下引發靜脈內壁膠原蛋白變性,刺激靜脈壁收縮、纖維化,實現對靜脈腔的永久關閉,以達到治療效果,靜脈腔關閉及血液倒流阻塞效果顯著,術后復發率低[15],且無明顯周邊組織熱損傷風險,無需血管剝離,可合理規避靜脈周邊神經組織損傷,術后不適感較輕,可快速緩解,而局部麻醉即可滿足手術麻醉需求,可用于多數全身麻醉不耐受患者的臨床治療中,臨床優勢顯著[16-20]。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患者治療有效率、大隱靜脈閉合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患者術后6 個月內靜脈曲張復發率為2.78%,低于對照組的21.62%,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術后殘留靜脈曲張血管數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患者殘留靜脈曲張血管直徑(1.55±0.21)mm、殘留靜脈曲張血管長度(3.64±1.24)cm 均短于對照組的(2.34±0.32)mm、(4.75±2.45)cm,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患者術后VAS 評分(2.16±0.94)分低于對照組的(3.65±1.34)分,術后疼痛持續時間(1.05±0.34)d、術后恢復時間(3.02±1.41)d 短于對照組的(3.75±1.48)、(7.21±2.37)d,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手術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第7 天,研究組患者患肢髂外靜脈血流速度(25.14±1.86)cm/s、股靜脈血流速度(26.87±1.57)cm/s、腘靜脈血流速度(18.25±1.22)cm/s高于對照組的(24.25±1.73)、(25.11±1.08)、(15.92±0.93)cm/s,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1 個月,研究組患者VSCC 評分(3.17±0.87)分低于對照組的(4.45±1.56)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在該項臨床研究中,僅對患者術后短期內并發癥風險予以評估,未涉及遠期并發癥風險評估,故需在后續研究中完善數據收集,明確兩類術式的遠期安全性。
綜上所述,腔內激光消融術對原發性大隱靜脈曲張治療效果與傳統高位結扎術相當,但腔內激光消融術治療中局部麻醉、泡沫硬化劑填充技術的配合均可有效提升病變靜脈血管閉塞效果,改善患者術后疼痛程度,在提升臨床康復速度的同時,降低復發風險,使患者病癥得到有效改善,且可減少手術并發癥,臨床效果確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