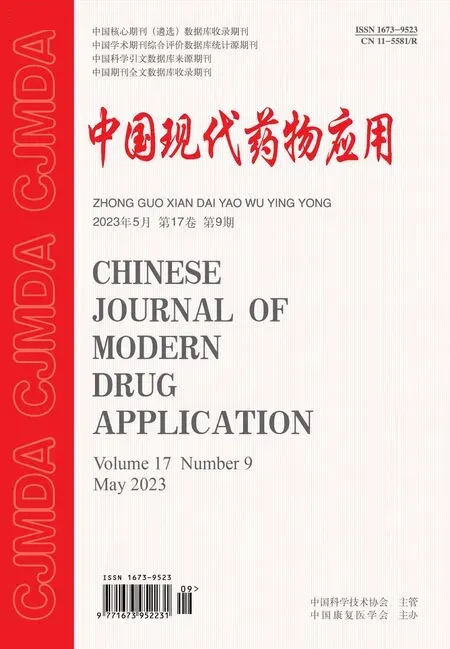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的特征及關系研究
劉浩 黃雪萍 周小艷 楊輝
抑郁癥也稱為抑郁障礙,是臨床較為常見的慢性精神疾病[1]。據統計[2,3],截至2017 年,全球抑郁癥患者數量約為3.4 億人次,病發率為2%~8%,我國抑郁癥患病率約為4.2%。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及教育模式的不斷改變,在家庭、學習、心理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抑郁癥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已逐漸成為青少年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4]。抑郁癥發病后多表現為長久性的抑郁心理、情緒異常等,部分患者亦可出現非自殺性自傷(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等不理智行為,即直接傷害自身或重復性傷害自身,但沒有自殺意圖,包括筆尖/針扎/刺傷、抓傷、掐傷等多種類型[5,6]。與正常冒險行為不同,NSSI 行為是通過故意傷害自身而達到緩解負性情緒的目的[7]。雖然通過心理干涉為主、藥物治療為輔等方法治療后具有一定效果,但總體療效欠佳,促使現階段有關青少年抑郁癥患者NSSI 行為已成為醫學領域關注的熱點[8,9]。覺知壓力是指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利因素或刺激事件為其心理所構成的威脅、困惑,可使其身心緊張、不適,且覺知壓力亦會進一步加重抑郁癥患者病情。而應對方式是指當其處于壓力環境下,個體所選擇的不同應對方式[10,11]。研究[12]發現,伴有NSSI 行為的抑郁癥患者極少采取尋找他人幫助、調節負面情緒等正向應對方式去處理問題,反之多數患者均伴有自責、放棄解決問題等情況。基于此,本研究探討伴NSSI 行為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的關系,為臨床早期開展NSSI 行為抑郁癥覺知壓力的調節工作提供一定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選擇2019 年6 月~2021 年11 月在本院治療的312 例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為研究對象,根據是否伴NSSI 行為分為研究組(伴NSSI 行為,209 例)和對照組(不伴NSSI 行為,103 例);將研究組患者根據覺知壓力評分分為過大壓力組(>25 分,42 例)和非過大壓力組(≤25 分,167 例)。研究組與對照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父母婚姻狀況、父親文化程度、母親文化程度、獨生子女、家庭年人均收入、居住地、人際關系、學習壓力等一般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本研究已通過本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同意。納入標準:①所有受試患者均符合《國際疾病分類(ICD-10)應用指導手冊》中相關診斷標準[13];②研究組患者均符合NSSI行為診斷標準,即通過刺傷、擊打、灼燒、割傷等行為進行自我損害而促使的輕、中度軀體損傷;③情緒較為穩定,能夠配合進行紙筆測試的患者。排除標準:①通過本院相關診斷確診為精神分裂癥或伴有其他精神病性障礙的患者;②臨床資料不全的患者;③伴有嚴重傷人行為或致殘行為的患者。
表1 研究組與對照組患者一般資料對比(n,±s)
續表1

表1 研究組與對照組患者一般資料對比(n,±s)
注:兩組對比,P>0.05
1.2 方法 ①NSSI 行為采用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ANSAQ)[14]問卷進行評估,該問卷用于了解患者在過去1 年的NSSI 行為發生情況。該問卷由12 個條目組成,包括組織不明顯損傷,即未促使機體組織遭受明顯傷害,包括抓傷、頭部撞擊等行為和組織明顯損傷,即機體組織損傷明顯、發生出血等,包括燙傷、割傷等行為。該問卷的Cronbach's alpha 為0.792。NSSI 行為發生總次數1~4 次則表示NSSI 行為偶發,≥5 次則表示NSSI 行為反復發作;②采用中文版壓力覺知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15]評估患者覺知壓力,該量表分為緊張感和失控感2 個維度,共計14 個條目,根據患者近1 個月內的自身感受情況進行評估,其中有7 個條目為反向計分,總分值為14~70 分,分數越高則表示個體感覺壓力越大,該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為0.78。根據相關[16]文獻將得分>25 分定義為過大壓力,即健康危險性壓力(Health Risk Stress,HRS);③采用特質應對方式(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17]問卷對患者心理狀態進行評估,該量表分為消極應對和積極應對2 個維度,共計20 個條目,積極分數越高則表示心理狀態越好,消極分數越高則表示心理越差。
1.3 觀察指標 分析研究組患者的臨床特征;對比研究組與對照組患者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評分,過大壓力組與非過大壓力組患者應對方式評分;并分析伴NSSI 行為的青少年抑郁患者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的相關性。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1.0 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相關性檢驗采用Pearson 相關分析。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組患者的臨床特征 研究組患者以拽頭發、筆尖針扎/刺傷最為常見,占比分別為17.70%、16.27%。見表2。
2.2 研究組與對照組患者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評分對比 研究組患者緊張感、失控感以及消極應對評分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兩組患者積極應對評分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研究組與對照組患者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評分對比(±s,分)

表3 研究組與對照組患者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評分對比(±s,分)
注:與對照組對比,aP<0.05
2.3 過大壓力組與非過大壓力組患者應對方式評分對比 過大壓力組患者消極應對評分顯著高于非過大壓力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兩組患者積極應對評分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過大壓力組與非過大壓力組患者應對方式評分對比(±s,分)

表4 過大壓力組與非過大壓力組患者應對方式評分對比(±s,分)
2.4 伴NSSI 行為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的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顯示,伴NSSI 行為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緊張感、失控感評分與消極應對評分呈正相關(r=0.192、0.212,P=0.005、0.002<0.05),與積極應對評分無明顯相關性(r=0.121、0.016,P=0.081、0.817>0.05)。
3 討論
青少年作為社會的特殊群體之一,其生理、心理均處于變化狀態,在此期間對生活、學習以及內外環境等方面均較為敏感,易出現偏激、片面等心理應激反應[18]。NSSI 行為又稱之為自殘或自創行為,亦為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社會強化和自動強化二者間相互作用的結果[19]。患者自行消極強化過程并采取NSSI 行為用以減少負性情緒,自傷后又積極強化自殘過程所得到的愉悅感,該種行為即屬于消極的應對方式,亦屬于釋放壓力、調節情緒的策略。然而NSSI 行為可直接損傷機體組織乃至誘發自殺,嚴重影響青少年人群的身心健康,為其家庭乃至社會帶來沉重負擔[20]。因此,分析NSSI 行為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特征,探討其覺知壓力和應對方式的相關性,有助于醫生了解其自覺壓力并引導其正確釋放壓力及幫助其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進而有利于改善患者抑郁情緒。
國外一項[21]針對11 個國家的青少年NSSI 行為調查結果顯示,約27.6%的青少年既往存在NSSI 行為。我國一項[22]針對抑郁癥患者NSSI 行為的調查結果顯示,NSSI 行為在抑郁癥患者中的發生率為45.45%,而本研究結果稍高于上述報道。分析原因可能為,青少年抑郁癥患者本身的人際關系就相對較差,在面臨較大學習壓力的同時其父母亦受傳統教育觀念的影響,進一步增加其心理負擔,但其又較為缺乏情感宣泄途徑與社會支持,促使多數青少年抑郁癥患者將這類負性情緒轉于自身,導致NSSI 行為增加。研究[23]表明,對青少年抑郁癥患者而言,NSSI 行為并不是以自殺為目的,多數患者僅想通過NSSI 行為緩解社交壓力所帶來的困難或減輕心理負性情緒,回避因孤獨感、空虛感帶來的悲痛、失落。而本研究通過分析伴NSSI 行為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特征發現,多數患者以拽頭發、筆尖針扎/刺傷最為常見,符合上述觀點。
覺知壓力是評估個體感受外界壓力的過程,而應對方式是自身在受到壓力時所選擇采取的方法,當個體所感知到的壓力越大,其抑郁程度越嚴重,且采取消極面對的幾率越高。研究[24]表明,通過調節策略有助于改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負性情緒,減少自傷行為。本研究通過分析研究組與對照組的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發現,研究組患者緊張感、失控感以及消極應對評分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一結果提示,青少年抑郁癥患者伴有較高的覺知壓力可能會進一步進行患者身心健康。同時黃馨瑤等[25]研究發現,腫瘤患者覺知壓力水平以及消極應對水平與其抑郁程度密切相關。提示,覺知壓力、應對方式與抑郁程度密切相關。本研究通過對伴NSSI 行為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覺知壓力與應對方式的相關性進行分析發現,伴NSSI 行為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緊張感、失控感評分與消極應對評分呈正相關(P<0.05),與相關研究報道相符。提示,覺知壓力異常升高與消極應對密切相關。分析原因可能為,個人在壓力環境下所采取的應對方式屬于自身管理內心壓力的主要因素,同時亦能決定個體在面對壓力時的應激強度;采取積極正向的應對方式在面對問題時可通過理性分析后采取合適的應對方案,且多數均會獲得一個較好的預期效果;而采取消極應對方式的個體在面對壓力時可能過于注重自身所感受到的壓力,較少采用積極正向的解決方式,進而增加了抑郁、焦慮等情緒的體驗。
綜述所述,伴NSSI 行為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的覺知壓力與其消極應對密切相關,臨床治療期間醫務人員可根據覺知壓力情況給予其重點關注,同時及時給予患者心理疏導,緩解其心理壓力,通過合理干預引導其面對問題時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進而有助于優化患者臨床療效。此外,本研究存在樣本量較少,且病例來源單一等不足,結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因此,相關結論還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