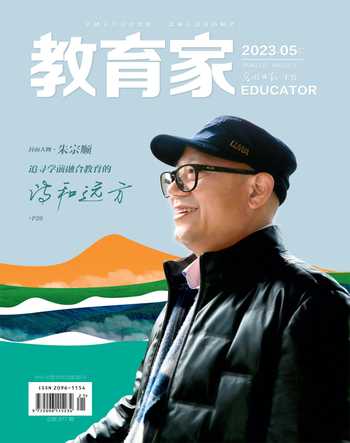郝冰:“林間最后的小孩”與他的守望者
米娜

當代文學作品中有這樣一類人物形象:手捧可樂,雙眼無神地盯著電視機里的動漫,習慣用物質代言歡樂的“塑料兒童”。他們對室外的一切毫無興趣,燦爛春光、夏夜星空、斜陽映照下的秋水與月光籠罩的山巒,對這群失去大自然賦予的靈性的孩子而言,遠沒有電視機里人造的畫面迷人。這樣的生活看似充實,實則虛無。
文學源于生活。看著眼前一個個與農田叢林保持著距離、一旦離開屏幕就百無聊賴的孩子,郝冰感到異常的失落。如何讓孩子在短暫的童年時光里感知大自然,感受生命的律動,彌補他們被現代生活吞噬的那部分快樂?郝冰仿佛一位“自然使者”,不停地追尋問題的答案。
讓雙腳幾乎沒有機會踩在泥土里的孩子走進自然
成為一名教師,是郝冰兒時的夢想。20世紀80年代,她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系,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如愿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在學校環境教育中心工作的她,做環境教育相關項目時,接觸到由民間環保先驅梁從誡先生創辦的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并邂逅了許多良師益友,他們聚在一起,致力于重建人與自然的聯結。
“跟隨‘自然之友腳步的那些年,我深受梁從誡先生的影響。他會騎自行車到高校為學生做講座,哪怕有時一場只有三五個聽眾,也會用心準備;他會二次利用別人用過的打印紙,連名片都是用這種紙張的背面打印出來的;每次在外吃飯,他都自備餐具,在保護環境這件事情上真正做到了身體力行。”郝冰回憶道。“已到耳順之年的梁先生沒有選擇安穩度日,而是四處奔波,盡全力發聲。從他的身上,我看見了一個知識分子對家國命運的擔當。”她感慨道。
那段日子,對郝冰而言意義非凡——從感受大自然的波瀾壯闊,到感悟人類在發展的同時對環境帶來的破壞,郝冰最初的心動漸漸轉為心痛。她決定用己之長,開鑿一條保護環境的通道。從教育入手,郝冰創辦了公益組織“天下溪”,編寫了《草海》《其其格的故事》等鄉土教材,想以鄉土教材推動鄉土文化,讓家鄉文化滋養孩子們的生命。“天下溪”還成立了鄉村圖書館,用心選擇滿足孩子們成長需要的書籍,承擔起培訓圖書管理員的責任。同時,開展自然體驗項目,試圖找到可持續發展自然教育的可行性方案。
當郝冰的自然教育事業如火如荼地進行時,她的兒子出生了。“我們生活在大城市,認為這里的教育資源是最好的。但我成為一個孩子的媽媽后,卻發現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雙腳幾乎沒有機會踩在泥土里,該怎樣在城市里養育孩子?”郝冰無法回答內心深處的問題。她發現以往自己的關注點都放在鄉村兒童身上,卻忽略了城市里的孩子。郝冰想起曾在鄱陽湖見到的一個小男孩,“他看一眼就能知道湖里有多少只鴨子”。在她看來,這是鄉村孩子與大自然朝夕相處后獲得的饋贈,是城里的孩子所匱乏的“能力”。“現代科技把孩子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眼睛和手指上,忽視了孩子是需要更廣泛運動和深度思考的。長期缺少與自然的直接接觸,已經讓越來越多的孩子患上了‘自然缺失癥,給他們帶來了不少生理和心理上的問題。”從那一刻起,她將目光從鄉村轉向了城市。
出于母親的本能,也出于職業敏感度,郝冰開始研究幼兒成長與發展的規律,研究早期教育與自然教育結合所產生的影響。“城里的孩子擁有相對豐富的物質條件,但戶外空間極為狹小,他們需要與自然產生聯結。”為了讓城市里的孩子們有機會走進自然,郝冰于2010年創辦了天下溪自然學園,并于2019年更名為天下溪青藍森林幼兒園(以下簡稱“天下溪幼兒園”)。“‘天下溪三個字出自老子的《道德經》,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我想在孩子們幼年時期給予他們溫暖的、堅定的、綿延不斷似水般的力量,不想以嚴厲、剛強的態度出現在他們的童年。”郝冰以“濡沐天真,滋養童年,溫馨共育”為辦園宗旨,以期在成人與孩子之間建立起良性的互動關系。“那一定是有溫暖、有信任且流動的關心,是可以幫助雙方共同成長的關系。”
觀察一盆植物的四季變化,也是一場自然教育
天下溪幼兒園所推行的教育理念,是郝冰將自然教育與東西方教育理念和文化相融合的嘗試。“我們的課程集中在自然、生活和藝術三個部分。自然部分,是幫助孩子建立與世界的最初聯系,觀賞花草魚蟲、感受四季變化,告訴孩子世界歡迎他的到來;生活教育,幫助孩子習得基礎的生活技能和人際交往需要注意的基本禮儀;藝術教育,是給孩子精神食糧,用水彩畫、手工編織、童謠等幫助孩子成為善于表達自我的人。”郝冰強調,課程使用“呼吸原則”,教師主導的活動是“吸入”部分,而活動中怎么玩、和誰玩等需要孩子自己決定的環節,則是“呼出”部分。在她看來,如果完全讓孩子“呼出”會很辛苦,可要是完全“吸入”,孩子就會很壓抑。此外,天下溪的課程安排也注重旋律感,一改往日周一至周五線性矩陣的模式,交叉重復開展不同類型的課程,以便孩子真正實現“學而時習之”。
為保證課程有效落地,讓孩子們感受到如家般的溫暖,郝冰一直將愛笑、有合作精神、追求進步作為招聘教師的三大條件。“笑臉是走進孩子內心的入場券;合作精神不僅有助于教師之間的合作,還是讓教師與孩子一同游戲的法寶;必須追求進步,是因為孩子一直在變,用一成不變的眼光是做不好幼兒教育工作的。”郝冰說道。
辦在森林邊上的天下溪幼兒園,為孩子們創造了在天氣允許的情況下去森林感受四季的機會。在郝冰看來,0-6歲是孩子最容易與自然建立聯結的年齡,此階段開展自然教育,不僅有助于孩子自信、自如地運用身體,還有助于讓孩子在探索感知中獲得經驗,從而促進心智的發展。
郝冰曾在一場直播活動中提到園所里不少孩子都是爬樹高手,甚至教師也會爬樹,其中就包括她自己。“爬樹是否會傷害樹?”“孩子在爬樹期間會不會受傷?”面對觀眾的提問,郝冰從自然教育角度給出答案:“孩子爬樹,不是一天就能順利完成的,是一個循序漸進、不斷訓練技能的過程,也是他們與大自然產生聯結的過程。保護自然,不是說不能觸碰樹木,而是在平衡人與自然關系的前提下,讓孩子融入自然、感知花草樹木,讓他們在體驗中意識到哪些行為會傷害自然。若一開始就將孩子與自然隔絕開來,那么教育便無從發生。”郝冰認為,真實的體驗需要孩子自主思考、獨立行動,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困難,但她堅信在真實體驗中習得本領,是自然教育的意義所在。
2019年8月,天下溪幼兒園發布了一則“森林小孩兒”招募信息,在北京招募參與公園自然教育活動的兒童,消息發出旋即滿額。郝冰特地安排多才多藝的教師負責此次活動,“有的會唱歌,有的彈得一手好吉他”。在她看來,帶孩子去戶外的教師不僅要有個人魅力,還要有特別的技能,才能將藝術教育與自然教育更好地結合起來。“森林小孩兒”也為一些無法進入天下溪幼兒園的孩子提供了接受專業指引、感受自然教育魅力的機會。
“家長們漸漸意識到城市里長大的孩子與自然相處的機會較少,同時,他們信任天下溪幼兒園,認可我們的理念與做法,才愿意送孩子參加我們組織的活動。”郝冰說道。疫情防控期間,看到孩子們無法在美好的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懷抱,郝冰提出家長可以帶孩子在家中做自然觀察。“如果有條件,我們可以帶孩子參加‘森林小孩兒這樣的活動;如果條件不允許,可以在室內做自然觀察,從時間維度理解自然。觀察一盆植物的四季變化,也是一場自然教育。”她非常重視對家長的引導,也感謝他們對天下溪的支持。“幼兒園就像由三個圈組成的大圓,第一圈是孩子,第二圈是教師,第三圈是家長社群。我們能走過這么多年,也得益于家長社群強有力的支持,其中也包括經濟上的資助,有的甚至將家搬到幼兒園附近。”郝冰感慨道。
先回歸自然,再走向職業身份
多年來,郝冰就像一個“自然使者”,不遺余力地挖掘著自然教育在早期教育階段所擁有的價值。為探索更加多元的自然教育方式,郝冰還做了兩件事——翻譯與培訓。她接連引進并翻譯了有“自然教育圣經”之稱的《與孩子共享自然》、提出“兒童自然缺失癥”的著名作品《林間最后的小孩》、環保運動先驅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等。“《寂靜的春天》這部書像是曠野上的一聲吶喊,揭示了工業革命進程所伴生的環境問題。蕾切爾對大自然的愛,以及她詩人般的語言、科學家般的嚴謹和面對真理的勇氣,都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顆種子,她是我遙遠的榜樣。”郝冰希望,用經典的環保主題書目讓更多人關注環境問題,關注自然教育。同時,她積極開展幼兒教師自然教育培訓,傳播正確的自然教育理念,還多次公開演講,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重要性。
2020年初,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和一系列自然災害接踵而來,越來越多人開始主動關注自然、討論自然,對如何與自然共處的反思達到空前熱烈的程度。此時受邀參加全國自然教育論壇的郝冰,從教育者角度出發做了一段引人深省的發言——當我們在做自然教育的時候,不能離開對人的理解,在服務于自然的同時,更要服務于當下的孩子。“孩子的教育是關于體驗和感受的教育,大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媒介。自然環境給了孩子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場景和材料,刺激著孩子所有的感官,幫助孩子建立與自己的關系、與他人的關系與世界的關系。”郝冰想要更多幼兒園承擔起這項責任,成為聯結孩子與自然的媒介。
那么,辦一所能夠聯結孩子與自然的高質量自然教育特色幼兒園需要哪些準備?郝冰的回答是,先回歸自然,再走向職業身份。“只有真正感受到自然的力量,才不會在自然教育的道路上感覺到累。”在她看來,自然教育的發生需要從教師自身開始,教師熱愛自然、了解自然,并且將自然教育理念貫徹到自己的日常言行與教育教學中,才能真正影響孩子。
“當前,可能有不少幼兒園因場地限制等因素無法開展自然教育。倘若我們認為沒有自然環境就不能做自然教育,或者自然環境比一切都重要,那將使自然教育狹窄化。如果幼兒園等待所有自然條件都具備了再開啟自然教育之路,孩子們可能也沒有什么創造性和樂趣了。”郝冰認為,自然教育沒有標準化的定義,她能做的,就是整理天下溪幼兒園的經驗,幫助大家厘清自然教育的脈絡及自然教育課程的編排原則,引導他們在遵循自然教育理念的基礎上,創造出最適合自己的課程體系。“天下溪幼兒園也有自己的局限,我們培養不出一眼就能數出多少只鴨子的少年,所以自然教育要因人而異,因時、因地制宜。”郝冰說道。
當被問及實踐過程中遇到過哪些難題時,郝冰堅定地回答:“沒有難題,做就是了。”從大學教師到幼教人,她的選擇與堅持,都出于一種深刻的愛。“大學教師的確是旁人羨慕的職業,但從我個人視角來看,幼兒教師在某種意義上比大學教師更重要,因為幼兒教師對孩子的影響是深遠的、持久的,是刻入生命的。”在郝冰看來,對于一個關注生命、關注自然、關注孩子成長的人而言,身份的轉變是順其自然,是一脈相承。她甘愿成為守望者,把自己曾感受到的自然的美與能量,帶給鋼筋水泥世界里的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