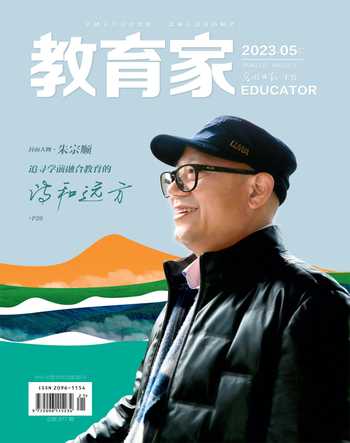當親子作業偏離預想軌道
本刊編輯部
許多幼教人認為,親子作業是增進親子感情、促進家園共育的好方法。實踐中,有的家長直接代勞,以一己之力完成各項任務;有的家長在網上直接購買符合教師要求的商品,簡單粗暴地上交了事;還有家長苦練十八般武藝,帶孩子一起“卷”出天際……家長叫苦不迭,一線幼兒園教師也時常有苦難言。讓我們傾聽他們的聲音,了解那些偏離了預想軌道的親子作業,為教師和家長分別帶來了哪些煩惱和困惑。
教師聲音
家長的過度參與難以規避
山東省東營市廣饒縣廣饒街道陽光幼兒園教師 吳素梅
顧名思義,親子作業是需要“親”與“子”共同完成的任務,任何一方缺席都會使布置親子作業的意義大打折扣。近年來,我深深地感受到,家長過度參與甚至包辦的現象屢見不鮮,讓親子作業“變了味兒”。
記得有一次,為了讓孩子們體驗制作不倒翁的樂趣,初步了解不倒翁“不倒”的原理,我們號召家長和孩子利用身邊的廢舊材料,共同制作一個獨一無二的不倒翁。待周一入園時,孩子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成果作品,其中一個不倒翁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底座是半球體形狀的青花瓷,身體是刺繡的碎花布包裹著的硬紙板,看上去既結實又精美。我詢問作品的小主人這個不倒翁是誰做的,又是怎樣做成的,小朋友非常自豪地告訴我:“這是我的一位阿姨在周末專門找人做的,今天早上在幼兒園門口才交給我。”至于材料的來源和具體的制作方法,他都用搖頭給了我答案。
孩子們帶來的作品中,制作精美的不倒翁不在少數。看著這些作品,孩子們異常興奮,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這不像一場幼兒園親子作業的普通展覽,更像是家長一手完成的成品玩具的聚會和比賽。這次親子作業給家長和孩子帶來的收獲是什么?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包辦式、成品式的作品?作為幼師的我們又該如何和家長溝通來規避這個問題?……我想,不少幼教人也在等一個答案。
家長的參與意愿不強
北京市懷柔區第四幼兒園教師 翟雪琪
我聽過幾位家長的吐槽,他們把親子作業當成是幼兒園強加給家長的輔導任務,因此配合的積極性往往不高。新冠疫情防控期間,為了能讓孩子加強鍛煉,我們每周向家長推送兩次教師錄制好的親子體能游戲視頻,告訴家長每天多利用家里的玩具及日常物品與孩子一起做這些游戲。因為不想給家長造成太重的負擔,我們調查后最終只選擇了兩人三足、袋鼠找朋友、踢泡泡等比較簡單且容易操作的游戲,但就實際反饋的情況來看,家長的參與度并不高。
在我們看來,這種情況已是常態。有時即使只需要家長幫忙準備一些學習材料,也經常有家長缺席;還有家長只做“表面工作”,上交一份低質量的作業草草了事。我們精心準備教育資源,認真籌劃每份親子作業,是希望能通過這種形式在發展親子感情的同時,推動孩子的全面發展。如今,家長不愿意配合的態度讓這項工作的價值變得空泛,也讓我們感到無奈。
親子作業成了教師交付成果的形式主義
江蘇省蘇州科技城天佑實驗幼兒園教師 姜雯
完成親子作業,本應是一件其樂融融的事情,但我們發現,它逐漸走向了教師交付成果的形式主義。由于幼兒教育十分強調環境的豐富性,我們有時也需要追求教育成果的外在表現。為了收集更多材料布置環境,部分幼師所下發的親子作業一般集中在手工作品、繪畫這幾類形式,容易讓家長產生倦怠,認為“親子作業都是美觀而有難度的作品”,于是家長網購成品作業的問題逐漸凸顯。策劃過程中,我也時常感到疑惑,一線教師應怎樣把控親子作業的難度、類型、次數等細節,才能使其既滿足成果展示的需要,又能最大限度實現親子作業的初衷。
家長聲音
誰來調整親子作業的時間、內容和形式
福建省廈門市幼兒家長 陳媽媽
我家孩子今年在幼兒園大班,老師平時布置的親子作業給我帶來了不少煩惱。首先是時間問題,算上親子共讀、做手工、外出參觀等各種類型,我們平均每星期都要完成一到兩項親子作業。有時老師晚上在微信群里布置作業,要求家長當天或轉天白天反饋,讓我們根本來不及準備。為了能按時完成任務,我們只能去網上買一些現成的材料,并在家里長期儲備一些手工作業,即便如此,網上的材料也不能完全符合老師的要求,很多時候我和孩子不得不連夜開工。
此外,我覺得親子作業的具體內容和布置形式也需要調整。對于幼兒園階段的小朋友而言,老師布置的很多內容難度嚴重超綱,導致如果家長不深度參與,就無法完成這份作業。記得老師曾布置過一次建筑主題的手工作業,要孩子和家長一起畫出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筑的區別,恐怕很多成年人都無法給出正確答案,更不要說讓孩子來理解并畫出兩者的區別。
再比如,老師曾要求家長和孩子共同完成一份原創微課視頻,我獨自承擔了拍攝、剪輯的任務,當我把成品發給老師后,卻得到了“需要用軟件重新修改”的回復,當時我便有了情緒:親子作業看重的是家長和孩子共同完成的過程,而非最后上交的成果,即使我把視頻修改得再精美,也是我作為家長一人完成的內容。更何況老師在微信群里布置作業時并沒有對微課視頻的內容提出詳細要求。聯想他們之前要求的打卡、拍照等一系列操作,我都有些懷疑老師要用這些作品參加比賽。
請關注家長的沉默和無奈
江蘇省南京市幼兒家長 蔡女士
我現在是一名自由職業者,曾經做過美術教師,因此我可以經常幫孩子完成一些精美的親子作業,但在很多雙職工家庭里,那些耗時長、專業性高的作業總讓家長們頭疼不已。
每次收到親子作業的通知,家長之間就會私下里吐槽。之所以說是私下里,是因為我們的班級微信群永遠沒有家長公開發言。名義上所有家長都沒有被禁言,但我們好像默認不在群里多說一句話,只是默默關注老師在群里發布的各項內容,即使對作業內容有疑問,也永遠是和老師或關系比較好的家長私聊解決。有時老師會將孩子們的親子作業拍照發到班級群相冊,我們才能看到其他小朋友的作品反饋。
不過,家長們的吐槽也只是“逞口舌之快”,抱怨過后依然會努力思考如何完成。有時我也不太情愿去做,但說到底還是沒有拒絕的勇氣。且不論個別幼兒園是否存在老師因此而區別對待孩子的問題,我不愿意讓我的孩子成為班級里拒絕完成親子作業的少數學生,因為不是每份親子作業都止步于上交這一環節,當老師在班上請孩子分享時,我相信沒有一位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只是坐在臺下看著其他小伙伴分享他們的作品,這對孩子的心理健康會有些負面影響。所以,對于老師布置的親子作業,我這個老母親既然接受了,就會認真對待,希望我們家長的辛苦能給孩子的幼兒園生活多留下一些美好回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