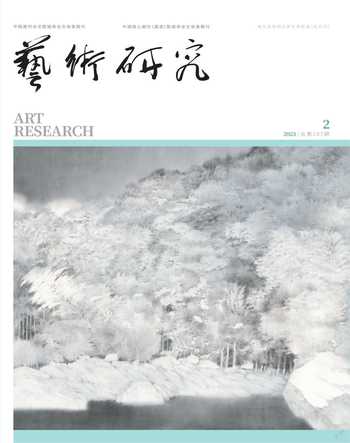在借鑒與融合中發展
張富蘭
摘要:西方音樂史學與民族音樂學是音樂學研究中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學科,無論是在學科的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上都有著非常明顯的差異。西方音樂史學的研究對象主要關注的是西方音樂歷史的著作,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是活態的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但是在當下,音樂學的研究方法呈現出多元的發展趨向,雖然他們它們的研究方法各異,卻呈現出了交叉與融合的趨勢。
關鍵詞:西方音樂史 民族音樂學 融合
德國音樂學家圭多·阿德勒把音樂學分為兩個研究板塊:歷史音樂學和體系音樂學。①西方音樂史研究和民族音樂學研究是分屬于這個學科的兩個不同板塊的研究,西方音樂史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史料文本的搜集和分析,而民族音樂學卻主要側重于對研究對象的田野考察,把音樂作為文化來進行研究,對音樂文化事象進行記錄和闡釋。民族音樂學作為一門較為年輕的學科,以它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多樣化的研究理論與方法獲得了音樂學界的關注,為音樂學界的打開了新的研究視角,使各個學科也不再僅僅局限于對音樂本體的分析與研究,例如,西方音樂史的研究就在不斷地吸收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同時,在民族音樂學的發展過程中,也在不斷借鑒西方音樂史等其他音樂學學科的研究方法。音樂學各個學科之間就這樣打破學科壁壘、融會貫通,進行跨專業跨學科的融合,以求達到更加理想的研究結果。音樂學各學科之間的融合,既是音樂學學科發展的要求,也是音樂學發展的必然。
一、學科發展歷程
(一)民族音樂學的興起
民族音樂學在起初被稱為比較音樂學,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王光祈留學德國,師從“柏林”學派重要人物霍恩博斯特爾,并將西方的比較音樂學介紹到中國,1980 年南京會議上,被正式定名為“民族音樂學”。民族音樂學是音樂學與人類學等其他人文科學的邊緣學科,因此在更廣闊的人文科學領域中也應該有它適當的地位。②關于民族音樂學研究,美國著名的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曾經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民族音樂學是音樂學與民族學兩個學科的有機融合。關于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范圍,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是以“非歐音樂”為主。著名的民族音樂學家奈特爾認為民族音樂學研究主要應該探討三種類型的音樂:無關文字社會的音樂、亞洲及非洲北部高文化中的音樂以及以口述方式來傳承的音樂。之后,孔斯特進一步將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范圍擴大至所有類別的非西方藝術音樂。由此可見,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范圍在不斷的擴張。在20 世紀60 年代,梅里亞姆提出的“三要素”(即概念、行為、音聲)理論,成為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經典方法。在20 世紀80 年代,美國音樂學家賴斯構建了一個更加全面的認知模式,他認為應該在更深更廣的范圍內來分析和研究人類音樂文化的形成,并提出了民族音樂學的經典的“三要素”研究方法,包括歷史的構建、社會的維系和個體的創造及體驗,這三個要素是交融互動、雙向聯系的。
綜合上述可知,在不同時期里,學者們對于民族音樂學的解釋有著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范圍在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民族音樂學領域對于研究文化中的音樂這一點是達成共識的,這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最重要的特征。對于大多數民族音樂學家來說,民族音樂學“把音樂作為文化”來研究,并不是排斥對音樂形態的研究,它的研究要求建立在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不能孤立地去看待音樂,要研究與之相關的文化語境。民族音樂學家梅里亞姆在《民族音樂學定義》一文中,將民族音樂學研究分為三個步驟:在田間搜集材料、記譜和分析、把分析結果放到相關背景中去討論。故研究,起點由“田野”始,以“文化”終,音樂居其間。田野是研究的出發點,也是第一步,所究對象在文化中存在,故音樂當受文化的全面關照。③
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總結起來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20 世紀80 年代以前的萌動期、80—90 年代民族音__樂學在中國確立、90 年代后在中國大陸的新發展。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發展的萌動期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學者是音樂學家王光祈和人民音樂家呂驥,其中,呂驥對于中國民間音樂的研究堪稱是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先河。早在1948 年,我國著名的音樂理論家呂驥在他的《民間音樂研究提綱》一文中,針對民間音樂研究的基本宗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們研究中國民間音樂,不應該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研究興趣,為研究而研究。主要的目的應該是首先了解現在在中國各地流行的各種民間音樂的情形,進而研究其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形成歷史與演變過程,獲得關于中國民間音樂各方面的知識,以為接受中國音樂遺產,建設中國新音樂的參考。”④談到研究中國民間音樂的目的時,呂驥認為,在對中國民間音樂進行研究時,要從音樂本體進行研究,發現它的內在規律,進而根據社會北京以及民間音樂的發展歷史進程進行符合實際規律的剖析,才能夠從中獲得科學的、合理的解釋,從而為建設中國新音樂提供合理性參考。由此看來,呂驥的思想觀念中已經有“把音樂作為文化”來研究的思想。他認為,研究民間音樂,應該根據社會生活,與其發展的歷史,予以合乎實際的解釋,這足以說明,他沒有孤立地看待音樂文化,而是把音樂放在人民生活的大的歷史背景中進行研究。這種觀點的提出,與同時期冼星海的思想相比較來說是一個具有前瞻性并很有突破的思想,這在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看出當時呂驥先生的民族音樂學研究理念,呂驥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的提出和當時呂驥指導下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所做的研究對于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的發展有著開辟道路的重大意義。因此,這就要求民族音樂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一方面要對收集到的音樂進行準確的記譜,并從音樂體系、樂曲結構、唱詞結構、演奏技法進行準確的分析;另一方面還要對族群所屬的生態自然環境、社會歷史環境等進行分析,找出支撐這種音樂所賴以生存的文化背景所在。
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新視角,給原有的音樂學科研究打開了新的思路、注入了新的養料,使各個學科的研究不再僅僅局限于對音樂本體的研究上,而是將視角拓寬至于音樂相關的文化背景的研究中去,從而使音樂學的研究與分析走向全面性、整體性的研究。
(二)西方音樂史學的學術傳統及研究瓶頸
音樂史學,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作品,它是把音樂文化現象以及與這種音樂文化現象關聯的諸事實作歷史性闡述和領會理解的學問。⑤西方音樂史的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人就開始借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的理論和思想對音樂的藝術性、社會性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西方音樂史,作為一門藝術史學,它主要的關注對象就是音樂作品本身,這其中就包含了對于音樂本體的關注和分析、對作曲家創作背景的分析、對音樂作品與社會歷史文化關系的研究等。由此可見,西方音樂史研究與民族音樂學研究有著截然不同的關注對象,西方音樂史研究對象主要限定在西方藝術音樂領域并更多的關注音樂作品本身。著名音樂理論家菲利普· 博爾曼曾在他的論文——《以色列的德國猶太人和室內樂——西方音樂史中的民族音樂學意義》中對西方藝術音樂的研究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傳統的西方音樂史研究將音樂文本以及作曲家的創作意圖放置到了一個無可比擬的主導地位之中,將藝術音樂作為一種完全脫離任何族群以及社會歷史背景的“純音樂”來看待。傳統的西方音樂史研究中孤立地看待音樂本體的方式,使得西方音樂的研究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傳統的西方音樂史研究只能向我們展示一個單一的、像鐵板一樣冰冷的音樂史,無法向我們展示出西方音樂史的多樣性。他認為西方的藝術音樂史是風格、體裁和社會背景的集中體現,是可以借用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的。
綜合以上兩部分來看待民族音樂學研究與西方音樂史研究,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民族音樂學注重音樂背后的文化,西方音樂史研究注重對于音樂文本的分析。
二、打破學術壁壘
進入到上世紀60 年代以來,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越來越多的被其他學科所吸收和借鑒。隨著各個學科研究的廣度與深度的不斷擴展,西方音樂史學的研究也在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上做了很多嘗試。在這個過程中,民族音樂學研究也開始重視對于音樂史學的關注和借鑒。
(一)西方音樂史研究范式的轉型
在過去,西方音樂史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對于文本、文獻的研究,這種較為單一的研究容易導致對于文獻分析的片面性。根據這一情況,托馬斯·圖里諾在《秘魯排簫風格的歷史和詮釋的策略》一文中指出:“歷史——就像身份認同與音樂資源所附屬的意義一樣——在不斷地被征用和重構,以滿足當今政治的需要,在這層含義內,歷史總是現代的。”這一觀點的提出,指明了對于文獻的解讀也需要共時性的研究,對于從史料入手進行分析的學者們,如何判斷史料的真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歷史學家王明珂認為,“歷史有多元的聲音,對歷史文獻的正確解讀應該是文本分析,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有助于歷史學家認識‘歷史的真象。”⑥因此,對于西方音樂史這門注重史料研究的學科來講,將研究視角納入到音樂所產生的社會背景、文化環境中看待,剖析音樂本體與其相關的歷史文化語境的相互關系,才能夠準確地傳達出史料的內涵。因此,民族音樂學注重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對于西方音樂史研究來講就顯得尤為重要,也被越來越多的西方音樂學研究者所重視。音樂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音樂的核心所在,理解、認識音樂必須找到音樂賴以生存的文化語境,將音樂現象納入到它所存在的文化語境中進行闡釋。
以往大多數的西方音樂史研究論文,關注點都是聚焦于音樂作品的和聲、曲式、配器等作曲技術理論層面和音樂風格流__派層面的內容,很少觸及對音樂背后的人文內涵的解讀與分析。上個世紀90 年代,于潤洋先生的《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分析》一文,作為音樂學分析、音樂評論的范本,將作曲家藝術作品的文本分析放在了作曲家所屬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使藝術作品的分析更具全面性和深刻性,為中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打開了一個更為寬闊的視野。正如于潤洋先生在文中所言“音樂學分析則應該是一種更高層次上的、具有綜合性質的專業性的分析。”于潤洋先生為“如何去分析一部音樂作品”這一課題做出了重要的嘗試,為音樂學研究者們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自此,西方音樂史的研究正在逐漸受到民族音樂學研究“文化中的音樂”的影響,更多地開始關注音樂背后“環境”的影響和作用。
由上述可見,在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西方音樂史已經打破了實證主義的歷史性研究維度,將目光放拓寬至共時性研究的維度,把音樂的史實放入到文化語境中去研究。
(二)民族音樂學研究視角的轉變
民族音樂學關注的是“活態”的音樂,注重對當下共時音樂的研究。民族音樂學自傳入中國以來,學者們更加強調共時性的研究,往往在研究過程中會忽略歷時性研究。因此,相對于音樂史學學科來說,民族音樂學研究較少關注對于音樂歷時性的研究。針對這一問題,上世紀80 年代,格爾斯談到“在研究所謂的沒有文字、沒有歷史的民族中,這些人群有神話、有傳說、有口頭流傳的歷史也應該作為研究的重要方面”。1987 年,賴斯喊出了“重建民族音樂學”的口號,他認為“音樂的生成過程是社會、歷史和個人這三個過程的完美結合,即人類按歷史構成音樂、由社會維持音樂并通過個人創造、體驗音樂。”⑦由此可以看出,音樂學家們在80 年代已經開始有將歷時性研究納入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思考,并且可以看出“歷史”的研究對于民族音樂學研究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民族音樂學在研究活態的音樂的同時,還必須關注音樂所處的文化背景的變遷過程。將歷時性研究與共時性研究相結合,有助于使我們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分析研究對象,捋清研究對象的發展歷程,使我們的研究更具有“科學性”。理查德· 魏狄斯在《歷史民族音樂學》中解釋道:“民族音樂學通常被描繪為是一個主要涉及至今活著的音樂家的表演和那些在當代社會各類表演中的角色的學科。每一類音樂及每一類社會都是綿延的歷史過程的現代結局,這種過程對于表演者可有可無,但對于來自局外的觀察者卻至關重要。”⑧這就更加直接地提出了歷史性思維對于田野數據分析的重要性和歷史視角對于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關鍵所在。
三、學科交融成為必然
綜上所述,音樂學研究的“學科”界限隨著學科的發展在不斷地擴展,學科間的邊界也越來越模糊,這是在學科的發展和前進中,各個子學科間的方法論不斷借鑒和融合所產生的。民族音樂學作為一門相對較為年輕的學科,研究方法非常靈活。西方音樂史研究作為一門有著悠久的研究歷史的學科,有著非常深厚歷時性研究傳統。兩個學科雖然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有著很大的差異,但是在學科的發展中都相互借鑒了對方的研究方法,為我所用,將歷時性研究與共時性研究以自身研究目的為依據有機地借鑒和統一起來,這種學科間交叉與融合的趨勢也是音樂學研究發展的必然要求。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鍛煉自己對于自己所收集到的歷史資料的鑒別和分析的能力,這對于我們更加理性地探究不同歷史環境下音樂文化的變遷和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這也就要求我們在進行少數民族音樂考察時,既重視史料的收集工作,也要對我們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判斷。由于并不是所有收集到的資料都是有價值和具有參考性的,這就要求我們對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進一步的探源、鑒別和考證,同時也對民族音樂學研究者的史料分析能力和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蔡際洲先生曾經在《中國傳統音樂研究30 年——關于學術規范的審視與學術創新的反思》一文中提到:“30 年來的實踐說明,理論創新功力不足,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主要為這樣幾點:其一,與我們的學術傳統有關,由于中西文化傳統的差異、中西治學特點之差異,我們在思考問題上總是習慣于‘演繹、而不善于‘歸納,總是喜歡將‘外來的、‘他者的理論與方法作為‘一般來指導我們的‘個別。”上文中蔡際洲先生所提到的問題也是值得國內音樂學研究者深入思考并作出改變的。因此,就我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而言,將西方的理論方法“為我所用”,杜絕理論的生搬硬套,找到適合我國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新道路才是進行理論研究的關鍵所在。
由此可見,音樂學各子學科之間并不存在著嚴格的理論劃分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同專業領域內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相互補充和互相推動的作用,因此,音樂學各子學科的互相借鑒和融合是音樂學發展的必然。
參考文獻:
[1]趙曙光.探析民族音樂學方法論對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的影響[J].音樂創作,2015(8).
[2]沈洽.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導論(上) [J].中國音樂學,1986(1).
[3]李方元.對梅里亞姆研究理論“三步驟”的思考與解讀——民族音樂學人類學取向與“兩張皮”困境[J].音樂探索,2011(2).
[4]呂驥.民間音樂研究提綱[J].音樂研究,1982(2).
[5]劉玲玲.論西方音樂史學研究中的“位” [J].藝術探索,2009(3).
[6]徐杰舜問,王明珂答.在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人類學學者訪談之二十八[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4).
[7]陳艷偉.交叉與互融——兼論西方音樂史學與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之關系[J].音樂創作,2015(10).
[8]陳艷偉.交叉與互融——兼論西方音樂史學與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之關系[J].音樂創作,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