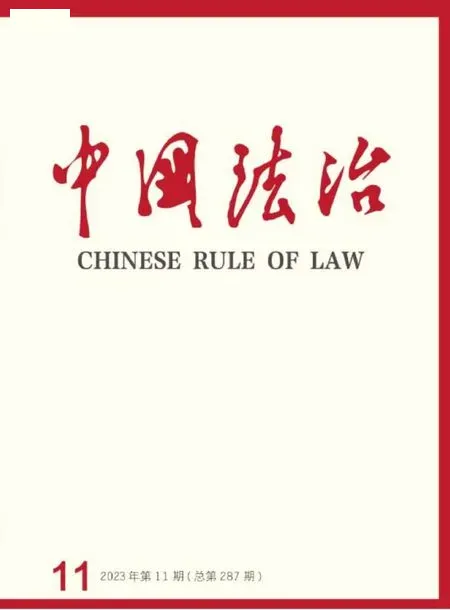調解的當代價值與科學定位
廖永安(湘潭大學法學院教授)
放寬歷史的視界,調解文化自古流淌于中華民族的血脈,成為中華法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顯著標識。無論是傳統中國的“無訟”文化,還是中國共產黨從陜甘寧邊區政權建立伊始確立的“著重調解”“調解為主”審判方針,調解始終挺在社會矛盾糾紛化解防線的最前沿。有學者指出,“說服—心服”的調解模式構成了中國糾紛解決的基本畫面。雖然我國1991年民事訴訟法刪除了“著重調解”,代之以“自愿合法調解”,但經歷21世紀初期的短暫調整后,“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又成為中國民事司法的基本方針。在這一過程中,經常有法律人基于西方現代法治主義立場對于調解持批判態度,認為調解“和稀泥”壓制公民權利意識,與法治不相容。諸如此類批判實際上是以西方法治圖景為判準指南,忽略了我國法治建設立足的基本國情以及社會轉型發展的實踐需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要重估調解的當代價值,在此基礎上對其重新定位,以滿足人民群眾的多元解紛需求。
一、調解的當代價值
(一)調解是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風險挑戰的有效方式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當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加。鑒于此,我國的法治建設必須立足于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順利推進。
無疑,我們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所提出的“風險社會”,風險社會的沖突集中表現在人與人、集體與集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糾紛,而應對風險社會的根本途徑在于用法治的確定性消除風險沖突的不確定性。傳統法學理論主張構建“訴訟中心主義”的糾紛解決機制,通過“一斷于法”定分止爭,然而,這種主張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其忽略了轉型發展過程中矛盾的“現實性”與“非現實性”以及“結構性”與“非結構性”交錯聚集,法律的滯后性往往無法預料和應對這種不確定性,因此,并非所有糾紛都能夠通過司法最終解決,作出非黑即白的判斷;另一方面,其忽略了我國在“風險社會”之外不同于西方的獨特社會語境,即有學者提出的“關系社會”和“多元社會”。“關系社會”沿著儒家社會傳統脈絡,重視人與人之間在社會網絡結構中的人際互動;“多元社會”意味著多元利益需求的相互交織。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確定性不可能完全基于馬克思·韋伯構建的形式理性法治而確立,相反,過度強調形式法治可能會導致社會發生崩潰,即所謂“法律對生活世界的過度殖民化”。
傳統法治力有不逮之處正是調解大有可為之處。調解從經驗、事實、歷史出發“就事論事”,通過其包容性和開放性特質,調和法律與習慣、強制與合意之間的沖突,有效彌合了社會變動與法律穩定性之間的縫隙,在糾紛解決的經驗累積中推動法律的形成和發展,實現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統一。
(二)調解是突出體現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糾紛解決方式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之一,廣泛而深刻的人民性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治的邏輯起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使法律及其實施充分體現人民意志。”
比較各類糾紛解決方式,調解突出體現了以人民利益為中心,核心在于其最為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調解具有自愿性、靈活性、包容性、開放性,以及與時俱進性,這些特征決定了調解能夠最大限度滿足人們的利益需求,并能實現關系修復與社會和諧的目的。相較而言,訴訟是由一群職業法律人在一個封閉的法空間中圍繞過去案件事實的挖掘和法律的適用而展開并作出最后的裁決。與調解相比,它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封閉性、機械性,以及滯后性特征。因此,將調解挺在前面,符合糾紛解決的基本規律,符合糾紛當事人的利益需求,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發展要求的突出體現。
二、調解的科學定位
基于以上兩種調解價值的全新認識,筆者認為要對調解進行重新定位。
(一)調解優先應當成為新時代國內國際糾紛解決的基本共識
在西方社會的糾紛解決機制中,訴訟曾長期處于正義綜合體系的圓心。在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調解長期處于糾紛解決的軸心。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由于對抗制訴訟帶來的訴訟遲延、成本高昂等弊端,西方興起了鼓勵非訴解紛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運動;面對我國實現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艱巨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我國有14億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負!”為此,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成為社會矛盾糾紛化解的首要選擇。國際調解中心名譽主席邁克爾·利斯在2012年ADR機制發展大會上曾預測,到2020年,ADR即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這個短語會有一種新的解釋。換句話說,到那時,訴訟可能已經變成了替代性的糾紛解決方式,而目前的ADR機制將成為糾紛解決方式中的主流。當前,調解優先的理念正成為中西方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共識。盡管爭議仍然存在,但強制當事人在起訴前參加調解正在西方尤其是歐洲法院大力推行并得到社會認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敷衍調解可能遭遇訴訟費用懲罰。在我國各地促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發展的地方性立法探索實踐中,調解被置于優先位置;訴前對于適宜調解的糾紛先行調解在各地法院實踐已久,從先行調解更進一步邁向調解前置也被提上立法日程。
調解之所以能夠在第三方糾紛解決機制中處于優先位置,不僅僅是因為其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價值特性,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其具有司法無法提供的目的價值,即從尊重當事人的主體性地位出發,協商對話,合作共贏,修復關系,實現社會自治、和諧與穩定。在此意義上,調解優先不僅契合中國社會主流文化的價值觀、道德觀以及追求和諧的社會目標,更具有跨越國界的意義。同時,調解無論是對民間糾紛解決,還是政治協商民主,乃至世界和平的國際關系處理,都具有重要的實用理性價值,體現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社會治理規律的科學把握。
調解這樣一種具有包容性的柔性機制根植于人類社會的深刻價值觀,應該推廣成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優先方式。主權國家之間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宗教等情況千差萬別,嚴格依法裁斷的相互承認性會大大降低。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是《聯合國憲章》確立的基本原則,在國際民商事爭議解決領域,聯合國大會2018年批準通過的《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具有堪比《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劃時代意義,標志著“調解全球化”的到來,彰顯了調解在解決國際商事爭議上的獨特價值;在國際公法領域,2022年,中國與20多個國家簽署《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共同協商在香港籌備建立“國際調解院”這一常設多邊政府間國際組織,填補了國際爭端解決體系中常設調解機構闕如的現狀。在單邊主義、冷戰思維抬頭的國際局勢下,這對于維護多邊主義、和平包容的全球治理體系具有重要意義。調解優先不僅是為了讓一國人民生活更美好,更是為了“讓世界更美好”。
(二)調解優先應當成為新時代法律人的必備思維
調解不同于仲裁與訴訟的最大區別在于,調解是一種賦權當事人的工具。美國法學家富勒也曾指出,調解的中心特征是令當事人重新認識彼此的能力,且該能力并不是將法律強加給當事人,而是幫助他們獲得對彼此關系和對對方態度的嶄新認識。基于此,筆者將調解與訴訟的思維差異概括如下:調解所打造的是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共同體,而訴訟所關注的是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對抗性;調解所堅持的是一種“做大蛋糕”的動態利益觀,訴訟所恪守的是公平“切分蛋糕”的靜態利益觀;調解所倡導的是一種“向前看”的綜合式思維,訴訟所遵循的是一種“向后看”的切片式思維。若將解紛與治病進行比較,生動地講,判決如西醫,哪里病切割哪里,是非如黑白,查明事實,追究責任;調解如中醫,講究調和,頭痛未必醫頭,而在于探求病痛的根源及其根本解決。
實踐證明,調解與仲裁、訴訟等第三方糾紛解決機制的程序結合已經成為行之有效的實踐機制。在民事審判中,“調解優先,調判結合”成為踐行“能動司法”理念,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統一的重要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提出:“要緊緊圍繞‘案結事了’目標,正確處理好調解與裁判這兩種審判方式的關系。在處理案件過程中,首先要考慮用調解方式處理;要做到調解與裁判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不論是調解還是裁判,都必須立足于有效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定分止爭,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在民商事仲裁中,我國《仲裁法》確立的“調解先行”原則使得仲裁程序中的調解在糾紛解決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每年近30%以上仲裁案件以調解、和解方式解決,而這樣一種“仲調結合”的法律文化正在向世界其他地方擴張。
當前,在我國落實“調解優先”最為迫切的任務是引導律師轉變思維方式,律師對調解的認知轉變是調解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西方ADR機制之所以能夠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律師群體從訴訟代理人向職業調解人的思維轉變。2010年,筆者在美國馬薩諸塞州訪學時曾觀察到,律師負有義務就調解的合適性向當事人提供建議;在我國香港地區,如果律師在處理案件時不了解或不考慮是否適宜調解,屬于違背職業操守。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自2017年開始已經試點律師調解制度,并且在相關改革意見中提出“推動建立律師接受委托代理時告知當事人選擇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的機制”。但客觀而言,當前我國律師職業群體從整體上尚未充分意識到調解業務的重要性,實踐中仍有很大完善發展空間。筆者認為,破解這一困境的關鍵在于要推進律師調解的市場化改革,讓調解符合當事人和律師的整體利益需求,充分調動律師開展調解的積極性,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統一、雙提升。
同時,我國高校法學院的教育也亟待轉變法律人才培養理念,從比較法視野來看,西方自ADR運動興起以來,無論是英美還是歐陸法學院都在法律專業技能教育之外,普遍重視調解等非訴課程教育改革,培養學生的調解能力以及協商意識。為了適應新時代糾紛解決需求,培養法科學生通過調解幫助當事人解決糾紛的意識和能力,我國法學教育應當加強調解課程的講授與訓練,為推進調解職業化建設儲備人才。同時,應當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的調解學知識體系,從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三個維度繁榮調解學科發展。
(三)調解知識應當成為新時代人民群眾的尋常學問
法學家們普遍認為,法律人具有獨特的思維方式,包含著一整套復雜的概念體系、價值體系、邏輯推理方式和一系列涉及權利義務和責任的分配體系。“法律是一門藝術,在一個人能夠獲得對它的認知之前,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這一出自英國大法官柯克之口的名言常被我國法律人津津樂道,并據此認為,解決糾紛只有自然理性是不行的,還須具有法律人的專業理性,由此在法律人與普通人之間豎起一道高高的法律專業高墻。然而,這樣的立場和思維容易使法律人過于關注自身利益,而法律人要贏得社會信任,就必須如有學者所言,反思乃至必要時要挑戰我們的職業現狀,對我們的知識、職業以及作為利益集團保持足夠的警醒。
立足以人民為中心重估“調解優先”,就是要讓調解知識“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人民群眾聽得懂、說得清、用得上的生存智慧。這意味著我國調解必須汲取人民司法發展道路的歷史經驗,堅持大眾化和職業化“兩條腿走路”,“陽春白雪”的專業化職業化調解旨在應對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復雜解紛需求,“下里巴人”的大眾化基礎性調解旨在回應不同地區間法治發展情況不同的基層解紛需求。《人民調解法》并未將人民調解員的準入資格限定為法律人,而是“公道正派、熱心人民調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識的成年公民”。面對調解這樣一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法治實踐,以所謂高門檻“法律人思維”而自傲的法律人應當放下精英主義的“傲慢與偏見”,因為“調解人思維”并非法律人的專屬,每一位成年公民在理想層面都可能成為調解人。“調解人思維”的制高點不是法律,而是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在此種意義上而言,調解是一門真正屬于人民、惠及人民的學問。法律人所應做的是要將理性平和、寬容協商解決矛盾糾紛的調解法治意識和相互尊重的權利義務觀念植入社會,讓人民群眾掌握調解并能夠從中受益,讓調解成為社會大眾解決矛盾糾紛的自發主觀性選擇。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甚至不應僅停留在大學法學院開設調解課程,應考慮從中小學開始面向全社會普及傳播調解文化,使調解理念厚植民心,調解文化賡續發展,以調解價值最大化、最優化實現法治建設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