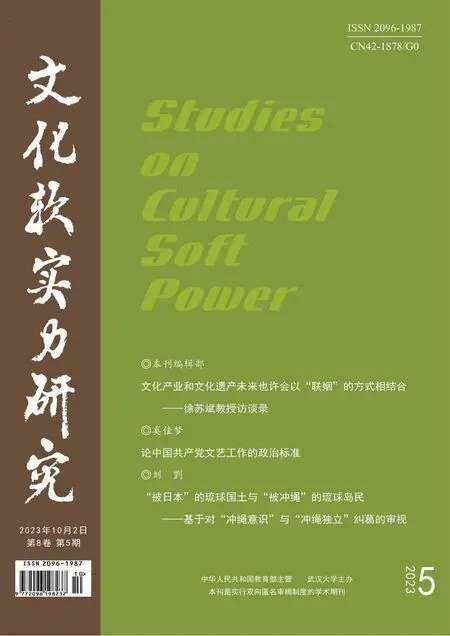以洪堡特語言哲學試析清代語言哲學轉向
李 帆 段滿福
一、 歷史背景
(一)哲學語境下的道學
清學的產生, 是一定歷史背景下的反思, 要了解清學, 有必要了解其產生的背景。 宋明時期的道學作為清學的歷史背景, 在分析清學的話題里必定會涉及。
宋明時期, 理學和心學被統稱為道學。 道學作為宋明時期的顯學, 有著完整且獨具特色的理論構架, 以儒學作為核心, 融入佛、 老的智慧, 在本體論與心性論上有極高的成就。 宋明道學因此常被看作典型的哲學理論, 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后的哲學高峰。
哲學這一個概念進入東方漢字文化圈早期, 一度被稱為“理學”, 西方哲學被稱為“西方理學”。當時, 在大部分學者眼中, 哲學所提出的問題、 解決的疑難、 對社會的影響, 和宋明理學非常相似,所以稱哲學為“理學”。 隨著時間推移, 學者對哲學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發覺“理學”不足以概括哲學所囊括的內容, 便又從浩瀚的漢字世界中, 找到“悊”字來表示這門學問, 自此才有了使用至今的“哲學”。
哲學與宋明道學的歷史淵源, 似乎早已注定道學是中國思想上最“哲學”的哲學。 如李巍教授在?清代哲學史: 基于“話語譜系”的新書寫?中對道學哲學地位總結的那樣, 以“概念譜系”來看, 宋明時代的思想最符合近代學者對哲學作為系統性、 體系性思想的認知[1]。
(二)基于經典的道學
道學思想的根基, 同中國歷史上其它朝代的思想根基一致, 是由經典而來的, 道學的哲學性也源于經典。 對于經典, 大抵有兩種態度: 訓詁詮釋與義理闡釋, 道學主要表現在義理闡釋, 通過經典來闡發思想、 架構體系、 形成系統。
對于義理的闡釋的重視, 同道學的形成背景有關。 道學產生的時代背景, 是漢代以經學為主的思想路徑傳承到唐代, 訓詁考證大肆發展, 以至于產生亂象。 宋學在這樣的現實面前, 有意地選擇了一條與漢學不同的思想路徑, 重義理闡釋、 輕訓詁詮釋。 基于經典的發展, 如果只是空談易理的部分, 就像是無本之木, 很難存活。 所以在道學沒有走向衰敗的時候, 有部分相關訓詁學存在的。?北溪字義?就是在道學發展過程中, 為了推進理學思想體系的建構, 所作的訓詁學讀本。 陳淳此書,強調概念間的聯系, 考證字義的目的在于闡發義理, 被當時道學家作為解讀?四書章句集注?的階梯[2]。 除陳淳的?北溪字義?外, 朱子的?訓蒙絕句?和程端蒙的?性理字訓?, 都是典型的道學家關于訓詁詮釋的作品。
在道學發展前中期, 基于經典解讀的必然性道路, 義理是重點, 訓詁因為歷史問題而邊緣化。并不是完全沒有訓詁、 考證的價值, 僅僅是對于經典解讀有所側重。
(三)宋學后期的空談現象
隨著道學的大成和道學影響的擴大, 尤其是理學成為當時學者幾近狂熱的信仰, 道學的問題逐漸顯露, 衰敗也隨之而來。 宋學的衰敗顯示為空談, 再將空談回歸文獻, 試圖托古取證, 所造成的思想亂像。
在宋學后期, 大肆發展“心即理”的主觀性一面, 將義理的闡發完全變為主觀思想的單一輸出,極端強調人的觀念表達。 這種主觀表達若是嚴謹的自我體系認知, 倒也無可厚非, 問題在于宋學的主觀表達一試圖托古自證, 二即將天理人欲嚴重的對立起來, 破壞本有的道德體系、 義理體系。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評注宋學前后的發展, 用了三個字: 悍、 黨和肆[3], 明末宋學就是“肆”, 這一個評價足以窺見宋學末期的學術狀況。
以私欲解經、 空言天理人性、 臆斷經典……, 宋學空談的現象持續到清, 清學者惠棟認為宋學空談是“不好古, 而好臆說”。 惠棟一方面認可宋學心性論的部分, 贊嘆其直接孔孟; 一方面主張古訓不可改, 經學不可廢。 惠棟從主觀意義上講, 是繼續宋學路線, 試圖通過扎實訓詁詮釋, 改變宋學“深而無本”的狀態, 從客觀上, 惠棟重訓詁的態度顯示著宋學向清學的轉向。
二、 清學
(一)對宋學的繼承與反叛
發展到清代, 宋學依然在一段時間占據學術的重要位置, 只是此時的理學不復宋明時的光輝,只留下空洞的臆斷, 思想成果幾近于無, 反倒產生了不少問題。 宋學后期引發的問題, 波及到學術、政治、 社會多個方面, 在空談義理、 臆想經典的亂象下, 以訓詁詮釋作為為學基本的清學產生了。
清學在學術上主張訓詁詮釋, 以經學史的視域看, 是清代古文經學的再一次興起。 古文經學重興是反宋學的表象, 本質上, 因為經歷宋學, 古文經學以回歸文本為目標的訓詁詮釋, 不能完全符合清學的為學目標。 作為清學的構建者, 戴震試圖通過訓詁來達到義理, 構建起一個以考證為基礎的義理闡發體系。 換言之, 以戴震為代表的清學大家, 實質上并沒有對于宋學的體系進行反叛, 而是對宋學構建體系的語詞進行重新的思考。 因為清學對宋學的反叛主要體現在語詞問題上, 吳根友教授將其稱為“后理學”[4]。 學術之外, 清學試圖通過經典來對時代問題作出回應, 尤其重視對政治的影響, 清學治用的思想, 是其對宋學反叛與繼承的結果。
清學至少在構建之初, 是存異于漢古文經學和宋學的新學派, 是試圖以訓詁詮釋為路徑, 以義理闡釋為目標的學派。 清學末期發展較前期而言, 更背離理學, 為了完全脫離理學的影響, 主張將“理”棄置不用, 此時的反叛一方面體現出宋學的影響依舊很大, 另一方面體現出學者的根本認識出現問題, 需要同清學前中期做出界別, 萬不能以清學末期特色批判清學。
(二)清學的特色
清代的學問, 最為關鍵的部分, 若過于訓詁詮釋學, 清學的特色, 常以“乾嘉學派”作為代表,說明清學在訓詁詮釋上功夫踏實、 深厚, 治學嚴謹、 細膩, 這是對清學最基本的認知。 學術的特色廣為人知, 且不贅述, 以下從學術根本需求和學者轉向進行分析。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清學特色? 同清學的學術轉變有關。 錢穆先生將清學的特色性轉變概述為從“尊德性”到“道問學”的轉變, 認為這個轉變是宋學到清學內在邏輯的轉變[5]1-20。 從錢穆先生的概述, 可以得出訓詁之學的興盛的原因, 就是“道問學”的需求。 因為“道問學”, 所以考辨成為學者主要的工作, 特點從抽象主觀的道德判斷轉變為客觀求真的考證治學。
若細致考察, 清學“道問學”的轉變可以劃分為不同時間段。 前期的“道問學”是以義理為目標的考證, 后期則是表現為“為訓詁而訓詁”的特色。 受能力所限, 前后期的差異且不論述, 僅以貫穿清學的“道問學”思路來說明。 以“道問學”為需求, 決定了清學的學術特色, 同時也影響了學者的認知。清學產生的人物近似當今的“學者”, 不再以儒、 道、 釋某家作為思想出發點, 是以“學”作為出發點的學術研究, 這是清學家在人的層面上的特點。
清學的特色以“道問學”轉向為中心, 產生了學問的特色, 踏實嚴謹的訓詁詮釋學; 產生了學者的特色, 以學問本身為主的“學者”認知。 這些特色使清學在語言學、 歷史學、 博物考證等方面倍受重視, 也使清學在哲學話語體系中常受詬病。
(三)哲學語境下的清學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 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 這個時期的哲學思想發展豐富多樣, 對中國傳統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清初思想的傳承與變革
明亡清興之際, 由于戰亂和政治動蕩, 大量文人士人紛紛背井離鄉, 尋求出路。 清初的思想發展在傳承明代儒家思想的基礎上, 也受到了其他學派的影響。 其中, 王夫之提出的“格物致知”思想,重新強調了實踐與知識的關系;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批判傳統儒家經典, 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對后來的思想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古文運動與經世濟民
清朝立國之后, 樸學興起并逐漸成為了新的儒學主流思想。 在清代初期, 盡管宋明新儒學沒有隨著明朝的滅亡而完全消失, 但是對于理學的批判非常嚴厲, 然而社會上的殿堂理學、 館閣理學和鄉間草野理學仍然存在。 清代前、 中期的眾多思想家, 如顧炎武、 黃宗羲、 王夫之、 顏元等, 以及戴震、 章學誠、 阮元和龔自珍等后來的思想家, 不僅是知識淵博的學者, 也是有著獨立哲學思想體系的哲學家[6]。 以考據作為核心學術目的的樸學思想對宋明理學進行了批判繼承, 對更早期的漢儒經學進行考證, 樸學又被稱為“乾嘉學派”, 戴震、 惠棟等儒學學者都是重要的清代樸學大師, 樸學內部又大體分為吳派、 皖派等派別。 主流的乾嘉學派以東漢古文經學作為主要的考據對象, 而樸學的另一支系常州學派, 則以西漢今文經學作為主要的考證對象。 由于局限于考據, 樸學對于儒學體系的革新較為有限, 但對于整合儒學的思想體系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乾隆皇帝即位后, 進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改革, 其中包括推行古文運動。 這一運動以研究古代文獻為主要內容, 影響了當時的哲學思想。 同時, 乾隆皇帝也倡導了“經世致用”的治國理念, 對中國清代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經世濟民的思想與實際問題相結合, 提倡實用主義與現實主義,為后來的思想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3.西學東漸與思想啟蒙
19 世紀中葉, 由于西方列強的侵略和中國的落后, 中國的思想界開始重視西方的學問。 此時,大量的西方哲學思想開始傳入中國, 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關注和思考。 其中, 王夫之和嚴復是最早接觸并傳播西方思想的學者, 他們在思想上積極融合中西學問, 開啟了中國清代思想啟蒙運動。
中國清代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多樣而豐富。 從清初思想的傳承與變革, 到古文運動與經世濟民的時期, 再到西學東漸與思想啟蒙, 最終達到維新思潮與百年變革的階段, 中國清代的哲學思想在傳統的基礎上與外來文化的交融下, 逐步呈現出自己獨特的面貌。 這一時期的思想發展, 無疑對中國近代的思想進步和社會變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用哲學的眼光看待清學, 主流評價是: 清學少有哲學性, 或者沒有哲學性。 少部分學者認為清學有哲學發展, 也會加一些限定詞, 表述清學哲學發展之緩慢。 清學的長處在于考證、 訓詁、 詮釋,這些內容似乎是不符合哲學所具有的思辨特色。
回歸到哲學認知問題上: 前文提到以“概念譜系”作為哲學要求, 自然以宋學為上, 以清學為末。清學作為宋學的反叛, 拿“概念譜系”分析清學, 多少存在問題。 相比拿舊譜系套新思想形態, 李巍教授提出“話語譜系”的清學哲學思路。 一如本譯做“理學”的哲學, 隨著發展發現“理學”無法涵蓋所有哲學, 拿“概念譜系”認識所有哲學, 也無法準確認識所有哲學的價值。
“話語譜系”是對吳根友教授所著?清代哲學史?一書的清學哲學新視角的提煉。 吳根友教授發表于?孔子研究?的論文中, 將新視角概括為清學的人文實證主義[7]。 話語譜系和人文實證主義, 都顯示著清學有從訓詁詮釋到義理闡釋的哲學思考, 具備一定的語言哲學的意味。
三、 語言哲學之路
(一)語言哲學
語言哲學是當代西方哲學中新興的一個概念, 是現代西方哲學界中影響最大、 成果最為豐厚的一個哲學流派。 語言作為獨立的哲學流派, 主要目的在于以哲學的方法來分析語言符號, 挖掘語詞背后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進行話語結構、 語意與語法的研究。
語言哲學家將哲學思考歸根于語詞上, 認為語言是哲學的源頭, 也是哲學活動的必備工具。 并且將語言哲學的源頭追根到柏拉圖, 認為早在希臘便有相關語言的哲學思考。 語言哲學的研究內容,大致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句法學研究, 討論語法及語法性產生的問題; 二是語義學, 研究符號及其所代表的意味; 三是語用學, 相較前二者, 語用學包涵范圍更廣, 主要研究語句的運用[8]。 語言哲學將“什么是正義”的問題轉向到“正義是什么意義”, 將語言學研究深入到哲學的層面, 對比語言學來說, 更重視意義理論的問題。 近現代語言哲學的興起, 引發了許多關注, 因為語言哲學的影響,二十世紀也被稱為“語言轉向期”。
語言哲學作為當代西方哲學中的重要流派, 內部因研究方向和認識分為不同的學派。 并且因為語言哲學仍處于一個在發展的階段, 所以在學派的判斷與研究范圍界定方面, 至今沒有可以被所有學者公認的標準。 基于事實與個人的能力, 在清學語言哲學轉向的認識上, 主要依靠的語言哲學體系是十九世紀德國學者威廉?馮?洪堡特的語言哲學體系。
(二)洪堡特語言哲學思想
洪堡特是十九世紀德國著名的教育家、 政治家、 語言學家和語言哲學家, 被稱為“普通語言學奠基者”。 我國大約從上世紀的80 年代開始, 對洪堡特的政治、 教育、 語言哲學等思想進行研究。 根據2017 年的相關統計, 我國對于洪堡特的研究約有149 篇, 其中關于洪堡特語言哲學思想的論文有78 篇, 經歷幾年的發展, 當下可見的洪堡特語言哲學相關論文數量有了較大增長[9]。 只是在研究具體內容上, 依然有很大一部分論文以“洪堡特語言哲學思想和漢語研究關系”和“洪堡特語用分析”作為中心。
研究洪堡特語言哲學和漢語哲學的關系問題, 主要是基于洪堡特語言哲學所強調的共通性與特殊性, 對漢語哲學進行反思。 洪堡特認為: “在語言中, 個性化和普遍性協調得如此美妙, 以至我們可以認為下面兩種說法同樣正確: 一方面, 整個人類只有一種語言, 另一方面, 每個人都擁有一種特殊的語言。”語言同民族精神息息相關, 因為民族精神不同, 所以語言和語法上有著很大的差異,這是語言個性化的一面; 語言具有普遍性是由人類本身所決定的, 人類的普遍性決定了語言的普遍性。 當前我國的語言哲學研究以普遍性作為重點, 在面臨西方語言哲學的挑戰時, 往往不能做出及時有力的回應, 勞思光批評中國哲學并不重視語言問題, 無法根本解決語言哲學提出的問題[10]。
洪堡特語用分析應用, 與洪堡特語言世界觀有關, 這是其語言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洪堡特的“語言世界觀”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體現出來: 一是語言與思維的關系; 二是語言與民族精神的相互作用, 兩者關系密切, 相互補充[11]。 民族的語言和其民族思維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一個民族的語言就是他們精神的體現, 同樣, 一個民族精神的體現就是他們的語言。 人們的世界觀是通過語言形成的, 使用不同的語言代表著不同民族其實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
洪堡特的語言哲學, 強調用語言的方式理解世界看待世界, 強調語言所形成的不同世界觀。 同時洪堡特十分重視“詞”, 從世界觀的角度挖掘“詞”的內在價值。 以洪堡特的語言哲學作為切入點,中國哲學中訓詁的成分本身就具有了哲學的意義。
(三)訓詁詮釋
就洪堡特語言哲學來說, 詞語有特殊的存在意義: 詞語是一種人們對生活事物或思想事物的命名, 是人們思想的結果, 也是世界觀的展現、 世界的主觀認識。
“訓詁”, 又稱“訓故”“故訓”“古訓”“解故”“解詁”, 是一門研究古代文獻中詞語的詞義、 漢語語言學和語文學的綜合性學科。 它的核心概念可以用通俗的語言解釋為“訓”(解釋)和“詁”(研究古代語言)的結合。 “訓詁”這一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漢時期, 當時魯國的毛亨編寫了一本名為?詩故訓傳?的書, 其中包含了三種古文注解方法, 即“詁”“訓” 和“傳”。 這些方法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解釋和理解?詩經?等古代文獻。 “訓詁”這一術語最早出現在漢朝的典籍中, 它從語言的角度出發, 著重研究古代文獻的文字和語法, 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這些古典文獻。 這為后來訓詁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成為中國古代文獻研究的重要方法。
訓詁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包括古代文獻中的詞義、 語法、 修辭等語言現象, 尤其是漢魏以前古書中的詞義。 這一學科的奠基著作可以追溯到戰國末期的?爾雅?。 在宋代, 訓詁學經歷了革新, 但到了元明時期, 呈現出逐漸衰頹的趨勢。 清朝時期, 訓詁學得到了顯著發展, 形成了乾嘉學派, 其中段玉裁、 王念孫和王引等學者為該領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清朝末年, 受到西方語言理論啟發的章太炎和黃季剛將原先的“小學”領域更名為“語言文字之學”, 標志著語言文字學學科觀念的初現。 章太炎被認為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奠基人之一, 他編著了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專著?文始?, 開創了語源學領域的新局面。
黃侃進一步發展了訓詁學的現代觀念, 他將其定義為研究語言解釋語言的科學, 不僅限于古代文獻中詞義的探討, 還包括對現代方言口語的詞義分析。 他的定義拓展了訓詁學的研究范圍, 使其不僅僅局限于文字解釋, 還包括對語言在社會學、 文化學等多個領域中的運用。 不同的訓詁學派別如“古漢語詞義學派”“綜合學派”“全面解釋學派”等, 雖然強調的側重點不同, 但都強調訓詁學的綜合性和廣泛性, 使其成為深入探討語言演變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工具。
訓詁學是中國哲學的內在需求, 訓詁字詞作為闡釋的開端, 以文字作為實在的對象, 從實在對象著手, 追尋考證文字、 詞語、 語法。 周大璞在?訓詁學要略?中明確指出, 訓詁學的研究核心在于詞義和詞義系統, 旨在揭示語義發展和演變的規律。 新訓詁學則是對傳統訓詁學的拓展, 強調語言研究的綜合性, 使其不僅僅是古代文獻的詞義解釋, 更涉及到社會學和文化學等多個領域, 為更全面地理解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 訓詁之學是以詮釋為目的的學問, 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 首先為訓詁學做了定義: “詁者, 古也, 古今異言, 通之使人知也。 訓者, 道也, 道物之貌, 以告人也”[12], 之后為訓詁學的治學道路進行了概括: “然則詁訓者, 通古今之異辭, 辨物之形貌, 則解釋之義盡歸于此”[12]。
劉潤清先生在?西方語言學流派?一書中, 以“只要講出一個詞, 就等于決定了表達思維過程中的整個語言”[13]來說明, 在洪堡特語言哲學中, 詞反映思維的特點。 訓詁詮釋字詞, 詞反映思維, 這是從概念意義上對訓詁學所具有的語言哲學性質進行的粗淺說明。 如果將話題僅停留在這里, 那涉及的話題將突顯在“洪堡特語言哲學思想和漢語研究關系”這一問題上, 清學本身并沒有特殊性, 不足以稱“清學的語言學轉向”。
戴震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中有: “經之至者道也, 所以明道者其詞也, 所以成詞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詞, 由詞以通其道, 必有漸。”[14]這是具有語言哲學氣質的明確論述, 但并不能直接說明清學具有語言哲學氣質。 清學的語言哲學轉向, 是重訓詁的實學學風, 清人對語言時間性的深刻認識, 以及經訓詁認識世界諸多因素相合才有的轉向。
四、 清學語言哲學轉向
(一)語言時間性
洪堡特提出了一種語言學觀點, 即語言是時空的產物, 這一觀點被稱為“洪堡特語言”的時間性論述。 根據洪堡特的觀點, 語言并非靜止的工具或者規范, 而是不斷發展、 變化的動態體系。 這個觀點主要包括以下兩個要點: 一是語言的歷史性, 即語言不僅反映了社會和文化, 而且是歷史的產物。 語言的變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產物, 它受到人們生活、 思維和經驗的影響。 這意味著語言不是靜態的, 而是在不斷發展和演變中。 二是語言的相對性, 即每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觀念結構和方式來表達世界。 每種語言都塑造了說話者的思維方式, 因此, 不同語言的說話者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看待世界。 這些思想深刻影響了后來語言學和文化研究的發展, 強調了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以及語言變化的歷史維度。
而語言的時間性特征, 在洪堡特語言哲學中突顯為對語言創造性的認識: “語言本身則是智能創造力量的產品”, 語言本身是一種精神的不自覺流射, 是一種從未靜止的存在。 洪堡特語言哲學主張語言是一種類似有機體的存在, 會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創造性是語言的根本特性。
語言的時間性是清學由戴震以來, 持續至今的認識。 戴震對宮室、 器具、 山川等等具體存在的考察, 也是基于語言時間性認識之上的, 這也是戴震對宋學的批判點之一: 沒有明確的對語詞對象的具體認識, 閱讀經典文本時, 無法理解經典文本中所包含的內容。 在器物層面進行區別, 在形而上的概念層面同樣進行一個時間觀上的考察。 比如“理”一字, 從造字開始論述, 再到宋學中“理”的含義, 對兩者進行繼承, 以清學的視角對“理”進行了說明。
清學繼承傳統經學的訓詁內容, 同時認識到自身與傳統訓詁之間, 必然有一定改變。 漢唐訓詁去古未遠, 清則不同, 更需要注意歷史變遷帶來的改變。 語言時間性, 是清學治學的潛在背景, 因為語言不是一成不變的存在, 所以從歷史的發展看待字詞, 成為了清學訓詁有別于漢唐訓詁的一點。清學或多或少有“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認識, 同時又以歷史整體看待訓詁, 在復古考證的同時, 認識到語言的創造性, 尊重語言時間上的不可逆性質。
清學以訓詁考察語言的時間性, 又代表著清學對言意問題的認識。
(二)言可盡意: 由訓詁體認義理
言意之辨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 爭論已久, 每個時代對言意關系的認識, 直接影響這一時代的治學理念。 清學對言意問題的答案, 是言可盡意。
清學言意的認知源于對宋學的批判。 戴震指出, 若“理”本身作為“完全自足”的存在, 后天知識活動的展開與否都不妨礙“理”本身的存在。 由此, 在對待學問的態度上, 必然走向的是“無待于學”乃至“廢學”的邏輯結論[15], 清學家將宋學的治學道路評價為偏離認識本質的治學道路。 清學的治學是: “故訓明則古經明, 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 而我心之所同然者, 乃因之而明”[15], 訓詁明經明理的實現可能, 是因為相信經典本身可以包含圣人的義理, 也相信他者可以通過語言理解圣人的義理。
在洪堡特語言哲學中, 語言同思維、 同世界觀聯系, 穩定有規律的思維與世界觀可以限制語言的變化, 避免因為變化而進入虛妄。 “語言和智力特性從深處的心靈相互協調地共同產生, 因為在一個已經形成的語言中, 人們使用最合理和最直觀的詞匯來表達他們對世界的看法。 這些詞匯以最純粹的方式重新表達了個體的世界觀, 并依靠其精致的結構, 能夠高度靈活地參與各種思維的組合。只要這種語言仍然保持其核心原則, 它就必定在每個人身上喚醒同一方向的共同精神力量。”所以語言可以傳承思維, 即可以傳遞義理。
(三)語言民族性
語言作為民族思維的形成基點, 是代代傳承的民族智慧, 語言文字可以影響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也伴隨著時代作用于語言。 清學的語言學轉向從某些角度分析, 也是民族認識的自覺轉向。
“中國”這個概念就體現出了語言與精神的雙向作用。 在宋前, 學者文人以“天下”來概括自然、政治、 文化上的可統范圍; 到宋時, 則轉向“中國”即“中央之國”, 體現了從宋前到宋后, 文人墨客對于民族的客觀認識。 到了清朝, 以漢字為基礎的訓詁詮釋學, 在語言哲學中, 可以看作民族認同的標志, 也是民族自我保存的要求。 洪堡特語言哲學上的“民族”概念, 是以語言來劃分的: “民族的定義應當直接通過語言給出: 民族, 也即一個以確定的方式構成語言的人類群體”。 就收集到的數據而言, 清代學者并沒有明確地將語言同民族問題共同討論, 僅從訓詁之學的興盛來看, 間接地顯現著語言哲學民族性問題。
洪堡特在語言和民族問題上有著深刻的見解, 他認為語言是民族的獨特財富, 是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他強調了進行語言研究時需要將其置于更廣泛的背景下, 進行系統和動態的研究, 而不是孤立地研究語言。 這一方法開創了一種獨特的語言研究道路, 將具體的比較分析與哲學綜觀相結合。 這種方法使洪堡特能夠深入審視不同民族的語言, 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洪堡特的核心思想是將語言視為反映特定文化和民族特征的工具, 而不是孤立的符號系統。 他堅信語言是人類精神力量的外在顯現, 各種語言和民族代表了不同程度、 不同方式的自我表達[16]。只要一個民族的精神以生動、 獨特的方式持續熠熠生輝并滲透于其語言, 那么這門語言就會得以不斷演變、 日益豐富。 與此同時, 語言的蓬勃發展也會為民族精神注入動力, 產生深遠影響。 這種相互影響和共同塑造使得語言成為文化傳承的有力工具, 同時也彰顯了精神與語言之間密不可分的紐帶。 換句話說, 語言是精神活動的必要工具, 也是精神活動所依賴的軌道[17]。
在他的學術生涯早期, 他并沒有將語言和民族問題作為主要研究方向。 直到1806 年, 他才開始深入研究語言, 并開始深入探討語言在民族生活中的作用。 他逐漸認識到一個民族的各種地理、 政治、 文化、 風俗、 制度等因素都可能發生變化, 并且這些因素與語言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關系。 這一領悟對于他后來的民族學和語言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語言是一個民族無法舍棄的核心元素。 他將語言比作一個民族生存的“呼吸”和“靈魂”, 強調了語言與民族之間的緊密關系。 然而, 洪堡特也認識到, 語言比個人特性和民族特性更加復雜和難以理解。 他將語言形象地類比為籠罩在山巔的云彩, 具有既具體又抽象的特質, 因此需要研究者站在哲學思辨的高度來進行深入分析。 他提出了一句著名的格言, 即“一個國家的語言即是這個國家的精神, 而這個國家的精神也即是這個國家的語言”。 他強調了語言與民族認同之間的緊密聯系。 這一思想對后世的語言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促使研究者將語言置于更廣泛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 以更全面地理解語言的演變和功能[18]。
“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 二者的同一程度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象。”這同樣是當今面對西方語言哲學挑戰時, 學者日趨重視漢語、 強調訓詁的原因之一, 也是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挖掘清學價值的原因之一。 本文僅以洪堡特語言哲學理論, 試析清學語言哲學認識如何可能。 清學的語言哲學認識強調漢語本身的獨立性, 最好的方式是從清學本身出發, 構架屬于中國哲學的語言哲學方向而不依托其他的哲學體系, 這當然需要學界諸君一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