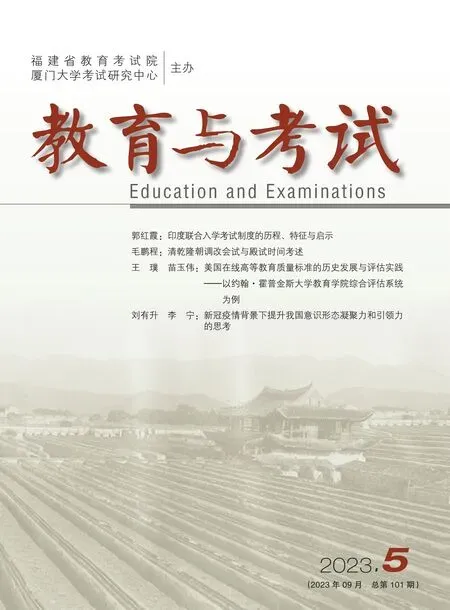楊萬里科舉觀芻議
楊巴金
科舉觀是指人們對科舉制度的認識與評價,包括個人對科舉考試的情感、態度與行為的審視。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南宋大詩人。他曾兩次參加禮部試,第一次于紹興二十一年(1151)落第,第二次于紹興二十四年(1154)中進士,亦是科舉制度的受益者。后來,他兩次兼任省試考官,多次參與地方解試命題,對科舉制度始終持支持態度,也有一些審視與思考。深入分析楊萬里的科舉觀,可以展示宋人對科舉考試的情感、態度和行為,以期對評價科舉制度和促進科舉學研究有參考作用。
一、楊萬里科舉態度分析
隋唐以后,儒家“學而優則仕”“學也祿在其中矣”等積極入世思想對讀書人有著強大的吸引力。翻檢楊萬里《誠齋集》,其中《千慮策》等詩文中有不少關于科舉制度看法的表述,他作為儒家學派衛道者之一,對科舉考試的態度始終是支持的。
(一)其本人態度
楊萬里24歲以《書經》舉于鄉,得解送禮部參加省試的名額。25歲應試禮部,名落孫山,28歲中進士第。應當說,耕讀傳家、詩書繼世是楊萬里家族的優良傳統。據光緒版《忠節楊氏總譜》載,其曾祖父楊希開,雖然未中舉入仕,卻個人出資興辦學堂,聘請兩位先生來教育本家族子弟,由彭恕先生負責訓導年長者,由曾姓先生負責訓導年幼者。如果族人生活有困難,他就代繳學費,甚至贈送衣食,促使學子成才,“同族中奉公(楊)存、梧州推官(楊)文明皆貧,公為之代束修,給衣食以玉成之”①。父親楊芾雖未獲得功名,卻是家鄉附近有名的教書先生,且十分重視對少年楊萬里的教育。楊芾精通《易經》,常忍著饑寒購買書籍,積得十年,藏書上千卷,且常指著藏書對楊萬里說:“是圣賢之心具焉,汝盍懋之!”[1]
在家族的影響下,楊萬里自幼勤奮讀書,廣師博學,說:“予為童子時,從先君宦學四方”[2]2083。他14歲拜鄉先生、阜田人高守道為師,17歲拜廬陵名儒王庭珪為師,21歲又拜劉安世、劉廷直為師,27歲再拜劉才卲為師,為兒子以后參加科舉考試打下堅實基礎。淳熙五年(1178)九月,時任常州知州的楊萬里題作《夜雨》長詩說:憶年十四五,讀書松下齋。寒夜耿難曉,孤吟悄無儕。蟲語一燈寂,鬼啼萬山哀。雨聲正如此,壯心滴不灰[3]143。那時楊萬里52歲,且攜家人待在異地他鄉,可以想象,他閑暇時教子讀書,又因秋夜之雨而“萬感集老懷”,于是寫詩回憶年少時苦讀詩書的情景,表達自己即使生活困頓,也要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思想情感,最終達到儒家“修身、齊家、治國,以平天下”之目標,其唯一實現的途徑,則是科舉入仕。
后來,楊萬里作為從科舉狹路沖殺出來的幸運者,給更擅長科舉、曾中博學宏詞科的鄉賢好友周必大回信說:某少也賤且貧,亦頗剽聞文墨足以發身,呆不解事,便欲以身殉文,不遺余力以學之,意何所成?雖成,竟何所用?[2]1046表明他無論是從自己人生價值的實現,還是從家族中興的角度,對科舉制度都有著高度的認同感。
(二)對兒子的勸勉
楊萬里極其重視耕讀傳家和詩書繼世。淳熙七年(1180)正月,楊萬里赴廣州任提舉廣東常平茶鹽,且攜長子楊長孺、次子楊次公隨行歷練。又因二子秋季要參加吉州解試,到達廣州后不久即安排還鄉。在兒子歸途中,他題作《得壽仁、壽俊二子中途家書》3首長詩予以勸勉,其三詩云:我昔如汝長,壯志在四方。集賢給筆札,秉燭促夜裝。平明出門去,振衣不彷徨。先君泫然泣,感我令我傷。先君顧我語,汝行勿斷腸。他日汝養子,此悲會身當。老懷追陳跡,心折涕泗滂[3]212。詩中作者回憶自己年輕赴試時,父親楊芾送別他的情景以及那時的雄心壯志,諄諄教導兒子讀書應試,殷殷鼓勵、舐犢情深躍然紙上。
該年九月,楊萬里又收到家信,得知楊長孺、楊次公因病未參加秋試,于是題作《得壽仁、壽俊二子書,皆以病不及就試,且報來期》詩2首,詩中說:“滿望鵬飛上,誰令馬不前……速來飲官酒,不用一銅錢。”[2]215詩中既有他對參加科舉而走上仕路艱難的感嘆,又有對兒子未能成功通過解試的一份失落,但更多的是對兒子寒窗苦讀以期以后蟾宮折桂的激勵。淳熙四年(1177),長子楊長孺以《書經》舉于鄉。待他出任修職郎、湖南零陵縣主簿時,楊萬里又題《大兒長孺赴零陵簿,示以雜言》詩相贈,教育兒子要珍惜入仕做官的機會,既要愛民如子,更要謙虛謹慎。這些詩文足可印證楊萬里是極力鼓勵兒子們讀書、科考和入仕的。
(三)對親屬的勸勉
楊萬里對近親子弟參加科考有很多勸勉詩文。對岳父羅天文的家族子弟,筆者依據《秀川羅氏族譜》、康熙《廬陵縣志》以及雍正《江西通志》等文獻,撰有《〈誠齋集〉所載岳父羅天文家族科舉人物考》,就其岳父家族涉及科舉入闈情況作過簡要考察,充分印證廬陵世家業儒之盛,彰顯古代吉安“耕讀傳家,詩書繼世”的濃厚氛圍。又如他題作《送安成羅茂忠》詩云:書臺佳士君章孫,句法來自西溪門。向來家住金谷園,珊瑚四尺蠟作薪。床頭黃金已散盡,買書卻鑄文章印。印成一字不療饑,仰天大笑還哦詩。諸老先生總參遍,只欠一瞻晦翁面。晦翁今已作貴人,君從何許去問津?勸君努力戰今舉,來年拜渠為座主。[3]538時慶元六年(1200)七月,因安福縣親屬羅茂忠拐道湴塘村,楊萬里送其參加秋試。詩中既有對羅氏家學的褒揚,更含對其赴試的鼓勵。依據詩意,可知羅氏曾拜朱熹為師,而朱老先生于該年四月去世。
(四)對友人的勸勉
首先是對童子科中舉者的鼓勵。楊萬里除對吉水縣谷村人李如圭題贈《送李童子西歸》外,還有《送蜀士張之源二子維、燾中童子科,西歸》詩:岷山玉樣清,岷水眼樣明。風流文采故應爾,又見張家雙驥子。小兒八歲骨未成,誦書新作鸞鶴聲。大兒十二氣已老,覓句談經人絕倒。豫章七年人得知,駃騠三日世便奇。天生異材能幾許?更飽風霜也未遲。[3]86時乾道七年(1171)秋季,四川人張之源2個兒子張維、張燾中童子科,作者題詩送他倆回鄉。南宋時,童子科雖有賜秘閣讀書、免文解兩種主要的安置方式,較好解決長期存在的“速成”與“善養”之間的矛盾,但是對童子科選才的做法仍多有爭議。從楊萬里的題詩看,他也看到了中舉者專重于誦記方面的選才差欠,但對童子科的選拔模式,仍是堅定的支持,認為此選拔模式能讓更多的優秀童子脫穎而出。
其次對科考失利士子多有勸勉。楊萬里對下第士子總是極力勸勉,鼓勵他們進一步潛心讀書,以期下次考得更好名次。紹熙元年(1190)春末,溫州薛子才因為落榜,作者送他回鄉,特意題作《送薛子才下第,歸永嘉》說:河東鸑鷟志青天,冀北麒麟受玉鞭。二十年前元脫穎,五千人里又遺賢。請君更草凌云賦,老我重看斫桂仙。趁取春風雙鬢綠,收科誰后復誰先?[3]408這是一首落第勸勉詩,從詩中可知,薛子才天資聰穎,志向高遠,卻參加科考20年仍未中舉。楊萬里不僅對其才學持肯定態度,而且說他終有一日會折桂登科。又如他給秀才歐陽清卿的信中說:初為吾友惜于失舉,至是不復惜。學進而身退,與身進而學退,此宜何惜?則子之失有司乎,有司之失子乎?辱書,其詞暇,其意迫,安于貧而勇于道,此某之所愿學者也。而子之心正如此,不知吾心之合于子乎,抑子心之吾合也?[2]1025宋代并無舉人稱謂,歐陽清卿因進士試落第,故仍稱秀才。從這類詩文中,能感受到人們對待落第的不同心境,在楊萬里看來,其實這是朝廷對人才的一種遺落。
二、參與科考命題和充當省試官
(一)主持湖南漕試
紹興三十二年(1162)八月,時任零陵縣丞的楊萬里選派至長沙,擔任湖南漕司主試,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充當科舉考官。漕試是宋代貢舉考試方式之一,始于北宋景祐年間,即針對轉運司類聚本路現任官所牒送隨侍子弟和五服內親戚,以及寓居本路士人、有官文武舉人、宗女夫等而舉行的考試。因轉運司又稱漕司,故名漕試,考試辦法類同于州郡的解試,漕試合格者即可赴省試。漕試結束后,楊氏題詩《考試湖南漕司,南歸值雨》。依據考試結果,錄取四川籍施淵然為漕試魁首。九月,他又送施淵然去參加省試,且題作《送施少才赴南宮》詩送別。
(二)第一次兼任省試考官
乾道八年(1172)春季,時任太常博士的楊萬里兼任省試考官,這是他第一次參與進士試事務。省試結束后,他題有《四月初二日進士唱名,萬里以省試官待罪殿廬,遇林謙之說詩。夜歸,又見林柬,因紀其事》詩:清曉朝帝所,就列復少須。不逢林夫子,于何得故吾?宮云霽猶未,宸風爽亦初。說詩憐新體,信美古則無。將無古人拙,未必今制疏。夜歸辱良訊,送似談笑余。病懷翻不樂,此意從誰舒?短歌紀幽事,老矣復焉如?[3]87省試一般是在春季舉行,又稱春試或春闈。該詩首句交代事由和地點,而作者在參與尚書省禮部試的閑暇時,抽空論詩。那時,朝廷正在舉行進士唱名儀式,作者待罪殿廬,與試館職同事、福建莆田人林光朝一起論詩,然后回家題詩記其事。待罪,系古代官吏供職的謙辭,表明自己隨時準備因失職而被治罪。
(三)第二次兼任省試考官
淳熙十四年(1187)正月,時任吏部尚書左司郎中的楊萬里兼任貢院參詳官,負責復查點檢試卷官所定的試卷等第,這是他第二次參與貢舉事務。他題作《三月二十六日殿試進士,待罪集英殿門》其一詩云:金戺瑤階日月邊,曉風花柳帶霏煙。千官劍佩鳴雙闕,萬國英豪到九天。玉座忽臨黃傘正,御題初出紫衣傳。小臣何幸陪諸老?待罪重來十六年。[3]299該詩還附有后序:“余壬辰春,亦以省試主司待罪。”首句“金戺”一詞,本義是指宮廷臺階旁金黃色斜石,詩中是代指省試主司,表明朝廷正在集英殿舉行進士策試,而作者兩次充當省試考官正好相距16個年頭。楊萬里不久后又題作《四月十七日侍立集英殿,觀進士唱名》詩,表明孝宗皇帝那天親臨集英殿,而殿試官、省試官及宰臣、館職等均入殿侍立,省試入闈者則等候于殿門外,朝廷依次傳唱他們姓名,中舉者接受皇帝賜予的科舉等第,之后便是舉行進士禮宴。
(四)第二次參與解試命題
慶元元年(1195)是楊萬里辭官回鄉的第四年,適逢吉州舉行秋季的解試,且請他參與命題。事后,他題作《擬吉州解試〈秋風楚竹吟〉詩》云:客子正行日,偏逢楚水秋。一風來瑟瑟,萬竹冷修修。吹作清霜骨,聲酣古渡頭。斑林寒更裂,碧節爽還幽。亦復披襟袂,長懷落月愁。少陵詩思苦,送別更冥搜。[3]503可以推想,那時吉州的主官出于楊萬里題詩作賦的崇高威望,于是請他負責第二場考試的命題。
三、對科舉制度的審視
科舉制度是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所謂科舉,就是中國帝制時代設科考試、舉士任官的制度”[4]。雖說楊萬里是科舉考試的受益者,但在參與科舉選士的實踐中,對其功能、標準、組織管理等方面均有一些理性的審視,且極為關注士子的道德修養和實際才能。
(一)對選拔標準的審視
科舉考試是以儒家學說為主,涉及政治和文化的雙重屬性。楊萬里曾作《千慮策》30篇,其中對人才、馭吏、選法、冗官等問題有不少深刻論述。作為一名儒家學說的衛道者,楊萬里總是極力倡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想,目的是為朝廷能選出更多治國安邦的人才,對官吏的清廉也有較好的警誡作用。如《千慮策·人才》開篇說:臣聞:人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疏,取之之途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杰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2]1379科舉考試除有選拔人才的作用外,還有養士和引導文風的功能[5]。楊萬里深刻認識到,人才乃是國家之寶,是朝廷政事之本,選拔人才首先是要把準德才兼備的原則,能不拘一格地選賢任能,而人才的來源,不能僅僅拘囿于科舉考試這一狹隘的途徑。自隋唐以來,科舉制度常是將讀書與做官相聯系,“唯有讀書高”的背后則是對當官的強烈愿望甚至是終生追求,這既不利于朝廷選才,也不利于士子本身成長,所以他主張求才不以細目,而取決于人的使用,能專意于興亡、治亂、經綸之事業。
更關鍵的是,楊萬里也看到科舉制度對士子“奪志”之害。他任常州知州秩滿,回鄉途中路經江西廣豐縣靈鷲禪寺,題詩云: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終夜鳴。流到前溪無半語,在山做得許多聲。[3]185這是一首寓言詩,作者借寫景而引發議論,影射所暗喻的社會世態。如第三四句即是諷刺那些經過科舉而走上仕途的達官顯宦,未入仕時曾有不少“宏論”,待有職有權有勢后,卻是隨波逐流,了無建樹。
楊萬里是南宋積極的主戰派,這與家族傳統、老師教誨所分不開。就家族傳統而言,族叔祖楊邦乂任建康通判時抗金被俘,寧死不降,最后被剖心而死;又如譽為“一日而并得二師”的胡銓,因秦檜賣國而上疏請斬,被貶新洲等。就老師教誨而言,楊萬里拜王庭珪、劉才卲等名士為師,所學內容是什么呢?“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學犯禁之說也。”[2]1304即學習被列為禁學的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人之學說,與那些為追求科舉勝出,或追求仕途晉升,拋棄道德修養,毫無愛國憂民之心的功名利祿之徒形成巨大反差,將愛國、忠貞、勤廉、憂民等視為基本準則。
(二)對考試內容的審視
北宋時,有不少士大夫要求變革科舉考試內容,即改詩賦為策論、為經義,且多有爭議。到南宋時,士大夫也認識到,既然科舉選官是以德才兼備為標準,就應該將詩賦與策論、經義相糅合。關于詩賦對科舉考試的影響,楊萬里說:“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為之;故其工,后無及焉。”[2]1246意思是說,詩歌在唐代之所以會繁榮鼎盛,最主要原因是科舉設有詩賦這一考試科目,使得士子傾盡心思來研究和創作詩賦,換句話說,“以詩取士”的制度措施促進了唐詩的繁榮,此舉不失為兩全其美之策。
即使在楊萬里功成名就之后,也常以科考的詩賦標準來檢驗自己的題詩功力。淳熙十一年(1184)初冬,楊萬里丁繼母憂期滿,因兩年多未曾作詩,第一首題詩即是《淳熙甲辰十月一日,擬省試“萬民觀治象”》,云:魏闕東風里,皇城曉日端。三朝垂治象,萬姓得榮觀。老稚看如堵,章程炳若丹。九天新雨露,一札妙龍鸞。遠覽《周官》舊,重瞻漢詔寬。歡聲將喜氣,銷盡柳邊寒。[3]255省試即是禮部試,可知他仍以進士試的標準來模擬題詩,以此檢驗自己題詩功力是否衰退,表明其內心對科考中詩賦試的認同。事實也是如此,科考中保留詩賦,能有效檢驗士子的藝術才華,策論能考查士子的政治見解,經義則驗證士子的經學功底,三者應是相輔相成的。
(三)對組織管理的審視
南宋比北宋科舉錄用名額有大幅度增長,但從官員的總數量角度而言,仍約有六成官員是靠恩蔭出仕,只不過非科舉出仕者,多是在基層擔任低級官吏而已。楊萬里對科舉入仕的數額,以及南宋政治體制所造成的冗官現象多有論述,如《千慮策·冗官》中說: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于太學、舉于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儉于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儉于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于千也。至于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校于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修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2]1417-1418“任子”是指因父兄的功績,得保任授予官職;“特恩”即皇帝所給予的特殊的恩典,如北宋統治者為防范失意士子心生異志,于開寶三年(969)規定,凡舉人參加過15次以上考試終場者,特賜本科出身。在楊萬里看來,特奏名和特恩等舉措的推行,造成官員人數急劇增多,百姓負擔就重,這也是一種社會腐敗,表示要采取措施革除冗官,提高科舉人才的適用性。他在《千慮策·選法》中說: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科甲之首者,不由于吏部,他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2]1410選法即是選拔官吏的法規。在他看來,即使通過科舉而勝出者,不少人是沖著功名利祿、飛黃騰達的目的,完全沒有為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之心,間接助長官場的黑墨、學術的墮落等行為的產生,這也是楊萬里最為痛心之處。
再如,為保證科舉考試的公平,南宋已有別頭試、鎖廳試、鎖院、封彌、謄錄等制度,又因古代中國宗法關系強大,人際關系復雜,無論采取何種取士制度,都可能會出現舞弊現象。楊萬里在《與材翁弟書》就言及這方面的特殊情況,說:某老謬不死,三忤濟翁矣。自丙午(1186)之秋,濟翁自吉州入京,是時某為都司,濟翁欲求作親弟牒試。某不敢欺君:以疏族為親弟,濟翁大怨,一忤也。戊午(1198)之春,濟翁又來求以假稱外人面不相識,而以十科薦。某不敢欺君,以族人為外人,濟翁又大怨,二忤也。今又有奸黨累人之怨,三忤也。[2]1074材翁是楊夢信的字,即作者族叔祖、抗金名臣楊邦乂的親孫子,他與堂兄楊炎正于慶元二年(1196)中同科進士。科舉之弊,歷朝都有,楊萬里信中所言及科舉中牒試、十科薦等,一方面表明作為最為剛性的科舉考試制度,仍有不少“鉆空子”之處,另一方面則是印證作者剛正耿直、認理不認親的優良品質。
四、對改進科舉制度的思考
楊萬里與兩宋時王安石、蘇軾、范仲淹、朱熹[6]等名士一樣,就科舉制度提出過一些改進主張,希望調和科舉與才學、教育之間的矛盾,提升選賢任能之實效。
(一)科舉與才學關系的思考
科舉考試是面向社會廣大讀書人,即使出身貧困的讀書人也可參加應試,而南宋時吉州參加科考人數更是高達總人口的2%,由此造就了廬陵地域崇文重教、重義尚節的文化外部表象,不失為一種較為公平的選才辦法。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要是考試,就會有一定的模式和套路。假若士子只是苦讀時文,僅追求和滿足于科考的需要,其通病就是撰文內容空洞,追求標新立異,甚至文章胡亂拼湊,所選之人有不少是毫無經世致用之能力的。楊萬里作為一位面對現實的理學家,明顯看到這方面的弊端。如面對鄉友、青年才俊王子俊多次在科考中敗北,楊萬里說:生之是行,志于得科目而已也?將其志不止于得科目而已耶?志于得科目而已也,則生之挾時之悅,生之鬻時之售,有余也,科目足道哉!其志將不止于得科目而已也,則予欲不言,得而不言耶……場屋之文,夸以賈驚,麗以媒欣,抑末矣,是之為也?士之言曰:“我將先之末,繼之本。”嗟乎!本以先猶末以繼,而又末以先者耶?是故為士者植其初,用士者計其終,不取士不與焉,蓋曰“姑以是取之”云爾……士之愚良,系不系于場屋之文哉?種玉者不,藝稗者不禾,奈之何其以末先、以本繼也![2]1228說到王子俊的才學,楊萬里曾給予較高評價:“吾友王子俊才臣,年十七時,所作《歷代史論》十篇也。是時老氣橫九州,毫發無遺恨。”[2]1569雖說王子俊很有才學,卻屢次在科舉考試中敗北,其原因是:楊廷秀嘗評材臣之文,謂史論有遷、固之風,古文有韓、柳之則,詩句有蘇、黃之味。至于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②王子俊年齡不大,卻博學多識,文學和史學均有較深造詣,又因他擅長晚唐五代時曾一度盛行的駢文,于是在北宋古文革新運動的大背景下,自然是遭受到閱卷者的打壓,致使部分有才之士無法脫穎而出。
(二)科舉與道德關系的思考
宋代理學家最為關注士大夫的道德修養,而科舉“只重時文,不重德行”的考試模式,必然導致部分士人不注重修身齊家和慎獨慎微。楊萬里認為,應將科舉考試與道德修養相結合,讓士人既讀書和科考,更要強調修齊治平。他為劉子和回信中說:某少也賤,粗知學作舉子之業,以千升斗為活爾,烏識夫古文樓轍哉?文于道未為尊,固也。然譬之瑑璞為器:瑑,固璞之毀也;若器成而不中度,瑑就而不成章,則又毀之毀也。[2]1045在他看來,不少士子不認真讀書,只是背時文應付科舉,猶如當今少數學生只重題海戰術,不注重獨立思考,這種人其實并無真才實學,只是一種讀死書、謀功名、求俸祿的社會寄生蟲而已。作為科舉考試的組織者和制度設計者,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應將個體的品德修養社會歷練放在更突出的地位,否則就是對社會毫無用處的廢料一塊,反而影響社會發展的導向。
(三)科舉與經世關系的思考
在南宋特殊的大環境里,朝廷應如何選拔人才,尤其是對宰相、武將的選任等,他均提出一系列成熟的思考方案。在他看來,應通過一定的手段來籠絡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將其納入國家管理的軌道。如《千慮策·人才》中說: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摩,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世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2]1383然而,古代科舉不受年齡限制,造成不少讀書人一生只為追求功名利祿,不事農桑,輕視勞動,毫無行道救世的責任感,過著社會寄生蟲般的生活。
此外,古代士大夫常認為,越是窮困不得志,詩文就會寫得越好,其見識和才能就會更凸顯。楊萬里在《歐陽伯威〈脞辭集〉序》《施少才〈蓬戶甲稿〉序》《〈千巖摘稿〉序》等序文中,均結合自身的生活際遇,既委婉表達對部分困迫詩人懷才不遇的同情,更有對他們才學和見識的推崇,如《歐陽伯威〈脞辭集〉序》說:予因索其詩文,伯威顰且太息曰:“子猶問此邪?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脞辭》一編,曰:“子不憐其窮而索其詩,子盍觀其詩而療其窮乎?予退而觀之,其得句往往出象外,而其力不遺余者也。高者清厲秀邃,其下者猶足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蓋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闖殆遍矣。”[2]1229此序文不僅高度評價歐陽伯威詩作的風格特色,肯定他認真探討前代詩人創作流派的精神,同時也表達作者對歐陽氏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
結語
科舉制度的目的是為封建王朝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之人才,自北宋以后,吉州逐步成為科舉考試重地之一,而楊萬里科舉之路雖說有小曲折,仍算是幸運者。就其內心態度而言,他也是科舉制度的堅定支持者,認為它能將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現實踐行,從而實現人生理想中“修齊治平”目標。楊萬里反對片面地追求科舉功名,極其重視道德修養,且有改革現行科舉制度的部分思考。應當說,他對科舉制的部分審視和相關思考,實是南宋士大夫的共識,所提出的科舉變革思維仍不夠系統。
注釋:
①參見光緒二十五年(1899)編修的《忠節楊氏總譜》,現收藏于其故里湴塘村。
②參見四庫本雍正版《江西通志》卷76《人物》之《吉安府(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