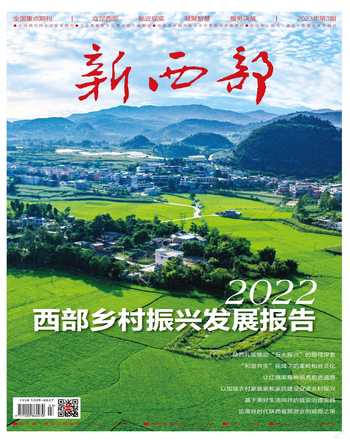“和諧共生”視域下的秦嶺和合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多次提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習近平總書記還曾強調,秦嶺和合南北、澤被天下,是我國的中央水塔,是中華民族的祖脈和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征。“和諧共生”視域下的秦嶺和合文化,在自然上和合中國南北,在人文上和合多元文化,在人與自然關系上體現天人合一之精神。秦嶺不僅是一座雄偉的自然之山,也是一座厚重的文化之山;不僅是一座地理山峰,也是一座精神高峰;不僅體現出包容特點,而且彰顯出和合理念。作為一座兼具重要自然與文化價值的亞洲重要山脈,秦嶺是中國文化中的“和合嶺”,綿延并傳承著和合理念與文化。因此,秦嶺也是中華和合文化的重要表征。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多次提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并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2020年4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秦嶺時強調,秦嶺和合南北、澤被天下,是我國的中央水塔,是中華民族的祖脈和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征。從“和諧共生”視域來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秦嶺“和合南北”,其實是指出了秦嶺的“和合”功能及其蘊含的“和合”文化。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和”與“合”早就存在。“和”最早見于甲骨文,指“音聲相應和諧”,為和諧、調和之義。周太史史伯最早提出“和”,他在《國語·鄭語》中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合”最早見于金文,指上下唇、上下齒的合攏,為相合、符合之義。《尚書·君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春秋時期,“和”與“合”并用,《國語·鄭語》有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指商契能和合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五教”,此處之“和合”,指的是協調倫理關系。中國傳統文化對和合的追求源遠流長、持續不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之江新語》中所強調的:“我們祖先曾創造了無與倫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這其中的精髓之一。”[1]
在中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演變進程中,秦嶺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典型代表,形成極具特色的秦嶺和合文化,具體表現在自然、人文以及人與自然關系三個重要方面。
秦嶺在自然上和合中國南北
秦嶺之所以廣為人知,主要是因為“秦嶺-淮河”一線是中國南方與北方的地理分界線,秦嶺橫亙我國中部,和淮河一起,將我國中東部一分為二,奠定了我國大陸的自然地理格局。同時,秦嶺主峰太白山拔仙臺又是青藏高原以東最高峰,海拔3771.2米。秦嶺的地理范圍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秦嶺,西起青海、甘肅兩省之邊界,東經甘肅進入陜西,貫通陜西中部,東抵河南中部,在秦豫交界處,分為三支:崤山、熊耳山、伏牛山,涵蓋青海、甘肅、陜西、四川、重慶、河南、湖北等六省一市,綿延1600公里。狹義的秦嶺,僅限于陜西范圍,東止灞河與丹江河谷,西界嘉陵江,南至漢江谷地,北抵關中盆地,東西長約400-500公里,南北寬達100-150公里。
作為中華地理的自然標識,秦嶺是亞熱帶和暖溫帶的分界線、濕潤地區與半濕潤地區的分界線、北方植物區系和南方植物區系的分界線,長江水系與黃河水系的分水嶺等,在地質、地貌、氣候、水文、生態、生物等自然地理方面有南北差異。但這一差異是具有和合性的,以氣候要素為例,秦嶺以南是亞熱帶氣候,秦嶺以北是溫帶氣候,從南往北跨越300公里,這就決定了秦嶺本身的氣候具有過渡性。氣候影響植被,所以秦嶺又是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同緯度地區北亞熱帶和暖溫帶過渡森林生態系統的典型代表。它在界分南北氣候的同時又和合南北氣候。和合學的創立者張立文曾撰《論氣候和合學》,認為“氣候動變對于天地萬物以及人類的影響和作用是一體的、共同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便是氣候和合學之所以能統攝錯綜復雜的氣候動變與自然、人文社會各學科的根據所在。”[2]其中雖然未提到秦嶺的氣候,但對研究秦嶺的和合氣候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王學斌指出,秦嶺“既界分了南北,又通連著南北。”[3]相對于“南北分界線”,黨雙忍和王斌提出將秦嶺稱為“南北過渡地帶”或“南北過渡帶”。黨雙忍指出,“所謂南北分界線,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帶,更多地表現出南北過渡地帶特征。秦嶺山里,既有中國的南方,又有中國的北方。既不是典型的北方,也不是典型的南方;或者說,既像是南方,又像是北方。其實,也是一種既南又北的格局。因此,秦嶺是中國的北方,也是中國的南方,中國的南方與北方共享了大秦嶺。”[4]王斌指出,將秦嶺作為南北過渡帶比起傳統稱謂的南北分界線更為合理。秦嶺南北的自然環境劇烈變化是水熱要素配置的臨界變化效應與秦嶺山體分異作用的綜合疊加,和合南北是從地理視角對秦嶺生態環境意義的深刻透視。[5]
因此,縱跨南北300公里的秦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具有和合性的過渡帶。在這一過渡帶內,既有南方地理特色,又有北方地理特色,形成不同的地理景觀共聚一山、和諧共生的情況。再以農業景觀為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曾指出:“兩大農業區的兩種農業體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響乃至在發展過程中發生互動等復雜情況。這樣一種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農業格局,一直影響到整個歷史時期,并且對鄰近國家的農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6]蘇先生所說的“兩種農業體系”,指的是秦嶺以北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旱地粟作農業系統和秦嶺以南以長江流域為核心的水田稻作農業系統。蘇先生說的“互補”和“聯系”,在秦嶺北麓的西安也有體現。在西安的長安區、高新區等地仍種植有被認為是南方的農作物水稻。秦嶺被譽為生物基因庫,也是因為它同時匯聚了南北動植物區系的諸多物種,生物多樣性豐富。
秦嶺在人文上和合多元文化
秦嶺不僅是一座雄偉的自然之山,也是一座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之山。《漢中府志校勘》記載,“其聲音山南近蜀則如蜀,山北近秦則如秦”,[7]這正是對秦嶺地區多元文化環境的真實寫照。秦嶺不僅和合了南北地理,也和合了多元文化。有人指出,秦嶺是中國南北的分界線,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秦嶺文化體現出極大的“兼容性”。在人文方面,秦嶺是中國南北方文化、中西方文化的聚合區和交匯區,西北有秦隴文化,西南有巴蜀文化,東南有湘楚文化,東北有燕趙文化和三晉文化。秦嶺皆能以博大的胸懷與其和諧共生。在肖云儒看來,“秦嶺是中華文化的‘十字交叉點。它把中國古代文明隔離開又銜接起來。這個‘十字的西北邊是秦隴文化區,西南邊是巴蜀文化區,東南邊是湘楚文化區,東北邊就是燕趙文化和三晉文化區,在空間上中國古代各個文明板塊大致是朝向這個‘十字,就是秦嶺、黃河十字聚攏集中的。”[8]秦嶺與周邊多元文化的諸多要素是在相互沖突中融合的,在這一動態過程中,往往會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這就是具有重要人文精神的秦嶺和合文化。因此,肖云儒所說的“隔離”又“銜接”,指的就是和諧共生。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周秦漢唐文化之所以能彪炳史冊,成為歷史長河中璀璨的明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秦嶺與周邊地區的文化能夠和諧共生,與周邊國家的文明能夠交流互鑒,并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將“和合”這一特性延續下來。
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儒釋道也是在秦嶺逐步和合的。宋虹橋指出,秦嶺的終南山為儒釋道文化的互補和合提供了天然環境。從西周建都于終南山北麓,至秦漢、隋唐時期,是終南文化融匯儒、佛、道等各家學說,充分發展、并確立自己作為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時期。[9]周人在秦嶺建立了一套以仁義禮智為核心的西周禮樂文化,倡導謙和有禮,威儀有序。這成為孔子儒學的重要淵源,孔子曾講:“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所以他畢生致力于復興周禮。西漢董仲舒在秦嶺山下的長安城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治國思想,經漢武帝推行,儒家學說成為官方正統學說。東漢的馬融承前啟后,傳承儒學。至北宋時期,張載在秦嶺太白山腳下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成為儒家學者的最高追求。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在秦嶺樓觀臺完成《道德經》,道家思想由此發源。樓觀道也依此而誕生。秦嶺山中的孫思邈雖為道士,但也融合佛教文化,如他的著作《千金翼方》中的“正禪方”“阿伽陀”等藥方藥名,均來自佛教文化。自兩漢之際佛教文化傳入秦嶺地區之后,歷經兩千余年,秦嶺及其附近的城市成為佛法僧的匯聚之地,成為佛教中國化的理論創新高地。佛教也在和儒道交涉過程中和諧共生,共同成為秦嶺和合文化的重要代表。
秦嶺在人與自然關系上體現天人合一之精神
秦嶺在自然上和合中國南北;在人文上和合多元文化;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同樣體現出和合的特點,這一特點,是通過天人合一表現出來的。人來源于大自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應當遵循自然規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的:“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天人合一”作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最高境界,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和合”:人不能獨立于自然之外,也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要達到平衡與和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到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專門強調了“天人合一”。錢穆曾指出:“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張岱年從“和合”角度對“天人合一”展開研究,他指出:“合有符合、結合之義。古代所謂合一,與現代語言中所謂統一可以說是同義語。合一并不否認區別,合一是指對立的雙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聯不可分離的關系。”[10]季羨林認為“天人合一”是“代表中國古代哲學主要基調的思想”,[11]不僅是中國,而且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
從和諧共生視域看,秦嶺文化中蘊含有豐厚的“天人合一”思想。秦嶺孕育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念,老子在秦嶺樓觀臺所著的《道德經》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出宇宙之間的基本結構是人、天地、道、自然。人應該清靜無為,謙卑自處,效法自然法則,尊重自然規律。老子還指出,萬物由陰陽而構成,和諧由陰陽而產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據統計,《道德經》共81章,有20章涉及和合思想,約占全文的四分之一,其中,言“和”者有七處,如“音聲相和”(2章)、“六親不和”(18章)、“沖氣以為和”(42章)、“和之至也”、“知和曰常”(55章)、“和其光”(56章)、“和大怨”(79章);言“合”者有二處,如“天地相合”(32章)、“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55章)等。
董仲舒在秦嶺山下傳播以和合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認為和合是天地的本原,他說:“中者,天下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循天之道》第七十七,《春秋繁露》卷十六)將《中庸》的中和觀念發揮得淋漓盡致。宋代張載居住于秦嶺北麓,著書立說,培養弟子,創立關學。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方面,他在《西銘》開篇寫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也是成語“民胞物與”的來源,意思是人民為同胞,萬物為同類,強調人民都是我的同胞,萬物與我都是天地所生。所以,要愛人,也要愛萬物,還要愛大自然,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體現,在傳統觀點的基礎上推進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探尋。
隋唐時期中國佛教誕生了八大宗派,其中多數宗派誕生于秦嶺,其多數祖庭至今仍立于秦嶺山中,如華嚴宗祖庭之一至相寺、凈土宗祖庭之一悟真寺、律宗祖庭凈業寺和豐德寺等。華嚴宗最重要的思想是“圓融”,強調“理事圓融”、“事事無礙”。具體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來說,華嚴宗認為人和自然是圓融的、和諧的,所以人要尊重大自然,善待大自然。大自然中的秦嶺高高聳立在中國大陸腹地的中央,具有調節氣候、保持水土、涵養水源、維護生物多樣性等生態功能, 此區域“自然地理相連、人文歷史共生、經濟社會相融,歷史地形成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核心文化圈、中華民族持續發展的核心經濟圈”。[12]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保護好秦嶺生態環境,對確保中華民族長盛不衰、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從和諧共生視域來看,秦嶺在自然上和合中國南北,在人文上和合多元文化,在人與自然關系上體現“天人合一”之思想,不僅是一座雄偉的自然之山,也是一座厚重的文化之山;不僅是一座地理山峰,也是一座精神高峰;不僅體現出包容特點,而且彰顯出和合理念。作為一座兼具重要自然與文化價值的亞洲重要山脈,秦嶺和合了自然、和合了文化、和合了人與自然,是中國文化中的“和合嶺”,綿延并傳承著和合理念與文化。因此,秦嶺也是中華和合文化的重要表征。我們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秦嶺自然和生態環境,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同時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秦嶺發展。
參考文獻
[1]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0頁。
[2]張立文:《論氣候和合學》,載《探索與爭鳴》,2015(10):5頁。
[3]王學斌:《“天下山川,以此為最”:作為中華民族祖脈的秦嶺》,載《中國民族》,2020(11):30頁。
[4]黨雙忍:《秦嶺簡史》,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9:334頁。
[5]王斌,秦嶺:《“南北分界”還是“和合南北”》,載《中學地理教學參考》,2021(13):79頁。
[6]蘇秉琦主編:《中國通史(第2卷):遠古時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序言10頁。
[7]嚴如熤修,郭鵬校勘:《漢中府志校勘》,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733頁。
[8]夏明勤:《秦嶺每一種表達都指向文化》,載《中國旅游報》,2010-5-14(010)。
[9]宋虹橋:《終南儒釋道互補的和合文化》,載《人民論壇》,2016(23):142頁。
[10]張岱年:《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01):1頁。
[11]季羨林:《“天人合一”新解》,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01):1頁。
[12]王碩:《當好秦嶺衛士守護“中央水塔”——六省一市政協環秦嶺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協商研討會議綜述》,載《人民政協報》,2022-6-23(5)。
作者簡介
景天星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