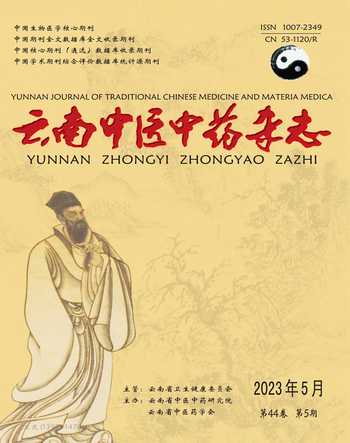基于“腸-腎軸”理論探討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慢性腎臟病的研究進展
李宜航 相學(xué)梅 牟曾熠 李志明
摘要: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由于患病率較高,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健康問題,如何延緩其病程發(fā)展、改善臨床癥狀,是一直以來研究的熱點。腸道微生物群的生態(tài)失調(diào)為防治CKD并預(yù)防其并發(fā)癥提供了重要靶點。在“腸-腎軸”的基礎(chǔ)上,探討了腸道微生物與CKD的相互作用,綜述了目前CKD的中醫(yī)內(nèi)外治法及西醫(yī)飲食療法,為改善腸道微生物群,改善腎功能損傷,延緩CKD進展提供治療新思路。
關(guān)鍵詞:腸腎軸;慢性腎臟病;中醫(yī)藥
中圖分類號:R692文獻標(biāo)志碼:A文章編號:1007-2349(2023)05-0110-06
慢性腎臟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這一概念首次是于2002年被提出的[1],是指由各種原因?qū)е履I臟結(jié)構(gòu)或功能出現(xiàn)異常≥3個月的一種臨床綜合征,可伴有腎小球濾過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的降低;或無明顯誘因出現(xiàn)GFR下降≤60 mL/(min·1.73m2)≥3個月,可伴有腎臟實質(zhì)性的損傷[2]。近年來,CKD發(fā)病率逐漸升高。2012年全國CKD流行病學(xué)報告,我國CKD患病率高達10.8%,約有1.2億成年人患有CKD[3]。2017年,全球約有6.975億人患有CKD,其平均患病率高達9.1%,其中我國CKD患者為1.32億[4-5]。該病起病隱匿,病程長,死亡率高,預(yù)后不良,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健康問題,其由多種腎臟疾病發(fā)展而來,晚期甚至可發(fā)展為尿毒癥。因此,如何更早、更有效地治療CKD已成為一個具有重要的社會及經(jīng)濟意義的問題。
“腸-腎軸”理論首次是由Meijers等[6]人提出的。該理論直接開啟了CKD與腸道微生態(tài)探索研究的新紀(jì)元[7]。至2015年,Pahl等[8]將該學(xué)說進行了補充完善,其核心觀點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點:第一,CKD患者由于腎功能受損,代謝廢物無法及時排出,積于體內(nèi),經(jīng)腸壁血管滲入腸腔引起腸道菌群紊亂,加劇腸源性尿毒素在血中積聚,進一步損害腎功能;第二,腸道菌群失調(diào),腸道上皮屏障受損,細胞間通透性增加,導(dǎo)致條件致病菌及腸源性尿毒素入血,激活機體免疫系統(tǒng),誘發(fā)全身微炎癥反應(yīng),導(dǎo)致腎臟微炎癥狀,進而加劇CKD病程進展[9]。
中醫(yī)中并無“慢性腎臟病”一詞,據(jù)其臨床表現(xiàn)的不同可歸屬于“水腫”“尿濁”等范疇。病機本虛標(biāo)實,涉及腎、脾、肺等多個臟器,以外感六淫為外因,稟賦不足、飲食失宜等為主要內(nèi)因[10]。隨病情進展,可滋生濕、毒、瘀等病理產(chǎn)物,最終導(dǎo)致虛實夾雜,遷延難愈[11]。《外經(jīng)微言》云:“是以補腎者必須益肺,補肺者必須潤腎。”又如《景岳全書》所言:“但二腸連胃,氣本一貫,故在《內(nèi)經(jīng)》亦不言其定處,而但曰大腸、小腸皆屬于胃,是又于胃氣中,總可察二腸之氣也。”正如上文所闡述的腸與肺相表里,并受事于脾胃,因此可以從肺與脾胃入手,發(fā)掘整理名老中醫(yī)療法,中西醫(yī)結(jié)合,以延緩其病程進展,恢復(fù)腎功能[12-13]。
1腸與腎相互作用
1.1腎病及腸在CKD患者中,往往會出現(xiàn)腸道屏障改變?nèi)珉[窩的延伸、絨毛高度改變、固有層與炎癥細胞的滲透、腸壁水腫、腸道上皮屏障受損、含氮代謝物及內(nèi)毒素入血、細菌移位等[14]。已有研究表明[15],CKD患者血液中尿素氮(BUN)增加可引起腸道黏膜損傷,從而引發(fā)炎癥。與健康人群比較,CKD患者腸道內(nèi)會出現(xiàn)微生物群在數(shù)量和質(zhì)量上的失衡,致病菌如腸桿菌的數(shù)量明顯增加,而有益菌如乳酸桿菌、雙歧桿菌明顯減少[1]。CKD患者常出現(xiàn)腸道菌群失調(diào),并且與腸源性尿毒癥毒素循環(huán)水平升高、炎癥和氧化應(yīng)激等因素有關(guān)[16]。
1.2腸病及腎腸道微生物群的改變與多種疾病的發(fā)展相關(guān),包括腎臟疾病[17]。微生物群是由多種微生物組成的復(fù)雜群落,在健康人體的腸道中,這種復(fù)雜群落是由千余個不同的物種,超過100萬億個微生物細胞組成的。健康狀態(tài)下,這些微生物與宿主處于共生關(guān)系。微生物群參與調(diào)節(jié)機體免疫系統(tǒng),抵御病原體,并調(diào)節(jié)體內(nèi)碳水化合物和脂類的內(nèi)源性代謝,從而有助于保持營養(yǎng)平衡[17]。其還被視為“代謝器官”,它維持體內(nèi)環(huán)境平衡,抑制病原菌生長,保障腸道功能和微生物穩(wěn)定[18]。
腸道菌群失調(diào)是造成腸道屏障功能受損的關(guān)鍵因素[14],并與各種疾病的發(fā)展有關(guān)[19]。有研究表明[20],腸道微生物群的構(gòu)成和功能的改變在CKD的發(fā)病機理和并發(fā)癥中起著關(guān)鍵作用。腸道作為血液和有毒化合物的連接,腸道上皮屏障破壞,其通透性增加,細菌及其代謝產(chǎn)物從腸道轉(zhuǎn)移入血是腸道菌群對CKD影響的主要機制[14]。
1.3腸、腎之間相互作用腎和腸道微生物群間存在著雙向相互作用:腸道微生物可能會產(chǎn)生潛在的有毒代謝物,而CKD可能會影響微生物群的組成并破壞腸道上皮屏障,促進內(nèi)毒素和細菌從腸腔轉(zhuǎn)移到血流中[21]。在CKD患者機體內(nèi),腸道微生物紊亂,引起尿毒癥毒素濃度升高,進而加速CKD發(fā)展,形成惡性循環(huán)[17]。除此之外,CKD患者的腸壁會出現(xiàn)組織學(xué)變化,腸上皮緊密連接破壞,導(dǎo)致通透性增加,細菌和內(nèi)毒素穿腸入血而致內(nèi)毒素血癥和全身性炎癥[20]。腸道菌群失調(diào)及腸黏膜損傷等改變,會使患者腎臟損傷加重,CKD進程加快,反之,腎功能惡化會破壞腸黏膜屏障,導(dǎo)致腸道生態(tài)失調(diào)。因此,CKD很可能導(dǎo)致腸道微生物群和腎臟之間錯誤的雙向相互作用[22],因此針對CKD的從腸而治理論應(yīng)運而生[15]。
從中醫(yī)角度而言,腸與腎同屬下焦,密切相關(guān),《寓意草》云:“夫人一團之腹,大小腸膀胱俱居其中”,又云:“邪結(jié)于腹之左畔,即左腎與膀胱為之府也。”兩者同處腹中,“中西醫(yī)匯通派”創(chuàng)始人之一唐宗海曾說:“大腸位居下部,又系腎之所司,<內(nèi)經(jīng)>云:“腎開竅于二陰。”又曰:‘腎為胃關(guān)。故必腎陰充足,則大腸腴潤。是以大腸之病……有由腎經(jīng)陰虛,不能潤腸者”;《辨證錄》云:“胃火盛而大腸之火亦盛,腎水干而大腸之水亦干,單治大腸之火,而不瀉胃中之火,單治大腸之水,而不益腎中之水,則大腸之水不生,而大腸之火亦不息”,五臟六腑皆屬一整體,臟腑相生相克、互相制化,腸與腎相互關(guān)聯(lián),互相影響。水液入腸,經(jīng)大腸傳導(dǎo)糟粕,小腸泌別清濁,脾胃升清降濁,使?jié)嵴呦職w腎,經(jīng)膀胱排出,清者上輸于肺,散布周身,起濡養(yǎng)作用。六腑傳化失司,五臟濁氣蓄積體內(nèi),無所出者,易發(fā)生臟腑傳變,腸與腎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腸-腎軸”是聯(lián)系其相互作用的關(guān)鍵[23]。《筆花醫(yī)鏡》中提及:“大腸者,腎陰之竅,傳道之官,受事于脾胃,而與肺金相表里……然腸口上接小腸,下通谷道,為諸臟泄氣之門,啟閉一失職,而諸臟困矣。”大腸與肺相表里,且受事于脾胃,肺陰下輸于腎,腎陰上滋于肺,陰陽互資,金水相生;脾乃后天之本,依賴于腎的蒸化,腎乃先天之本,依賴于脾氣運化,兩者相互資生,運化水液。生理互資,病理則互相傳變。肺脾腎功能失司會影響到大小腸的功能,引發(fā)泄瀉、便秘等疾病,進而使腸道菌群紊亂。脾為氣血生化之源,脾虛則運化無力,臟腑失養(yǎng),累及腸則可致腸道傳導(dǎo)失司,引發(fā)腸道菌群數(shù)量、分布等改變[24]。故而想要治療CKD可以以腸為出發(fā)點,利用肺與脾胃,中西結(jié)合,臟腑同治。
2中醫(yī)與CKD
2.1中醫(yī)內(nèi)治法
2.1.1單味藥及其有效成分就目前研究而言,從“腸-腎軸”治療CKD多用清熱解毒類及補益類中藥。其中,治療CKD的單味藥以大黃、黃芪最為常見。
大黃對CKD的作用機制包括促進尿素及肌酐的排泄、抑制腎小球硬化的進展、改善微循環(huán)、減輕殘腎單位“高代謝”狀態(tài)以及免疫調(diào)節(jié),其主要有效成分為大黃素、大黃酸[25]。臨床上,CKD患者易出現(xiàn)便秘的癥狀,這更加加劇濁毒的蓄積,出現(xiàn)惡性循環(huán)。使用瀉下攻腸的方法,對便秘癥狀療效顯著,這也與“腸-腎軸”理論相合。大黃苦寒,生可強攻瀉下,制可緩攻瀉濁,使?jié)岫緩哪c而出,保護殘余腎功能[26]。
黃芪補益脾氣,行肺脾經(jīng),可以提升腸道黏膜免疫水平,抑制腸道炎癥;還可以抑制結(jié)腸屏障蛋白的降解,抑制腸道屏障的損傷;有效改善氧化應(yīng)激從而延緩腎損傷[27]。其具有“類激素”效應(yīng),能夠降低尿蛋白,從而保護腎功能[11,28]。
除上述兩味常用中藥外,還有許多中藥被應(yīng)用于腎臟疾病的治療當(dāng)中。如益智仁,可燥脾溫胃,能夠提高疣微菌科和乳酸桿菌科的相對豐度,降低理研菌科和毛螺旋菌科相對豐度[29]。姜黃素具有修復(fù)腸道屏障,調(diào)節(jié)腸道菌群,降低大腸桿菌志賀菌屬和擬桿菌屬等致病菌的含量,增加乳酸桿菌等有益菌的含量,減輕腎臟的炎癥和纖維化,保護腎功能的作用[30]。三七注射液能保護腸道粘膜屏障,改善腸道微生物生存環(huán)境,保護菌群多樣性,從而起到延緩腎損傷進程的作用[31]。烏藥水煎液可促進家兔胃腸動力,能有效改善腎小球纖維化程度,還可通過調(diào)節(jié)肌酐清除率和血清肌酐水平保護腎功[32]。丹參莖葉作用雖弱于丹參根與根莖,但仍然表現(xiàn)出腎保護和調(diào)控腸道微生物多樣性的作用[33-34]。高劑量茯苓能顯著提高腸道雙歧桿菌的水平,而白術(shù)多糖具有促進益生菌生長的作用[35]。
2.1.2中藥復(fù)方中藥復(fù)方也被大量應(yīng)用于腎臟疾病的治療中。大黃甘草湯可促進尿毒素排出,其靶點不在腎,而可能是“腸-腎軸”[36]。補脾益腎方為黃芪復(fù)方,可減少致病菌相對豐度,增加益生菌相對豐度。還能夠促進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修復(fù)腸道屏障,改善腎功能[37]。通腑泄?jié)岱侥苷{(diào)節(jié)腸道菌群,抑制氧化應(yīng)激,改善機體炎癥反應(yīng),減輕腎間質(zhì)纖維化,延緩腎損傷[38]。清腎顆粒可通過調(diào)節(jié)腸道菌群、降低炎癥因子、保護腸道粘膜的作用而保護腎功能[35]。黃葵四物方能夠顯著抑制尿毒素硫酸對甲酚(Paraccresol sulfate,PCS)前體對甲酚在腸道細菌內(nèi)的合成,從而降低體內(nèi)PCS的含量,通過抑制腸源尿毒素生成環(huán)節(jié)減輕CKD腎臟損傷[39]。縮泉益腎方可以上調(diào)擬桿菌門,下調(diào)厚壁菌門[40]。七味白術(shù)散抑制金黃色葡萄球菌、產(chǎn)氣桿菌和沙門氏菌,促進腸道酵母菌[41]。扶正化瘀降濁方通過調(diào)節(jié)芽孢桿菌屬、乳桿菌屬、纏結(jié)真桿菌屬、Family_XIII_AD3011菌屬四種細菌生物標(biāo)志物和腸源性有害代謝物,抑制炎癥反應(yīng)和腎小管間質(zhì)纖維化,減少了CKD早期的腎臟損傷[42]。諸多研究證明,中藥及復(fù)方在治療CKD上做出了巨大貢獻,為臨床應(yīng)用提供了治療方向。
2.2中醫(yī)外治療法中醫(yī)外治療法也多用于臨床,與內(nèi)治法相比,優(yōu)勢在于:藥物不通過胃腸道等消化系統(tǒng),不會被肝、腎等分解代謝。可防止首過效應(yīng),減輕藥物療效,還可避免藥物對其他器官產(chǎn)生不良影響[43];其方法多樣、操作靈活簡單、效專力宏、直達病所、奏效迅速;能夠多途徑給藥,且安全性高,毒害性小[43]。中醫(yī)外治療法之灌腸療法最早見于《傷寒雜病論》中的“蜜煎導(dǎo)法”及“豬膽汁導(dǎo)法”。其有兩方面,一是可通腑利腸,以通二便,使?jié)岫緩亩愣ィ欢鞘顾幬锝?jīng)腸入肺,再入腎而發(fā)揮藥效,這與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的“腸-腎軸”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44]。
益腎泄?jié)岱铰?lián)合中藥保留灌腸的中醫(yī)“內(nèi)外同治”一體化治療方案能夠有效改善CKD患者癥狀,可通過調(diào)節(jié)“腸-腎軸”減輕內(nèi)毒素血癥,保護腸道粘膜屏障,延緩CKD的進展[45]。益腎湯經(jīng)結(jié)腸透析可降低CKD3-5期患者大腸桿菌水平,升高雙歧桿菌、嗜酸乳桿菌水平。其可改善患者腸道微生態(tài)狀態(tài),抑制體內(nèi)微炎癥反應(yīng),延緩腎損傷,減輕患者臨床癥狀效果顯著[46]。除上述灌腸液外,仍有許多方劑被應(yīng)用于此。諸多研究表明,中藥聯(lián)合結(jié)腸透析可增加CKD患者結(jié)腸毛細血管壁通透性及物質(zhì)交換,排出體內(nèi)毒素,改善殘余腎功能[46]。大黃附子湯既可通腑泄?jié)幔腋阶臃醋糁蓽p輕大黃之苦寒,使內(nèi)蘊之濁邪從腸腑排出,可用以搶救尿毒癥[26]。
除灌腸療法外,常用的外治法還有艾灸療法。這是一種以艾為主要材料的方法,借灸火之溫和熱力,艾絨燃燒的溫?zé)岽碳ひ约八幬锏淖饔茫ㄟ^透皮吸收和呼吸作用,刺激經(jīng)絡(luò),從而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艾灸中脘、關(guān)元和神闕等腹部穴位可以改善CKD患者排便困難、排便時間長等不適。艾灸腎俞等穴位聯(lián)合中藥及常規(guī)治療可以降低CKD患者血清肌酐、BUN、24h尿蛋白總量,升高血清白蛋白[47]。
3西醫(yī)治療
由于CKD患者會出現(xiàn)腎功能損傷,本該由腎臟排泄的尿毒素在體內(nèi)積蓄,會進一步加速腎功能的減退[36]。尿毒癥毒素一般是根據(jù)其生化性質(zhì)進行分類,分為:低水溶性分子(分子量<500 Da)即小分子尿毒素、較大的中等分子(分子量>500 Da)即中分子尿毒素和蛋白結(jié)合分子即蛋白結(jié)合類毒素[17]。其中,大多是腸源性尿毒素。這類腸源性尿毒素毒性更強,更難于被血液透析所清除[36]。清除這種毒素能明顯減緩CKD進展,改善患者預(yù)后。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1)通過調(diào)節(jié)腸道菌群,降低此類毒素的合成,如益生菌和益生元。(2)口服腸道吸附劑,如活性炭吸附劑。(3)緩泄劑緩解便秘癥狀,如魯比前列酮[15]。
3.1益生菌益生元益生菌和益生元的使用是常見的治療方法[17]。有證據(jù)表明,益生菌和益生元可以在CKD中重建腸道微生物群的共生關(guān)系[48]。益生菌能夠改善動物和人的腸上皮屏障功能。益生菌由活菌組成,如乳酸桿菌、鏈球菌和雙歧桿菌,通過食物或補充劑攝入,可改變腸道菌群,影響炎癥狀態(tài),從而降低尿毒癥毒素的產(chǎn)生[17]。近年來,許多臨床試驗和實驗研究表明,益生菌可以調(diào)節(jié)宿主的代謝,通過改善血脂異常、血糖譜和血壓或CKD參數(shù)來改善全身性疾病表型。益生菌的效果與其抗炎、抗氧化和腸道調(diào)節(jié)特性有關(guān)[49]。益生元是能促進有益菌的生長和抑制其他菌群的一種碳水化合物[48,50]。如抗性淀粉(RS),對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的生長有促進作用,增加代謝物生成,從而帶來許多有益健康的好處[51]。有研究表明[52],在腎切除大鼠中補充RS2可導(dǎo)致雙歧桿菌增加,盲腸pH值和尿毒癥毒素產(chǎn)生減少,通過平衡擬桿菌門和厚壁菌門的比例,并改善腸道屏障完整性來恢復(fù)腸道微生物群落共生關(guān)系。
3.2口服活性炭活性炭吸附劑AST-120由直徑0.2-0.4毫米的多孔球形碳顆粒組成。其不溶于水和普通有機溶劑。AST-120可以吸附各種尿毒癥滯留溶質(zhì),降低毒素在肝臟的代謝,加速其前體化合物的代謝。AST-120是通過胃腸隔離來減少全身性腸源性尿毒素吸收[20]。口服AST-120可降低血清中除硫酸吲哚酚外的幾種尿毒癥滯留溶質(zhì)的濃度,延緩CKD的進展[6]。藥用炭片是一種新型炭化高分子材料的腸道吸附劑,具有多孔結(jié)構(gòu),能夠從胃腸中吸附肌酐、尿酸等有毒物質(zhì)。其不被分解,經(jīng)腸道排出體外,使體內(nèi)毒素隨之排出。這些毒素排出體外,不在體內(nèi)循環(huán),從而使其在體內(nèi)的積存量降低,可改善因滯留的毒素引起的消化道癥狀,減緩腎功能損害[53-54]。
3.3緩瀉劑CKD患者可能會出現(xiàn)慢性便秘。魯比前列酮是一種氯離子通道激活劑,可促進自發(fā)排便。這是治療慢性便秘的一種安全有效的藥物[55]。魯比前列酮以加速腸源性尿毒素的排泄降低BUN濃度,減少血液中腸源性尿毒素的含量,也可以增加腸道益生菌,并防止腎小管間質(zhì)損傷、腎纖維化和炎癥[15]。還可改善腸道微生物群以減緩CKD進展和尿毒癥毒素的積累[56]。
4小結(jié)
在西醫(yī)治療方面,近年來,CKD的治療策略旨在調(diào)節(jié)腸道微生物群,恢復(fù)共生關(guān)系,并促進CKD患者腸道來源的尿毒癥毒素的清除。以飲食方法改變腸道微生物群落的組成,來作為CKD的治療方法。益生菌、益生元、魯比前列酮都可以針對腸道菌群失調(diào),以減輕尿毒素蓄積等方式而改善腎功能;活性炭吸附劑AST-120在國內(nèi)應(yīng)用較少;藥用炭片存在口感差、吞咽困難、容易導(dǎo)致便秘等缺點,部分患者不能堅持用藥。
在中醫(yī)方面,目前中藥攝入方式多以口服為主,需要經(jīng)過胃腸道的消化吸收,其本身需要經(jīng)腸道菌群發(fā)生反應(yīng)而成為最終的有效成分,這與腸道生態(tài)環(huán)境有著密切聯(lián)系。中藥通過影響腸道菌群,產(chǎn)生藥理作用,對腸道結(jié)構(gòu)屏障、微生物種類等產(chǎn)生改變,但其具體的干預(yù)機制仍然有待進一步探索;從已有文獻來看,目前僅有對少部分中藥作用于“腸-腎軸”的報告,如大黃、黃芪等。如何將其他作用于肺脾腎的中藥與“腸-腎軸”聯(lián)系起來,并探索其作用機制可以作為下一階段的探索研究的方向;中藥有一定的腎毒性,可能會為患者帶來腎臟的負擔(dān),從而引起腎臟疾病的加重。利用中藥相殺或不同的炮制方法可以減輕其毒性,進一步增強治療的有效性,減少可能的治療風(fēng)險,提高患者生活質(zhì)量;外治法擁有法多靈活的優(yōu)點,可以避免一定藥物的不良反應(yīng),且其能補內(nèi)治之不足,內(nèi)治與外治結(jié)合,可作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中藥的研究規(guī)模常常比較小,仍然局限于動物實驗中,但動物模型難以完全還原人體腸道的生理狀態(tài)。擴大研究規(guī)模,進一步研究腸道微生物與CKD的作用機制,對臨床治療CKD有著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雷芷晗,呂靜.基于腸腎軸理論談通腑泄?jié)岱ㄖ委熉阅I臟病[J].中醫(yī)藥學(xué)報,2022,50(1):7-11.
[2]謝建偉,焦劍.“肝腎同源”在慢性腎臟病治療中的應(yīng)用[J].中華養(yǎng)生保健,2021,39(11):8-9.
[3]姚吉強,付滿玲,袁葉飛.基于網(wǎng)絡(luò)藥理學(xué)的趕黃草治療慢性腎臟病蛋白尿的物質(zhì)基礎(chǔ)及作用[J].中國老年學(xué)雜志,2021,41(22):5006-5011.
[4]張舒飛,朱琳,周萍.慢性腎臟病與腸道菌群相關(guān)性的研究進展[J].實用醫(yī)學(xué)雜志,2020,36(12):1684-1688.
[5]吳宇,周晶晶,姜世敏,等.慢性腎臟病病因構(gòu)成及變化趨勢分析[J].中華健康管理學(xué)雜志,2021,15(5):442-445.
[6]Meijers B,Evenepoel P.The gut-kidney axis:indoxyl sulfate,p-cresyl sulfate and CKD progression[J].Nephrology Dialysis Transplantation,2011,26(3):759-761.
[7]Mafra D,Borges N A,Lindholm B,et al.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gut microbiota imbalance:An intriguing relationship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J].Mitochondrion,2019,47:206-209.
[8]Pahl M,Vaziri N.The Chronic Kidney Disease-Colonic Axis[J].Seminars in dialysis,2015,28(5):459-463.
[9]陳翀,孫偉.基于腸腎軸概念從腎-肺-大腸軸談孫偉教授治療慢性腎臟病的經(jīng)驗[J].西部中醫(yī)藥,2019,32(5):74-77.
[10]楊紅利.“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在慢性腎臟病治療中的運用[J].中國民間療法,2021,29(23):4-6.
[11]張敏,方立明,韋玲,等.抵當(dāng)湯加減治療慢性腎臟病脾腎氣虛兼血瘀證臨床研究[J].河南中醫(yī),2021,41(8):1174-1177.
[12]曹燦,蘇濤,尹新鑫,等.黃芪當(dāng)歸合劑治療慢性腎臟病的中醫(yī)療效靶標(biāo)研究[J].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腎病雜志,2021,22(11):968-971.
[13]李星瑤,趙延紅,蔡子墨,等.溫陽化濁方治療慢性腎臟病(1~3期)臨床觀察[J].醫(yī)學(xué)研究雜志,2021,50(3):72-75.
[14]王英明,李建省,閆燕順,等.腸道菌群與慢性腎衰竭的相互作用及中藥干預(yù)研究進展[J].中國實驗方劑學(xué)雜志,2022.
[15]吳晨悅,張樹明.根據(jù)“腸-腎軸”理論治療慢性腎臟病的研究進展[J].中國微生態(tài)學(xué)雜志,2020,32(3):364-368.
[16]Mafra D,Borges N,Alvarenga L,et al.Dietary Component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Disturbed Gut Microbiota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J].Nutrients,2019,11(3):496.
[17]Chen Y,Chen D,Chen L,et al.Microbiome–metabolome reveals the contribution of gut–kidney axis on kidney disease[J].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2019,17(1).
[18]畢江麗,方敬愛,張曉東,等.慢性腎臟病中腸粘膜屏障損傷研究進展[J].中國血液凈化,2021,20(12):846-848.
[19]Cao C,Zhu H,Yao Y,et al.Gut Dysbiosis and Kidney Diseases[J].Frontiers in Medicine,2022,9.
[20]Sircana A,De Michieli F,Parente R,et al.Gut Microbiota,Hypertension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recent advances[J].Pharmacological Research,2018.
[21]Fernandez-Prado R,Esteras R,Perez-Gomez M,et al.Nutrients Turned into Toxins:Microbiota Modulation of Nutrient Propertie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J].Nutrients,2017,9(5):489.
[22]Onal E M,Afsar B,Covic A,et al.Gut microbiota and inflammation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their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J].Hypertension Research,2019,42(2):123-140.
[23]焦書沛,姜晨.“腸-腎軸”理論研究現(xiàn)狀及分析[J].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腎病雜志,2017,18(7):656-658.
[24]錢虹利,謝麗萍,韋泉西,等.從脾腎論治慢性腎臟病研究進展[J].遼寧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2018,20(12):154-156.
[25]王冠然,宋立群.中醫(yī)藥治療慢性腎臟病的研究進展[J].環(huán)球中醫(yī)藥,2020,13(3):518-523.
[26]于翔,祝一葉,孔薇,等.基于《金匱要略》角度的國醫(yī)大師鄒燕勤運用大黃治療慢性腎臟病經(jīng)驗[J].時珍國醫(yī)國藥,2021,32(11):2759-2761.
[27]莊雪峰,律廣富,林賀,等.黃芪對大黃誘導(dǎo)的腹瀉模型大鼠腹瀉的治療作用及其機制[J].吉林大學(xué)學(xué)報(醫(yī)學(xué)版),2022:1-11.
[28]陳子林.腎康注射液治療慢性腎臟病3~4期的臨床研究[J].中醫(yī)臨床研究,2021,13(24):86-87.
[29]李凱,馬天鵬,牛坤,等.益智仁防治糖尿病腎病相關(guān)研究述評[J].中國中醫(yī)藥現(xiàn)代遠程教育,2021,19(3):192-195.
[30]胥雪玲.姜黃素調(diào)節(jié)尿酸性腎病大鼠的腸道菌群并改善腎功能[D].青島:青島大學(xué),2021.
[31]麥文頂.三七注射液對慢性腎衰竭大鼠腸道菌群多樣性結(jié)構(gòu)變化的研究[D].南寧:廣西中醫(yī)藥大學(xué),2021.
[32]劉嘉欣.縮泉丸對糖尿病腎病db/db小鼠腎功能保護作用研究[D].成都:成都中醫(yī)藥大學(xué),2021.
[33]蔡紅蝶,宿樹蘭,郭建明,等.丹參對糖尿病腎損傷大鼠腸道菌群多樣性的影響[J].中國中藥雜志,2021,46(2):426-435.
[34]徐卓,項想,尚爾鑫,等.丹參莖葉總酚酸對2型糖尿病腎病小鼠腸道菌群和短鏈脂肪酸的調(diào)節(jié)作用[J].藥學(xué)學(xué)報,2021,56(4):1035-1048.
[35]陳雪莉,呂勇.基于“腸—腎軸”理論探析清腎顆粒對慢性腎衰竭的預(yù)防作用機制[J].陜西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2021,44(1):77-80.
[36]韓文貝,劉瑩露,萬毅剛,等.慢性腎臟病腸道菌群失調(diào)的病理機制、治療策略及中藥的干預(yù)作用[J].中國中藥雜志,2017,42(13):2425-2432.
[37]莫業(yè)南.補脾益腎方通過調(diào)整腸道微生態(tài)影響AhR通路治療慢性腎臟病的機制研究[D].廣州:廣州中醫(yī)藥大學(xué),2021.
[38]戴銘卉,孔薇.基于腸腎軸理論探討通腑泄?jié)岱秸{(diào)節(jié)腸道菌群清除慢性腎臟病模型大鼠尿毒癥毒素的機制[J].中國中醫(yī)基礎(chǔ)醫(yī)學(xué)雜志,2018,24(8):1073-1076.
[39]陸靜波.基于尿毒素代謝調(diào)控的黃葵四物方防治慢性腎衰作用機制研究[D].南京: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2020.
[40]倪雅麗,姚宇劍,湯燦,等.縮泉益腎方與益智仁對糖尿病腎臟疾病小鼠療效及腸道菌群的影響差異研究[J].海南醫(yī)學(xué)院學(xué)報,2021,27(11):820-826.
[41]王歡,曾奧,曹蓉,等.七味白術(shù)散調(diào)節(jié)腸道微生態(tài)的物質(zhì)基礎(chǔ)[J].世界華人消化雜志,2014,22(13):1773-1777.
[42]Chen Z,Wu S,Zeng Y,et al.FuZhengHuaYuJiangZhuTongLuoFang Prescription Modulates Gut Microbiota and Gut-Derived Metabolites in UUO Rats[J].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2022,12.
[43]魏麗鳳,王琳.中醫(yī)外治在慢性腎臟病治療中的應(yīng)用[J].世界中醫(yī)藥,2019,14(8):2225-2228.
[44]易慶蓮,王億平,梁曉平.中藥腸道療法在慢性腎臟病治療中的應(yīng)用[J].中醫(yī)藥臨床雜志,2020,32(12):2213-2217.
[45]王祎熙,李霞,馮珍鳳,等.中醫(yī)內(nèi)外同治法對慢性腎臟病3~4期患者“腸-腎軸”的影響[J].現(xiàn)代中西醫(yī)結(jié)合雜志,2022,31(7):888-893.
[46]黃海平,聶開蘭,何娜,等.益腎湯經(jīng)結(jié)腸透析對慢性腎臟病3~5期患者腸道菌群、微炎癥的影響[J].國際中醫(yī)中藥雜志,2021,43(12):1199-1203.
[47]陳侃俊,王麗莉.艾灸治療慢性腎臟病的應(yīng)用及機制研究[J].針灸臨床雜志,2022,38(1):99-103.
[48]Chen H,Wang M,Chen Y,et al.Alisol B 23-acetate attenuates CKD progression by regulating the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and gut–kidney axis[J].Therapeutic Advances in Chronic Disease,2020,11:254075550.
[49]Cavalcanti Neto M P,Aquino J D S,Romo Da Silva L D F,et al.Gut microbiota and probiotics intervention: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management of cardiometabolic disorders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J].Pharmacological Research,2018,130:152-163.
[50]Hutkins R,Krumbeck J,Bindels L,et al.Prebiotics:why definitions matter[J].Curr Opin Biotechnol,2016,37:1-7.
[51]Shamloo M,Mollard R,Wang H,et al.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cross-over trial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resistant starch prebiotic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ReSPECKD)[J].Trials,2022,23(1).
[52]Esgalhado M,Kemp J A,Azevedo R,et al.Could resistant starch supplementation improve inflammatory and oxidative stress biomarkers and uremic toxins levels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A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Food Funct,2018,9(12):6508-6516.
[53]李巖.中藥保留灌腸聯(lián)合藥用炭片治療慢性腎衰竭療效觀察[J].工企醫(yī)刊,2007(5):8-9.
[54]張攀科,徐雪峰,楊科朋.藥用炭片聯(lián)合中藥直腸滴入治療慢性腎功能衰竭47例[J].中醫(yī)研究,2012,25(5):39-41.
[55]陳繼紅,劉瓊,高坤,等.孫偉教授運用“轤腎延衰”理論治療慢性腎臟病臨證經(jīng)驗闡述[J].世界科學(xué)技術(shù)一中醫(yī)藥現(xiàn)代化,2019,21(4):684-688.
[56]Mishima E,F(xiàn)ukuda S,Shima H,et al.Alteration of the Intestinal Environment by Lubiprostone Is Associated with Amelioration of Adenine-Induced CKD[J].J Am Soc Nephrol,2015,26(8):1787-1794.
(收稿日期:202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