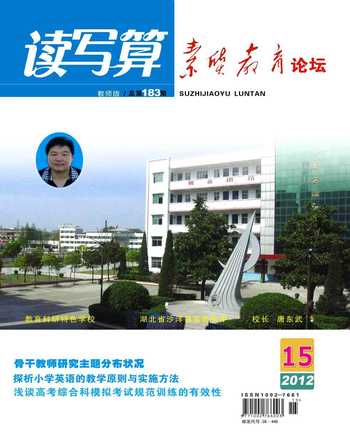把愉悅的情感滲透在英語教學中
張玲燕
在小學英語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充分考慮到兒童的心理、生理及年齡特點,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以激發興趣,把認知與情感活動結合起來,讓學生在英語學習中充分體驗愉悅,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
一、體驗樂趣,樹立學習信心
小學階段是英語的啟蒙階段,也是學習的有利時期。但對學生來說,這又是從未接觸過的嶄新學科,在新鮮、好奇的同時,也難免會有畏難的情緒。在這一學習的初始階段,教師應該循序漸進,讓學生過好入門關。一開始,我放慢速度,面向全體學生,在對每一個單詞的發音和口型,每一句話的語音語調都做到教準、教實的同時,更注重讓每個學生都有鍛煉的機會,尤其是那些性格內向的學生,更是讓他們屢屢品嘗成功的喜悅,逐步樹立學習英語的信心。在這一階段,盡量增加游戲和歌曲、表演等內容,利用英語學習中美的東西,激發他們學習的欲望,為以后的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氣氛感染,愉悅心境,營造和諧氛圍
心理學家Rogers指出:“創造良好的教學氣氛是保證進行有效教學的主要條件。”只有創造和諧輕松的課堂氣氛,才能使學生輕松愉快地走進課堂,和教師相互配合進行有效學習。在課堂教學中,可采用“微笑和點頭,專心聽他說”的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
三、創造和諧融洽的師生關系,強化教師的親和力
教和學是一對矛盾,作為矛盾雙方的代表教師和學生,如何和諧融洽師生關系,對完成教學目的至關重要: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學生心理環境中的重要因素。教師關心、愛護、尊重每個學生,師生間就能保持民主平等的關系,相互尊重,同時,也有利于學生產生積極的情感。“親其師,而信其道。”和諧、融洽的師生關系是緩解因學習造成心理壓力的關鍵。小學生的心理特點告訴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學生“親師性”較強。如果某個教師的親和力較強,他們就對某個教師有好感,學生就會熱愛尊重這位教師,那么,他們就會把熱愛、尊重教師的情感遷移到學習中來,其力量是無窮的。反之,如果不喜歡某位教師,就會對這位教師產生逆反心理,對他的課也不重視,不感興趣,也不愿意花功夫,自然也學不好。所以,教師要以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學生,要深入到學生的學習甚至生活中去,真誠地去關心他們,愛護他們,尊重他們。要和學生們打成一片,了解他們的興趣、愛好和情緒的變化,有的放矢地去幫助學生。
四、在課堂教學中注重對學生情緒的控制,激發積極情緒,消除或抵制消極情感
作為一名好的教師,要能指導學生學會控制不良情緒,減輕心理壓力。
1.創設情景,引導學生積極思維。課堂教學要始終堅持以學生實踐為主旨,教師要創設相應的教學情景幫助學生感知、理解,營造民主、互動的師生關系,讓學生主動參與到教學中來,自主地尋找問題,發現問題,然后自行解決問題。如學習有關西方的圣誕節文化時,我先引人中國的春節。設計了幾個問題讓學生思考回答:What is your favourite festival?What festival is the most impmtant in China?What do you do before Spring Festivals? What presents do you get? What do people say to each other when they meet?這就為新課作了很好的鋪墊。課后,我還讓學生自制節日賀卡,用英語寫上祝福語,送給他的親朋好友。像這樣將學生置身于特定的情景和英語氣氛中,學生不知不覺就參與到課堂活動中去,從而促進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同時也形成了教學相長、生動活潑的課堂局面。
在小學牛津版英語教材中,通常運用錄音機、圖片、語言描述、動作表情演示等方式,創設和渲染氣氛,使學生自然轉向置身于教材的情景之中,在自覺不自覺中去看、去聽,去說,去感受,達到掌握運用語言的目的。例如在教day at the Palace Museum時,我給學生展示一張故宮的圖片,告訴學生:This is the Palace Museum.接著出示一張故宮的平面圖,并介紹道:Do you know these different Palaces?向學生介紹故宮里的重要宮殿:Taihe Palace,Baohe Palace、Huangji Palace、FengxianPalace等。并且告訴學生:There are mariybeautiful things to see in the Palace Museum.We can see some old things such as the goldenthrone,some works of art, pottery and someChinese paintings there.這樣既提高了學生的積極性又幫助學生理解了生詞的含義。
2.恰當運用肢體語言活躍課堂氣氛。課堂教學中教師運用一些姿態表情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活躍課堂氣氛,收到直觀的效果,提高學習的效率。如教“現在進行時”的時候,教師可以傲各種動作,如放風箏、跑步、關門等,讓學生問答:What are you doing?l''m fly mga kite,等。正因為這些動作表情直接作用于學生的各種器官,從而能引起大腦的神經興奮,激發興趣。
3.在實踐中滿足學生的“成功欲”。每個人都渴望成功,成功會增強人的自信心,激發學習的興趣和熱情,激勵人們去追求更高的目標。教師在教學中要為學生創造成功的機會,激發他們潛在的成功期望,讓他們更多地嘗到成功的喜悅。但在平時的教學中一定要注意,教師要根據不同類型的學生,提出不同的學習要求,給每個學生有展示的機會。如果,有的學生出了差錯,也要講究糾正錯誤的技巧,多激勵,少批評;多講道理,少責備,避免挫傷學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五、創造輕松愉快的學習環境,營造和諧的心理氛圍
一節課的課堂環境如何,對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影響很大。教師要為學生創造一個輕松愉快的學習環境,要為學生營造一個和諧的心理氛圍,這對培養學生樂學的良好的心理素質和提高學習效率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教師要以滿腔的熱情全身心投入課堂教學,表情要輕松,目光要親切,態度要和藹。其次,要定于深厚的教學情感。第三,增強教學的藝術效果。教師教學藝術感投入的多少,教師教學成功與否,又與教學藝術感染力有直接關系。因此,我們每個教師想提高課堂教學效率也必須提高教學藝術水平。
總之,作為一名小學英語教師,在不斷提高文化素質和業務能力的同時,也必須用自己積極的情感去感染學生,讓愉快的情感始終貫穿于英語教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