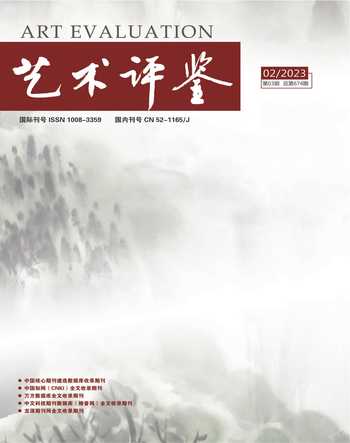聲音景觀視域下的西藏山南春耕音樂
張銳
摘要:西藏是一個自人類誕生以來就有著農業活動的地方,其農業萌芽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隨著農業發展而衍生出的春耕音樂,通過視聽結合構成意象空間,是表達人們思想情感和社會現象的一種藝術形式。本文將以“山南春耕音樂”為研究對象,從“聲音景觀”的定義出發進行解讀,試圖搭建起“春耕音樂”與“聲音景觀”兩者之間的“音樂”這一橋梁,以此來探究西藏山南春耕音樂中可見、可聞,與不可見、不可聞的音樂文化。
關鍵詞:山南春耕? 春耕音樂? 聲音景觀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3)03-0069-04
一、聲音景觀
“聲音景觀”簡稱“聲景”。該詞匯最早由20世紀60年代末加拿大著名音樂學家、聲音研究者謝勒梅所提出,同時也是近年來西方民族音樂學家常用的一個概念。“聲音景觀”以背景、聲音以及意義為研究對象,其中“背景”因素包含音樂的地域環境、表演場域以及演奏行為等;“聲音”因素包含音樂的體裁、風格特征等;“意義”因素包含音樂的社會功能、使用方法、文化內涵等。湯亞汀在《音樂的流動景觀與家門口的民族音樂學》一文中引述了美國音樂學家謝勒梅《聲音景觀:探索變化中的世界的音樂》一文對“聲音景觀”的定義:“一種聲音景觀,即一種音樂文化有特色的背景、聲音與意義。”其定義中的“背景”是指“表演地點”和“表演者與聽眾的行為”;“聲音”指“音色、音高、音值、音強”;而“意義”則指音樂本身的含義及其對表演者與聽眾生活的含義。國內學者季凌霄總結歸納將“聲音景觀”定義為從時間與空間的維度來考察我們所在的周圍環境,通過人的聽覺、視覺等方式來解讀聲音文化的意義。除此之外,聲音景觀也包括那些聽不到的、看不到的聲景。通過以上眾多學者的觀點可以得知,“聲音景觀”作為一個外來引進詞匯,學者們對它的概念進行了新的詮釋,可總結為:是通過“背景、聲音、意義”三大元素來探究音樂文化的一種藝術理論。
“聲音”是由物體振動而產生的聲波。對于“景觀”的界定,音樂學家薛藝兵在《流動的聲音景觀——音樂地理學方法新探》一文中認為,在地理學中“景觀”是一種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綜合體,而在音樂學中“景觀”指的是一種視覺可見的和視覺不可見的音樂。所以,我們需把“聲音景觀”這一學理概念放置到音樂語境中,并賦予它音樂的特性,以此來探究音樂中的聲音景觀。
綜上所述,“聲音景觀”就是一種在內隱與外顯相結合的基礎上,通過對音樂的背景、聲音以及意義進行可見、可聞,與不可見、不可聞深描的一種方法論,運用此種方法論來探究山南的春耕音樂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之一。
二、山南春耕音樂“聲景”中的“背景”
聲音景觀是一種從音樂背景、聲音以及意義三層面來進行的解讀。它對音樂背景的研究主要從音樂的地域環境和表演場合等視域出發。山南春耕音樂的形成由無數次的歷時性文本和共時性文本疊加而成,所以它不是由單一的元素構成的,因此,研究山南春耕音樂的背景應將聲音景觀融入其中。
(一)山南春耕音樂的地域環境
山南春耕音樂的地域環境主要由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兩方面構成。
自然地理環境是指一定社會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山南市位于西藏自治區南部,岡底斯山脈至念青唐古拉山脈以南,雅魯藏布江中下游地區。它的地形屬于典型的谷地,土地資源非常豐富,氣候為溫帶干旱性氣候,江河眾多,占據著全市最大的河流雅魯藏布江,平均海拔在3700米左右。具有“西藏糧倉”美譽之稱的山南種植著大量的春耕作物,春耕音樂也隨之孕育而生。
人文環境指的是社會本體中所隱藏的無形環境。受到萬物有靈觀念影響的山南人民,在原始時代無法正確認識到農業生產的客觀規律,便幻想著有偉大的農業神在控制著農作物的生長,主宰著他們的命運,于是他們便會祭祀農業神靈,而在祭祀中所唱的音樂作為“人——神”交流的媒介,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類以祭祀農業為基礎而衍生出的音樂,筆者認為它們也屬于春耕音樂的一個重要部分。當然,除了上述帶有祭祀性質的春耕音樂以外,山南勞動人民在日常的耕作中也會唱具有勞動性質的春耕音樂,雖然曲調不一,但是每種勞動都有與之相對應的勞動歌。如耕地有耕地歌、播種有播種歌以及灌溉有灌溉歌等,種類繁多。
(二)山南春耕音樂的表演場合
楊民康在《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一種從藝術切入文化情景的表達方式》一文中提到美國表演民族志學者理查德·鮑曼曾說過:“表演是交流行為的一種方式,是交流時間的一種類型。……它以某種特殊的方式被框定,并在觀眾面前予以展示。對于表演——表演的實際實施——的分析,凸顯著交流過程的社會、文化和審美維度。”這段文字中所闡釋的“表演”是執行者與被執行者在特定語境中相互交流的過程。
山南春耕音樂的表演場合主要有兩處,即有關農業祭祀的節日和農田。前者指的是人們為了能夠在春耕過程中實現莊稼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愿望,會在特定的時間舉行農業祭祀節日活動。如春播之時的開耕節,在這個開耕儀式中,人們會在儀式開始之際唱開耕歌,儀式結束后山南有些地方還會唱藏戲、跳果諧。這時春耕音樂的表演場域有一定的講究,一般會選擇在去年收成較好的農田或對當地有特殊意義的農田里舉行。原因是,在萬物有靈的西藏,人們認為每一塊田地都有自己的守護神,舉行開耕儀式是希望執儀者能夠通過此項儀式活動達到與神靈交流的目的,其中音樂在這個儀式中扮演著媒介的角色,同時執儀者與信眾在這一特定的場域中彼此之間也有了充分交流,具備了表演的性質。總之,春耕音樂作為開耕節音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娛人、娛神的功能。后者指的是山南人民為緩解在田地里勞作時的疲憊而唱起的春耕音樂,此時的音樂具備了勞動歌的性質,有節拍交替變化、節奏自由、旋律優美、歌詞朗朗上口、內容通俗易懂等特點。人們歌唱時會隨著身體的律動而做出與勞動相應的舞蹈動作,這時的表演行為主要是服務于春耕,同時也具備了娛樂、交流、緩解疲勞等功能。
綜上所述,山南春耕音樂的表演主要集中在農田和節日兩大場域,不同的場域中所演唱的春耕音樂發揮著各自的作用。趙書峰在《儀式音樂文本的互文性與符號學闡釋》一文中論述到:“儀式中的能指是以音聲的形式體現在儀式場景中,形成一系列‘能指域(或者稱為‘音聲場域)以及與其對應的‘所指域(象征功能域)。儀式的有效性、靈驗性是依靠上述兩者構成的復合‘域作用下完成的。”以上這段文字中筆者認為,“能指域”指的是演唱者在相對不固定的場域中演唱,但是無任何宗教性的意義。當山南春耕音樂的表演場域在正常勞作的田間時,他們所唱的歌曲是“能指”的,而所在的農田就是一個典型的“能指域”。“所指域”指的是在特定的語境中表演,并且賦予了“語境”宗教性的寓意。當山南春耕音樂在節日祭祀性的場域演唱時,他們所唱的歌曲是“所指”的,執儀者通過演唱歌曲向神靈傳達自己的心愿,此時的歌曲是演唱者與聽眾彼此之間進行交流的媒介,從而具有了宗教性的象征意義,而進行祭祀的場合就是“所指域”。
三、山南春耕音樂“聲景”中的“聲音”——以克松社區開耕節為例
在聲音景觀中,對于“聲音”這一解讀主要從音樂本體出發,通過剖析音樂中的可讀文本,以達到解讀春耕音樂的目的。
(一)克松社區開耕節簡述
藏歷新年結束后,按照山南的當地習俗,家家戶戶便開始準備春播事宜,而春播的第一步就是舉行“開耕節”。山南開耕節每年舉行的時間按照藏歷以及物候特征進行推算,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定的差異,其時間一般在藏歷的二月或三月份左右。山南市乃東區克松社區的開耕節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該村是第一個推翻莊園經濟的,是民主改革的第一村 ),所以每年都舉辦得非常隆重。克松社區開耕節的大致流程可分為兩天:第一天即節日前一天裝扮耕牛以及準備節日所需的祭祀用品;第二天即節日當天,早晨八點左右儀式開始舉行,人們到達祭祀場域進行煨桑,之后便開始唱開耕歌(歌詞的寓意為五谷豐登),此環節結束后人們開始敬獻哈達(敬獻對象:鐵牛、騎手、播種者、每戶的代表人),隨后便開始先用鐵牛耕地,然后村民進行松土(邊松土邊唱開耕歌),當整個開耕儀式流程結束后,村民們就聚坐在一起唱藏戲、跳果諧。該社區舉行開耕節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在開耕前征得祭祀對象“薩達”的同意,并且告知“薩達”離開將要開耕的這塊土地,免得受到傷害;二是希望莊稼的守護神能夠保佑土地肥沃和產物豐收。
克松社區的開耕節是山南春耕音樂演唱的典型場域之一,對其進行研究可以了解其折射出的山南春耕音樂的共性特征。
(二)開耕歌的音樂本體分析
張伯瑜老師在《論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音樂本體分析:認知與結構》一文中認為:“音樂具有結構性,所以才有音樂分析。結構是作品的內在骨架,在音樂表層上往往看不出來,需要進行專業化的分析才能把其體現出來。”音樂本體分析是對作品內在骨架的剖析,通過揭示音樂文化的內涵,從而達到深層認知音樂的目的。
克松社區開耕節儀式所呈現的歌舞具有旋律優美、節奏自由以及歌詞通俗易懂等特點,且男女老少皆可唱。歌曲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早上八點左右村民們有序排列站成三排時唱的開耕歌。這首開耕歌的歌詞大意為“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其演唱時間是在藏歷二月或三月份左右,演唱地點在克松社區“開耕節”儀式場域。儀式當天會演唱兩次,分別是早上八點左右唱開耕歌時和執儀者排隊松土時。演唱的人員為克松社區村民,演唱者男性、女性皆有,他們在隆重、莊嚴的氛圍中將開耕歌唱給了這塊土地的薩達,以此來告知薩達人即將要開墾這塊土地,希望它暫時離開這塊土地免受傷害,同時也希望它能夠保佑莊稼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此首開耕歌的隊形排列共有兩種,一是在唱開耕歌時,排列成三橫排且隊形不變貫穿全曲:第一排,按從左到右順序依次為男信眾者(1名)、女信眾者(2名);第二排,按從左到右依次為女信眾者(1名)、男信眾者(9名)、女信眾者(5名);第三排則與第二排隊形排列完全相同,每一排的演員都手拿綁有哈達的八齒木耙。 二是執儀者在松土時,共有四橫排且隊形保持不變:第一排,執儀者全為男性,共9名;第二排和第三排執儀者全為女性,各12名;第四排從左至右依次為女信眾者6名,男信眾者6名,女信眾者3名,每一排的演員同樣手拿綁有哈達的八齒木耙。這時信眾者們與前面唱開耕歌時的狀態發生了變化,在演唱時還增添了與松土相應的舞蹈動作。
經過筆者的調查,分析出克松社區“開耕節”中的這首開耕歌曲為單聲部的二段體結構,共A、B兩段,調式為F羽六聲調式(加變徵),無引子和結尾,整體節奏較為自由,有一定的彈性,音域較廣。
A樂段共有兩個樂句,其主題材料相同,各3小節,屬于非方整性樂句,拍號為4/4拍,其速度以每分鐘65拍的行板進行。首先a樂句由調式主和弦4b6ⅰ小三和弦為主題材料貫穿全句,采用了大量密集的十六分音符,音的實值較短,音程之間以級進為主,音域為八度,旋律走向上下波動進行。第一小節的次弱拍與第二小節的強拍之間的連音線符號使旋律的走向更加具有衍生性,第二小節也是唯一一個小節出現了F羽六聲調式的偏音——變徵,出現了兩次,渲染了一種抒情、婉轉的氛圍,尾音以平行一度的純音程結束,整個樂句旋律柔和。a1樂句的主題材料是在a樂句基礎上的變化發展,共有3小節,這一樂句出現了大量的“附點”節奏型,連續的高音推動著旋律向前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該句和a句的結尾相同,同樣以尾音平行一度的純音程結束,起到了呼應的作用。
B樂段只有一個c樂句,共四小節,屬于方整性樂句,此時的拍號由原來的4/4拍變成了2/4拍,其速度以每分鐘70拍的小行板進行,調式依然沿用了F羽六聲調式(加變徵)。c樂句以新的節奏音型出現,全句采用了大量的“切分”型節奏,改變了常規的節奏規律,使音符的強拍和弱拍發生變化和強調,大量調式主音的出現使旋律具備了羽調式的柔和。音程多以小二度、小三度進行,旋律在大量“切分”節奏型的影響下進入了全曲的高潮部分,最后結尾以色彩柔和的小三度結束全曲。該樂句一共反復了三次,每次反復旋律相同但歌詞不同。B樂段的演唱者屬于齊唱的形式,演唱氛圍也由A樂段的莊重轉變為輕松、歡快的氣氛。
綜上所述,這首開耕歌曲屬于典型的單聲部二段體結構,同時具有民間音樂節奏自由、歌詞通俗易懂的特點,全曲采用的調式調性為F羽六聲調式(加變徵)。
四、山南春耕音樂“聲景”中的“意義”解讀
美國音樂學家謝勒梅將“聲音景觀”中的“意義”定義為“音樂本身的含義以及表演者與聽眾生活的含義。”在這一定義中,“聲音景觀”的“意義”除了可見、可聞的本身含義之外,還有情景中不可見、不可聞的含義。
一年之計在于春。農業是人類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產的首要條件。山南作為西藏農業的主要種植區,春節過后便進入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耕備耕期。當地農民在春耕時為了緩解疲勞就會唱起娛人、娛神的春耕音樂,該音樂體裁在文化內涵中具有可見、可聞和不可見、不可聞的兩大意義。
(一)可見、可聞的山南春耕音樂
如今,在這個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電子音樂產品比比皆是。現在的我們想要聽音樂似乎不需要去特定的娛樂場所,只要一個電子音樂產品,如手機就可以實現聽音樂自由。所以當代人把音樂順其自然地理解為了一種聽覺的反應,若要談論到音樂中的視覺便非常陌生。但是別忘了,在1887年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以前,人們是無法記錄聲音的,若想要聽音樂就必須到固定的表演場所去觀賞聆聽。正是由于這種固定場所的存在,才既有“聽”到的音樂,也有“看”到的音樂,所以在探究音樂時不可忽視音樂所呈現出來的一系列情景。
山南春耕音樂是一種典型視聽相結合的音樂形式,其中可見、可聞的音樂情景元素非常之多,但是它們都有著鮮明的邏輯。如在解析山南春耕音樂中,可以發現可見的音樂情景分為場域內和場域外兩大類,其中場域內又分為表演現場、表演者以及表演行為;場域外可分為現場的聽眾和現場的互動表現。而可聽的音樂情景同樣也可分為兩大類即場域內和場域外,其中場域內包含了音樂的節奏和節拍旋律;場域外包括觀眾的聲音和現場互動的表現。這些可見、可聞的音樂元素都有著明確的對應對象,并且每一對象所呈現出來的表征都具有獨特的寓意。如在可見場域內,表演者即動作的發出者在表演時首先會根據固定程式進行演出,然后再根據動作發出者的主觀意愿進行一系列的即興性表演,當然這種即興性并不是隨意、毫無章序的,而是在固定程式的基礎上進行的即興創作。
綜上所述,山南春耕音樂的現場除了可聽的音樂元素以外,可見的音樂元素無論是場域內還是場域外都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音樂作為一種時間與空間相結合的藝術,可聽的音樂元素可以通過時間進行傳播,但是可見的音樂元素則是需要在多維的空間內進行的,所以可見、可聞的這兩種方式是傳播音樂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但是根據筆者目前所搜集到的文獻資料來看,當下我國許多學者對于音樂的研究一直遺存著“音樂是時間的藝術”這一觀點,往往忽視了空間其實也是音樂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不可見、不可聞的山南春耕音樂
音樂作為一種藝術與文化相結合的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當我們把它看作是一種隱含與顯現兼并的文化因子時,人們常常會忽略它的隱含意義。山南的春耕音樂除了上述所描述的顯現文化因子之外,同樣也有一些不可見、不可聞的音樂元素,這種內隱的音樂元素同樣值得我們去深入挖掘。不可見的山南春耕音樂主要包括選擇場域的寓意、執行者表演時的心理活動和外在行為、現場觀眾觀看時的心理活動和外在行為等宗教象征性寓意。而不可聞的山南春耕音樂主要包括表演者的“無聲即內心”、響器的“無聲”以及現場讀者的“無聲”等一切聽不見的聲音,卻又彰顯出山南的春耕文化內涵。如山南春耕音樂歌詞具有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寓意;歌曲的旋律、節奏都具有與勞動韻律相結合的特點;儀式場域里所進行的煨桑、安放白石、安放切瑪等都體現了宗教元素的內涵。這些文化內涵在春耕音樂中,使音樂在娛人功能的基礎上增加了娛神的功能,以此極大地豐富了春耕音樂文化。
五、結語
西藏春耕音樂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縱貫數千年,其中蘊含著無數寶貴的音樂文化遺產:果諧、諧欽、勒諧以及藏戲等。這些歌舞和戲劇都是通過辛勤的勞動人民世代傳承下來被民間接衍的。聲音景觀是近年來民族音樂學界頻繁出現的一個新概念,筆者通過這一學理概念對山南的春耕音樂進行了剖析,得出文化語境中的音樂由眾多內隱和外顯的元素構成的結論,但是目前我國對音樂內隱文化的探究較為缺乏,基于此,相關人士應該注重對其進行闡釋。
參考文獻:
[1]湯亞汀.音樂的流動景觀與家門口的民族音樂學——讀謝勒梅新著《聲音景觀:探索變化中的世界的音樂》[J].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01(04):91-94.
[2]薛藝兵.流動的聲音景觀——音樂地理學方法新探[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8(01):83-88.
[3]楊民康.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一種從藝術切入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J].民族藝術,2016(06):16-22.
[4]趙書峰.儀式音樂文本的互文性與符號學闡釋[J].音樂研究,2013(02):19-26.
[5]張伯瑜.論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音樂本體分析:結構與認知[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4(04):1-7+91-92+175-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