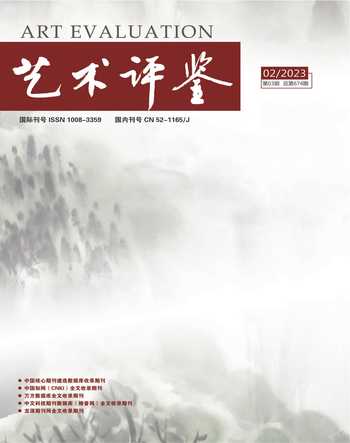論藝術歌曲《紡車旁的格麗卿》的特征及演唱方法
曹嘉惠 王冬弘
摘要:《紡車旁的格麗卿》是舒伯特于1814年創作的一首藝術歌曲,這也是他創作的第一首狹義上的藝術歌曲,西方音樂史以這首歌曲的誕生為標志將1814定義為藝術歌曲的誕生之年。本文通過對《紡車旁的格麗卿》的創作背景及藝術特色、藝術價值的分析,探討演唱者如何通過細膩的音樂處理來表現《紡車旁的格麗卿》的情感與魅力。
關鍵詞:舒伯特? 《紡車旁的格麗卿》? 藝術歌曲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3)03-0077-04
弗蘭茨·舒伯特是浪漫主義時期奧地利作曲家,他的創作主要集中在藝術歌曲領域。其藝術歌曲結合了詩歌、人聲與鋼琴,使古老的德國藝術歌曲“利德”散發出了新的活力。舒伯特出生于維也納的郊區,從小就表現出了非凡的音樂天賦,很快就超過了給他上課的父親和哥哥的水平。 1808 年,十一歲的舒伯特被送到了寄宿學校,在那里他熟悉了約瑟夫·海頓、沃爾夫岡·阿瑪迪斯·莫扎特和路德維希·范·貝多芬的管弦樂。1813 年底,他離開了寄宿學校,回到家與父親同住,在那里他開始學習該如何成為一名教師。但他同時繼續與安東尼奧·薩列里一起學習作曲,并且仍然多產。1828 年 3 月,他舉辦了一場自己的作品音樂會,遺憾的是這也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風光的音樂會。他在 8 個月后去世,享年 31 歲,官方將病因歸咎于傷寒。
舒伯特在世時只在維也納有一小群崇拜者,但在他去世后的幾十年里,人們對其作品的興趣大大增加,如:門德爾松、舒曼、李斯特、勃拉姆斯等就是其作品的擁護者。今天,舒伯特被列為西方音樂史上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其作品仍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舒伯特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共留下藝術歌曲600余首,有著“藝術歌曲之王”的美譽,而《紡車旁的格麗卿》則是他最重要的藝術歌曲作品之一。筆者將分析這首歌曲意義非凡的原因,并探究作為一名演唱者該如何在最大限度上表現出該歌曲的情感與魅力。
一、《紡車旁的格麗卿》的創作背景
1813年底,為了避免服役、補貼家用,舒伯特在父親的學校里成為一名老師,同時進行音樂創作。舒伯特熱愛浪漫主義文學,此時19世紀歐洲又正逢由文學領域興起的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浪漫主義思潮,并很快蔓延到了音樂領域,在教課的間隙中,他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偉大詩人的崇拜——將他們的詩歌譜寫成歌曲。至此,西方音樂史上立起了一道新的里程碑,古典主義時期曾經被認為是雕蟲小技的藝術歌曲,在舒伯特的藝術歌曲創作中得以確立,并成了我們今天所聽到的欣賞價值極高的音樂藝術品。1814年也被稱為“藝術歌曲的誕生之年”。
二、《紡車旁的格麗卿》的藝術特色
歌曲采用了德奧藝術歌曲的典型音樂結構——分節歌的形式,大量重復句的使用正是德奧民間歌曲的特征。該歌曲的曲式結構為:前奏2+A9{a4+a5}+間奏2+B16{b8+b8}+A9{a4+a5}+間奏2+ C26{c8+c12+c”6}+間奏5+ A9{a4+a5}+間奏2+ D28{d8+d8+d”12}+ A4{a4}尾奏d2。歌詞取材于歌德的詩劇《浮士德》悲劇第一部第十五節《格麗卿的房間》,少女瑪格麗特被浮士德匿名贈予一副耳環,她愛上了風流英俊的浮士德。章節描繪了瑪格麗特對浮士德的愛慕,她每時每刻都牽掛著他,就連在紡車旁干針線活時也會因不能看見他而患得患失。詩歌的內容本身充滿了重復的語句,歌曲中作為基本主題反復出現的A段,在詩歌中也是在同樣的位置反復出現的,與分節歌的形式十分相配。在《紡車旁的格麗卿》之前,以貝多芬、莫扎特的創作為代表的藝術歌曲,甚至是舒伯特本人的早期作品如《哈加的悲歌》中,鋼琴聲部都只有“伴奏”的功能,單純具有襯托人聲旋律的作用,雖然典雅精致但是缺少朗誦性,不符合狹義上藝術歌曲的特點,這首歌曲開創性地使用音樂為歌德的《浮士德》描繪布景,讓音樂與詩歌產生了共鳴,是典型的德奧浪漫派藝術歌曲——德國利德。
(一)音樂與詩歌相互襯托
與器樂曲不同,藝術歌曲是在濃厚的文學熏陶下誕生的產物,每個作曲家都有著自己偏愛的詩人和題材。如馬勒的晚期藝術歌曲多采用充滿對生命與死亡的思考的呂克特詩歌;拉赫瑪尼諾夫則傾向于采用同時期愛國詩人普希金、托爾斯泰等人的詩歌;而于舒伯特而言,德國詩人席勒與歌德是他最為青睞的題材。雖然舒伯特使用《浮士德》作為題材有向歌德以及他的詩歌表示崇高敬意的成分,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在通過音樂“復刻”詩歌——作為19世紀德奧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他更多的是通過作曲來詮釋自己對《浮士德》的理解,在洞察詩歌韻律和形式基礎的基礎上擺脫詩歌外部結構束縛,對詩歌的內涵進行自己的解讀。這體現出舒伯特在早期就具有了同時兼顧各種表現因素的能力
曲目以變化分節歌的結構完成,和聲大部分時間都在小調中進行,其中穿插著一些頻繁集中的遠關系轉調,具有很強烈的語氣色彩,如第13小節:“沒有他在身邊,我的心如同墳墓”的調性由上一句的C大調轉變為d小調。每一句歌詞都是弱起,以契合主人公幽咽的語調。分節歌的A段不停地在新材料B段、C段和D段之間重復:“我心緒不寧,我心事重重,我再也、再也不能平靜。”
在B段中,格里卿歌唱浮士德的離去對她的折磨之深:“我若失去他,就像失去生命,我頭腦昏昏沉沉,神志模糊不清。”從20小節起出現了大量同音反復,效仿格里卿失神地喃喃自語,第25小節旋律上揚,隨后又下落,在28小節停留在相差八度的屬音上,通過旋律的跌宕突顯出格里卿因害怕失去浮士德而失魂落魄的狀態。
在C段中,格里卿回憶著記憶中浮士德的樣子,她在任何曾經見到浮士德的地方等待:窗邊、門前等。她想起舉止優雅、儀表堂堂的浮士德,格里卿想念他的擁抱和親吻。整個樂段的旋律線條始終上行,愈發激昂,和聲的走向也不復之前的晦暗色彩,并且頻繁地出現了轉調,由晦暗的小調逐漸轉為明亮的F大調,以豐滿的音響效果配合上文提到的那些畫面:d—a—F—g—bA—bB。這一創作手法頻繁出現在舒伯特日后的歌曲創作中,如《你是安寧》中“只憑你光輝的一瞥”這一句,舒伯特使用了由降E大調到降C大調的美妙轉調,和《紡車旁的格麗卿》一樣給人以晴光泛彩的明亮之感。格里卿深陷甜蜜的回憶無法自拔,無法控制自己的思緒,當唱到 “他的吻”時,歌曲迎來了情思奔放的巔峰,單詞“吻”被加上了延音記號,隨即人聲進入休止,扮演紡車的鋼琴伴奏亦戛然而止,暗示少女格里卿已陶然忘情,不能繼續手中的工作。接下來的3小節是連接A段與D段的橋梁,鋼琴在“很弱”的力度下重新彈奏起不協和的和弦,音樂重新跌回平靜但憂郁的d小調中,正如格里卿從回憶中醒來,重新拾起針線回到現實。
再次重復A段的自言自語后,火熱的愛情再一次占據了格里卿的內心,D段第83小節出現了漸強記號,并且在“將他抱緊,將他親吻”這兩句歌詞上就已經標記了f和ff,之后的音高與力度不僅沒有下滑,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sf力度,將主人公對情人的思念毫無保留地表達。隨著鋼琴織體的漸弱和漸慢,整個作品走向了取材于A段材料的尾聲,格里卿的呢喃消失在了紡車的轉動聲里。
(二)鋼琴伴奏與意境的結合
舒伯特通過典型的“描繪性”音型引導聽眾將聽覺與視覺聯結,將音響視覺化。例如鋼琴伴奏一開始便以連綿不斷的六連音扮演正在轉動的紡車,左手八分音符配合著斷斷續續的節奏型代表著格麗卿踩紡織機腳踏板的動作,配合著右手連續獨立旋轉的十六音符營造了不安和焦慮的氛圍,為格麗卿隨后的喃喃自語做鋪墊。在第二段句末,當唱到“他的吻”處時,由于格麗卿已陶然忘情,沒有注意到紡車隨著記憶中浮士德的靠近旋轉得又急又快,以至于扯斷了紡線,使原本不停旋轉的紡車突然停了下來。此時鋼琴伴奏突然從流動音型變為柱式和弦,連續不斷的音型突然變成具有結束感的穩定音型,正是在模仿驀然停止轉動的紡車,并將全曲推向了一個小的高潮。片刻之后,格麗卿回到了現實中,緩緩地繼續搖動著紡車。此時人聲消弭,間奏的旋律斷斷續續地響起,分解和弦式鋼琴伴奏逐漸恢復流動,展現了意猶未盡的樂思。
此外,為了保持音樂描寫的一致性和完整性,鋼琴伴奏的尾奏使用了前奏的材料,從歌曲內容上可以解讀為:格麗卿在傾訴過對浮士德的思念后不得不回歸現實,繼續著手頭的工作;從音樂性上來看,尾聲與前奏的統一性使全曲首尾相銜接,在原有的基礎上達到了更高的藝術效果,全曲的音樂性得到了升華。
三、《紡車旁的格麗卿》演唱分析
(一)咬字與語言
《紡車旁的格麗卿》用德語演唱,需要表演者掌握詩歌的語言,保證輔音清晰、元音飽滿。例如:第一句“我已失去安寧,我內心沉悶”沒有經過長久德語發音練習的人很難將“ist schwer”中四個輔音清晰自然地連讀,演唱者需要由慢到快將歌詞讀熟,再根據歌曲的速度節拍朗讀歌詞,最后再加入旋律。在B段格里卿喃喃自語的部分,大量的同音反復使旋律帶有強烈的宣敘調色彩,演唱者應注意德語的頓挫和韻律,不可依賴曲譜上意譯過的中文翻譯,而是應該認真查明每個單詞的意義,準確地將需要強調的單詞或音節把握住。通常,作曲家會將語氣較重的詞語放在強拍子上,因此遵循4/4拍內的強弱變化也有助于增強歌唱的抒情效果,作曲家通常會將本就為重讀音節的部分置于位于整個小節的最強拍,演唱者也應該加以強調,將單詞中的重讀音節唱出阻尼感。在德語作品中,除了在日常的練聲中經常練習的常規元音外,還會遇到三個德語特有的變元音,因此平時要將這些元音加入練習。
(二)演唱技巧
“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既得其術,即可至遏云響谷之妙也。”歌唱的方法不過是氣息的科學運用與發聲器官的舒展擴張,難點在于將兩者協調地結合在一起,并在一首歌曲中從容地將正確的發聲狀態保持到結束。
這首作品的曲式結構為分節歌形式,A段共出現了3次,每一次歌唱的情感要都要較上一次更加細膩,推進式地重復歌唱,而不是單一地將一段缺乏層次的旋律復述。在第一次出現時,演唱者不能太過追求放大格里卿哀怨的心境,如果第一次唱這句話就用上最豐沛的感情,會導致整首回旋曲缺少層次,演唱者只需要用嘆息般的語調輕輕吟唱就足夠。在第二次、第三次演唱時雖然逐漸展露出思念成疾的痛苦,但依然要在作曲家的力度標記下歌唱,以達到歌聲在強弱快慢之間轉折徘徊的效果。在第10小節“我再也不能找回平靜”中存在一個由do到fa的四度跳音,這里不但涉及由低音到高音的連接,還涉及由元音“u”到元音“i”的轉換,由于較高的音為閉口音,演唱者容易出現“擠”“卡”等技巧上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演唱者在這一句開始前就為高音做準備,在fa的高位置上唱前面的中音區,避免出現因氣息不夠深沉而出現的咽部肌肉代償。在練習時可以暫時省略兩個元音之間的輔音“t”來對這一旋律中的元音轉換進行專項訓練。在第29小節“我可憐的心,已經碎裂成片”中,作曲家使用了一連串下行的音符來表現格麗卿失魂落魄的心境,在這里演唱者需要注意聲音的狀態,不要隨著音高的降低而變化,應始終保持后咽壁積極抬起的狀態,讓聲音始終保持在高位置。
兩小節的伴奏之后,歌曲進入了第二部分。作為回旋曲主題的A段第二次出現時演唱者可以加入更明顯的強弱變化,和第一次出現時形成對比。C段主要內容可概括為格麗卿沉浸在與浮士德有關的回憶中,結尾的“他的吻”是整首歌曲的第一個高潮,在演唱C段時情緒要“如潮水般”層層遞進,凸顯出格麗卿愈加熱烈的漸進式情緒變化,c與c兩句不需要使用雄厚的氣息,避免破壞溫柔恬靜的音色,直到第65~68小節將歌曲推向第一個高潮,演唱者將力量厚積薄發,將整段在這一特強的音上圓滿結束。在C段中作曲家使用了大量的不協和音以及半音來描寫格麗卿憂郁痛苦的思念,演唱者應重點熟悉這一部分的音準,在練習這一部分時可以先唱音名,直到內心聽覺完全熟悉了旋律的走向,再加入歌詞。
5小節的間奏之后歌曲進入第三部分,A段再次重復,演唱者可以較前兩次更加夸張地表達這一段的情緒,比如將第81小節的“永遠”一詞加以強調;或通過忽略吸氣口,將78小節到82小節進行連音處理,一口氣唱完“我再也不能找回平靜”這一句歌詞來表現出角色苦悶的語氣。在接下來的2小節間奏中,演唱者需要在短暫的時間內進行充分的休息,如調節聲帶狀態、穩定喉頭位置、平復呼吸等,因為歌曲即將進入節奏緊湊、旋律激進的D段,演唱者若在疲勞的狀態下演唱,面對接下來唱到頻繁出現的高音時會很被動。另外,雖然在曲譜上從101~111小節都標記了sf特強,但是在演唱時需要靈活應變,若一味地以最強音演唱,則這10小節只能以旋律的變化來區分層次,會導致音響效果僵硬,應注意讓聲音的強弱隨著調式的變化而加強,達到作曲家要求的層次分明效果。在中高聲區連續的歌唱需注意保持喉頭的穩定,尤其是在高音區遇到閉口音的時候,如第95小節的“wie”,演唱者需要用唱開口音的開闊狀態唱閉口音“i”,又如第99小節的“ge”這一音節,在第98小節,歌曲迎來第二個旋律與情緒的巔峰,是這首體量龐大的藝術歌曲中最激動人心、最有力的部分。格里卿痛定思痛、情難自禁,她高聲宣誓道:“如果能再次見到浮士德,定要與他長相廝守,直到死亡讓我們分離!”這一句充分表現了格麗卿滿懷激情的內心世界,作曲家標注力度記號依然為特強,演唱者要提前準備好飽滿的氣息,橫膈膜保持下沉的狀態,要求演唱者聲音高亢、振奮人心但不聒噪刺耳,將這句話唱出激情澎湃的重量。但是情緒的宣泄不要超過自己的控制范圍,要在能力范圍之內做最恰當的表達,過猶不及的表現只會讓聲帶機能平添損耗。當D段結束后,以基本主題為材料的尾聲A出現,在演唱A時應該將D段的奔放感情與A段的平靜形成的對比表現出來,氣息要像控制風箏的線一樣牢牢把控住,讓尾聲部分在漸弱中進行,并將整首歌曲的結束處理得像微弱的燭火一樣“緩緩熄滅”。
(三)情感表達
藝術歌曲相比詠嘆調的確在感情上更為克制,《紡車旁的格麗卿》卻是少有的例外之一,在演唱力度上由“很弱”到“特強”的極大區間即使在詠嘆調中也較為少見,它在音樂性與文學性上對比都很強烈,內容上有著明顯的情緒波動,需要演唱者借鑒在詠嘆調中的歌唱特點,張弛有度、娓娓道來地將歌詞唱給觀眾。在演唱這首作品時,我們不僅是站在第一視角扮演格麗卿,更是作曲家將作品呈現給觀眾的媒介,演唱者必須明確地表現出舒伯特的創作特點以及浪漫主義和德奧藝術歌曲的音樂風格;感情應當張弛有度,不宜過度,在尊重作曲家意志(即譜面音樂記號)的前提下進行二度創作。
在C段中格里卿沉浸在關于浮士德的回憶里,演唱者的情緒應該一改之前與心上人不得相見的痛苦,歌聲變為浸著幸福的溫柔吟唱,呈現出格里卿提起浮士德就會心潮澎湃的樣子。浮士德的翩翩風采在格麗卿的腦海里浮現:她看到他走過來,對她微笑,對她深情地凝視,對她說話,握起她的手,然后吻了她。這一段音樂的情緒表現是隨著歌詞內容中浮士德的漸漸靠近而越來越激動的。當琴聲與人聲進入休止后,演唱者應繼續全身心沉浸在音樂里,以達到聲斷情不斷的藕斷絲連的效果,在樂思上給觀眾足夠的遐想空間。D段需要和第三次出現的尾聲A段形成鮮明的對比。想要將情感傳達給觀眾,要避免過于相信“感覺”這一抽象的概念,以免造成歌唱缺乏感情或聲臺形表超過表演范圍的結果,給觀眾帶來“聲淚俱下、涕泗交頤”之感。演唱者在扮演格麗卿的同時,可通過閱讀《浮士德》原著并結合自身修養、經歷與情感,適度與人物共情,但不能完全沉溺其中,而是在心中時刻以“內心聽覺”的第三方視角客觀地審視自己,精準地把控音樂形象。若內心聽覺不夠精確,也可以使用錄音錄像的方法來解決。
聲樂是一門結合了音樂、舞臺和表演的藝術,需要同時滿足觀眾在聽覺、視覺上的欣賞要求,除了在演唱方面的表達,肢體和神情上的發揮也同樣重要。著名大提琴家馬友友曾經說過:“作為音樂家,你需要讓自己超越技藝的桎梏表達情感,最糟糕的做法就是一動不動面無表情。情緒是用來表達的,但太多的情緒會使得能量的傳遞效率降低。”好的舞臺形象與肢體動作不但可以引人入勝,更能夠幫助表演者進入角色,發揮表現力。演唱時的體態與動作需要舒展自如,最忌猶豫畏縮、欲做還休。《紡車旁的格麗卿》作為藝術歌曲,并不需要大幅度的肢體表演,但是要注意聲音與體態的協調,從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來強化基本主題,層層推進,體現出三個插部漸入佳境的層次感,讓觀眾即使聽不懂德語,也能感受到音樂內容的前后對比。
四、結語
舒伯特的《格車旁的格麗卿》是世界上第一首用音樂為詩歌描繪畫面、將鋼琴伴奏的地位提升到和人聲等同的藝術歌曲,其在西方音樂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一般認為,藝術歌曲自這首歌曲的出現開始成為一種精致的音樂藝術品,而《紡車旁的格麗卿》則是西方音樂史上的一道里程碑。演唱者應充分了解作曲家以及寫作背景,并結合譜面標記進行解讀與二度創作,這樣才能將作品高水平地呈現給觀眾。
參考文獻:
[1]瓦而特·杜爾.弗蘭茨·舒伯特藝術歌曲[M].騎熊音樂出版社,1980.
[2]保羅·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樂[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3]張曉鐘.從《紡車旁的格麗卿》看藝術歌曲的特征[J].云南藝術學院學報,2001(02).
[4]李雅晴.藝術歌曲演唱與歌劇演唱的差異分析[J].大眾標準化,2019(16).
[5]楊帆.《紡車旁的瑪格麗特》的解析[J].北方音樂,2012(03):73.
[6]趙瑩.淺析舒伯特藝術歌曲的創作特點——以《紡車旁的瑪格麗特》為例[J].文教資料,2012(24):82-83.
[7]孔一銘.淺析舒伯特的藝術歌曲《紡車旁的瑪格麗特》[J].黃河之聲,2014(10):81.
[8]左開菊.簡析舒伯特《紡車旁的瑪格麗特》和《魔王》中的抒情因素[J].云南藝術學院學報,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