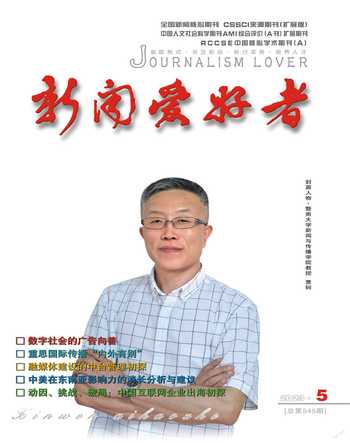青年群體的精準傳播策略研究
李瑋 李煜
【摘要】數字媒體環境與移動傳播語境下,信息生產與消費方式巨變,對青年群體的影響尤為顯著。從青年的心理結構、媒介使用、政治參與角度出發,聚焦其常用、善用的新媒體平臺,通過文本分析和在線訪談,分析目前正能量思想傳播模式與方案的優勢和不足,指出影響傳播效果的問題,從平臺、形式、內容、路徑四個層面,有針對性地提出精準傳播策略。
【關鍵詞】青年群體;精準傳播;政治參與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互聯網引發信息生產與消費方式巨變,使以青年群體為代表的網絡新用戶影響力與日俱增,為新時代正能量思想傳播工作提出新的挑戰與機遇。融合媒介環境和移動傳播語境下,如何運用青年易于理解并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正能量思想,提升傳播效果,是本文探討的核心問題。具體包括:(1)青年群體在心理認知、媒介使用、信息消費和政治參與方面具有哪些典型特征?這些特征如何影響其對正能量思想觀念的接受與反饋?(2)以青年群體為傳播對象,當前正能量思想傳播主要通過哪些新媒體平臺展開?存在哪些問題與不足?(3)結合青年的心理、社會、文化特征,如何從平臺、形式、內容、路徑四個維度精準設計,運用合適的傳播方案與策略,提升思想傳播效果?
本研究聚焦青年群體,通過文本分析與訪談,選取微信、微博及B站作為文本分析平臺,對10名青年訪談,了解傳播現狀與效果,探索傳播主體對象之間的內容匹配程度,找出存在的問題,提出精準傳播策略。
二、青年群體的社會心理、媒介使用與政治參與特征
青年是踐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核心群體,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力量。年齡在18歲至40歲的青年人,他們出生或成長階段伴隨各類數字技術的發展和迭代,使用互聯網比例高,擁有內在技術悟性,且具備使用信息技術與工具的能力[1],常被稱為“數字原住民”,或“數字土著”“千禧一代”“數位原生世代”等。[2]互聯網對青年的思想接受與反饋有巨大影響,主要體現在心理認知、信息消費、政治參與方面。
(一)社會心理特征
社會心理是民眾對于社會生活的認識、情感和意向的一種表達,它是社會變遷與時代精神的真實寫照。當下青年在虛擬世界和現實生活邊界越發模糊的情況下,通過互聯網獲得滿足感,并期望能將其在現實生活中重構,體現出青年人較為多元、多重矛盾和多層差異的社會心理。這些心理特征大多能從“躺平”“廢柴”“喪”等網絡熱詞中體現。相比于經驗,文化更能喚醒人們彼此間心理上的互相依賴,即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因此,從文化著手,找尋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對青年正向引導,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
(二)媒介使用與信息消費特征
我國青年伴隨互聯網發展成長。受訪者反饋,首次觸網時間從1995年至2005年不等,即小學或初中階段。作為中國網絡社會的重要行動主體,青年既是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的體驗者、參與者,也是新技術、新模式的引領者和推動者。[3]受訪者日均上網時長3—6小時,推動數字媒介發展,而數字媒介環境也是其信息消費的重要場域。受訪者普遍在B站參與度更高,主要關注生活區和學習區。在信息表現形式偏好上呈現多元差異。在媒介接近原則上,他們廣泛關注新聞資訊類、娛樂社交類平臺,也不排斥其他傳播媒介,如展覽、文藝匯演、影視作品等。
(三)網絡政治參與特征
青年始終是政治參與的重要主體,是推動社會變革與發展的重要力量。網絡是青年關注政治議題和參與政治討論的重要渠道。訪談發現:(1)政治類議題方面,青年認為官媒發布的信息資訊最權威、最全面,如央視網、《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2)傳播平臺方面,他們主要聚焦微博、微信、B站等新媒體平臺;(3)傳播形式方面,除宏觀政策、媒體報道以外,青年更希望通過多元化、泛議題、多角度、碎片化的表現手法,在休閑娛樂中參與政治。受訪者認為,以新冠疫情為代表的公共衛生事件,促使其個人對于網絡政治參與的主觀意愿、價值觀認同都有顯著性提高,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作用凸顯。
三、新媒體傳播渠道個案分析
(一)微博:主陣地逐漸轉移
微博是一個相對公開的場域,具有用戶草根化、內容精簡化、傳播碎片化的特點。[4]在互聯網出現以前,思想傳播是嚴密的組織架構,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宣傳其政治主張,并通過個別談心、集體座談等形式“廣交朋友”。[5]而借助微博傳播,打破既往以職業或經濟利益、社會階層為劃分依據,傳播對象統稱為“網民”。研究發現,微博的思想傳播效果不顯著:(1)正能量思想相關報道較長,受限于微博字數;(2)青年在該平臺主要關注娛樂八卦和社會熱點;(3)相關議題實效性弱,不在熱搜榜;(4)內容較少或未能引發青年人共鳴。然而,微博傳播速度快、范圍廣、內容精練,青年用戶黏度強,目前仍具有一定的傳播影響力。
(二)微信:“圈層化”裂變式無縫連接
微信具有熟人社交屬性,其公眾號用戶年輕化、圈層化,具有高效互動的傳播優勢。研究通過對截至2019年12月的243個全國縣級以上官方微信公眾號分析,發現傳播內容聚焦工作動態、解讀方針政策、講述經典故事、弘揚優良傳統,具有鮮明的主流話語體系宣傳特點[6],蘊含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一脈相承的核心精神。然而,通過訪談了解到,不少青年群體認為此類公眾號傳播對象、傳播內容都與切身利益無關,不會關注。
(三)B站:“破圈”的多元文化社區
B站是青年群體主陣地,內容生產和消費模式緊密圍繞青年特點展開,在傳播主流思想層面效果顯著,典型代表如2017年“共青團中央”帳號入駐B站、2020年跨年晚會受到多家主流媒體好評,這些成績都為正能量思想傳播提供了良好范本,目前相關內容主要分布在:(1)知識區;(2)生活區;(3)音樂區;(4)電影區等。正能量思想相關內容,在B站中傳播量最高,其次是公眾號,微博傳播力最弱,多個官方賬號已停更。B站中傳播主體多元,但尚且沒有官方賬號。B站視頻中的話語方式、媒介敘事方式符合青年群體接受習慣、信息消費習慣。同時也反映出青年對正能量思想持擁抱態度,為數字媒體環境下相關內容傳播提供了借鑒意義。但在內容形式上,B站平臺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可讓更多青年用戶參與其中,如參與內容創作、上下層聯動。
(四)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青年群體中知識分子多、黨外人士多且隊伍擴張和影響力日益增大,是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然而對這一群體的思想傳播仍然存在滯后性和不適應性,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未能把握與利用不同新媒體平臺特性,充分挖掘其傳播優勢。第二,社交媒體賬號多,內容形式創新少。在眾多傳播主體中,運營狀況良好、閱讀總數過萬的不足1/10,大量公眾號更新不規律、不頻繁、受眾面較窄,個別閱讀量僅為個位數。對此,青年受訪者認為,應增加公眾號中短視頻傳播形式,以及B站中歌曲、漫畫形式。第三,傳播對象范圍較為寬泛,精準度與聚焦力不足。雖不同平臺用戶特征差異化顯著,但傳播內容雷同,對青年群體認知、認同度提出挑戰。
四、對青年群體的精準傳播策略
(一)平臺精準
青年群體的信息消費存在泛平臺瀏覽的特點。目前官方賬號或合作賬號的平臺覆蓋面還不夠廣泛,尚未達到官方媒體占領主戰場的目的。青年群體常用的社交媒體平臺主要有微信、微博、抖音、B站、小紅書等;音視頻平臺有喜馬拉雅、小宇宙、騰訊視頻、愛奇藝、優酷視頻等;資訊類APP有今日頭條、澎湃新聞、學習強國等;國際新媒體有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等。部分互聯網KOL的平臺選取,通常以官方媒體政務號為導向。當然,平臺選取還需多媒介渠道合作,將重點置于青年常用、愛用的平臺,而非僅僅從傳播量一個維度考慮。一些傳播量較小的平臺,其用戶黏性相對更高,如樊登讀書、小宇宙等,同樣有較為理想的傳播效果。
(二)形式精準
不同新媒體平臺的側重點不同,其傳播形式亦有所區別。微博以140字為要求,內容不可過長,人們主要瀏覽微博熱搜。微信訂閱式的公眾號,人們閱讀的內容與自我興趣更加契合,且具有熟人社交功能。B站等以青年群體居多的平臺中,生動、活潑的特性賦予傳播形式上的多元化。但訪談發現,無論在何種平臺,短視頻形式都必不可少:個別互聯網KOL也在嘗試將宏大的理論拆解成多個短視頻。
(三)內容精準
通過對已有平臺中的文本分析發現,內容上存在趨同現象,多是宣傳主導思想。盡管個別公眾號在嘗試以文化為切入點,但其內容局限于當地文化,容易導致平臺中內容雜糅的現象。因此,應探索正能量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中一脈相承的文化特征,如“和合文化”“家國情懷”“大一統思想”,以文化故事的形式進行傳播。
(四)路徑精準
官方相關公眾號傳播對象主要是意見領袖或代表人士;從多個官方賬號及自媒體創作者相繼退出微博也可看出,這一平臺已不再適用,青年人僅借助它緊跟時事熱點。抖音和B站是青年群體的聚集地,現階段應大力發展。當前正能量思想傳播路徑主要是從官方到代表人士,但在二級傳播中呈現路徑不暢、不通、不順的現象。代表性人士中不少是網絡大V,但他們在網絡中傳播的議題與核心思想關聯度不大,更多是基于自己的知識結構進行創作,并沒有達到通過他們進行思想傳播,并讓更多青年人認同的目的。此外,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均為70后,他們的年齡與青年群體存在天然的代際差異與隔閡。因此,在傳播路徑方面,也應加強對青年群體互聯網KOL的培養,保持傳播路徑從官方成員再到青年互聯網KOL的暢通,才得以使正能量思想的傳播效果呈裂變式增長。
五、精準傳播效果:青年群體的文化認同
精準傳播的關鍵實現路徑是“主體詢喚—情感勾連—文化認同”。主體詢喚需要傳播者高度參與。通過進駐青年群體主戰場如B站、抖音等新媒體平臺,以其樂于接受的傳播形式——歌曲、漫畫、歷史精講,融入青年人喜愛的文化元素——二次元、動漫、網絡語言,激發青年群體在情感上產生共鳴。通過這樣的路徑,達到認同整合的目的,具體體現在三個維度:第一,內容層面,認同思想工作需要在黨的領導下開展。認同中國共產黨人的“傳家寶”,在新時代還應繼續加強,了解其深層的“和合”文化等精髓,有助于個人思想的提升。第二,程度層面,相較于傳統的思政教育,青年通過親身參與到具體活動中,更易于加深他們對正能量思想的認同程度。第三,表現形式層面,多元化的表現形式更有助于青年理解正能量思想。總的來說,當青年在其常用的新媒體平臺接收符合其價值觀、與自身利益相關、形式多元、可學習新知識或產生思想共鳴的內容,那么之后也會關注相關議題,或找尋更多內容。感興趣者則會通過在網絡中搜索關鍵詞、找尋相關的歷史書籍、電影、紀錄片深入學習。當他們通過自我學習而非宣傳式灌輸,可能會改變其原有的一些看待問題的角度,并體現在其日常生活中。最后,在與他人交往中通過人際傳播,線上線下互動,進行二次傳播、多平臺、多層級、圈層化傳播,從而達到傳播效果最大化,即讓更多的青年群體知道、了解、認知、認同正能量思想文化的目的。
六、結語
本研究厘清正能量思想在當下的新媒體主陣地傳播現狀,結合18—40歲青年網絡用戶的社會心理、媒介使用、信息消費、網絡政治參與特征,找尋思想傳播現存問題,并從平臺、形式、內容、路徑四個維度提出精準傳播策略,通過“主題詢喚—情感勾連—文化認同”模式,達到思想在新媒體平臺中傳播效果最大化的目的。在理念上,提出組織化政治工作為主,傳播化文化理念為輔的傳播策略。在新時代,面對具有“數字原住民”典型特征的青年,在通過政治思想教育方式傳播正能量思想的同時,輔以通過文化浸潤式傳播,推廣中國歷史文化知識,只有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才能全面接受和理解正能量思想。在實踐層面,提出平臺、形式、內容、路徑四個方面的精準傳播策略。唯有生產出更適用于符合新媒體場景化、圈層化、個性化特征的信息,才能達到傳播效果最大化的目的。
(本文為2019年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委托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項目“網絡統戰與新媒體治理”中期成果,項目編號:ZK20190109)
參考文獻:
[1]VodanovichS,SundaramD,MyersM.Digitalnativeandubiquitousinformationsystems[J].InformationSystems Research,2010,21(4):711-723.
[2]曹培杰,余勝泉.數字原住民的提出、研究現狀及未來發展[J].電化教育研究,2012,33(4):21-27.
[3]陳丹引.數字獲得感:基于數字能力和數字使用的青年發展[J].中國青年研究,2021(8):50-57+84.
[4]楊曉茹.傳播學視域中的微博研究[J].當代傳播,2010(2):73-74.
[5]郭忠華.新時期網絡環境下的統一戰線建設與民主發展:以微博為中心的論述[J].中共四川省委省級機關黨校學報,2013(2):19-24.
[6]吳凡.新媒體時代下網絡統戰工作路徑構建:基于統戰部官微的內容分析[J].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30(04):29.
(李瑋為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煜為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博士生)
編校:鄭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