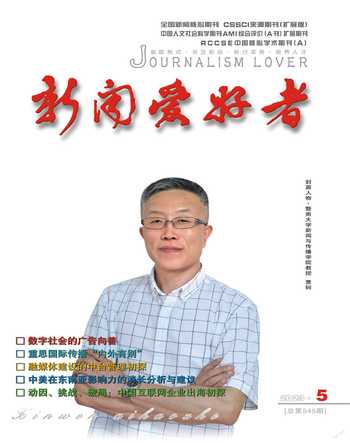風險識別與價值重構: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的路徑探究
包國強 常華科
【摘要】當前,數字化已經從文化產業發展的實現工具,轉變為與文化產業深度交融的外在環境,在此語境下,創新作為產業變革的驅動力量,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化產業的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也面臨著種種風險:政策層面的治理風險、市場層面的圈層化風險、技術層面的數據安全風險和價值鏈層面的整體性風險。基于數字化創新理論指出,文化產業的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需要從政策、市場、技術和國際四個層面來尋找突破口與價值重構路徑,進一步推動我國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
2017年文化部出臺的《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強調,“建設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生態體系”。[1]在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當下,文化產業的發展程度反映了一個國家價值體系的影響力以及經濟的發展潛力。在新一代數字技術與文化產業深度融合發展的大環境下,文化產業研究應該將相關主體和要素相聯系,以整體性、動態性的眼光深入考察。因此,文化產業數字化的創新理論研究應該從“創新系統”走向“創新生態系統”,基于創新生態系統的生長性、棲息性和動態性來迎合互聯網生態,助推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2]本文以此為出發點,對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展開研究。
一、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的內涵及建設的戰略意義
在數字化時代,信息技術與文化產業的深度融合改變了產品與服務形態、企業組織結構,也在更深層次重塑了文化產業的生態。在數字化創新生態之中,各要素之間的關系被凸顯,并且,在數字創新的理論視角下,文化產業越發具有網絡狀、自組織、自生長的特點。本文基于生態學中的生態位理論,構建了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的結構關系圖。
(一)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的內涵
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就是利用數字化的資源與能力,將數字理念與物理組件重新組合并深度嵌入到文化產品與服務之中,進而形成一個良性的創新體系。首先,文化產業的數字化創新生態內部形成了一種網狀的結構關系。數字化浪潮下文化產業不像是一條生產線,而更像是一個生態系統。[3]其次,數字化創新生態下的文化產業可以自發與其他產業融合,也就是說,自組織、自生長成為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的演化特點。
(二)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的戰略意義
首先,文化產業需要在正確的政治導向上發展才能保證內容創新不會偏離時代主旋律,因此文化產業的數字化有利于我黨保證創新理論、宣傳手段的先進性。其次,堅持創新驅動文化產業發展,可以使本民族的集體記憶在更廣的范圍內引起共鳴,進一步強化民族的自信心與凝聚力。再次,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也能進一步強化市場的主體地位,并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為制度的改革與調整提供經驗。最后,文化產業的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可以有效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并且可以進一步鞏固和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二、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的現狀與問題及挑戰
(一)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的現狀
市場環境不斷優化。一方面,對于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構建的政策扶持力度在近年顯著加大。為響應我國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各地有關部門都積極出臺相關政策,優化市場環境。例如,上海市出臺《上海市關于促進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實施意見》,北京市計劃到2035年實現公共文化基礎設施的全面數字化。另一方面,在平臺化浪潮下,文化產業的商業模式也有所創新。“IP熱”現象令精品化的原創IP成為企業塑造獨特形象、聚斂流量的法寶,在未來有望形成“平臺+IP+文創電商”的商業模式。[4]
技術與產業鏈深入融合。首先,在內容制作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在文化產業中的創造性應用不僅提高了制作效率和信息的豐富程度,也進一步擴大了文化產品的制作主體。其次,在內容的呈現方面,通過移動終端播放的視頻成為主要呈現形式。5G技術以其高速率低功耗的特點為受眾提供了沉浸式的效果體驗。最后,在內容的審核方面,區塊鏈技術可以做到對UGC內容的高效審核。[5]
(二)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的問題
從供給端來看,文化產品生產低質量、同質化的現象明顯。一些影視劇一味尋求明星引流,想要通過粉絲群體來帶動收視率的增長而不重視內容與形式的創新,進而導致作品無法滿足受眾認知和娛樂需求。從媒體平臺維度來看,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頭部企業與媒體的資本實力差距明顯,容易引發平臺壟斷現象,不利于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的建構。從技術維度來看,文化產品版權保護問題頻出。以抖音和快手為代表的短視頻平臺就頻頻出現違規搬運、盜版侵權等情況,這種現象嚴重阻礙了內容創作者的創作熱情。
(三)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面臨的挑戰
尼葛洛龐帝認為,數字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決定了現代人的生存特點。[6]數字技術在帶給文化產業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使文化產業面臨著種種挑戰,具體表現為:創新供給“失靈”、渠道擴散“失序”、內容消費“失控”。這三個維度之間相互作用并形成了惡性循環,挑戰著數字化創新生態的建構。
1.創新供給“失靈”:傳統商業觀念使文化產品供給端陷入“創新者的窘境”
克里斯坦森在《創新者的窘境》中指出,企業如果過于注重客戶當下的需求,反而無法開拓新市場。[7]當下,我國文化產業也面臨著頭部企業無法進行“破壞性創新”的困境。一方面,頭部企業由于其本身的組織管理模式、用戶規模已經趨于穩定,很難做出革命性變革。另一方面,當低質量的文化產品與服務體量過于龐大時,一些中小型企業或個人的精品化內容往往因為欠缺資本優勢與用戶數量,從而無法廣泛傳播。因此,未來導向的創新思維的缺失,不利于文化產品與服務的創新。
2.渠道擴散“失序”:平臺各自為戰,數據互聯互通受阻
數字化創新具有可溯源性(traceability)、可交流性(communicability)和可關聯性(associability)等特點[8]。因此良性可持續的數字化創新生態,需要以平臺化的服務和數字化的文化產品為中心,建構不同平臺之間、線上與線下之間互聯互通的動態化網絡格局。但是,當下我國的文化產業數字化進程過于注重形式與內容的創新,不同平臺、不同領域之間仍然存在以自身的數據資源優勢來進行壟斷競爭的現象。平臺之間的炒作與壟斷競爭,將會使數據的互聯互通受到阻礙,進而使“創新”的傳播渠道變得狹窄、單一。
3.內容消費“失控”:水平化發展的消費市場無法匹配產消一體化的“智眾”需求
伴隨著消費市場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消費者對于文化產品的內容與形式的廣度與深度都有了全新的要求。一方面,利基市場的市場空間不斷擴大,數字技術在打通了移動終端接收壁壘的同時,也激發了“長尾”活力。另一方面,作為能夠熟練使用互聯網技術,并對信息內容作出理性判斷的“智眾”,[9]用戶也有自主參與到內容生產和制作過程的訴求,精品化的UGC內容也是創意的重要來源。但是,相關反饋機制的缺失使用戶的文化產品生產訴求無法得到有效表達,不利于文化領域的意義建構和傳受雙方的價值共創。
三、文化產業數字化生態“風險”分析
(一)政策層面的治理風險
文化產業因其本身的意識形態價值指向,因而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說,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趨勢下,文化產業的管理體制創新倘若不能及時跟進,就可能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文化強國建設的順利進行,甚至在更深層次影響到民族文化自信的建構。[10]國家對于文化產業的相關政策,一方面要滿足人民多樣化的文化產品與服務需求,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要對不良現象進行監管和政策干預。因此,政府相關部門應該權衡鼓勵與監管的力度與效度,否則可能會面臨國家形象和政府公信力受損的風險。
(二)市場層面的圈層化風險
數字技術一方面賦權了個體,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構筑了以趣緣為導向、社交關系為介質的圈層化壁壘。亞文化以小眾、高滲透率的特點讓群體成員在互動的過程中強化了主體間的認同感。不同于傳統的圈層化社群,互聯網時代的圈層化社群范圍更廣、人員構成更復雜。[11]一些自媒體、平臺刻意制造話題也進一步加劇了圈層化的負面影響,阻礙了文化產品在市場中的流通。
(三)技術層面的數據安全風險
首先,數字技術開放性的特質使原創內容版權保護的難度有所提升。數據竊取風險可能發生在文化產品制作、傳播和消費等環節。在數字化的文化產業市場,盜版現象呈現出彌散化、難以定位等特點,該現象也打擊了創作者的創新動力。其次,在內容呈現維度,以算法技術為代表的智能化推薦機制,也在以“座駕”的形式限制著人的自由度,影響著人們對于世界的正確認知。海德格爾就對技術所帶來的便利保持警惕,他認為如果人類將這種“座駕”奉為圭臬,那么風險也會隨之而來。最后,在互聯網平臺中的用戶數據如果聚集在少數企業手中,將會嚴重阻礙內容供給端向多樣化演進的趨勢,甚至對國家信息主權造成威脅。
(四)價值鏈層面的整體性風險
在全球化趨勢下,從宏觀的整個行業到微觀的個人都在面臨著不同程度的風險。按照烏爾里希·貝克的觀點,人類正在從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逐漸步入風險社會(Risk Society)。[12]文化產業的價值鏈長、涉及范圍廣,尤其是在疫情期間產品生產、內容擴散、消費體驗等價值鏈全環節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有關風險根源于區域之間的文化產品生產能力存在較大差異。從媒體融合的角度來看,四級融合的格局尚未形成。產業管理模式不成熟和數字技術資源缺乏嚴重阻礙了區域的文化創新能力。從本質上來講,以上風險的深層次原因是產業鏈不健全所導致的文化產業整體抗風險能力下降。
四、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重構路徑
(一)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原則和目標
數字化創新,是突破了傳統線性創新邏輯的一種網狀的、動態的創新思維。文化產業在進行數字化創新生態的建設進程中需要把握開放共享、以人為本、系統思維這三個基本原則,才能提升創新主體的廣度、技術應用的深度和文化產品的效度。
1.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的原則
開放共享——數字化創新的必要條件。根據梅特卡夫定律,用戶的數量直接決定了一個網絡的價值。[13]因此,在互聯網時代“連接”是創造價值的必要條件。文化產業應該秉持開放共享原則,以精品化的內容連接不同平臺、不同領域的數據與用戶,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
以人為本——數字化創新的目的和歸宿。在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中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強化科技為民、文化為民的理念。通過文化產業的數字化創新優化人民群眾在文化消費中的場景體驗。與此同時,把握好“基層”這個連通群眾文化消費“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接觸點。
系統思維——為數字化創新營造政策環境與市場環境。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并重。一方面,要發揮政府對于文化產業及其相關活動的引導與監管作用,統籌資金、人才、項目等資源;另一方面,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激發創新的內在動力與活力。
2.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的目標
首先,要拓寬創新主體的廣度。令文化消費人群也參與到創作的過程中,形成人人參與、實時交互的創新格局。鼓勵小眾文化領域的自媒體生產優質內容,進而帶動文化產業創新發展,加速良好生態格局的建構。其次,要提升技術應用的深度。利用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打造更豐富的文化產品與服務的體驗場景和更高效的版權保護效率。最后,要強化文化產品的效度。對于相關企業而言,應該承擔起社會責任,在充分連接產業鏈上下游的基礎上,更加注重文化產品對社會的實際效益。
(二)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的路徑與措施
中國經濟正處于提升發展質量的關鍵階段,因此需要發展數字經濟來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在以創新為生命線的數字化創新生態中,文化產業的數字化發展產生了新環節、新鏈條和新的活動形態。本文將從政策、市場、技術和國際層面提出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建設的路徑和措施。
1.政策層面:治理體系創新 促進文化產業管理現代化
首先,要促進文化產業管理體制現代化。以建設公共文化服務型政府為目標,構建中央與地方、官方與民間共同治理的良性循環。當下,我國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結構存在很大差異,媒體資源分配不均。因此,更應該賦予地方文化行政部門更大的自主權,并且,面對數字化時代文化內容的飛速增長,更應該注重管理體制的創新,借鑒國內外改革經驗。其次,要促進文化產業管理能力現代化。第一,應該健全文化產業法律及相關標準,從行政管理手段為主到依法管理手段為主。第二,應該順應互聯網時代的分眾化趨勢,構建分布式、精細化的管理模式。第三,應該尊重文化藝術規律,重視人民的娛樂訴求和文化需要。[14]
2.市場層面:打通數據壁壘 暢通文化要素在全產業鏈的流通渠道
首先,實現數據互聯互通。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具有跨界融合性,渠道與數據已經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打通不同平臺、組織的數據壁壘,可以為數字化創新生態營造重要條件。[15]其次,以數據為連接,推進文化產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融合發展。利用文化本身包容開放的特性,打造“文化+旅游”“文化+科技”等多種模式。例如,在第四屆進口博覽會上,西藏自治區非遺節目、張大千作品《五亭湖》等節目和作品通過多種數字化渠道,成功實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當代呈現。
3.技術層面:提升數字技術的智能化應用 產出高附加值的文化產品
首先,在內容制作層面,應該運用數字技術對傳統文化進行智能化呈現,將傳統元素與現代審美結合,并且,文化產品供給端應該以數字技術的優勢,深耕專業化、精品化的內容,為消費者提供沉浸式的消費體驗。需要指出的是,要警惕在藝術品的批量化生產過程中藝術品自身的“靈韻”喪失。[16]文化產品在數字化的進程中,為了便于規模化生產和傳播,需要統一的生產流程與消費載體。但是,文化產品價值取向的大眾化并不等于粗制濫造。文化產品不能成為“復制品”,而應該具有自身獨有的特點。
4.國際層面:以問題導向和戰略思維 助力我國文化產業向價值鏈高端躍遷[17]
在現代科技迅猛發展的大環境下,數字技術深刻影響了文化產業價值鏈。在此語境下,數字化創新的能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全球文化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因此,面對當下復雜的國際環境,應該堅持問題導向與戰略思維,以政策環境資源為基礎、以生產要素資源為引擎、以市場要素資源為保障,助力我國文化產業轉型升級,并且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也應該積極吸收別國的成功經驗。
五、結語
當下,我國正在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在此語境下,創新成為發展的首要任務和重要動力。良好創新生態建設的首要前提是思維的創新。在數字化進程中,文化產業學界和業界應該摒棄以往線性、單一的分析視角與運營思維,以生態化思維來應對文化產業的發展問題。文化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保障。正因如此,在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構建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生態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為2021年上海市社科規劃項目“基于高質量發展的上海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研究”(2021BXW006)成果;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中資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構建與推進機制研究(編號:22&ZD319)]
參考文獻:
[1]文化部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J].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17(28):104-108.
[2]曾國屏,茍尤釗,劉磊.從“創新系統”到“創新生態系統”[J].科學學研究,2013,31(01):4-12.
[3]威廉·J.克林頓,小阿伯特·戈爾.科學與國家利益[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31.
[4]陳少峰.未來導向的文化產業商業模式創新[J].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17(02):38-41+97.
[5]張收鵬.區塊鏈技術在傳媒業的創新應用[J].新聞戰線,2018(23):120-122.
[6]尼葛洛龐帝.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J].信息經濟與技術,1997.
[7]克萊頓·克里斯坦森,胡建橋.創新者的窘境[J].華東科技,2019(6):19.
[8]Yoo Y,Lyytinen K J,Boland R J,& Berente N.The next wave of digital innovation: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A report on the research workshop digital challenges in innovation research[R].Ssrmn EleetronicJoumal 2010.
[9]包國強,黃誠,厲震安.智眾時代:“智眾傳播”的特征及其未來發展趨勢——融媒體背景下基于受眾與媒體關系根本性變革的思考[J].新聞愛好者,2021(1):15-19.
[10]范玉剛.“健全文化產業體系研究”的問題導向、多維價值與時代關切[J].學習與探索,2020(10):120-130.
[11]韋曉寧.亞文化資本視角下的圈層綜藝研究[D].廣州:華南理工大學,2020.
[12]Beck U.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Risk Society:Questions of Survival,Soc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J].Theory Culture & Society,1992,9(1):97-123.
[13]Alberts.Network Centric Warfare:Developing and Leveraging Information Superiority[M].CCRP Serials Publication,2000:102-200.
[14]祁述裕.國家文化治理建設的三大核心任務[J].探索與爭鳴,2014(5):7-9.
[15]柳卸林,董彩婷,丁雪辰.數字創新時代:中國的機遇與挑戰[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20,41(06):3-15.
[16]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王才勇,譯.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3:79.
[17]談國新,郝挺雷.科技創新視角下我國文化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的路徑[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54(02):54-61.
(包國強為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兼任互聯網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球文化旅游產業與軟實力協同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常華科為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上海大學全球文化旅游產業與軟實力協同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編校:鄭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