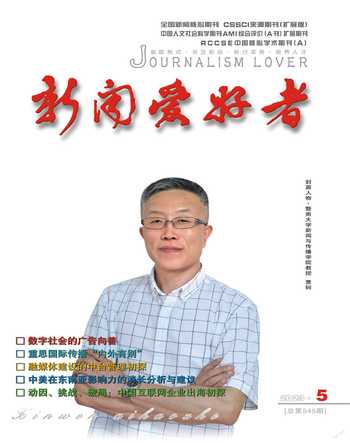《萬國公報》視野中的郭嵩燾使西
楊波 李珂
【摘要】1876年,清廷第一任正式駐外公使郭嵩燾赴英謝罪,成為中外矚目的外交事件。《萬國公報》對此進行了持續關注和報道,同時轉載推介郭嵩燾的出使日記《使西紀程》,使其禁而不絕,逆勢流傳。《萬國公報》充分利用媒介話語的優勢,塑造了一位“星使冠冕”的郭公使形象,在“舉世謗議”之中為郭嵩燾贏得了寶貴的輿論支持。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近代報刊作為重要的媒介工具,逐漸嵌入晚清帝國的政治肌體,在深刻影響政治人物個體命運的同時,也推動了晚清社會的轉型和嬗變。
【關鍵詞】《萬國公報》;郭嵩燾;《使西紀程》;媒介形象
1875年,清政府委派郭嵩燾為出使大臣,為平息馬嘉里事件,赴英通好謝罪。1876年12月,郭嵩燾踏上西行之旅,次年1月抵達倫敦。1879年1月銷差回國。作為開明士大夫的代表,郭嵩燾對西方文化進行了深入考察,記錄赴英行程的《使西紀程》(以下簡稱《紀程》)對西方文化多有褒揚,引起輿論嘩然,《紀程》被毀版查禁,郭本人也受到陵鑠詆毀,幾不能自存,成為近代文化史上一個重大的輿論事件。《萬國公報》堅定地站到了郭嵩燾一邊。《萬國公報》(1868—1907)由美國基督教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創辦,經歷了《中國教會新報》《教會新報》和《萬國公報》三個階段。在近40年的存續期內,《萬國公報》由早期的教會報刊,轉型為報道新聞時事、介紹西學新知、評論中外時局的綜合性報刊,是晚清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傳教士中文報刊。《萬國公報》對郭嵩燾出使給予高度關注,刊發報道和評論37篇,并連載其《使西紀程》,在當時“舉世謗議”的輿論環境中給予郭嵩燾不遺余力的聲援和支持,為讀者呈現了一個與“名教罪人”迥然不同的“星使楷模”的正面形象。這是學界尚未關注到的重要史料,對這一新聞事件的解讀可以豐富我們觀照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維度,為報刊媒介與政治人物的互動研究提供生動范例。同時,也可從中一窺近代報刊這一“政治晴雨表”,如何介入晚清士大夫的個人生活,深刻參與到晚清社會劇變進程之中。
一、《萬國公報》報道中的“郭星使”
1876年11月25日,《萬國公報》刊出短消息《中國欽差領事出洋》:“中國欽差郭君嵩燾已于十月初四日到滬公館,在廣肇公所,俟劉君潮清來滬,一同出洋。”宣告郭嵩燾與副使劉錫鴻即將出洋,拉開了大清帝國正式遣使西方的序幕。此后,《萬國公報》陸續刊出系列報道、評論等37篇,分布在不同的版塊下:“大清國事”(5篇)、“大英國事”(8篇)、“各國近事”(17篇)、“政事”(4篇)、其他(4篇)。如此高密度地持續關注一個政治人物,這在《萬國公報》是不多見的。《萬國公報》在1877年6—8月間還連載郭嵩燾的《紀程》,使其禁而不絕。《萬國公報》對郭嵩燾的海外行程進行了跟蹤報道,覆蓋其領命出使、公務交涉、考察游歷和卸任回國的各個環節。最后一篇評論《采郭侍郎論》延續到1880年10月23日,時間跨度達4年。這些文字可分三類。第一類是介紹其外交活動的短消息和通訊,聚焦“郭星使”的海外生活,展示其席不暇暖,為國折沖樽俎的外交行程。既有遞交國書、賑災募款這樣的交涉公務,也有參觀兵工廠、造船廠、博物院、大書院、格致院的考察參訪,還有宴請各國使節的交際茶會。“郭星使”在這些場合表現得穩妥得體,在公務考察時“無不認真觀習”[1];定期舉辦茶會,聯絡邦交,“極盡賓主之歡”[2];還主動為英國水手醫院捐款,以示“一視同仁”,可謂“無負使臣之選矣”[3]。他卸任后,《萬國公報》還援引《字林西報》,在滬的各國公使商議歡迎郭嵩燾返程,以顯敬愛之意及敦睦之情[4]。此類新聞數量最多,篇幅較短,語言精練得體,恪守新聞的客觀性原則,較少評論。
第二類是郭嵩燾本人的言論、奏稿和文牘。如選登郭嵩燾感謝英國政府向中國山西災區募集賑災款的照會和郭關于禁煙的奏稿,表彰其身在海外,不忘家國的義膽忠心。1877年3月17日,郭嵩燾出席倫敦勸禁鴉片會并致詞:“禁煙之事其言曰鴉片流毒中國,危害深矣……本大臣于諸公從中商辦相機而行。為蒼生請命之要舉也。鴉片之害,中西人皆知之,而皆欲禁之矣。”[5]《萬國公報》肯定其發言“深切著明,而能得其大要者也”。會后,郭向朝廷奏請查禁鴉片,《萬國公報》從福建官報中抄錄了奏折原稿。郭嵩燾認為禁煙的關鍵在于強化對官員的稽查,“養士大夫之廉恥”[6],禁煙政策應遵循“教化轉移之意多,防范操切之術業少”的原則,義正詞嚴的御前陳詞,印證了其言行合一的拳拳之心,也使其在海外吸食鴉片的謠言不攻自破。《萬國公報》還選錄香港《循環日報》,連續刊發兩篇《采郭侍郎論》,編選郭本人對洋務外交的認識,并加編者按:“當今之時,處今之勢,能辦理洋務者,惟郭筠仙侍郎一人而已。”[7]
第三類是對郭嵩燾的評論,集中在其卸任歸國后。這些文字極力贊揚其通洋務,識大體,行事穩妥,才學兼備的品性為人。《英日報論郭公使不辱君命》指出郭嵩燾克服語言不通、事多初創等困難,出色地履行了外交公使的使命:“郭公不諳西國語言,一切措施本多棘手之處,且事屬創始,更難攸往咸宜。而郭公則經濟素優,不避嫌阻,事無巨細,竭力經營,尤能藹然可親,虛懷下問,故于西國所有事宜,凡有益于中國者,無不留心考究,以祈擴華人之見聞也。”[8]他主動與外國官員保持良好關系,展示了中國彬彬有禮、儒雅大方的國際形象:“英國官商士民多有佩服者,無不友愛。”[9]《大英歌頌中國公使》極力稱贊其外交上開拓性的貢獻,認為他是“中國欽差中第一人”[10]。《萬國公報》刊發社論《論使臣不辱君命》,稱他“為星使之弁冕,即為后任之楷模”[11]。社論后附英國詩人傅澧蘭(Humphrey William Freeland)的贈別詩,詩稿先見倫敦新報,后由林樂知與蔡錫齡譯成中文。郭嵩燾被描繪成“愛國忠君”的國之棟梁。[12]郭離任后,英國民眾深為惋惜,甚至“日切遐思,時深企慕,幾若一日思君十二時矣”[13]。
《萬國公報》的報道介紹了郭嵩燾的海外日常外交生活,言行得體,從容自如。郭本人的奏稿文字,凸顯其卓爾不凡的眼界胸襟。眾多評論又強化了西方官員和民眾眼中“郭星使”勤勉干練、思想開明,又極具人格魅力的形象。三者構成一個意蘊豐富的新聞語義場,將讀者引入這一擬態環境中,為讀者呈現了一個近乎完美的“郭星使”。
二、《萬國公報》與《使西紀程》的逆勢流傳
郭嵩燾出行前,與總署議定每月完成日記一冊,呈達總署。1877年1月,他在倫敦將途中日記約2萬字編為《使西紀程》,上呈朝廷。同年4月,同文館刊印此書,隨即引起軒然大波。出使日記兼具公務文書與私人書寫的雙重性質,當郭嵩燾寫下“西洋政教修明”“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戰國殆遠勝之”之類的真實感想,力圖將眼中的西方圖景和政治理念呈現出來時,《紀程》已觸犯帝國的政治禁忌,成為一種危險的文本形式,當時輿論沸騰,幾不可收拾。同時,《紀程》批評荷蘭侵占殖民地“撫綏無術,遂至畔亂”[14],招致荷蘭公使抗議。1877年6月16日,御史何金壽奏請將《紀程》“嚴行毀禁”。為維護帝國尊嚴,杜絕異端思想,朝廷下令將《紀程》毀版查禁。但《萬國公報》對此置若罔聞,自1877年6月2日起開始連載:“此稿中國京城業已成書矣,茲照書登報。”[15]告知讀者,《紀程》已譯成英文,在香港《西字新報》刊出,“西國人見此書中之意,多顯郭欽使之卓識也”[16]。兩個月內,《萬國公報》分9次將《紀程》連載完畢,為當時國內公開傳播的唯一渠道。《申報》也與1877年5月28日刊發廣告:“是書詳述由滬至英京沿途風土形勢、人情物產,歷歷如繪,兼及考據議論,博達精通。一時西事諸書,罕其儔匹。想有識者當能共欣賞焉。”[17]但朝廷發布禁令后,售書廣告于6月4日戛然而止,直至1884年5月8日,才又刊出廣告,告知讀者《紀程》“售價二角”。
晚清新聞出版的立法滯后于實踐,長期處于官方的默許狀態,直至1900年《欽定憲法大綱》頒布,才首次明確了出版言論的相關內容。《萬國公報》敢違反禁令,原因在于其外國宗教報刊的身份,以及租界保護形成的體制外言路的屏障。當然,《萬國公報》在連載時也考慮到部分內容的敏感性,對個別表述作了修訂。《萬國公報》處理官方事務歷來非常慎重,堅持客觀中立:“其中國之官政是非,不便預聞。”[18]后來為爭取上層官員讀者,又重申:“凡中國官場以及審案定罪公允與否,非本報所欲聞,即他處有寄文請錄者,亦置之不問。”[19]在《紀程》查禁風波中,《萬國公報》打破常規,積極為郭嵩燾辯誣澄清,認為《紀程》字字征實,言之有據:“凡西人不足之處,皆從實書明,寄與總理衙門,并無一言粉飾。”在郭嵩燾陷入困境、無處容身之時,《萬國公報》大聲疾呼:“不見妒于西國之執政大臣,不貽譏于西國之文人教士,而中國或有人非之譖之,是誠何心!”強烈譴責事件背后的陰謀論和構陷者,站在西方文化立場上,表示對郭的同情和支持。《紀程》連載穿插在相關報道和評論中,新聞、評論與日記均圍繞核心人物和議題進行編排設計。《萬國公報》在關注中外交涉等國內外事件時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提綱挈領的新聞報道,簡潔扼要;二是內容豐富的當事人的日記游記,真實可感。這是政論刊物重要的辦刊特色。對郭嵩燾的新聞、報道和評論,因他者的觀察視角、思考方式和價值評判的差異,與《紀程》形成一種對話式的互文關系。
《萬國公報》逐步從單一的教會傳播渠道,發展成信局為主,輪船為輔的寄遞和售賣模式,極大地拓展了發行網絡,擴大了影響力。后期對讀者群的定位轉向精英讀者,即上層官員和知識分子,扉頁上的英文按語:“this magazine circulate among the mandarine and leading merchant throughout the empire”即為明證。這樣的信息傳播方式重塑了晚清帝國的信息傳播網絡和社會權力運行機制,也解構了晚清帝國政令必行的權威性。張佩綸對日記毀而不絕、禁而愈傳的情形很無奈,因《萬國公報》等接續刊刻,“中外傳播如故也”[20]。1885年之后,隨著遣使外交的常態化,朝廷對《紀程》的查禁已名存實亡,《紀程》被推為晚清出使日記的代表作之一。1889年,薛福成出使前向光緒皇帝力薦此書。載振便稱贊:“出洋日記,近人所著,首推郭嵩燾之《使西紀程》、薛福成之《四國日記》。”[21]《紀程》從被官方刊印,到被禁毀,再到廣為傳播,最后經典化這一戲劇性的過程中,《萬國公報》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萬國公報》與郭嵩燾媒介形象的建構
新聞報道的焦點往往難以對準事件最核心的本質,新聞采編其實是一系列汰選、過濾和編輯的過程,決定報道內容,應采取什么立場以及如何配置相應的版面空間。[22]郭嵩燾被指為“勾通洋人”“干犯名義”,儼然淪為名教罪人。《萬國公報》的報道評論及連載,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內建構了一個信息密集、指向明確的新聞話語場域,將一位為國前驅、見識宏遠的郭公使呈現在讀者面前。這個截然相反的媒介形象的建構,得益于《萬國公報》的精心謀劃,有意規避了對郭不利的負面信息,試舉三例。
一是奉命出使的過程。郭出使前曾多次以身體不好為由請辭,慈禧太后兩次召見,他才忐忑不安地踏上使西之旅。《字林西報》透露了一波三折的過程:“renews his application to be allowed to retire into privacy ; pleading ill-health as the renson.Medical certificates are often enough used, in Europe,as convenient shields for a retreat, which has quite other real causes.”[23]身體原因常被用來作隱退的托辭。《字林西報》還揣測,郭請辭的另一個原因是反對派建議削減駐英使館的費用。《萬國公報》有意回避公使遴選的曲折過程,讀者自然無從得知背后隱情,留下郭欽差欣然領命,為國折沖樽俎的印象。事實上,他出發前“心緒惡劣,不堪名狀”[24],內心的掙扎、焦慮與惶恐在日記中一覽無余。后來,他得知曾紀澤即將接任,難掩脫離苦海的輕松:“茍延性命以歸,實所深幸。”[25]
二是郭嵩燾與劉錫鴻的矛盾。劉原系郭舉薦,但二人的性格與行事風格差異甚大。劉曾多次揭發郭出洋以來的不當舉動,引發朝野議論,加上何金壽、張佩綸等人的彈劾,郭極為惱怒,二人反目。為避免矛盾升級,清廷將劉錫鴻調至德國。《萬國公報》輕描淡寫地告知讀者:“前放駐英副欽差候補三品京堂劉公,今奉上諭,著加二品頂戴,升調德國欽差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行文照會各國駐京欽差矣。”后來,朝廷將二人裁撤,三年任期未滿,即改派曾紀澤和李鳳苞繼任。《萬國公報》卻發布消息:“郭劉兩欽使現因三年期滿,其英法欽使改派世襲侯爵曾劼剛京堂紀澤。德國欽使改派現駐德國管帶學藝幼童李丹崖部郎鳳苞。”[26]郭劉二人不合,一方面因清廷任命兩人為正副使,不符國際慣例,埋下隱患;一方面也因郭敏感多疑,意氣用事。郭嵩燾與曾紀澤有姻親之誼,但辦理使館交接時差點鬧翻。正副使共事不易,前后任交接之難,絕非紙面上的一派祥和。
三是郭嵩燾在使館舉辦招待會。社交禮儀差異的背后,暗含著文化習俗、價值立場的齟齬和權力的角逐。西方茶會、招待會、舞會等交際活動是日常外交的延伸。郭內心對交際應酬很排斥:“西洋以此為酬酢常儀,而吾心實苦之。”[27]在海外期間疲于應付,但為聯絡感情,他任期內,分別在倫敦和巴黎使館各舉辦了一場招待會。前者尤為引人注目:“至者五百余人,所費蓋千四五百金。”[28]此舉開中國駐外使館宴請各國公使的先河。《萬國公報》極為贊賞:“一時觥籌交錯,賓主聯歡,極盡和好之誼。”新聞中的郭欽差從容不迫,與日記中為應酬苦惱的郭嵩燾判若兩人。《萬國公報》強調:“郭公夫人往法蘭西京城游玩,以擴眼界,身為命婦而得游中外,其福較他人為厚矣。”[29]說明當日郭夫人未出席宴會。中國傳統禮法視婦女出席公共宴會為大忌,這是為避免郭嵩燾的“夫人外交”被政敵構陷,為其作的澄清。
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是讀者對其認識、情感和意志的總和,它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讀者對郭嵩燾形象的基本判斷,建立在《萬國公報》等媒體傳達的具體事件、人物和場景的具象細節,以及觀照問題的價值立場與評價標準之上。《萬國公報》帶有鮮明的西方中心主義,郭嵩燾承認“西洋……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戰國殆遠勝之”。這與《萬國公報》的價值立場契合。《萬國公報》有時擺脫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發表議論。如記述郭參觀酒廠:“若使當年竹林七賢、飲中八仙諸君至此,安得不垂涎乎?”[30]介紹郭劉二人在倫敦游覽時得到當地官員的盛情款待,又發表評論:“英國待中國欽差若是之恭而有禮,未識英國欽差駐扎北京有此尊崇否也云云”。[31]這些細節流露出文化中心主義視角下的優越感。
郭嵩燾思想的先進性得益于長期的讀報習慣。出國前,他最關注《申報》;在海外,《泰晤士報》《晨郵報》《標準》等西方報刊成為其了解輿情,開展外交的信息工具。通過參觀報社、出版社等機構,與記者報人頻繁接觸,他對新聞出版的生產機制已有切身體會,具備了一定的輿論觀念與媒介素養:“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報。議論得失,互相辯駁,皆資新報傳布。執政亦稍據其所言之得失以資考證,而行止一由所隸衙門處分,不以人言為進退也。”[32]這些認知稱不上系統,但已深刻影響到信息接收與體驗方式,并作用于外交實踐。他非常看重自己的輿論形象。郭嵩燾曾就畫像事件與《申報》產生名譽糾紛,揭示出他對媒介背后附著的“輿論權力”的忌憚,認識到輿論足以操控個人的形象與名譽,影響其政治前途。當他抄錄嚴復翻譯的《泰晤士報》評論時,慎重刪去“甚盼郭欽差回國于執政大臣中得一要位,參與機密”[33]。他知道過度的輿論干預會招致朝廷的反感與猜忌。
郭林私交甚密。出國前,林曾贈其《中西關系論略》一書。1879年4月,郭返回上海后,兩人一同參觀徐家匯教堂。林樂知將傅澧蘭的贈詩譯稿送給郭。郭將譯文全文抄錄,并書寫楹聯,托張聽帆轉交傅澧蘭作為答謝。《萬國公報》刊登《譯英人傅澧蘭贈別郭瀛仙星使詩》,郭嵩燾是知情的。因此,《萬國公報》這次慧眼獨具的媒介運作,更像是與當事人心照不宣的一次合謀。
四、結語
隨著《萬國公報》等中西報刊的崛起,中國已被世界信息交流網絡囊括其中。外交官處于中西交會的最前沿,也是最早出現在聚光燈下的公眾人物。張佩綸曾抱怨:“各國交涉事件,非親其事者,雖京官無由知。”這是因媒介技術的限制導致信息傳播的不對稱,造成海內外聲氣難通,君臣同僚之間的隔膜與不信任,先知先覺者的言論往往被深閉固拒的后知后覺者視為異端邪說。媒介形象的建構是一個復雜動態的過程,至關重要的是社會語境的變遷。大眾媒介所塑造的“象征性現實”有自身的局限性,人是立體的而非扁平的,郭嵩燾也不可能像《萬國公報》所呈現出來的那樣完美。同時,報刊作為有著自身獨特邏輯的社會化建制,不僅記錄新聞事件,已深深嵌入政治肌體之中,成為帝國統治機器的一部分。《紀程》的禁而不絕,充分說明帝國對輿論的控制已非一道諭旨可以實現。《萬國公報》利用傳播和觀念合一的媒介優勢,借助郭嵩燾的海外見聞,在實踐層面實現了輿論的批判建言功能,在影響政治人物個體命運的同時,也推動了晚清社會的轉型和嬗變。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報刊與域外游記的傳播和影響研究(1840—1911)”(18BZW11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中國星使游歷[J].萬國公報,1877(461).
[2]中國郭欽憲宴客[J].萬國公報,1878(517).
[3]郭星使助銀入水手醫院[J].萬國公報,1877(440).
[4]設法接待欽差[J].萬國公報,1879(534).
[5]詳述戒煙會中大官紳董事與中國公使問答[J].萬國公報,1877(439).
[6]郭欽差奏禁鴉片稿[J].萬國公報,1877(449).
[7]釆郭侍郎論(選錄香港循環報)[J].萬國公報,1880(610).
[8]英日報論郭公使不辱君命[J].萬國公報,1878(519).
[9]贈別中國郭欽差詩意[J].萬國公報,1879(536).
[10]歌頌中國公使[J].萬國公報,1879(527).
[11]論使臣不辱君命[J].萬國公報,1879(537).
[12]譯英人傅澧蘭贈別郭瀛仙星使詩[J].萬國公報,1879(537).
[13]懷郭筠仙欽使[J].萬國公報,1879(549).
[14]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4:45.
[15]使西紀程(未完)[J].萬國公報,1877(441).
[16]使西紀程已翻西字[J].萬國公報,1878(474).
[17]使西紀程出售[N].申報,1877.
[18]本書院覆信[J].教會新報,1873(225).
[19]本報現更名曰萬國公報[J].教會新報,1874(295).
[20]張佩綸.奏為密陳風聞郭嵩燾遣使英國其禁書傳播如故交接回逆擬請將其撤回事[J].澗于集奏議卷一,民國十五年澗于草堂刻本.
[21]載振.英軺日記凡例[M].長沙:岳麓書社,2016:10.
[22]李普曼.輿論[M].常江,肖寒,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277.
[23]KwohSung-tao[N].TheNorth-ChinaDailyNews(1864-1951),1876(3).
[24]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4:20.
[25]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4:718.
[26]出英副欽使升調德國欽差大臣[J].萬國公報,1877(440).
[27]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4:625.
[28]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4:626.
[29]欽使大宴西員[J].萬國公報,1878(503).
[30]中國郭欽差觀酒廠[J].萬國公報,1879(530).
[31]中國郭劉兩星使游玩名勝之區[J].萬國公報,1877(455).
[32]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4:402.
[33]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4:821.
(楊波為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珂為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
編校:張如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