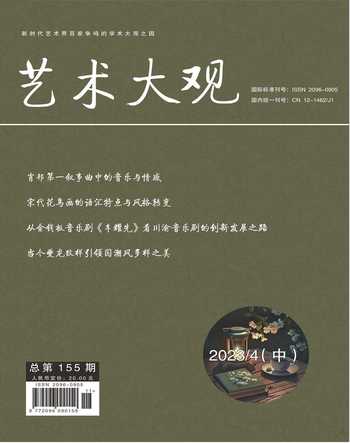肖邦第一敘事曲中的音樂與情感
闕爍
摘 要:肖邦創作的《g小調敘事曲》,是其標志性體裁四首敘事曲中的代表作,與其他音樂作品一樣,《g小調敘事曲》通過獨特的曲式結構及自身音樂材料的發展,向人們展現了豐富、完整的音樂情感表達過程。本文將從音樂本體和感情發展方面著手對全曲進行分析。
關鍵詞:肖邦;g小調敘事曲;音樂材料;情感發展
中圖分類號:J6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11-00-03
由波蘭作曲家,愛國主義鋼琴詩人肖邦于1835年完成,出版于1836年的《g小調敘事曲》,是其四首鋼琴敘事曲中的第一首,也是最為經典的一首。肖邦學家們普遍認為,就這首敘事曲的內涵、氣質與意境而言,這首《g小調敘事曲》一定程度上源自密茨凱維奇創作的充滿了愛國主義悲壯情懷的敘事性長詩《康拉德·華倫洛德》。密茨凱維奇和肖邦都是波蘭偉大的民族詩人。密茨凱維奇是用文字寫詩的詩人,而肖邦則被稱為“鋼琴詩人”。同肖邦一樣,密茨凱維奇在波蘭生活的二十幾年也正是波蘭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因此作品給人以強烈的現實感,洋溢著愛國主義激情。
作為愛國主義作曲家的肖邦正是在密茨凱維奇詩歌《康拉德·華倫洛德》的情感激發之下,創作出一個為拯救祖國而不惜犧牲個人生命和愛情的英雄形象。在創作技法上突破了傳統的奏鳴曲快板的曲式框架,進行了大膽的創新與超越,而產生的一首驚世駭俗之作。
一、引子
引子(第1-8小節),預示著呈示部主部的主題:引子是g和聲小調,而后的主部主題也是g和聲小調,無獨有偶,引子和主部主題在終止式上也選用了相同的和聲進行:Ⅱ-Ⅴ-Ⅰ。引子部分通過選用降Ⅱ6的“拿波里和弦”,讓其富有語氣化的鋪墊,隨著第一個重音的開始,仿佛是一位老者在莊重地告知大家,他將要訴說一個悠遠的故事,并留下懸念(第8小節和弦未解決),引領聽眾跟隨他走入故事情節中。
二、呈示部
呈示部(第8-94小節)依次由主部、連接部、副部以及結束部四部分構成。
(一)主部
主部(第8-36小節),在和聲上大致遵循Ⅴ-Ⅰ。在主題材料中,作曲家反復沿用了在引子的后半句中如人在嘆息般的下行音調及半音進行。在6/4 拍不穩定的節奏和g和聲小調的共同作用下,進入全曲第一大部分(8-36小節)。第一大部分分為兩大句:8-16小節和16-36小節,這是同頭異尾的兩句。其中第8、第9小節和第10、第11小節是2小節+2小節屬于“問答”式結構,從這兩小句的音樂線條走向上看,可以讓人感覺到作曲家將音樂的語氣進一步形象化,將一位低聲呢喃、猶豫不決的主人公人物形象通過音樂表現出來,后面第二句(16-36小節)則在后面部分(21-36小節)進行了大量的擴充,最后在36小節的第一拍才得以解決,其中還包含有典型的具有浪漫主義時期特征的華彩片段,體現出音樂主人公的豐富內心情感變化的過程,而這些音樂描繪出的畫面,可以通過想象恍若眼前。
和聲方面:第一句可以分為兩個小句,從第一句的和聲上我們可以看出,是從Ⅴ-Ⅰ的進行,然后由屬到主接著是重屬而后回到屬。第二句和第一句一樣,和聲功能上,由Ⅴ-Ⅰ,然后有個小的離調,到降B大調的Ⅴ,然后解決到降B大調的主音,接著到其導音。弱起的休止音符搭配下行回落音調讓人開始感覺神經緊繃、內心緊張不安。第二大句和第一大句的開始是一樣的,當從第21小節開始,便是主到下屬、然后是主、接著下屬、再是主。同樣的和聲功能重復(24-25小節),其中第25小節的最后一個和弦是g小調的重屬導,于第26小節解決到降三音的屬,接下來是g小調的導七到主的重復進行,第30小節先到下屬再回到主,然后又是下屬到屬,從第33小節開始轉到了平行關系的降B大調,34小節降B大調的主和Ⅱ級,然后在g小調上的K46,屬七到主解決[1]。
(二)連接部(第36-67小節)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第36-48小節)是主部的補充,由主部主題材料派生而來:是4+4+4的結構,第36小節到40小節與第40到44小節是平行樂句,其中跨小節連線造成的切分節奏型搭配向下模進的音型使音樂的情緒開始變得不安起來。在情緒上,后四小節更進一層,所以作曲家在第40到44小節時值相對長的二分音符上寫上了強音記號,表現出情感上的進一步激烈升級。
第二部分(第48-65小節)是通過柱式和弦的半分解與如同波浪般的琶音音型由g和聲小調向降B大調逐漸過渡轉換的一段,在節奏上打破了6拍子的強弱節拍規律,音樂變得更富動力感,同時進一步推動情感發展。
第三部分(第65-67小節)最明顯的音樂材料是四五度和聲音程的加入,這一創作構思堪稱精妙,肖邦不僅巧妙運用四度和五度音程為后面的副部在音樂材料上做了鋪墊,同時四度和五度在鋼琴上模擬出來的圓號音效也是肖邦喜歡且常用的創作手法,圓號樂器所具有的溫暖的田園色彩,毫不違和地預示性地在音樂氛圍上將音樂非常自然地過渡到了副部。
(三)副部
副部(第67-82小節)是非常甜美的一段,高音聲部以級進下行二度居多,像是戀人之間的輕柔傾訴,伴以低音聲部的琶音音型,如田野溫和的晚風輕輕拂過……雖然這一段的和聲進行與主部主題相同,都是屬到主,但是在音樂色彩上和音樂性格上卻是迥然不同在:副部主題處于以主部主題g和聲小調的Ⅵ級音為主音的bE大調上,從調式調性上講這屬于遠關系轉調,使得副部主題陳述的不穩定性得到增強,同時也進一步強調了副部主題與主部主題之間所產生的派生對比。另外,雖然主部主題與副部主題在調性關系上并沒有像普通奏鳴曲式所要求的主—屬調性的對比,但是對比仍然存在,它體現在音樂的情緒內容上:相對于主部主題的焦慮與糾結不安,副部主題的情緒緩和了很多,讓人感覺被寧靜、舒緩、溫暖、輕柔所包圍。這一片段猶如一個特寫鏡頭里面的一幅恬美畫面:一對親密的戀人在月光下耳鬢廝磨,竊竊私語[2]。
(四)結束部
結束部(第82-94小節)在音調和節奏上引用了主部主題的材料,后來運用降E旋律大調的降六級和降七級音,使音樂獲得柔和的小調色彩。在和聲上,結束部是副部的補充。在重復使用Ⅰ-ⅲ-Ⅴ7-Ⅰ的終止式的同時,強調了強拍上主音降E音的應用。年輕的男子準備要告別自己心愛的戀人但是非常不舍(第83-88小節),經過一番思想上的掙扎,他終于決定去投入戰斗保家衛國(第89-94小節)。
三、展開部
展開部(第94-165小節)由展開的主部、展開的副部和插部三個部分組成。展開部使用音區移位、力度轉換、轉調、豐富和聲織體等手法使音樂發展進入高潮。
(一)展開的主部
展開的主部(第94-106小節)在前面幾小節的“問答式”結構與呈示部主部基本相似,但是在a小調上進行。篇幅上有所縮減,在由升F升G等重復多次后,終于過渡到副部的主音——A音,而屬持續音的一再強調,預示著下一個主題的展開。
(二)展開的副部
展開的副部(第106-125小節)由降E大調轉換為展開部主部材料的a小調同名大調A大調;力度上也有明顯的大篇幅增加,寬廣的和弦支撐豐富了和聲織體:由呈示部中的單音旋律轉化為密集的和弦進行,在左手的和弦下相得益彰。旋律走向和音程關系方面,展開的副部與呈示部的副部基本一致。而后通過頻繁轉調和模進,在連續級進上行的八度音程的推動下,將音樂推向高潮。保留原有的旋律對織體進行填充,象征著主人公擁有大愛情懷的同時,內心又不失細膩柔情。
(三)插部
出現插部(第126-166小節)是因為展開部中發現了新的主題。它由兩部分組成,采用“諧謔”式的寫法,但實際上是為后面的高潮段落做鋪墊。
第一部分(第126-137小節)雖是以連續的八分音符作為穩定的旋律音型,但是營造的卻是緊張不安的情緒氛圍,和聲上,直到最后都沒有得到解決,用開放的半終止結束該段落,這種緊張感預示著音樂中第一個高潮的到來。
第二部分(第138-166小節)帶有諧謔性,其音調材料來自引子第3小節的C-G-B-bA-G-#F,同上一部分一樣,密集的八分音符在不斷重復該段落的主題的同時通過半音模進不斷積蓄前進的力量。緊接著在上行旋律的全音模進與和聲模進的共同作用下,音樂終于進入調性沖突最尖銳的高潮。與此同時,音樂中苦惱矛盾等錯綜復雜的情感也在一連串的轉調離調中散發出來。緊接著,急速下行的走句式音階,讓之前的煩悶一掃而光,而屬和弦的引入為再現做好準備[3]。
四、再現部
再現部(第166-206小節)由三個部分構成:再現副部、再現結束部和再現主部。作曲家在這里,為了滿足音樂情感的雙重要求,一反常態地將奏鳴曲式中的主部和副部的位置進行倒置,即用副部在前,主部在后的倒裝再現的結構來滿足發展音樂動力性的需要,這也是此曲最大的結構特點之一。
(一)再現副部主題
再現副部主題(第166-180小節)與呈示部的副部主題相比,在調性調式、節拍節奏、和聲結構上都上保持不變,但是在音區上作曲家開始往高音區作適量擴張,織體上也相對更飽滿豐腴一些。力度方面,也有著鮮明的對比。隱藏在和聲中的旋律聽起來圓潤、豐滿,肖邦將音樂元素大致相同的兩個樂段,巧妙地稍加處理,就馬上形成了對比。連續三次出現五連音的擴充樂句,暗示主人公有著英雄氣概,亦不失浪漫情懷。這段更加豐滿的副部主題也象征著主人公的思想感情開始由月光下與戀人耳鬢廝磨的小愛升華成民族大愛。
(二)再現結束部
再現結束部(第180-194小節)仿佛回到呈示部結束時候的平和歲月。不僅調式調性與呈示部的結束部相同(bE旋律大調),在和聲上也基本一樣,不同的是音樂在情緒上變得更加肯定,此時主人公已完全明確了自己的心意,將專心投入保家衛國的戰斗中。
(三)再現主部
再現部中的主部主題(第194-208小節)是在呈示部的主部主題基礎上進行了變化和壓縮。調式調性上,與呈示部的主部主題一致(同為g小調)。和聲上,再現主部也基本按照屬—主進行。不同的是,和聲中屬持續低音的延續,似乎變得更加不安,像是隱含著不好的預兆,而后第206、207小節,作為與尾聲相連的過渡的兩小節,激烈的情緒在強有力的雙音中奔涌,一步步緊逼全曲的第二個高潮——尾聲。
五、尾聲
尾聲(第208-264小節)是全曲的第二個高潮,有力量的急板,2/2拍。可以分為導入、中心和收束三部分。其中導入部分(第208-216小節)左手的節奏型每一小節都是固定的,節奏特點在右手聲部,重音在每一拍的后半拍上,打破了原本較穩定的節奏形態,使音樂中不穩定的因素增加,迫使音樂產生往前運動的動力,使得節奏具有動力感,加之火熱的急板速度和完全終止式的和聲結構,整段樂曲猶如一陣狂掃而來的疾風暴雨。
中心部分(第216-250小節)肖邦巧妙運用與引子中相同的降二級的“拿波里和弦”給g和聲小調增添了大調的明朗色彩。而后右手聲部中隱藏的級進旋律,經過層層模進,終于到達最高點,然后以氣貫長虹之勢一瀉而下,塑造出主人公大義凜然、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
收束部分(第251-264小節)樂曲的最后是非常恢宏有氣勢的:第253小節和第257小節是呈示部主部主題的材料的又一次出現,形成了主題上的“首尾呼應”。而后反向八度由慢加速到同向八度,整個過程力度是fff, 奏響了全曲山崩地裂般的最強音,激昂壯烈地向人們宣告英雄的悲劇性人生從此落下帷幕,僅留一聲長長的嘆息(最后一個長音)。
六、結束語
肖邦的《g小調敘事曲》無論從大到曲式結構、和聲調式調性布局,小到音型、節奏型包括休止符的處理,都是獨具匠心,精致巧妙的,每一處都有著精心的設計,這些“設計”并不是在炫耀他的創作技法有多高超,這些嘔心瀝血的“設計”的背后是他為了創造“花叢中的大炮”,是他的拳拳愛國赤子之心。肖邦將音樂本體與所寄托的情感結合得渾然天成:其中包括在曲式結構上也可以大膽創新——倒裝再現原則的運用,使得肖邦的《g小調敘事曲》具有拱形對稱的結構特點。通過這種特殊的曲式結構來承載敘事曲這一新型體裁。正是通過這一新型體裁的承載,作品包含的情感內容才能體現得如此有血有肉,淋漓盡致。除此之外,《g小調敘事曲》在音樂中所表達的英雄性和民族性也是少有的。它是肖邦鼓勵波蘭人民奮起反抗抵御外侵的“大炮”,是當之無愧的“肖邦最富有獨創性的作品”。
參考文獻:
[1]李丹陽.肖邦敘事曲的節奏特征分析及在曲式結構中的意義[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2013,31(01):159-163.
[2]伍樂.淺析肖邦敘事曲與密茨凱維支敘事詩的關系[D].南京藝術學院,2009.
[3]王旭青.音樂敘事理論——新視閾下一種音樂分析方法的探求[J].中國音樂學,2011(03):9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