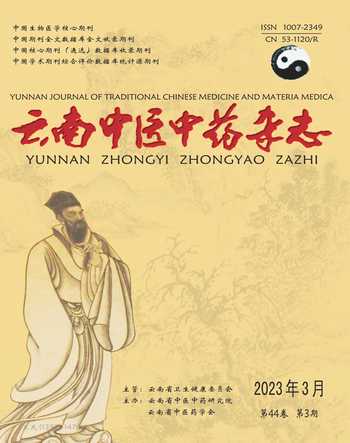360例慢性腎臟病3-4期患者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探析
徐云暉 王億平 湯忠富



摘要:目的 探討慢性腎臟病3-4期患者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及其與相關(guān)因素的關(guān)系,為中醫(yī)藥防治慢性腎臟病提供理論依據(jù)。方法 采用回顧性分析方法收集符合診斷標準的360例慢性腎臟病3-4期患者,對中醫(yī)證型、臟腑病位、證候要素、年齡、原發(fā)疾病、CKD分期、實驗室指標等進行統(tǒng)計分析,探討不同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及其與相關(guān)因素的關(guān)系。結(jié)果 CKD 3-4期患者臟腑病位主在腎293(81.4%)與脾245(68.1%),虛性證候要素主為氣虛236(65.6%)和陰虛137(38.1%),實性證候要素主為濕熱215(59.7%)和血瘀201(55.8%);本虛證以脾腎虧虛證189(52.5%)為主,標實證多兼夾,多見濕熱證215(34.7%)及血瘀證201(32.5%);標實證在本虛證中分布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本虛證中患者主分布在45~59歲154例(42.8%)、69~74歲113例(31.4%),原發(fā)病主為慢性腎炎150例(41.7%),年齡、原發(fā)疾病在本虛證中分布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CKD分期在本虛證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標實證中年齡、原發(fā)疾病、CKD分期分布均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多分布于濕熱證及血瘀證;各項實驗室指標在本虛證中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除iPTH外各實驗室指標在標實證中均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結(jié)論 CKD 3-4期患者中醫(yī)證候分布呈本虛標實、虛實夾雜的特點,本虛證以脾腎氣虛證為主,標實證以濕熱證和血瘀證為主,治療上當(dāng)補益脾腎以扶正,兼顧氣血陰陽之不足,清熱利濕、活血化瘀之法貫穿全程,積極控制原發(fā)疾病、改善營養(yǎng)狀況、糾正礦物質(zhì)代謝紊亂有利于保護患者腎功能,改善患者生存質(zhì)量。
關(guān)鍵詞:慢性腎臟病3-4期;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
中圖分類號:R6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23)03-0042-06
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各種慢性腎臟疾病或累及腎臟的系統(tǒng)性疾病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引起腎功能進行性減退,并產(chǎn)生各種臨床癥狀和代謝紊亂的一種綜合征,具有發(fā)病率高、進展快、知曉率低等特點。流行病學(xué)資料顯示,亞裔成年人患病率約為11.3%[1],我國目前慢性腎臟病患病率為10.8%[2],且不斷進行性升高。慢性腎臟病3-4期是疾病進展的重要階段,有效評估、積極治療并發(fā)癥,有助于延緩CKD進展;中醫(yī)藥在防治慢性腎臟病進展具有肯定療效,準確辨證分型,審證求因,有助于改善患者生存生活質(zhì)量,延緩早中期腎功能進一步惡化,本研究通過對360例CKD 3-4期患者中醫(yī)證候及相關(guān)因素進行統(tǒng)計分析,探討患者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及防治措施。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納入對象為2020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于安徽中醫(yī)藥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腎內(nèi)科住院的CKD 3-4期患者360例,年齡(54.22±14.15)歲,其中男192例,女168例。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yī)診斷標準 參考《腎臟病學(xué)》[3]及KDIGO 2012年提出的《慢性腎臟病評估與管理臨床實踐指南》[4]。
1.2.2 中醫(yī)證型診斷標準 參考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腎臟疾病專業(yè)委員會2015年學(xué)術(shù)年會擬定的《慢性腎衰竭中西醫(yī)結(jié)合診療指南》[5]及《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dǎo)原則》CRF中醫(yī)分型標準[6],中醫(yī)辨證為本虛證與標實證,本虛證分為脾腎氣虛證、脾腎陽虛證、氣陰兩虛證、肝腎陰虛證及陰陽兩虛證,標實證分為水濕證、濕熱證、血瘀證及溺毒證。
1.3 研究對象
1.3.1 入選標準 (1)符合CKD 3-4期診斷標準及中醫(yī)證候標準。(2)年齡為18~85歲。(3)估算腎小球濾過率eGFR<60 mL/min/1.73 m2,>15 mL/min/1.73 m2;且納入前3個月內(nèi)eGFR變化幅度<30%。
1.3.2 排除標準 (1)孕婦或哺乳期患者。(2)精神病患者或無法合作者。(3)合并有腫瘤、心、肝、腦或造血系統(tǒng)等嚴重原發(fā)病者。(4)納入前6個月內(nèi)接受皮質(zhì)類固醇、非類固醇類抗炎藥或免疫抑制劑治療者。(5)合并有感染性疾病包括尿路感染或非感染性炎癥疾病患者。(6)存在急性尿路梗阻性疾病,需行外科手術(shù)治療。
1.4 研究資料 收集患者年齡、原發(fā)疾病、CKD分期、中醫(yī)臟腑病位、證候要素、中醫(yī)證型及實驗室相關(guān)指標。
1.5 統(tǒng)計學(xué)方法 采用SPSS 23.0統(tǒng)計軟件對數(shù)據(jù)進行統(tǒng)計分析,符合正態(tài)分布的計量資料(x±s)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率的顯著性差異用χ2檢驗;非正態(tài)分組計量資料采用非參數(shù)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1為統(tǒng)計學(xué)差異顯著。
2 結(jié)果
2.1 中醫(yī)臟腑病位與證候要素分布規(guī)律 CKD 3-4期患者臟腑病位主分布在腎293(81.4%)與脾245(68.1%)(見表1)。虛性證候要素以氣虛236(65.6%)和陰虛137(38.1%)為主要表現(xiàn),實性證候要素以濕熱215(59.7%)和血瘀201(55.8%)為主要表現(xiàn),少見于溺毒84(23.3%)(見表2)。
2.2 中醫(yī)證型分布情況 CKD 3-4期患者本虛證中脾腎虧虛證189(52.5%)、脾腎陽虛證84(23.3%)、氣陰兩虛證47(13.1%)、肝腎陰虛證31(8.6%)、陰陽兩虛證9(2.5%);標實證中單個標實證中濕熱證46(12.8%)、血瘀證35(9.7%)、水濕證30(8.3%)、溺毒證10(2.8%),標實兼證中,濕熱兼血瘀87(24.2%)占比最多、水濕兼濕熱41(11.4%)次之,水濕兼溺毒最少11(3.1%)(見表3)。各標實證均在脾腎氣虛證中分布最多,陰陽兩虛證中最少,標實證在本虛證中分布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42<0.05),其中溺毒證在各本虛證中分布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03<0.01),余標實證分布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見表4)。
2.3 中醫(yī)證型與年齡、原發(fā)疾病、CKD分期關(guān)系
2.3.1 本虛證與年齡、原發(fā)疾病、CKD分期關(guān)系 表5示本虛證中,患者主分布在45~59歲154例(42.8%),69~74歲113例(31.4%)次之,75~85歲年齡段最少37例(10.3%),年齡在本虛證中分布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42<0.05);45~59歲、60~74年齡段中,主見脾腎氣虛證及脾腎陽虛證,本虛證分布差異分布具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21<0.05,P=0.029<0.05);脾腎陽虛證在各年齡段間分布差異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06<0.01),余本虛證型在年齡段間分布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CKD 3-4期患者原發(fā)疾病多見于慢性腎炎150例(41.7%)、次為高血壓腎病89例(24.7%)及糖尿病腎病73例(20.3%),原發(fā)疾病在本虛證中分布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48<0.05),其中慢性腎炎在各本虛證中分布差異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04<0.01);脾腎氣虛證在原發(fā)疾病中分布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34<0.05),脾腎陽虛證分布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03<0.01)。CKD3期與4期患者本虛證中多見脾腎氣虛證及脾腎陽虛證,CKD分期在本虛證間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
2.3.2 標實證與年齡、原發(fā)疾病、CKD分期關(guān)系 表6示標實證中,患者主分布于45~59歲240例(38.8%),75~85歲年齡段最少85例(13.7%),各年齡段在標實證中均多見濕熱證及血瘀證,年齡在標實證中分布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原發(fā)疾病主為慢性腎炎313例(50.6%),其次高血壓腎病151例(24.4%),各原發(fā)病多見濕熱證及血瘀證,較少見于溺毒證,原發(fā)病在標實證中分布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CKD 3-4期患者標實證中多見濕熱證及血瘀證,分期在標實證中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
2.4 中醫(yī)證型與實驗室指標的關(guān)系
2.4.1 本虛證與實驗室指標的關(guān)系 各項實驗室指標在本虛證中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其中Scr、BUN、Hb、Alb、Ca、P、iPTH統(tǒng)計學(xué)差異顯著(P<0.01)。脾腎氣虛證和氣陰兩虛證患者Scr、BUN、UA、P、iPTH指標低于脾腎陽虛證及肝腎陰虛證,eGFR、Hb、Alb、Ca指標高于脾腎陽虛證及肝腎陰虛證,隨著病情進展遷延,陰陽兩虛證中各項指標最差,提示腎功能損害嚴重、營養(yǎng)狀態(tài)差、伴骨礦物質(zhì)代謝紊亂(見表7)。
2.4.2 標實證與 與實驗室指標的關(guān)系 為避免其他標實證型兼夾產(chǎn)生影響,故選用單個標實證患者實驗室指標進行比較。除iPTH外各項實驗室指標在本虛證中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其中Scr、BUN、UA、Hb、Alb、P統(tǒng)計學(xué)差異顯著(P<0.01)。血瘀證及溺毒證Scr、BUN、iPTH指標高于水濕證及濕熱證,eGFR、Ca指標低于水濕證及濕熱證;
Hb指標濕熱證及血瘀證優(yōu)于水濕證及溺毒證;濕熱證及溺毒證P、UA指標高于水濕證及血瘀證,Alb指標低于水濕證及血瘀證(見表8)。
3 討論
本病在中醫(yī)學(xué)中屬“癃閉”、“關(guān)格”、“水腫”、“虛勞”、“溺毒”等范疇,病機特點為正虛標實,正虛有氣、血、陰、陽之虛損,標實為濕、熱、瘀、毒等差異,慢性腎臟病位主在腎,涉及脾肺,兼顧五臟,肺脾腎調(diào)節(jié)水液代謝、泌別清濁功能障礙,致脾腎衰敗,濕濁水毒潴留。360例CKD 3-4期患者臟腑病位主分布在腎293(81.4%)與脾245(68.1%);虛性證候要素以氣虛236(65.6%)和陰虛137(38.1%)為主要表現(xiàn),實性證候要素以濕熱215(59.7%)和血瘀201(55.8%)為主要表現(xiàn),少見于溺毒84(23.3%)。本虛證中主為脾腎虧虛證(52.5%),次為脾腎陽虛證(23.3%)、氣陰兩虛證(13.1%)、肝腎陰虛證(8.6%),陰陽兩虛證(2.5%)最少。本虛的關(guān)鍵病機為脾腎虧虛,脾腎兩臟又互為因果,腎為先天之本,臟腑陰陽之根,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早期以脾腎氣虛為主,隨著病情進展,氣損及陽,久病及腎,腎陽虛不能溫煦脾陽,脾陽久虛損及腎陽,而致脾腎陽虛陽損及陰,終致陰陽兩虛,故治療上補益脾腎是扶正治療的根本大法。標實證中單個標實證多見濕熱證46(12.8%)、血瘀證35(9.7%),標實兼證中占所有標實證型的66.4%,其中以濕熱證及其兼證最常見,其次為血瘀證及其兼證。正氣虧虛,水濕氣化不行,蘊久化熱是濕熱形成的主要途徑,激素、溫補類藥源性損害、飲食失慎及偏嗜亦導(dǎo)致濕熱的產(chǎn)生;《素問·痹論》云:“病久入深,營衛(wèi)之行澀,經(jīng)絡(luò)時疏,故不通”,提示久病常瘀,血瘀既是致病因素,也為病理產(chǎn)物,正氣虛損,氣血運行無力、陽虛寒凝血滯、陰虛血粘難行,有形之邪阻滯脈絡(luò);溺毒是一類具有粘滯、重濁、稠厚等特性的病理產(chǎn)物或致病因素,久病虛損,肺、脾、腎臟腑氣化失司,致溺毒內(nèi)生,溺毒阻塞氣機,易挾痰、濕、瘀等證,隨著腎功能衰退,五臟衰敗漸進為邪盛病重之證。本研究數(shù)據(jù)顯示,360例患者基本病機是腎虛熱瘀,脾腎虧虛為本,濕熱瘀血蘊毒,產(chǎn)生溺毒之邪,彌漫三焦,故治療上應(yīng)以為扶正祛邪為治則,扶正以顧護脾腎為主,補其氣血陰陽之不足,祛邪當(dāng)以清熱利濕、活血化瘀。大量研究表明中醫(yī)中藥的運用在慢性腎衰竭患者中取得了確切的療效[7-8],保留灌腸法加強通腑泄?jié)峤舛咀饔茫R床上聯(lián)合中藥制劑灌腸,促進腸蠕動、增加腸內(nèi)滲透壓及結(jié)合腸道內(nèi)毒性物質(zhì),促進毒性物質(zhì)經(jīng)腸道排泄[9];中藥藥浴對于慢性腎衰患者皮膚瘙癢、水腫等癥狀有較好療效,利用中藥溫水浴促進循環(huán)和皮膚半透膜的生物特性,促進出汗排毒,達到代償性治療的目的[10]。穴位貼敷選用益氣、溫陽、活血藥物,經(jīng)過皮膚的滲透作用和穴位刺激經(jīng)絡(luò),改善局部血循環(huán),改善腎功能[11]。
360例CKD 3-4期患者主分布在45~59歲年齡段,一項2657例CKD中晚期患者病因及相關(guān)因素分析中,各期患者年齡主分布在41~60歲[12]。45~59歲、60~74年齡段本虛證多見脾腎氣虛證及脾腎陽虛證,分布具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標實證中多見濕熱證及血瘀證,分布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病齡較低患者,病情尚輕,隨著疾病遷延,正氣虧虛逐漸加重,標實證型多兼夾,出現(xiàn)多種并發(fā)癥,患者生活質(zhì)量下降。患者原發(fā)疾病主為慢性腎炎,次為高血壓腎病及糖尿病腎病,一項937例慢性腎功能衰竭病因調(diào)查中顯示,慢性腎小球腎炎為主要病因(26.15%)、糖尿病腎病及高血壓腎損害分別占比25.51%、14.41%[13]。本虛證型中多見脾腎氣虛證與脾腎陽虛證,標實證中多見濕熱證及血瘀證,原發(fā)病中慢性腎炎病例最高,符合慢性腎炎蛋白尿的“脾腎虧虛為本”的病機特點;高血壓、糖尿病是CKD發(fā)病的重要危險因素,血壓及血糖升高加重腎臟負荷,引起腎小球內(nèi)壓力升高,引起腎血管病變,促進腎小球硬化,導(dǎo)致腎缺血性損傷發(fā)生率增加,相關(guān)研究表明高血壓及糖尿病因素對于患者靶器官損害直接相關(guān),是導(dǎo)致腎功能衰竭、動脈粥樣硬化、腦卒中、心腦血管疾病重要危險因素[14-15]。CKD分期與證型分布情況顯示,3-4期患者本虛證以脾腎氣虛證最為多見,次為脾腎陽虛證,前期以氣虛、陽虛為主,隨著疾病的進展,逐漸向陰陽兩虛轉(zhuǎn)化;邪實證中3-4期患者以濕熱證,瘀血證多見,脾腎虧虛,水液代謝失常,水氣、濕濁等產(chǎn)物無法及時排出,蘊久生熱、成瘀、成毒,以致疾病后期血瘀證、溺毒證比例增多。故對于早期患者,用藥當(dāng)以補益脾腎為主,固護陰陽為要,兼以清熱利濕、活血化瘀。
本研究實驗室指標表明,各指標在本虛證中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除iPTH外各指標于標實證中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Scr、BUN、eGFR、UA是腎功能的體現(xiàn),脾腎氣虛證和氣陰兩虛證指標優(yōu)于脾腎陽虛證及肝腎陰虛證,隨著病情進展遷延,氣損及陽,陽損及陰,終致陰陽兩虛,陰陽兩虛證中各項指標最差,提示腎功能損害嚴重;水濕證及濕熱證Scr、BUN、eGFR指標優(yōu)于血瘀證及溺毒證,濕熱證及溺毒證UA指標高于水濕證及血瘀證,濕熱下注膀胱,氣化失司,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致脾腎功能衰敗,瘀血溺毒既是病理產(chǎn)物也是新的致病因素,慢性腎臟病發(fā)展到晚期,腎小球率過濾極度低下,體內(nèi)代謝產(chǎn)物無法排出而出現(xiàn)血肌酐、尿素氮等水平極速升高。Hb、Alb反應(yīng)患者營養(yǎng)狀態(tài),本虛證中陰陽兩虛證營養(yǎng)狀況最差,提示腎功能受損嚴重;標實證中水濕證及溺毒證Hb水平最低,濕熱證及溺毒證Alb水平最差,疾病后期病理產(chǎn)物積聚,因其腎功能不可逆,腎單位受損,促紅素分泌減少,血色素低,故會表現(xiàn)血紅蛋白水平低下。Ca、P、iPTH反應(yīng)骨礦物質(zhì)代謝,血瘀證及溺毒證iPTH、Ca指標最差,濕熱證及溺毒證P水平最高,繼發(fā)性甲狀腺功能亢進(SHPT)是礦物質(zhì)代謝紊亂重要表現(xiàn),也是CKD-MBD患者最常見并發(fā)癥,矯枉失衡學(xué)說指出慢性腎衰竭引起機體代謝失衡,通過機體適應(yīng)性代償糾正失衡,同時可能導(dǎo)致新的損害引起新的失衡[16],低鈣血癥刺激機體iPTH分泌,進而促進腎小管磷的排泄糾正高磷血癥,但腎功能明顯損害時導(dǎo)致血磷升高,鈣磷乘積升高,增加動脈粥樣硬化及心腦血管事件發(fā)生率。
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可能因樣本量不足存在偏倚,納入研究的指標特異性及精確性有待完善。綜上所述,CKD 3-4期患者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呈現(xiàn)本虛標實、虛實夾雜的特點,本虛證以脾腎氣虛證為主,標實證以濕熱證和血瘀證為主,患者常合并多種基礎(chǔ)疾病,且易并發(fā)腎性貧血、骨礦物質(zhì)代謝紊亂等多種并發(fā)癥,治療上當(dāng)補益脾腎以扶正,兼顧氣血陰陽之不足,清熱利濕、活血化瘀之法貫穿全程,積極控制原發(fā)疾病、改善營養(yǎng)狀況、糾正礦物質(zhì)代謝紊亂有利于保護患者腎功能,改善患者生存質(zhì)量。
參考文獻:
[1]Esposito C,Torreggiani M,Arazzi M,et al.Loss of renal function in the elderly Italians:A physiologic or pathologic process[J].The Journals Gerontology Series A: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2012,67(12):1387-1393.
[2]Zhang L,Wang F,Wang L,et al.Prevalence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China:a cross-sectional survey[J].Lancet,2012,389(9818):815-822.
[3]王海燕.腎臟病學(xué)[M].3 版.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8:1053-1058.
[4]KDIGO,KDIGO 2012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J].USA.NNF,2012:1024.
[5]陳香美,倪兆慧,劉玉寧,等.慢性腎衰竭中西醫(yī)結(jié)合診療指南[J].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雜志,2015,35(9):1029-1033.
[6]鄭筱萸.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dǎo)原則[S].北京:中國醫(yī)藥科技出版社,2002:188-19.
[7]劉紅亮,張琳琪.慢性腎臟病中醫(yī)證候研究進展[J].河南中醫(yī),2020,40(5):807-809.
[8]謝 婷,俞東容.慢性腎臟病中晚期的中醫(yī)證候與治療[J].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腎病雜志,2019,20(6):547-548.
[9]王立媛,王億平,茅燕萍,等.中藥優(yōu)選方保留灌腸聯(lián)合高位結(jié)腸透析對慢性腎衰濕熱證患者CysC、PTH 水平及營養(yǎng)的影響[J].陜西中醫(yī),2020,41(7):917-919.
[10]劉萊萊,段娟.從“開鬼門”理論探討中藥藥浴療法清除尿毒癥毒素[J].新中醫(yī),2013,45(7):189-190.
[11]徐鵬,黎創(chuàng),毛煒,等.慢性腎衰竭的中醫(yī)一體化治療方案探討[J].世界科學(xué)技術(shù)-中醫(yī)藥現(xiàn)代化,2013,15(5):990-993.
[12]李娟,劉虹.2657 例 CKD3 到 5 期患者病因及相關(guān)因素分期[J].中南大學(xué)醫(yī)學(xué)報.2008,10(5):45.
[13]王宗謙,尹麗,張思晴.慢性腎功能衰竭 937 例病因分析[J].中國實用內(nèi)科雜志,2013,(33)1:58.
[14]Noshad S,Mousavizadeh M,Mozafari M,et al.Visit-to-visit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is related to albuminuria variability and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J].J Hum Hypertens,2014,28(1):37-43.
[15]Yu JM,Kong QY,Schoenhagen P,et al.The prognostic value of long-term visit-to-visit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on stroke in real-world practice:A dynamic cohort study in a large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hinese hypertensive population[J].Int J Cardiol,2014,177(3):995-1000.
[16]王辰,王建安.內(nèi)科學(xué)[M].3版.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5:701.
(收稿日期:2022-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