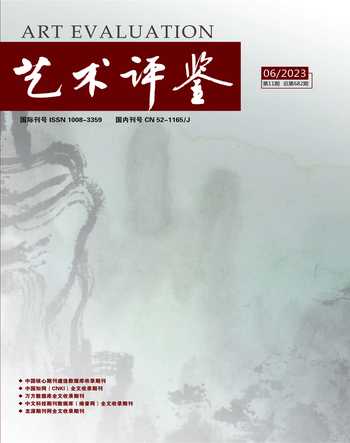從異質同構理論看當代舞蹈審美“新現象”
宋春穎
摘要:異質同構是格式塔心理學中的核心理論,是構成格式塔“完形”的重要形式。格式塔認為在不同的領域中存在著同樣的形態或結構,當這些不同領域的物質在形態或結構等趨于一致時,相互之間會產生作用,實現異質同構。格式塔對于異質同構并沒有將其范圍固定化,因此本文以異質同構分析當代舞蹈審美,并總結出“平衡”“重疊”“交互”三大特征。
關鍵詞:異質同構? 舞蹈審美? 新現象
中圖分類號:J705
異質同構理論是由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魯道夫·阿恩海姆所提出的,是格式塔心理學的核心觀點,并且格式塔心理學以“異質同構”來解釋審美經驗的形成。要了解異質同構,首先要對格式塔的原理有所了解。“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一詞的音譯,其意思是“完形”,強調完整性,“形”是指由知覺活動組織和建構經驗的整體性。格式塔心理學認為任何一種完形的內部都存在一種張力,也就是一種“力的圖式”。不同的完形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關系,當性質相同的“力”構成完形時,為“同質同構”;當性質不同的“力”構成完形時,為“異質同構”。在審美活動中,格式塔心理學派認為:“在外部事物、藝術式樣、人的知覺(尤其是視知覺)、組織活動(主要在大腦皮層中進行)以及內在情感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統一。它們都是力的作用模式,而一旦這幾個領域的力的作用模式達到結構上的一致時,就有可能激起審美經驗。”這就是格式塔異質同構核心理論。
舞蹈藝術與異質同構關系的建立基于兩點:一是舞蹈完全以人的肢體為語言,本身傳遞的就是“力的行為”,阿恩海姆認為“每一個視覺事物都是一種顯著的動力事件”,從視覺的角度,人體就形成“力的圖式”。二是在舞蹈審美活動中,舞蹈藝術品與觀眾在空間上存在著情感溝通。所以,一方面是基于舞蹈本體而言,另一方面是舞蹈審美包含的主客關系,可以試圖將舞蹈與異質同構相關聯,以對舞蹈審美進行更進一步挖掘。身體、心理、時間、空間是舞蹈藝術的四要素,平心說:“身體是舞蹈的物質載體和技術本質,心理是舞蹈的靈魂和藝術本質,空間是身體(物質)存在的綿延,時間是心理(精神)的綿延。”從異質同構最初的定義和來源來看,似乎異質同構理論僅僅可以對舞蹈本體的身心層面進行解釋,但通過對異質同構的進一步剖析與全方位解讀,可以發現異質同構理論不僅僅涉及身心的同構、審美活動中主客關系同構,還可以從空間上、創作上、不同藝術門類以及不同媒介與舞蹈的異質同構,以此來解釋當代舞蹈審美中出現的“新現象”:平衡、重疊與交互。
一、平衡:審美建構的主客共情
“不管是從視覺上說,還是從物理上說,平衡都意味著其中所有活動達到停頓時所持有的一種分布狀態。也就是說,對于一件平衡的構圖來說,其形狀、方向、位置諸要素之間的關系,都達到了如此確定的程度,以至于不允許這些要素有任何些微的改變,在這種情形下,整體具有的那種必然性特征,也就可以在它的每一個組成成分中呈現出來。”阿恩海姆陳述了在繪畫構圖中的“平衡”,以及“平衡”的重要性。雖然這是具象中的“平衡”,但放在抽象的舞蹈審美活動中同樣適用,從異質同構理論看舞蹈審美活動,在審美的主體與客體之間便存在著這樣一種“平衡”而又穩定的關系。
從審美的角度看,舞蹈表演者通過身體語言傳遞出獨有的“張力”,這種“張力”通過某種方式傳遞給審美主體,從而喚起情感共鳴。從物理學的角度來判定,一種力是不可能單獨存在的,必然存在著與之相互作用的力,那么在審美活動中的主體也必然存在一種力,這種力來自審美主體的內心欲求。心理學家分別從物理領域和心理領域對這兩種力進行了劃分。在舞蹈審美活動中,舞蹈藝術品的傾向性“張力”是存在于物理領域的力;另一種力存在于心理領域,即欣賞者內心世界中。從格式塔的“完形”概念來看舞蹈審美的過程,則是心與物的完形,心與物的同構,即“心物同構”,或者說是“心舞同構”。從前文中可以看出,阿恩海姆認為想要繪畫作品能夠完整呈現、準確表意,就要實現各個要素的平衡。將阿恩海姆的平衡構圖理論用于舞蹈審美活動進行分析,在這個審美活動的“構圖”中各要素也需要“平衡”:審美主體與客體的兩個場域,以及上文提到的兩個“力”之間存在的平衡。審美主體心理領域的“力”與審美客體物理領域的“力”,二者相互作用,當作用性趨于一致時,傳遞給對方的就會是最和諧的訊息或是最飽滿的能量,在審美主體與客體之間就會形成持續的穩定關系。
“力”的異質同構連接了心理領域和物理領域,并最終使二者達到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但是僅僅兩個不同性質的“力”的同構是不能直接形成平衡關系的,中間必然存在著某一動態過程,來擔任兩種“力”相互作用的媒介,這種過程能夠將審美主體與客體的力進行“交互”,使得一方作用,另一方被作用,這一過程便是“移情”。德國心理學家T.立普斯認為:“移情是一種積極主動的投射。”美感的產生是由于審美時人們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審美對象上去,將自身的情感與審美對象融為一體,或者說對于審美對象進行內在模仿,即“由我及物”或“由物及我”。朱光潛指出:“人在觀察外界事物時,設身處在事物的境地,把原來沒有生命的東西看成有生命的東西,仿佛它也有感覺、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動,同時,人自己也受到對事物的這種錯覺的影響,多少和事物發生同情和共鳴。”通過移情主體將自身的情感傾注到客體上,客體又將意味傳遞給主體,在這一過程中主體與客體雙向建構彼此所需,“異質同構”了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移情”在異質同構中作為一種過程或者說是動作,所承擔的是“力”相互作用。
審美活動的構成要素包括兩個場域中的主體與客體,以及連接審美主體與客體的移情。存在于主體與客體的“力”通過移情相互作用建立“平衡”,最終實現舞蹈審美的主客共情。舞蹈詩劇《只此青綠》中就存在這樣的平衡。象征中國傳統符號的“青綠”率先向觀眾傳遞了“美”的視覺體驗,觀眾在接受作品的這種“美”的張力時進行思維意識的轉換,產生除視覺之外的審美欲求,觀眾將這種欲求通過移情加注于作品。作品通過移情又向觀眾傳遞出宋代畫家王希孟的工匠精神、《千里江山圖》的雄渾氣勢,以此使得觀眾產生文化自信,從而實現平衡。
二、重疊:媒介融合的創新表達
按照阿恩海姆的看法:“只有保持某種程度的自我獨立,才是‘部分的真正特征。一個部分越是自我完善,它的某些特征就越易參與到整體之中……沒有這樣一種多樣性,任何一個有機的整體(尤其是藝術品)都會成為令人乏味的東西。”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對獨立性的強調,組成整體的每個個體也都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整體。異質同構的完整不僅僅針對一個大整體,它也強調了大整體中各個部分的完整,也就是說異質中每個“質”都是一個獨立且完整的個體。正是因為個體的獨立性,使得個體可以與外界構造自己的獨特形式。阿恩海姆基于視知覺的形式提出了“重疊”,并將它作為異質同構的一種方式,他認為重疊“可以通過使各種形式關系在一個更加統一的式樣之內集中,而使這些關系得到控制和加強”,這與上一節中的“平衡”有著密切關系,外部的“重疊”最終也是為了保持內在的“平衡”。在如今大融合的時代,單一的媒介開始面臨著機遇和挑戰,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單一媒介生存的邊界逐漸模糊,媒介融合現象現已成為一種流行趨勢,舞蹈也在這場媒介風暴中履步向前。將阿恩海姆的“重疊”映射到舞蹈的整體發展環境中,舞蹈趨向于與外界環境融合的狀態,當舞蹈的內部實現穩定的平衡態后,它開始作為一種完整的、獨立的個體,與外界中的其他媒介融合生存。通過“重疊”實現視覺的疊加效果,也是當代舞蹈審美中一種獨特的現象,表現出個體與個體在視覺空間上“融合”的特征,如舞蹈與自然環境、與人工環境的融合,舞蹈與技術的融合等。
舞蹈與環境的異質同構通過重疊呈現出“融合”的形態,從舞蹈的起源來看,這種“融合”是在回歸中創造新審美。通過重疊將舞蹈作為一種獨立的完整的個體與環境交融,通過“同構”,從而創造出全新的視覺體驗。如今,舞蹈跳脫出傳統劇場而走向社會環境中已成為舞蹈界非常流行的現象,動態的舞蹈為靜態的環境注入了活力,而不同的環境也為舞蹈提供了多樣靈感。舞蹈藝術家們開始試圖主動尋找舞蹈與環境的契合進行創作,對特定的環境做出實際的回應,使舞蹈與環境二者融合共生,突破各種局限,從而給觀者帶來身臨其境的視覺審美體驗。在河南衛視舉辦的“端午奇妙游”端午特別節目中,舞蹈水下飛天《祈》就非常直觀地詮釋了舞蹈與環境的融合,飛天與水環境本是毫不相干,但是舞者卻可以通過水而反重力,真正實現了“飛”,完美展現了《洛神賦》中的那句“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讓觀者贊嘆不止。
如果說舞蹈與環境的重疊是“回歸”,那么舞蹈與技術進行重疊則是“進階”。技術并不是一開始就伴隨著舞蹈的,而是在時代的推動下逐漸形成的審美現象,尤其是如今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多種媒介產生,更是給人們帶來全新的視覺盛宴。藝術家們總能發現不同尋常的,錄像藝術的潛在的具有創造性的功能被充分發掘,它“可以記錄同步發生的行為、表演或事件,也可以將同一空間中的屏幕影像、錄像裝置和環境相并置,還可以將膠片、影像造型和錄像裝置等多媒體雜糅、交叉或融合”,借此影像藝術逐漸形成,舞蹈影像也緊隨其中萌生并發展。集成化的時代催促著舞蹈與各種媒介交融,舞蹈影像現已成為當代舞蹈跨媒介交融的最重要的表現形式。通過舞蹈影像可以克服很多技術上的困難,比如上文提到的水下舞蹈,長時間在水下舞蹈是有非常大的難度的,但通過影像剪輯進行拼湊和鏡像剪切便可以保障舞蹈的完整性。
信息化時代的快速發展催促著多種媒介的產生。在舞蹈與技術融合的范疇中不只有舞蹈影像,舞蹈與科技的交互碰撞也在這場風暴中嶄露頭角,藝術家與觀者都渴望在科技和舞蹈的相互探索中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以再次豐富舞蹈的創造性表達。河南衛視春晚中的舞蹈《唐宮夜宴》,作品利用數字媒體創設舞蹈環境,從而實現了博物館與舞臺的時空轉換,在不知不覺中帶領觀者穿越;還有由唐詩逸主演的《西河劍器》,舞者手中的劍并不是傳統的舞蹈道具,而是虛擬的“劍”,這種虛擬道具的應用真的實現了收放自如。除了這種空間上的突破,還有舞臺表現手法上的創新,比如“人影共舞”的互動式多媒體舞蹈表演,在這種表演形式中,數字媒體不是作為背景或是道具,而是也成為“表演者”,與舞者互動。在這場藝術與科技交融的視覺盛宴中,“人”從一個表現的主體逐漸變成啟發式的關鍵媒介,這些虛擬的影像是創作者通過對人體生命結構深度剖析進而進行數字媒體編程所形成的“概念化”人體。
“每一種媒介都提供了轉譯模特之突出特征的最佳方式”。無論是舞蹈與環境,還是舞蹈與技術,都是舞蹈對于媒介時代到來的直接回應。在當下多元化的時代,帶有創新性的事物的出現總歸是有意義的,“多種媒體形式要打破傳統的單一模式,提供不同的表達方式”,這也是舞蹈在跨媒介發展中的必然趨勢,是當下時代價值的體現。
三、交互:多元手法的交融互鑒
“一個‘部分越是自我完善,它的某些特征就越易參與到‘整體中”,并且能夠在這個整體中始終保持完整而不被其他因素破壞影響。在上一節中探討了舞蹈作為一個完整的物質與其他媒介在外部空間環境中的同構融合,通過研究會發現雖然舞蹈與其他媒介的邊界逐漸模糊化確實帶來了許多創新性的體驗,但當站在舞蹈的角度去思考這一現象時會發現舞蹈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被削弱了,尤其在舞蹈與科技同構中,似乎舞蹈長于抒情的特點逐漸被淡漠。針對這樣尷尬的境地,舞蹈需要以更完美、完整的姿態投入到與其他媒介的博弈中,它需要新鮮的血液來充沛自己。藝術是相通的,舞蹈在與其他藝術建立關系的過程中呈現出“交互”的姿態,不同的藝術為舞蹈提供了多種創作靈感,從多元藝術中汲取營養,使得舞蹈有了更多的資源構建自己的獨特性。
在舞蹈與多種藝術同構中,首先想到的便是作為同源藝術的音樂。從最初的樂舞到舞蹈與音樂分別成為獨立的藝術,秉承著事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發展規律,今天的舞蹈又與音樂產生了交融,雖然音樂與舞蹈看起來一直沒有分開過,但音樂對舞蹈是在創作上的滲透,是當下最顯著的。比如,卡農作為一種復調音樂形式,其擁有特殊的技法,“它以連續的模仿為基礎,當一個聲部還未結束時,另一個聲部就以模仿的形式開始”,在舞蹈作品中常看到的“流水”,與卡農技法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通過舞者身體上的“卡農”,表現情緒的起伏漲落,比如從身體的小關節到大關節的身體律動,幅度由小及大,以體現表演者情緒的迸發和情感宣泄;或是通過整體調度上的“卡農”,表現群體意象或精神氣質,如舞蹈《小溪·江河·大海》中的“流水”,給人一種連綿不斷之感。
作為動覺藝術的舞蹈藝術與影視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從宏觀上看,兩者都具有“動”的特征。不同的是影視的“動”來自鏡頭的捕捉,而舞蹈的“動”,一方面來自人體,另一方面來自觀者形成的視知覺活動中,即在前文提到的審美主體與客體的“力”的同構。舞蹈也在影視的創作中對號入座,并從中汲取具有創造價值的資源,“蒙太奇”影視創作技法就是其中之一。蒙太奇最早是應用于建筑學中的一種創作手法,有安裝、組合、構成之意,即將各部分通過安裝、組合等構成一個整體。通過諸多影視藝術家從不同角度對蒙太奇技法進行解讀,最終將蒙太奇的主要特點歸結為:第一,具有敘事功能;第二,通過鏡頭的聯結調動觀眾的理智和情感。舞蹈也充分利用了蒙太奇的這兩大特點,實現了自身優化。大部分的舞蹈影像都采用了“蒙太奇”鏡頭編創,通過“蒙太奇”讓鏡頭為舞蹈而舞動,使舞蹈影像擺脫了機械性的復制,讓同一個舞蹈作品在鏡頭下有了不一樣的表達,如在大理舞蹈季中的舞蹈影像作品《轉山》,創作者將作品從劇場轉換到自然環境中去,在不改變舞蹈原本結構、內容條件下通過對鏡頭進行“蒙太奇”的拼貼、重組,向觀者展現了更為深刻的生命輪回之美。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唐代詩人、畫家王維對于詩歌與繪畫藝術特征的描述,繪畫與詩歌自古就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在如今藝術交融的環境中,藝術家們更多專注于詩歌與繪畫“寫意性”的共通。隨著人們對于審美的高度追求,以身體語言為媒介的舞蹈藝術也開始了對“詩情畫意”的追尋。眾所周知,詩歌是以語言表達為媒介的文學藝術,也正因為文字是人們無法通過感官直接感受的,所以會使人們產生無盡的遐想,這也為詩歌意境的營造創造了條件。中國古代詩歌深受道家哲學和美學思想的影響,表現出虛中有實、虛實相生的藝術特色,舞蹈也應充分利用這種虛實結合的創作手法,構建自己的象外之象、境外之境,如舞蹈詩劇《只此青綠》《節氣江南》等。繪畫是以色彩和線條為表現媒介的藝術,相比詩歌,繪畫的呈現更為“直觀”,繪畫也常常通過這種“直觀”來調動觀者的聯想或想象以實現“言外之意”的表達。在中國畫中常用“留白”手法進行創作。“留白”是中國傳統繪畫特有的意象創作手法,它以“不著一字”“不染一色”來營造出幽靜空谷的幻想和“無畫處皆成妙境”的審美旨趣。舞蹈也常從不同的角度采用“留白”進行意象和意境的塑造,以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舞蹈詩劇《大方無隅》以道家“大方無隅,大器免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為創作主體,表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道家美學觀,這部作品的“留白”主要體現在整體結構、舞臺美術、人物動作、服裝化妝、背景音樂等方面都追求“減法”。不得不說詩歌和繪畫對于舞蹈的意境美產生了功不可沒的影響,通過與詩畫的交融,進一步營造了舞蹈的“詩情畫意”之感。
在藝術大融合的時代,各門藝術都在不停地“拿來”和“給予”,以編織更完美、更完整的自我。無論是何種藝術門類,給予舞蹈的都不只是單方面的,在取“精華”過程中,舞蹈要始終保持本體的堅固穩定以構建完善自身的獨特性。
四、結語
格式塔的異質同構理論雖然只對知覺經驗進行了分析,但根據其概念,實際上異質同構適用范圍是很寬泛的,“平衡”“重疊”與“交互”是本文試圖對異質同構的發展,通過研究也表現出契合。時代在進步,技術在進步,審美在不斷變遷,在當下的審美“大熔爐”中,相信舞蹈藝術還會呈現出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姿態,異質同構是否還可以用來解釋舞蹈藝術還有待深度探究。
參考文獻:
[1]滕守堯.審美心理描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4-95.
[2]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M].滕守堯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5-435.
[3]平心.舞蹈心理學[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3.
[4]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教程[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21.
[5]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6]張朝霞.新媒體舞蹈概論[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24-30.
[7]羅鑫.什么是“全媒體”[J].中國記者,2010(03):82-83.
[8]于潤洋.西方音樂通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6.
[9]傅正義.電影電視剪輯學[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
[10]彭峰.藝術學通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