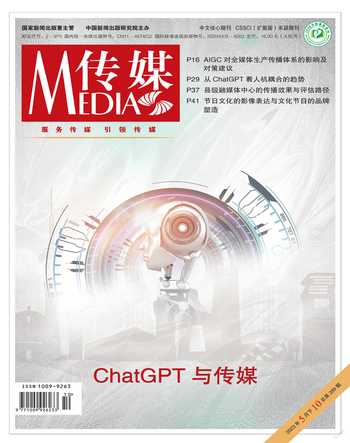基于媒體視角的賈樟柯電影媒介美學研究
薛洋瑤
對電影語言和電影美學的選擇,構成了不同電影導演及其影視作品的特色。換言之,展開對電影本體和電影美學的研究,自然也是和電影導演及其作品創作分不開的。事實上,現有的電影美學研究和電影美學探索,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向現實語境下電影創作實踐的靠攏,即將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密切結合起來。學界和業界在導演、影視作品、聲畫等常規創作項目上進行了持續研究,為窺見中國電影美學的嬗變、推動中國電影美學理論研究和中國文化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
不可否認,電影作者本身往往成為電影美學分析的“元命題”。而“影戲之作者實為導演”,是大多數人接受的觀念。作為戛納國際電影節終身成就獎“金馬車”的獲獎者,賈樟柯導演在電影界的影響力不言而喻。一直以來,賈樟柯和他的電影作品都受到了學界、業界的重視。曾任法國權威電影雜志《電影手冊》主編的國際知名影評人讓-米歇爾·付東(Jean-Michel Frodon)對賈樟柯的電影世界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和總結,其記錄和寫就的《賈樟柯的世界》一書通過鮮活的資料呈現賈樟柯的創作“世界”、多維視角標識賈樟柯的電影美學、內外對話勾勒中國電影的肌理。它既讓電影愛好者對賈樟柯電影知識譜系和電影美學有更全面的認識,也對電影創作群體的美學實踐有所助益。
鮮活資料呈現賈樟柯的創作“世界”。通常來說,學界往往沿著哲學、精神分析學和政治學等學術路徑對電影作品、現象或思潮進行探討,進而深入挖掘電影實踐的美學特征和文化意義。一方面,聚焦于具體的影視作品,探究電影本身的審美特性和表達方式。另一方面,將影視創作置于中國或世界影視史的坐標上進行考察,即文藝研究中的“代”(或“流派”)的概念。不同的研究取向,也經常指向一個共通點:電影導演成為影史研究的重要研究對象。恰如美國著名影評人安德魯·薩里斯(Andrew Sarris)在《走向電影史的理論》一書中所提出的,一部電影史能夠合乎邏輯地把自己限定為一部電影導演的歷史。電影導演,他們既在電影之內,也在電影之外;既是屬于電影本身,同時也是超越個體生命的社會的、歷史的存在。
在讓-米歇爾·付東所記錄和寫就的這部著作里,他用鮮活的資料編織了一張完整的關于賈樟柯的信息、事件、人物、思想之網。它從賈樟柯具體的創作經驗出發,聚焦于賈樟柯對自己電影的講述及作者本人對賈樟柯從1994—2015年的電影作品的解構,并根據賈樟柯本人的文字節選及其合作者趙濤、余力為等對往事的回憶,巧妙地呈現出了賈樟柯的創作“世界”。可以說,本書既立足于賈樟柯的自述維度,從個人化的經歷與體驗出發,從童年時期到成長時期,從故鄉記憶到世界舞臺,耐心十足地勾勒出賈樟柯的個人氣質;而他者的視角又將賈樟柯電影鑲嵌進具體的歷史情境和現實場景,為理解賈樟柯的創作“世界”提供了另一個維度,進一步將其拍攝過程、創作理念、蛻變歷程等梳理成線索,使賈樟柯的時代精神、時代意義可感、可視。此外,本書收錄了賈樟柯電影百余幅劇照與其工作照,引導影迷和讀者打開這份賈樟柯電影的藝術檔案,進一步通達其電影美學和思考方式。
多維視角標識賈樟柯的電影美學。北大教授戴錦華曾評價賈樟柯是一位不執著于自己風格標簽的電影導演,他自覺且靈活地在藝術/商業、國際電影市場/本土市場、都市/鄉村、超級大都市/內陸小城、“普通話”/方言、獨立/機構、“作者”/類型(電影)、紀錄/虛構(電影)等坐標間滑動。可見,與賈樟柯的對談及對其作品的回望,也是對中國電影史、世界電影史、中國電影藝術和世界電影藝術的回望,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這也不難理解,近年來學界、業界紛紛將目光轉向賈樟柯,對其文本(包括但不限于電影文本)進行細讀,探討其電影實踐的美學特征和文化意義。本書也不例外,它結合賈樟柯對談、電影文本和合作者采訪等多維視角,梳理賈樟柯電影創作思想,標識其電影美學創造和藝術流變:他者關懷下的影像“寫作”、文化自覺下的多層次美學。總的來說,體現了作者“人本內涵的現代電影”和“影像本體的藝術電影”的研究立場。
事實上,“人”對于導演來說是最重要的。電影因細節的、具體的、大寫的“人”而成立。如周星、粟牧在《百年背景下的新世紀中國電影現實題材分析》一文中所闡釋的,百年中國電影就是現代社會現實的影像,折射生活、表現現實,描繪當下社會,成為中國電影最為重要的任務。在本書的多維視角分析下不難發現,無論是在創作開端,還是盛譽滿載后,賈樟柯始終貫徹的是他者關懷下的影像“寫作”。為了尋找賈樟柯電影美學的形成,作者通過向賈樟柯的成長經歷要答案,從一問一答中,賈樟柯的創作思想躍然紙上。他所呈現的是現實社會的復雜性,包括復雜的人物命運、復雜的人物內心世界、復雜的人物關系,在這份錯綜復雜里賈樟柯的個人特質反而愈加清晰——他的影像“寫作”經驗總與“人”有關。另一方面,本書也從賈樟柯長大后的經歷去尋找其電影美學的形成淵源。眾所周知,賈樟柯的創作起點是從故鄉和故鄉記憶開始的,直到現在,他仍然從故鄉去眺望世界。而在時代的巨輪下,“人”才是賈樟柯電影的真正源頭。他把觀察視野和思考角度帶向了汾陽,帶向了社會個體的生命歷程里。譬如他的“故鄉三部曲”——《小武》《站臺》《任逍遙》,從一開始就讓我們鎖定中國小縣城里具體的人。大千世界里的普通個體得以獲得社會關注。可見,賈樟柯電影所呈現的,是一道復雜的社會、歷史、政治的解析題。
如果說賈樟柯帶來的是對社會個體尤其是底層人、邊緣人的“電影新目光”,那么使其始終活躍且不被標簽定義的則是文化自覺下的多層次美學。這份自覺和靈活,恰好印證作者稱謂他為“最大膽的現代電影創作者、最新技術和美學的貢獻者”。作者敏銳且耐心,提問樸素卻精確,緊緊抓住賈樟柯個人思想之錨,條分縷析一位中國電影導演的電影創作和生命體驗。除了人物的新視角,賈樟柯在電影形式和審美創造上不斷探索。在本書里,作者同樣追問了賈樟柯所處的“中間位置”,即紀錄片與劇情片的聯系和區別。在電影美學實踐中,形成獨樹一幟的“賈氏”紀實美學。另外,賈樟柯頻頻提及中國傳統文化如“說書”、繪畫等,彰顯其文化融合與傳承自覺。與中國文化的有機融合,是賈樟柯電影美學實驗與探索的重要方向之一。如《天注定》采取了中國的敘述傳統“說書”這一民間藝術的痕跡。事實證明,文化自覺下的多層次美學使賈樟柯導演及其作品在喧嘩的眾聲中發出更大的聲響,且深遠綿長。他在歷史與當下、民族與個人、宏觀視野與生動細節中不斷形塑自己的美學風格。此外,探索電影新可能離不開新技術的運用。正如賈樟柯自己提到的,他對新技術極為關注,每一項新技術都給電影美學帶來新東西。至此,賈樟柯電影世界變得愈發清晰。
內外對話勾勒中國電影的肌理。縱覽百年中國電影發展史,我們會發現,“世界視野的民族電影”“中國電影走出去”“文化自覺”等描述經常被提及。尤其隨著時代的發展,國內電影和國際電影兩個生態之間充滿合作、競爭的張力。對于國內的電影創作實踐來說,其使命在于講好“中國故事”、塑造“中華形象”,加速了當下中國真正文化自覺的確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現代性需求下,中國電影界與國外電影界的對話必不可少。此書正是外國學者對中國電影導演的矚目與提問,通過內外對話勾勒中國電影的肌理。毫無疑問,集理論視野、美學風格、現實主義、當代思維、批判自由等特性于一身的賈樟柯成為讓-米歇爾·付東甚至是法國影評界的“中國電影文化代言人”。憑借作者過人的敏銳與直覺,他對賈樟柯及其電影做出了精準的概括。
以影像為途徑,觀照賈樟柯的電影美學,實際上是一個進入中國電影史的有效切入點。作者與賈樟柯的對話,以“史的眼光”切入到中國電影的歷史現場,緊緊圍繞著中國歷史發展脈絡,深入探討賈樟柯電影美學特性及其基本規律。恰如作者所形容的,賈樟柯的電影可被稱為“長河電影”和“網狀電影”。一方面,賈樟柯作為現代化和城市化中的小鎮導演,他的電影中的故事承載著悠久的歷史和政治文化史,見證了中國的變遷。他通過故鄉這個窗口,觀察中國,觀察世界。從以1979—1989年時代為背景的《站臺》,到表現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的《小武》,到21世紀初的《任逍遙》,再到2002—2003年的《世界》《三峽好人》,這些影像記錄著賈樟柯對1970年代至今中國巨變的看法,這些電影是對急速變化的時代做出的現實回應。賈樟柯也坦言,想要辦一個回顧影展及繼續拍大規模系列影片,通向另一個故事或無窮無盡的其他故事,更好地描摹中國社會。另一方面,本書作者的影評序列從側面構造出賈樟柯電影的“編年史”,以一種歷史性闡述來論證賈樟柯影像的美學偏好和“當代”精神。總的來說,本書的描述體系和脈絡兼具文獻性、真實性和反思性,使得讀者以窺見中國電影的高光時刻。
時至今日,研究者們已然無法忽視賈樟柯的電影美學對中國電影史、世界電影史的重要價值。本書作者試圖通過多個維度去確認賈樟柯所處的位置,其中不乏本人訪談、影視評論、影視作品、文學作品等,既有鮮活豐富的文本素材,也有富有見地的專業見解。通過本書走進賈樟柯的創作“世界”,觸摸中國電影的美學肌理。可以說,本書構成了有趣的智識回應,既對電影愛好者發出邀請,也是可供電影創作者參考的重要“工具書”。
作者單位 青海師范大學新聞學院
本文系青海師范大學2023年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淺析賈樟柯電影中的視聽表達創新”(項目編號:qhnucxcy202309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編輯:李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