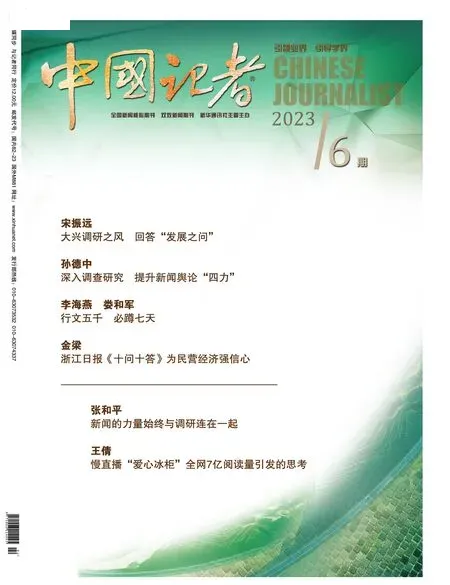勘誤他者 加強自我
——突破西方“信息繭房”的思考
□ 王洪江
當下,民族主義、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對外傳播的外部傳播環境發生很大變化,中國發展令人艷羨,一方面給對外傳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另一方面,受眾端的挺華和反華力量博弈升級,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輿論戰、科技戰,一些國家搞“污華”“反華”“辱華”“亂華”傳播,受眾囿于“信息繭房”,群體極化現象加劇,經濟新聞對外傳播擔負著對外講好中國經濟故事、宣介好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使命,其敘事認同之路光榮而艱巨。
一、對外講好中國經濟故事面臨挑戰
就講述中國經濟故事而言,新華社對外經濟新聞報道的敘事既有一些行業性強的新聞報道敘事的共性特色,又有新華社作為國家通訊社的權威性、面對海內外受眾、服務各類媒體客戶所獨有的特點。其敘事特色比較突出的有以下方面:
第一,專業性強,術語多、有門檻。經濟學知識因其專業性較強,有一定的報道門檻。經濟新聞敘事過程中會涉及許多經濟領域專業性問題,有特有的專業知識和專業術語,是專業性比較強的報道門類。
第二,季節性強,重復多、數字多。經濟新聞對外報道因為涉及很多經濟數據的定期發布,比如年度、季度、月度的各種經濟數據,如GDP、進出口數據、物價、房價等,因此季節性很強。而且,這類數據發布都有一定的專業表達方式,涉及的數字也多,很容易顯得枯燥。
第三,服務性強,雖相關、感覺遠。經濟新聞對外報道敘事具有較強的服務性。無論政府、企業還是個人,在制定和優化經濟決策的時候都需要大量有效的經濟信息作為參考,專業、客觀的經濟新聞有利于幫助政府、企業、個人做出正確的決策,提高政府、企業的決策效率、增強市場活力,而錯誤、片面的經濟新聞則可能誤導決策者和普通人,嚴重的甚至會擾亂經濟秩序。經濟新聞貌似離普通人的生活很遠,其實人都生活在經濟運行之中,須臾不可離,經濟新聞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第四,知識性強,同時具有監督功能和國際輿論引導作用。新華社對外經濟新聞的敘事功能眾多,既傳播經濟知識,又指導經濟生活,既有監督社會經濟活動的功能,又有為創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而服務的國際輿論引導作用。
上述經濟新聞對外報道本身的特性給從事經濟新聞對外報道的傳播者提出了一定的門檻要求,這構成了一部分內在挑戰因素。
就外部挑戰因素而言,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本文重點探討其中兩個挑戰:“信息繭房”和逆全球化。
(一)民族主義與極化傳播助長“信息繭房”效應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國家躁動不安,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美國打著“國家安全”“美國優先”旗號實行“脫鉤”“斷鏈”,堂而皇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
民粹主義方面,由于西方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增長乏力,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黑命貴”“抗議警察暴力”等社會矛盾激化,精英對社會的引導功能和決策能力下降,普通大眾因為社交媒體大行其道而從輿論的邊緣走向中心,但普通大眾的情緒往往被極端勢力利用,加重了民粹主義。
在互聯網時代,一方面,社交網絡全球普及,政客們利用社交網絡、大數據、精準推送等手段助推了互聯網極化傳播;另一方面,主流媒體在權威信息披露、引導教化和評價功能方面的功能被社交媒體消解,社交媒體反而更加具有“民意基礎”,網絡世界呈現“后真相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社交媒體的碎片化傳播、技術支持下的智能推送和熟人社交網絡等助長了“信息繭房”效應,受眾生活在像蠶繭一般的“信息繭房”里,難以考慮周全。這些都為對外講好中國經濟故事制造了頗具時代烙印的困難與挑戰。
2006年,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在《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一書中率先提出了“信息繭房”概念。桑斯坦對“信息繭房”概念原文表述為:“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信領域”,并通過列舉的方式說明其危害性:“如果公司建立了信息繭房,就不可能興隆,因為其自己的決定得不到內部的充分挑戰”。[1]
互聯網海量信息喂入用戶,信息爆炸,反而導致了受眾如同困在蠶繭里的蠶寶寶,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一畝三分地;或者變成困在密室里的孤獨的說話人,只能聽到自己的回聲。這樣,同質化的聲音不斷得到加強,滋生出盲目自信和極端主義。
有調查顯示,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會點擊閱讀自己訂閱的微信公眾號推送的他們不感興趣的或者觀點不同的文章。[2]
(二)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比較突出的表現是美國“退群”和對中國的二元對立思維,這是冷戰思維。有學者認為這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后遺癥,美西方一些國家認為全球化使中國奪走了西方國家的制造業和就業機會,因此奉行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
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問題在于產業空心化、過度金融化,在于長期以來依賴的貨幣戰爭和殖民策略。
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罔顧事實、倒行逆施,客觀上給對外講好中國經濟故事帶來了新的挑戰,這些國家利用其在媒體上“西強我弱”的傳統優勢,誤導西方受眾,蠱惑人心,先入為主地破壞中國的海外形象,把西方衰落的原因錯誤地怪罪于中國的競爭,零和思維仍然有市場。
面對挑戰,中國經濟新聞對外傳播需破除圍繞西方受眾編織的“信息繭房”,對外講好習近平經濟思想、全球發展倡議和“一帶一路”合作等系列中國經濟故事,推動全球化良性發展。
對外講好中國經濟故事不妨從兩方面破“繭”,尋找突破口:一方面,要勘誤西方作為“他者”對于中國經濟的負面敘事;另一方面,要加強中國“自我”對于自身經濟故事的正面敘事。
二、勘誤他者敘事:校正有關針對中國經濟的奇談怪論
西方受眾長期被西方輿論裹挾,難以突破“信息繭房”,因此,要想對外講好中國經濟故事,首先要進行他者敘事勘誤,校正針對中國經濟的奇談怪論。
在中國全球化進程中,“自我”不斷地被“他者”講述,中國經濟故事也不斷地被西方媒體講述,無論西方媒體如何標榜“客觀平衡”的新聞專業主義,其報道偏好或偏見都顯而易見。西方主流媒體長期處于國際輿論的主導地位,雖然其中不乏對中國經濟發展相對客觀、主流、正面的報道,但是,對于中國發展的偏見也長期沒有得到矯正,從而導致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談怪論層出不窮。比如“中國經濟崩潰論”“中國經濟威脅論”“中國對外剝削論”“中國匯率操縱論”等,雖然這些論斷偏離了中國發展的事實,但是一些西方媒體熱衷炒作兜售,時不時地拿出來炒作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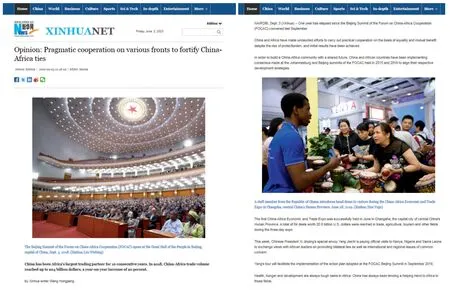
□ 新華社駁斥“中國非洲剝削論”報道截圖
西方大肆炮制、鼓噪這些不實論調,憑借其強大的國際傳播力裹挾受眾,借以鞏固其西方中心敘事。“崩潰”“操縱”等論調是為了抹黑、棒殺中國的敘事目的,而“威脅”則是為了達到捧殺的敘事目的,意在讓中國讓渡更多經濟利益,承擔與發展中國家不相符的責任。
(一)“中國經濟崩潰論”
西方屢屢炮制的“中國經濟崩潰論”屢屢崩潰,促使他們崩潰的不只是中國的經濟穩步發展這種“硬實力”,更有中國國際傳播力上升這種“軟實力”的配合。
當下,利用全國兩會、經濟數據發布、博鰲亞洲論壇、廣交會、消博會等重大經濟熱點權威發布、先聲奪人、針鋒相對地進行報道、解讀中國經濟發展故事已成為新華社對外講述中國經濟故事的常態,留給西方歪曲報道的空間逐漸縮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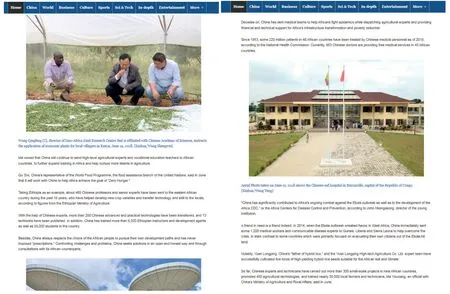
□ 新華社駁斥“中國非洲剝削論”報道截圖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需要認識到,西方之所以仍然樂此不疲地故伎重演,其動機并不單純。改革開放之初,西方媒體就已經開始炒作所謂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崩潰論,直到近期,“中國崩潰論”仍被一些西方媒體守缺抱殘,盡管中國早已不是過去的中國,而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之一。但是,一些西方媒體依然在美中貿易戰前后興風作浪,比較典型的是2018年年底“習特會”前夕,《紐約時報》推出 “中國規則”專版,用系列文章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多方面“剖析”中國,明褒暗貶。系列報道將中國一直在為亞洲和非洲的大壩、橋梁、港口和發電廠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描述為中國的“現代馬歇爾計劃”。報道影射中國在搞同盟和聯盟,將經濟與政治故意混為一談,把經濟問題政治化;報道還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污蔑為制造“債務陷阱”,號稱中國“在努力贏得新聯盟、開拓新市場的同時,中資項目正在重塑金融和地緣政治關系,但受惠國和中國的代價可能都很高。北京有時還被指控利用其基建投資計劃,讓合作伙伴陷入債務陷阱,然后將他們的資產據為己有。”[3]西方這種做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們不能等閑視之,要奮起反擊。
其實,這種論調并不新鮮。2001年7月,《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作者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Gordon G.Chang)提出:“與其說21世紀是中國世紀,還不如說中國正在崩潰。”2002年,美英主流媒體報刊陸續拋出“中國經濟的增長是虛假的”“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等論調,阻礙投資流入中國的目的赤裸裸地寫在了報道里。一直到2010年,他們的手法并沒有翻新多少。謊言說千遍也是謊言,但是他們仍然說個不停,“中國經濟站在懸崖上”“中國房地產泡沫比迪拜糟糕1000倍”等謊言層出不窮。章家敦于2015年和2016年先后在美國媒體上刊文言之鑿鑿地稱“中國經濟最多撐一年”“中國經濟在2016年崩潰”。[4]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2021年9月,津巴布韋第一大報《先驅報》發表評論文章《不做美國的反華棋子》,抨擊美國收買寫手,美國駐津使館通過研討會等形式以每篇文章1000美元出價收買記者抹黑中國在該國投資。
雖然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事實勝于雄辯”,但是,真理不辯不明。新華社繼續駁斥“中國經濟崩潰論”勢在必行,要用更為詳盡、全面、及時的對外經濟報道,揭露西方謊言,勘誤西方不實報道,引導受眾客觀看待中國崛起。
(二)“中國威脅論”
雖然“中國經濟威脅論”與“中國經濟崩潰論”走了不同的極端,但也有市場。
隨著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經濟實力日益增強,特別是在全球衰退之時中國仍然能夠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由此,美西方認為中國有意對抗美國,尋求取代美國,威脅其霸權地位,故而宣揚“中國威脅”,“中國經濟威脅論”甚囂塵上。
西方妄加揣測中國經濟發展下去勢必導致“國強必霸”,該論調是19世紀“黃禍論”的翻版。學者孔新峰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面對“站起來”而未“富起來”的中國,西方開始有“黃禍論”“世界能否養活中國人”等論調,這是“中國威脅論1.0”;面對“富起來”而未“強起來”的中國,西方輿論展開“中國新殖民主義”“商戰”等論調,這是“中國威脅論2.0”;當下,面對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走獨立自主道路,西方輿論展開了“滲透”“軟實力”等新型說辭,這是“中國威脅論3.0”。[5]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炮制了“修昔底德陷阱”,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的守成大國,而現存守成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他回顧了世界歷史上16次類似案例中,有12次導致了戰爭的結果。這樣的理論為偏愛“沖突”報道的西方媒體提供了“炮彈”。
“中國威脅論”以及各種變體是西方利用其強大的話語優勢,中傷、貶低、攻擊、抹黑中國發展和中國的國際作為,是以冷戰思維揣測、臆斷中國發展的行徑,目的是阻礙中國的全球化進程。
西方媒體這類報道層出不窮,各有側重。以CNN為代表的一些媒體多以歪曲捏造事實進行煽情敘事,而《紐約時報》等媒體則擅長渲染所謂“中國威脅”,引發西方人對中國產生“恐懼”。
通過包括新華社在內的中國媒體的集體努力,一些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中國崛起不僅不是對世界的威脅,而且還為世界和平發展提供了保障。包括“中國經濟威脅論”在內的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正在新華社等外宣媒體客觀報道的對沖下式微。
(三)“中國對外剝削論”
“中國對外剝削論”中,最廣泛被外媒所編造的一個論調是“中國非洲剝削論”,隨著“一帶一路”的推廣,又有了不同類型的翻版。對此,在反駁“中國非洲剝削論”這類不實報道時,以新華社為代表的外宣媒體注重突出中非關系是基于平等、雙贏、互利基礎上的雙邊關系,著重描繪中非關系現實及前景展望,耐心做解釋性報道和引導性報道,這種方式非常奏效。
新華社駁斥“中國非洲剝削論”的報道形式多樣,既有消息、綜述、特寫,又有評論這種更為直接的方式。比如,2019年9月3日,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一周年之際,新華社策劃了一系列選題,強化中非友好合作關系,駁斥西方“中國非洲剝削論”等不實論調,“務實合作將強化中非關系”系列評論指出:盡管世界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非卻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果。在中非共建命運共同體的共識指引下,中國和非洲國家一直在2015年和2018年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和北京峰會上達成共識,協調各自的發展戰略。健康、饑餓和發展問題始終是非洲面臨的艱巨任務,中國一直在這些領域向非洲提供幫助。文章用事實和數據說話,列舉中國對非糧食、醫療和抗疫援助,人員交流。進而,引用中國官員的表態,中國將繼續派遣高級農業專家和職業教育教師到非洲國家,進一步擴大在非洲的培訓,幫助培養更多的農業人才。同時“借嘴說話”,講述中國幫助非洲實現“零饑餓”的目標;中國連續多年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為非洲創造了大量財富和就業崗位;中國從來不是殖民者,也永遠不會殖民;中國的非洲政策與西方殖民者的政策大不相同,西方殖民者自發現非洲大陸起就開始分裂非洲和攫取非洲大陸的資源。系列稿件獲得良好采用,有效引導了中國涉非輿論。
我國主流媒體類似涉非輿論策劃報道已成為對抗西方相關負面輿論話題的有力武器。
(四)“中國匯率操縱論”
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也是慣用伎倆,賊喊捉賊,目的是為其國際貿易服務,打壓中國外貿和投資。
對此,新華社的對外報道重在揭露西方虛假宣傳的“雙標”和賊喊捉賊的強盜邏輯。2019年,美中貿易戰持續不斷升級,美國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而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的借口之一竟然是“國家安全”。
歷史上,美國曾經將韓國和中國臺灣列入過匯率操縱國/地區名單。1994年7月,中國曾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中國匯改取得超預期的成功,開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然而人民幣匯率不跌反升,當年12月,美國將中國移出名單。
事實上,美國才是最大的匯率操縱國。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的說法,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連搞三輪量化寬松,美元匯率出現大幅下跌,在當時其量化寬松就被質疑為貨幣戰爭。
新華社在反駁“匯率操縱論”時,兼顧闡釋我國匯率政策及其正當性,清楚地介紹中國匯率政策堅持以我為主,不搞競爭性貶值。
三、加強“自我”敘事:中國經濟“光明論”與“共贏敘事”
要想突破西方受眾的“信息繭房”,僅僅靠勘誤他者敘事還不夠,中國經濟故事的版圖還需要由“自我”來講述。
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要向世界回答“我是誰”這個“自身性”問題。這就要同時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和加強“共贏敘事”。而且,講述中國經濟故事“共贏敘事”需要以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為前提,否則世界與中國“共贏”就缺乏說服力。
(一)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
唱空中國經濟的論調一次次不攻自破,卻又一次次卷土重來,新華社對外持續反擊,用事實說話,宣介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中國經濟“貢獻論”。
同時,經濟發展是有周期的,在持續宣介中國經濟長期光明向好的基礎上,新華社經濟新聞對外報道尊重經濟規律和短期經濟起伏和波動,兼顧觀點平衡。
新華社在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方面已經有一些經驗積累,值得梳理。
1.走專業化道路
一是把握時機,在宣傳報道中要巧妙把握時機,讓話題為我所用,及時有力出擊,有效應對外媒歪曲報道。比如,2023年兩會期間,新華社利用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對于民營經濟的表態,闡明“黨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要引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增強信心、輕裝上陣、大膽發展,實現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報道獲得了包括法新社在內的100多家外媒采用,有效回擊了西方對于中國經濟“國進民退”方面所做的不實報道。
二是主動設置議題,有效引導輿論。我們雖然不能影響西方受眾怎么談論,但是我們或可以影響受眾談論什么。比如,在2023年世界濕地日當天,新華社播發了《中國聚焦:中國新增國際重要濕地18處》等系列稿件,闡明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獲得近百家外媒轉引。類似利用國際紀念日主動設置議題、引導國際輿論的做法在新華社已經駕輕就熟,做得非常專業。
三是報道專業化。經濟報道對專業要求較高,外媒財經編輯大多是該領域專家,我們也在大力提升報道的專業水準。
2.加強調查研究
經濟新聞對外報道需要記者和編輯對國際經濟熱點事件、全球經濟存在的問題和發展趨勢進行長期跟蹤調研,否則會落伍,調研是否深入、是否持之以恒非常重要。
要保持經濟新聞對外報道記者隊伍穩定,培養專家型記者和編輯,各有所長,傳統的經濟問題要研究,經濟熱點現象也要有專人負責關注梳理,如經濟增速、人民幣匯率、“一帶一路”等可作為日常經濟專題,建立數據庫,而像黑天鵝現象、灰犀牛現象等經濟話題和國內外知名經濟人物也需要專門關注積累,厚積薄發。
3.中國立場,全球視野
經濟新聞對外報道要“以我為主”,堅持中國立場,這毋庸置疑。但是,要想西方受眾接受,對外報道要非常注重全球視野、貼近受眾,在尊重事實基礎上立意高遠,視野開闊,不拘一格。
近年,新華社開通了小語種專線、國別專線,與世界各地主流媒體加強了合作供稿,促進了稿件在當地媒體落地,甚至整版落地,提供專版,增強了全球影響力。
新華社還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加強當地雇員和報道員隊伍建設,雇員在許多國家都按需而設,不設上限,這些舉措都進一步加強了新華社在全球的影響力。
4.中國故事,國際表達
致力于使報道貼近受眾思維和閱讀習慣,用受眾習慣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報道,注重對外經濟稿件與受眾的相關性。例如,新華社在報道福耀集團2014年收購通用汽車公司代頓工廠時,記者強調之前該工廠關門,約1000名員工失業,如今工廠重獲生機,2000多名工人在這里忙碌。這種報道方式貼近受眾關切,為海外受眾所接受,具有說服力。
同時,加大“借嘴說話”力度,多請“外國的和尚”來念“中國的經”,把“自己講”和“別人講”結合起來,提高可信度。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西強我弱”的總體格局仍未發生質變,我們的聲音仍存在傳不出去、傳不遠或者即便傳到了外國受眾耳朵里也很難入腦入心的問題,對外經濟報道的短板依然必須正視。我們的對外經濟報道要更加講究采寫技巧,讓全球受眾聽得懂、聽得進、入眼、入腦、入心。
(二)中國經濟故事的“共贏敘事”
在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的基礎上,“共贏敘事”是講述中國發展故事、中國與世界合作共贏故事、中國的全球發展觀的生動實踐。
首先,中國經濟故事的“共贏敘事”要求敘事主體了解其他國家的國情和文化,主動站在受眾文化立場思考彼此異同點,尋找彼此的利益交匯點、思想共同點和情感共通點。
其次,“共贏敘事”必須圍繞中國與世界合作共贏為敘事內容。特別是對于一些對中國有抵觸情緒的國家,可通過“共贏敘事”展示中國與世界的良性經貿互動助力雙贏、多贏,講述過 去、現在和未來的中外共贏故事,消除彼此誤解,傳遞共贏預期。
第三,要通過“共贏敘事”展現人類團結的力量,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
“共贏敘事”包含一體兩面:一方面,要通過傳遞“中國發展,惠及世界”理念,推進共贏,對外報道可持續將這一理念自覺、有機地揉進日常經濟數據發布程序報道和重大經濟事件等報道之中;另一方面,需要旗幟鮮明、絕不手軟地反擊抹黑中國、造謠中傷的負面行徑。
針對種種歪曲抹黑,新華社專司中國新聞對外報道的對外部常態化加強經濟報道策劃,從輿情收集、組織策劃、力量調遣、輿情監控、事后效果、總結改進等方面都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鍛煉出了一支有戰斗力的中國經濟新聞對外報道隊伍;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對中國的抹黑歪曲往往經濟政治不分家,二者很難剝離開來,所以,反抹黑報道也必須打經濟和政治報道的組合拳。
總之,講好中國經濟故事需要從正反兩方面努力,既要宣揚“自我”“共贏”正面敘事,又要抑制“他者”負面敘事、破除“信息繭房”。此文粗淺探討意在拋磚引玉,久久為功。
【注釋】
[1](美)桑斯坦.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M].畢競悅,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79.
[2]吳婉玲:《移動社交時代信息繭房效應實證研究》[J].浙江傳媒學院碩士論文,2018年.
[3]《紐約時報》“中國規則”系列報道[G].The New York Times: China Rules,2018年.
[4]孫志:《美國大選前瞻:焦慮作祟 美對華或趨強硬》[G].大公報.2016年4月13日.
[5]孔新峰:《滲透論是威脅論的新變種》[N].《人民論壇》.2019年第24期,第1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