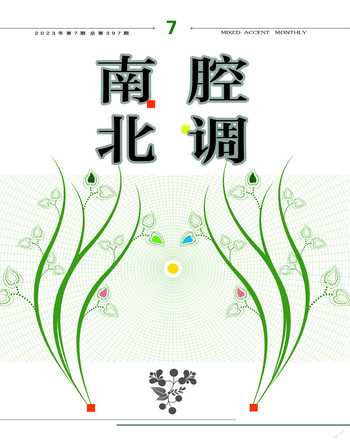從馬斯洛動機理論看陶淵明和梭羅的隱逸行為
黃細蘭
摘要:陶淵明和梭羅雖身處不同時代,出生在不同的國度,成長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一致選擇簡樸的隱逸生活,這種行為背后的本質原因值得探究。以馬斯洛動機理論為切入點,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的隱逸行為背后具有表達和應對的不同屬性,陶淵明的隱是拒“偽”存“真”的內在性格壓倒大濟蒼生的社會理想,而梭羅則是有意識地將“隱”作為宣揚超驗主義思想的生存實驗。在需求層次上,他們呈現出高度的相似性,都置自我實現的需求于生理需求之上,以辯證的眼光看待貧與富的關系,在物質生活極度貧乏的生存狀態下,積極探索精神領域的豐富性,實現精神上的巔峰體驗。
關鍵詞:陶淵明;梭羅;動機理論;自我實現
東晉詩人陶淵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中國文學史上彪炳千古的大家,他以躬耕自資的田園生活為底本,將詩意理想融入細碎日常,創作出不少膾炙人口的田園詩,為中國文壇注入一股真淳自然的新風,鐘嶸將他譽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詩品》),梁啟超稱贊他是“僅次于屈原的最有個性的作家,秉持自由和自然的人生觀,是最快樂的人”[1]。梭羅(公元1817年-1862年)是19世紀早期美國文壇巨匠,一位以“隱逸”著稱的超驗主義作家,曾孤身一人在瓦爾登湖畔野居,并寫下舉世聞名的《瓦爾登湖》,他在書中詳細描述隱居過程、生活來源、瓦爾登湖的四時變化,以及對閱讀、獨處等精神生活方式的獨特理解。
陶淵明和梭羅都用親身實踐和文學作品,來彰顯自己理想的生命形式,這吸引了一些研究者的關注。如《從對“樸”的訴求看梭羅與陶淵明的“隱逸”》一文,從他們對“樸”的訴求的一致性分析入手,結合他們的生平和作品進行比較研究[2];而《中西文人歸隱行為的文化闡釋——陶淵明與梭羅之歸隱行為比較》一文,以陶淵明、梭羅的歸隱行為和其詩文為出發點,探究并比較他們歸隱行為深處蘊涵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思想淵源[3]。概括下來,他們主要是從某一特質或文化視域來考察他們的隱逸行為,但對隱逸行為的不同屬性、心理層面的驅動因素的挖掘則稍顯不足。因此,本文嘗試以馬斯洛動機理論為切入點,還原陶淵明和梭羅不同的歷史語境和現實狀況,去探究他們隱逸行為的屬性差異,以及他們安貧樂道的內在原因。
一、隱逸行為的雙重屬性:表達與應對
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在其代表作《動機和人格》中,將行為分為兩種,分別具有表達屬性和應對屬性。表達屬性常常是沒有動機的,主要由有機體的狀態決定,與深層性格結構有關,多半是因為被釋放或被解除抑制,表達行為的目的就是它本身。而應對屬性則指有目的和有動機的行為,更多地由外部環境和文化變量決定,典型的應對屬性是作為手段的行為,試圖去解決或處理一個問題,往往涉及行為以外的事物。[4]
陶淵明和梭羅雖然都選擇隱逸的生活方式,但他們的行為屬性卻有明顯差異。陶淵明在“仕”與“隱”中反復搖擺,認清出仕就必須抑制自我曲意逢迎,歸田才能釋放本性自在生活,所以,他隱逸不為博得清名,而是厭偽存真的性格壓倒大濟蒼生的理想。梭羅的隱逸則帶有強烈的目的性,他有意識地按照超驗主義思想的指引,在瓦爾登湖做了一場生存實驗,意在用行動應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物欲橫流的現實,向世人宣告什么是“真正的人的生活”。
(一)表達對“大偽”世風的抗拒
縱觀陶淵明的一生,我們可以將41歲劃為分水嶺。從29歲第一次出仕到41歲辭去彭澤令,在這12年間陶淵明經歷五次“仕”與“隱”的糾結,最后決心在田園度過晚年,對人生的態度也從建功立業變為隨遇而安。細讀陶淵明的整本詩集,我們可以發現“志”一共出現了15次,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陶淵明不斷地表露自己心懷大志。在《雜詩·其五》中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5]在《讀山海經》中再次提到“猛志固常在”[6],可見青年時期的陶淵明有著大濟蒼生的高遠志向。
這種價值取向與儒家思想和其家世有關。陶淵明早期常與儒家經典為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7](《飲酒》其十六)。而曾祖父陶侃是晉國的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父親和祖父也都做過官。《晉書·陶潛傳》記載:“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8]雖然到了陶淵明這一代家道衰微,但出生在仕宦家庭,陶淵明免不了耳濡目染,想要成就一番事業重振家門榮光,29歲時寫的《命子》詩就是這種理想的一個印證。陶淵明在詩中先是回溯先祖榮耀,再對曾祖父陶侃表達了敬仰,最后在詩末勸導孩子成為棟梁之才:“夙興夜寐,愿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9]足見當時的陶淵明是極力推崇建功立業的,這既是一篇激勵孩子的詩,也是一篇自剖心跡的詩。
但客觀現實令陶淵明大失所望,魏晉時期門閥制度森嚴,政權被世家大族壟斷,普通文人在官場上得不到重視,加上陶淵明個性耿直討厭逢迎,所以經常感覺自己與官場格格不入。在《與子儼等疏》的信中,陶淵明說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10]。陶淵明不止一次將自己歸入“拙”的范疇,說歸隱之舉是“守拙歸田園”,找不到適當的營生是“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11]。我們知道陶淵明本人才華橫溢,所以這里的“拙”并非如他所言的與才智對立,而是與“偽”對立。陶淵明曾痛斥:“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12]世風虛偽,人心不古,忠孝節義這些優良品質被拋棄,官場上盛行追名逐利、爾虞我詐。這樣的生存環境讓懷有志向卻無法施展的陶淵明倍感痛苦,他無力改變大環境,只好辭官歸隱潔身自好。
可辭官又要面臨生活無以為繼的問題,在求生和存真的矛盾中,陶淵明又去做了幾次官,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厭惡官場。在第三次出仕期間寫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中,陶淵明說偶然得到一個做官的機會就去了,臨走前自我寬慰只是暫時與田園分別:“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13]可見他的內心是時時牽掛著回去的,對仕途并沒有多大熱情。到第四次出仕,陶淵明開始反問自己辛苦從役是為了什么:“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14](《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他感覺身體總是被束縛著,天性總是被抑制著。陶淵明最后一段為官經歷是最為著名的彭澤令,時年41歲,他已全無建功立業的宏志,只剩養家糊口的意圖。當被要求束帶迎接前來巡查的督郵時,陶淵明深感人格尊嚴蕩然無存。《晉書·陶潛傳》這樣寫:“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15]這個故事向來被認為是陶淵明高風亮節的表現,但仔細品味后我們可以發現,陶淵明的言行是由個性原則支配,而不是由社會原則來支配。換言之,陶淵明本性正直厭惡虛偽,所以與充斥著等級制度與腐敗傳統的官場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五次為官的經驗中,他一遍遍體會心為形役的痛苦,束帶只是摧毀他社會理想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積極嘗試、反復權衡、對自我性格分析后,陶淵明慎重而堅定地選擇了歸園田居,直至終年。
總之,陶淵明的隱逸抉擇,一方面是由于污濁的外部社會環境所迫,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內在性格拒絕被世俗同化使然,是拒斥“偽”文化,追求“真”性情的必然結果。陶淵明那些流芳千古的作品,直接表達了他當時的某種生存狀態,他的隱逸與創作行為,都帶有濃厚的表達屬性。
(二)應對“物欲”文明的實驗
在梭羅這里,情況變得不同,隱居不是目的而是手段。1817年,梭羅出生于帶有濃厚清教氣息的康考德,從哈佛大學畢業后在家鄉當了幾年老師,1841年開始轉行寫作,1862年病逝。梭羅是超驗主義創始人愛默生的追隨者,一生與其保持良好的友誼。在梭羅的價值體系中,清教主義和超驗主義是兩股重要的思想力量。清教主義崇尚自由,提倡過勤勞儉樸的生活,以一種苦修的態度來虔誠地凈化心靈;而超驗主義則“從唯心主義的原則出發,強調精神至高無上、直覺絕對感知,對盛行于歐洲大陸的物質文明持有尖銳的批評態度”[16]。兩者十分和諧地構成梭羅的生存哲學,推動他去實踐自己所推崇的理念。
“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美國,正是以犧牲個性、自然,犧牲人與自然的和諧為代價的資本主義經濟躍進時期。”[17]大自然被當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整個社會充斥著對財富的強烈渴求,機械化、工業化的文明進程像洪水猛獸,吞噬掉一座座山林,毀壞了一條條河流,自然環境遭到嚴重侵蝕,人與自然漸行漸遠。
在這種欲望膨脹、逐利無度的社會環境下,梭羅敏銳地觀察到人被各種外物所縛,無法擺脫無休止的勞動,也無法擁有真正的生活和完整的自己。他以鄰居為例,說明了外物對人的壓抑和異化。一個人一生下來就可以繼承不動產和牲畜,這在常人看來是一件幸事,可梭羅卻說鄰居不幸繼承了田地、廬舍、牛羊和農具,因為得到容易擺脫卻很難。打理田地和牛圈使鄰居陷入不得解脫的苦役中,他們一個勁兒地勞作,幾乎到了要窒息的程度,他們本是土地的主人,可實際上卻變成土地的奴隸。生活的重壓對有產者尚且如此,對無產者就只可能更為殘酷,梭羅鞭辟入里地剖析了無數勞動者的悲慘命運:沒完沒了地干粗活,根本無暇體會生命的美好果實,心中滿載憂慮,無知又卑微地在塵土中啄食。
梭羅感覺目之所及,無論是有產者還是無產者,都生活在別人的銅幣中。他批判被財富奴役的生存方式,認為那是一種“非人”的生活,真正的“人”的生活是回到自然,行動自主精神自由地存在著。完整的自己則意味著拒絕被異化為資本積累的工具,按照個人的天性發展自己。因此,在1945年的夏天,28歲的梭羅借了一把斧頭,在文明社會里劈開一條裂縫,從這個口子出發,只身前往瓦爾登湖畔,開啟為時兩年零兩個月的隱居生活,以親身實踐的方式建造自己的“理想國”。他十分坦誠地說:“我到林中去,因為我希望從容地生活,只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18]
梭羅在隱居期間,奉行自食其力的原則,把對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他親手砍白松樹搭建木屋,種植糧食和蔬菜;他不用床簾和墊子,將文明社會的必需品視為華而不實的多余物;他一年只工作六周就覆蓋全年的開銷,對自己的時間和生命擁有絕對的掌控權。因此他感慨:“倘若我們今天生活得儉樸,生活得明智,在這個地球上養活自己并不是什么累人的事情,而是一種消遣。”[19]在《瓦爾登湖》中,梭羅以輕快的語調,將自己的生存經驗數據化,把花銷和收入全部公之于眾。在他筆下,“我”擺脫了文明社會紛繁復雜的浮華追求,成為自然之子,在風雨晴雪中體會天人合一的美妙,過著一種充實豐盈的斯巴達式生活。可以說,梭羅的書一直在肯定人的主體精神,向世人宣告人可以擺脫外物對人的枷鎖,一手創建理想的生活方式,獲得身心自由和個人發展,即“人類無疑是有能力來有意識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 [20]。
細讀陶淵明和梭羅的作品,我們能驚喜地發現頻頻出現的互文性,陶詩可以被用來概括梭羅的生活理念,梭羅的很多做法可以被視為陶詩的最佳注解。如陶淵明表達人生觀的詩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21]與梭羅的見解如出一轍:“只要我們用意志控制自己的心靈,我們就可以高高地超乎任何行為及其后果之上;世間萬物,無所謂好壞,就像滔滔洪流,從我們身邊經過。”[22]而梭羅親力親為、勤勞肯干的生產實踐,與陶詩“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23]的重農思想一脈相承。
如前所述,陶淵明與梭羅在求真求簡方面具有一致性,但他們的隱逸行為卻呈現出表達和應對兩種不同的屬性。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陶淵明的隱居時長是梭羅的十倍。對陶淵明而言,隱居本身就是目的,每一天的隱居生活,就是在實現自己的生命理想。而梭羅只是將隱居作為一種生命實驗,證明人有能力掙脫文明社會的層層束縛,拒絕物欲的腐蝕,在自然中凈化心靈,獲得自由與解放。所以當他覺得實驗成功后,就又回到文明社會的懷抱,為廢除美國蓄奴制度的理想而奔走。
二、需求層次的上下顛倒:貧富辯證法
在動機理論中,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從低到高分為金字塔型的五個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感的需求、歸屬感以及對愛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一般而言,人對需求的滿足是逐層上升的,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先滿足吃飽穿暖的生理需求,以及其他匱乏性需求,最后才會出現自我實現這種成長性需求。可陶淵明和梭羅的人生軌跡顯然將這一順序徹底顛倒,他們把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需求擺在首位,而生理需求則退居到次要地位,這是否意味著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在他們身上失效了呢?
其實不然,馬斯洛在解釋需求層次理論時,就考慮到了順序顛倒的可能性,他特別指出需求層次的順序并非固定不變,高層次需求是物種進化和個體發育的高級階段,一個人“需求的層次越高,對純粹維持生存的迫切性就越低”[24]。同時,馬斯洛將自我實現者分為非巔峰型與巔峰型兩類,非巔峰型的自我實現者更務實,他們往往是社會里的強者,成為諸如政治家和改革者這樣的杰出人物;而巔峰型的自我實現者,“活在‘存在的疆域里,生活在詩意的、美學的世界里,生活在象征的、超驗的世界里,屬于一種神秘的、個人的、非機構性宗教,屬于一個目的性體驗的世界”[25]。他們很可能成為詩人和哲學家。陶淵明和梭羅顯然屬于后者,他們都在物質極度貧乏的狀況下,成功進入一個美的、超驗的世界里。
(一)固窮守志
眾所周知,陶淵明的物質生活窮困潦倒,但精神世界卻充斥著詩意與美。在衣食無著的現實里,他想象出一個與世無爭的桃花源;在辛勤勞作的日常中,他捕捉一個個詩情畫意的畫面。驅動陶淵明能夠安貧樂道的思想,是田園生活無限貼近他的自然本性,他也在這種生活里完成自我實現。
在陶淵明的諸多作品中,描寫貧窮生活的詩作比比皆是。如在自傳性質的《五柳先生傳》中,陶淵明十分寫實地描繪居所破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生存境況:“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26]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里,再次抒寫“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27]。晚年,他甚至窮到要去乞食的地步:“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28](《乞食》)在絕筆《自祭文》中總結平生:“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绤冬陳。”[29]毫無疑問,“窮”成為貫穿陶淵明隱居生活的一條主線,也是我們理解陶淵明偉大之處的一個背景。窮,一方面是因為陶淵明并不擅長務農:“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30](《歸園田居其三》);另一方面是天災人禍的摧殘,陶淵明晚年遭遇幾場火災,導致生活愈加困頓:“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31](《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與物質的貧乏和缺失相對的,是陶淵明在精神上顯得富足且快樂。寫早出晚歸的艱苦勞作,他不是滿腹牢騷,而是傾吐遵守本心的歡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32]房子被大火燒光,他沒有悲痛欲絕,而是以平常心淡然處之:“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33]乞食遇到善解人意的好心人,他從未扭扭捏捏,而是開懷暢飲毫不客氣,還因結識一個新朋友而開心:“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34]陶淵明的隱居生活不像梭羅那樣離群索居,人際交往也給他帶來很多歡樂。他曾為了與同心同德的人做鄰居特意搬家,并描繪相處的細節:“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35](《移居二首》);與好友外出郊游,他感嘆人應該盡情享受當下:“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36](《游斜川》)。四季輪變和自然美景更是引發陶淵明的無限詩情,讓他留下了諸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37]的千古名句,還有“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38]的詠雪佳作。這是因為陶淵明既有儒家“一簞食一瓢飲”憂道不憂貧的思想基礎,又深受老莊“抱樸守真”哲學思想的影響,由此形成超然物外的曠達心態。
陶淵明在生理需求得不到基本滿足的條件下,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我實現。他忠實于自己的天性,在物質極度貧乏的客觀現實下,獲得濃烈豐富的主觀體驗,以審美的眼光看待稀松平常的自然景物,在日復一日的歸隱生活中能夠“詩意地棲居”。可見,陶淵明并不依靠外部世界來獲得滿足,而更多依賴自身發展和自我完善,所以才能以無比灑脫的心態,來看待眼下的一切不幸和苦難。
(二)貧富一體
梭羅認為生活的真正需要和生活的手段是不同的,一個人真正需要的僅僅是食物和保暖,舒適的家具、各種裝飾物、外界的訊息都是多余的。面對人人追逐的財富,梭羅用數據表明維持基本生活不需要太多錢,多余的錢無法買到靈魂所需的東西。在梭羅的價值體系中,貧窮并不是難以忍受的苦事,相反,“貧窮只不過是將人限制在最有意義的生活里,一個人越是能夠放得下很多東西,他就越富有”[39]。至于生活的手段,梭羅認為大部分人從事各式各樣的驚人苦役,活在忙碌無知的沉淪狀態中,他們被生活的表面所遮蔽,無法看清人生的本質是追求獨立和自由。回歸自然的極簡生活,成為梭羅極力倡導的生活手段。
為了向世人證明極簡生活的正確性與可操作性,梭羅事無巨細地描寫隱居瓦爾登湖的過程與樂趣。他羅列建造木屋、購買種子、生活收支的清單,比較完備地展示隱居的價目表,以示其實他用極少的錢就能獲得生活的真正需要。經梭羅統計,他在瓦爾登湖畔搭建的木板嚴實、抹以泥灰的木屋共計支出28.215美元,農場一年的日常開支是14.725美元。當然,這些數據因歷史變遷已經不再具備參考價值,卻反映出人類探索生活方式的勇氣,并提供實現個人價值的一種可能路徑,因而具有超越一時一地的象征意義。
與文明社會物資充足、選擇多元、追求享受的生活相比,梭羅的隱居生活似乎顯得物資貧乏、清苦單調、孤獨寂寞,但梭羅自己卻樂在其中。梭羅在《瓦爾登湖》中記錄了隱居時的大量趣事,他寫因煮食馬齒莧而心滿意足,意在說明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食物,并且保持健康與活力;他認為黃昏時分遠處傳來的牛叫聲仿若天籟,因看到貓頭鷹而感到高興;他覺得阻礙外出的綿綿細雨非但不讓人沉悶,還既滋潤豆子又讓自己十分愜意……世人往往通過去娛樂場所或參加社交活動來尋歡作樂,但梭羅無需依靠外部的刺激產生多巴胺,而是將生活本身視為娛樂。他覺得瓦爾登湖永遠充滿新鮮感,大自然的變化永遠能給他帶來驚喜,回歸自然的生存方式溫柔、天真且鼓舞人心。用梭羅自己的話來說是:“當我享受著四季的更替流轉,我相信,無論什么東西都不能使生活成為我沉重的負擔。”[40]梭羅進而總結,如果我們有自主行動、自我管理、自我決策的力量,從而自由設計并經營我們的生活,我們將不會被寂寞和無聊吞沒。
梭羅是一位非常真誠的作家,他直言寫《瓦爾登湖》的目的是振臂高呼傳播勇氣,呼吁新英格蘭人降低物欲以獲得精神自由,哪怕最后只喚醒鄰居,他也覺得這樣做是值得的。這透露出梭羅對人類懷有深深的同情、悲憫和愛,雖然他偶爾也會對他人感到厭煩,免不了發幾句牢騷,但他是發自內心地想幫助他人,希望同胞有進步有發展。梭羅還有很強的正義感,對社會懷有烏托邦式的幻想,所以,他離開瓦爾登湖后,余生都在從事廢奴運動。
“貧”與“富”本是截然不同的兩極,可陶淵明和梭羅卻以辯證的思維看待兩者,從而實現了從“貧”向“富”的動態轉化。因不想被外物束縛,陶淵明和梭羅選擇隱居,隨之承受簡樸窮困的物質生活。但貧窮并沒有摧毀他們的意志,反而使他們在精神領域的探索異常深入,在大自然這個絕佳場域中,他們獲得豐富的精神體驗和審美感受,并將內在思想的耕耘外化為雋永的文學作品。換言之,物質貧困推動陶淵明和梭羅向精神富足的方向發展,而精神上的巔峰體驗讓他們更加安貧樂道,最終達到生命圓融和諧的境界。
結 語
陶淵明和梭羅分別為中美兩國的隱逸大家,都鐘情自然遵守本心,以清新之態在文學史上留有濃墨重彩的一筆。以馬斯洛動機理論重新審視他們,我們會發現他們的隱逸行為含有表達和應對的不同屬性:陶淵明是為“隱”而隱,通過隱居來表達拒偽存真的生活理想;梭羅是為“證”而隱,利用隱居來應對工業文明,證明人可以擺脫被金錢奴役的命運。雖行為屬性不同,但他們在需求層次上卻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都將自我實現的需求置于生理需求之上。他們用親身實踐向世人宣告,物質上的貧乏并不阻礙人實現自我價值,相反能讓人更加純粹地體會精神領域的豐富多彩。
參考文獻:
[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九十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8:13.
[2]李潔.從對“樸”的訴求看梭羅與陶淵明的“隱逸”[J].蘭州學刊,2007(12).
[3]王國喜.中西文人歸隱行為的文化闡釋——陶淵明與梭羅之歸隱行為比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8(07).
[4][24][25][美]馬斯洛.動機與人格[M].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21:153-154,121,188.
[5][6][7][9][10][11][12][13][14][21][23][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晉]陶淵明.陶淵明集[M].逯欽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117,138,96,29,187,119,145,71, 79,37,84,175,49-50,48,197,42,81,42,82,48,56,45,89,78.
[8][15][唐]房玄齡.晉書·陶潛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2460,2461.
[16][17]史志康,主編.美國文學背景概觀[M].上海:上海外語出版社,2004:72,73.
[18][19][20][22][39][40][美]梭羅.瓦爾登湖[M].李暮,譯.南京:譯林出版社,72,55,71,107,65,104.
作者單位: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