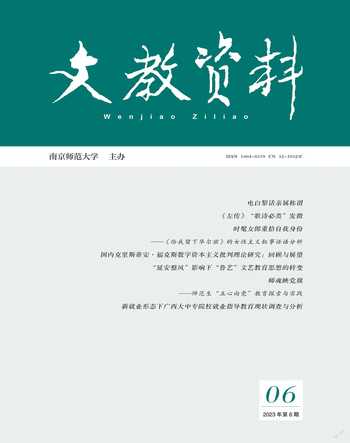論小學兒童詩美育功能的實施路徑
楊洋
摘 要:兒童詩與兒童的審美知覺、內在情緒關聯十分緊密,因此具有較高的美育價值,承擔著小學語文美育的重要功能。美育功能的實施最終需落實于審美感知力、審美想象力、審美理解力、審美創造力等審美能力的培養。具體而言,可以通過以下路徑加以實施:重誦讀,培養學生的審美感知力;借形象,激發審美想象力;抓意象,提升審美理解力;用仿寫,發展審美創造力。在兒童詩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注重審美氛圍的營造和學生積極主動性的調動,在潛移默化中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小學 兒童詩 美育
在語文教學中,美育和智育、德育一起承擔著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重任。所謂美育,即“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通過各種美的事物,培養學生的審美欣賞、審美表現、審美創造能力,同時促進他們德、智、體、美、勞等素質全面和諧發展的教育”[1]。美育功能的實現最終需落實于審美感知力、審美想象力、審美理解力、審美創造力等審美能力的培養。但是美育不同于智育,如杜衛所言,“審美不僅是認識,它首先是一種體驗,關聯著人的感覺、欲望和生活感受,是一種個體性的、具體的生命狀態,它直接關聯到人性的完整和諧與生存幸福,是一個生存范疇”[2]。審美能力的培養不應僅注重知識技能的維度,還應該從學生的生存體驗出發,從他們的生命狀態出發。也正因此,與兒童的生活狀態、內在情緒、審美知覺關聯緊密的兒童詩十分適宜作為美育實施的載體。從兒童詩教學入手進行美育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
一、重誦讀:培養審美感知力
在低學段語文教學中,兒童詩承擔著重要的美育功能。2022年版《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 (以下簡稱“《課程標準》”)強調:“第一學段(1—2年級)誦讀兒歌、兒童詩和淺近的古詩,展開想象,獲得初步的情感體驗,感受語言的優美。”[3]教材的具體編排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據統計,部編版小學語文教材一年級上冊共有10篇兒童詩、一年級下冊有7篇、二年級上冊有5篇、二年級下冊有5篇。總體來看,兒童詩在低學段的課文中占比較高。《課程標準》不但規定了教學內容,還強調了教學目標。對于低學段學生而言,美育的重心并非探究詩歌的內在深層意蘊,而應放在初步的情感體驗和語言感悟兩個方面,也就是說,培養學生的審美感知力是語文美育的入門之法。
審美感知力是指感官感知美的能力。美育的要義之一即是培養能發現美的眼睛、具有音樂感的耳朵,調動感官感知美的敏銳度,提升學生對美的感受能力。《課程標準》也指出了兒童詩美育的途徑——誦讀。語文初學者面臨著識字不多、理解力不高的現實困境,通過反復誦讀可以逐漸實現對聲音、情感、節奏的把控,初步感受到語言之美。兒童詩普遍具有節奏鮮明、朗朗上口的鮮明特點,如一年級上冊《雪地里的小畫家》:“下雪啦,下雪啦!/雪地里來了一群小畫家。/小雞畫竹葉,小狗畫梅花,/小鴨畫楓葉,小馬畫月牙。/不用顏料不用筆,幾步就成一幅畫。/青蛙為什么沒參加?他在洞里睡著啦。”
全詩押“a”韻,活潑愉快。如果把“小雞畫竹葉”“小狗畫梅花”“小鴨畫楓葉”“小馬畫月牙”的位置調換,隨意安排,則全詩的韻律就會被打亂,也就形不成語言的美感。在反復誦讀中,小學生逐漸會形成對語言美的敏銳感受。
由字音組成的語音層是文本的存在基礎。聲音的組合本身不但蘊含美感,還可以傳達情感。我國古代文學特別注重聲音的運用,總結出了上古四聲的發音特點:“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玉鑰匙歌訣》)由此亦可看出聲音和情緒強弱之間的關聯。現代詩歌語言仍遵循著上述規律,用明快強烈的語言來傳達慷慨激昂的情感,用不太響亮的聲音、黯淡的文字、緩慢的語調來表達悲傷低沉的情感。如三年級下冊《童年的水墨畫·林中》:“松樹剛洗過澡一身清清爽爽, /松針上一串串雨珠明明亮亮。/小蘑菇鉆出泥土戴一頂斗笠,/像一朵朵山花在樹下開放。/是誰一聲歡叫把雨珠抖落,/只見松林里一個個斗笠像蘑菇一樣。”“清清爽爽”“明明亮亮”“開放”“一樣”,押的是“ang”韻,明快強烈,傳遞出一種精神抖擻的情緒狀態。詩能激蕩人的情感,激勵人的意志,但是這些最終需要通過聲音來實現。朗讀的意義也正在此。在和原文達成共鳴之后的朗讀,可稱之為“美讀”,就是把作者的感情在讀的時候傳達出來。課程目標中要求學生能有感情地朗讀課文的深層邏輯即在于此。
反復誦讀還可以幫助學生掌握節奏。作為一種有規律的外在形式,節奏滿足了人的審美知覺的需要。“節奏能給人以快感和美感,能滿足人們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要求,每當一次新的回環重復的時候,便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見到老朋友一樣,使人感到親切、愉快。”[4]兒童詩的節奏感通常較強,如《拍手歌》的“你拍一,我拍一,/動物世界很新奇。/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錦雞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 /雄鷹飛翔云彩間。/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會寫字。”回環往復的節奏容易帶來輕松愉快的美感。反復誦讀可以形成對語音、節奏的把握,亦可完成對情感的體驗,最終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學生的語感。
二、借形象:激發審美想象能力
“想象”一詞在新課標中頻繁出現。第一學段要求誦讀兒歌、兒童詩,展開想象;第二學段要求“誦讀優秀詩文,注意在誦讀過程中體驗情感,展開想象,領悟詩文大意”[5];第三學段要求“閱讀詩歌,大體把握詩意,想象詩歌描述的情境,體會作品的情感”[6]。可見審美想象力是語文美育需要著力培養的核心能力。對于高學段的學生而言,審美想象力的激發有賴于詩歌文本的不確定性,而對于低學段的小學生而言,則更需要借助具體可感的形象。具體可感的形象構成的畫面,對小學生的吸引力更大。這就要求教師能夠觀察、體悟到兒童詩中的審美元素及其形成的審美規律。
(一)色彩的呈現
二年級下冊《彩色的夢》極富想象力,描繪了小朋友用彩色鉛筆創作的由藍天、太陽、白云、野花、森林、雪松、小鳥、小屋構成的和諧畫面。此詩著重突出了色彩的呈現:“腳尖滑過的地方,/大塊的草坪,綠了;/大朵的野花,紅了;/大片的天空,藍了,/藍——得——透——明!/在蔥郁的森林里,/雪松們拉著手,/請小鳥留下歌聲。/小屋的煙囪上,/結一個蘋果般的太陽,/又大——又紅!”“綠了”“紅了”“藍了”等相關的色彩詞語被單獨列出,更為精妙的是,在描繪了畫面下方的大塊綠草坪、大朵紅野花之后,視線轉到上方的大片天空,寫出“藍了”之后,重點強調了“藍——得——透——明”,一種澄凈的藍色帶來的寧靜愉悅的感覺油然而生。相同的,小屋煙囪上的太陽,居于畫面上方,“又大——又紅”極富視覺沖擊力。
如果說《彩色的夢》中色彩較多,組合精妙,那么四年級下冊的《白樺》則色彩較少:“在我的窗前,/有一棵白樺,/仿佛涂上銀霜,/披了一身雪花。/毛茸茸的枝頭,/雪繡的花邊瀟灑,/串串花穗齊綻,/潔白的流蘇如畫。/在朦朧的寂靜中,/玉立著這棵白樺,/在燦燦的金暉里/閃著晶亮的雪花。白樺四周徜徉著/姍姍來遲的朝霞,它向白雪皚皚的樹枝/又抹一層銀色的光華。”此詩以白色為主調,卻不單調。同是白色仍有銀色、潔白的區分,富有層次感。玉立的白樺配以金暉、朝霞,白色在金色、紅色的映襯下流光溢彩。誦讀此詩在頭腦中所形成的畫面給人以光華奪目的美的享受。
(二)光影的交織
三年級下冊的《童年的水墨畫·溪邊》用生動簡潔的語言勾勒出了一幅畫面,其中光影的運用頗為巧妙:“垂柳把溪水當作梳妝的鏡子,/山溪像綠玉帶一樣平靜。/人影給溪水染綠了, /釣竿上立著一只紅蜻蜓。/忽然撲騰一聲人影碎了,/草地上蹦跳著魚兒和笑聲。”水墨畫的特點之一即是簡淡。在這幅水墨畫中,波光并不明亮,人物衣服上也沒有光斑,整個世界仿佛都被溪邊垂柳的倒影染綠。釣竿上的紅蜻蜓減輕了綠色世界中的壓抑和沉悶感,將前三句中光影交織營造的氣氛平衡至靜謐。第三句釣起被甩到草地上的魚兒打破了靜態的水墨畫,歡笑聲打破了安靜的氛圍,光影的破碎與人們情感的轉換直接相連,瞬間生成。
光影的變幻還可以與詩歌的敘事相結合。如四年級下冊《在天晴了的時候》:“新陽推開了陰霾了,/溪水在溫風中暈皺,/看山間移動的暗綠——/云的腳跡——它也在閑游。”新陽和陰霾的變幻不但帶來了色調明暗的調節,也昭示著時間的變動,更重要的是,光影的變化和人的內心情感相關,陰郁被明朗代替。溪水被微風吹起漣漪,云朵投下暗綠的影子,整體呈現出一種溫和閑適的氛圍。如波德萊爾的《應和》中所描繪的那樣,在藝術的世界中,“香味,顏色和聲音都相互呼應”,嗅覺、視覺、聽覺、觸覺等各種感官混融一體。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應注重詩歌的這一特征,細致分析文本,激發學生審美感官的參與。
(三)時空關系的建構
如果說色彩、光影以可見的感性形式為激發學生想象力提供了堅實的文本基礎,那么詩中時空關系的建構則提供了讓學生想象力飛翔的空間。如《田家四季歌》精選春夏秋冬四季中充滿詩意的圖景加以并列組合,時間就蘊含于這四季的流轉之中。而葉圣陶《小小的船》則頗具空間營造之妙:
“彎彎的月兒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兒兩頭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見閃閃的星星藍藍的天。”
在此詩的前兩句所營構的空間中,“我”和月亮位于上下結構,“我”以遠觀、仰視的角度可見月兒彎彎,像條小船。“我”大月小。在三四句中,“我”飛上了月亮,空間發生變化。由遠及近,由大變小的“我”坐在月亮上,以前遙遠的星星和藍藍的天空瞬間置于眼前,變小的“我”也沉浸其中。 在這首詩中,空間層次豐富,在大小、遠近的瞬間變幻中,眼前的圖景發生了奇妙的變化,更能激發學生的想象力。兒童詩更符合兒童的認知水平和審美趣味,多注重通過具體可感的形象構筑畫面、表達情緒。教師在關注具體形象的同時,還應注意畫面感與想象力的激發的重要關系,借形象分析培養學生的審美想象能力。
三、抓意象:提升審美理解能力
無論是對詩歌進行審美感知,還是審美想象,最終都要導向對詩歌本身的理解,也就是新課標中提到的“詩歌大意”“詩文大意”。“意”較為虛幻抽象、不好捕捉,而象則較為具體,因此通過象來掌握意成為可行的路徑。象是言與意的中介,它是可以用語言加以描繪、具體呈現的,同時它又是為了表情達意的。所謂“意象”也因此具有了多重審美意蘊。
(一)意象是以具體可感的形態出現的
《祖國多么廣大》一詩中,“廣大”一詞對于低學段的小學生來說較為抽象,不好理解。詩歌選取了從北到南三組不同的意象加以展示:雪花飛舞的大興安嶺、柳枝發芽的長江兩岸、鮮花盛開的海南島。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氣候、風物的巨大差異對“廣大”進行了感性地呈現。《大小多少》一詩的手法運用與《祖國多么廣大》有異曲同工之妙。大小多少是抽象的數量詞,此詩用一頭黃牛和一只貓、一群鴨子和一只鳥,一個蘋果和一顆棗,一堆杏子和一個桃進行對比,給學生以直觀的感受。學生只要對這些意象進行了把握,也就能理解詩歌之意。
(二)意象蘊含著豐沛的情感
進入藝術世界中的象已非外在客觀的自然之物,它經過了詩人的選擇、加工和再創造,在具體感性物態之中交融、傳達著作者的主觀情意。如《繁星(七一)》一開始就表明了詩歌的主旨,即是對于往昔的美好追憶。詩歌共選取了三組意象來傳達“永不漫滅的回憶”:月明中的園中、藤蘿的葉下、母親的膝上。教師在講解的時候無論是把這三組意象聯結起來,想象成一幅作者漫步在月夜的小園中、走到藤蘿葉下、趴在母親膝頭聽她講美妙故事的動態圖,還是將三組意象分開解析,想象為朦朧月色中的小園、靜靜垂落的紫藤花下,母親溫暖的膝上三個靜態畫面,都不妨礙對這首詩的理解,更為重要的是理解這三組意象中蘊含的情感。可以說對于以上意象所蘊含的情感的體悟決定著能否對此詩之美進行掌握。這三組意象所傳達出來的寧靜、安適、溫情才是作者永恒的回憶。
(三)意象沉淀著豐厚的文化意蘊,具有象征意義
詩歌多義、蘊藉的審美空間,主要由意象的象征意義建構。象征既是物象本身,又超出物象本身。這種特質在四年級下冊《繁星(一五九)》中表現得較為明顯。“風雨”這一意象在詩中出現兩次——天上的風雨和心中的風雨。前者指自然界的惡劣天氣,是客觀物象本身。后者則指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難,這是超出客觀物象本身的含義。在一首詩中“風雨”兩次出現,從真實自然物象過渡到更為深層的文化意義,因此更容易被學生理解。而六年級上冊《有的人》中“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就更為抽象,“活著”“死了”的交錯使用更加大了理解的難度。只有挖掘出兩者的多重意蘊,才能準確地把握詩歌。
正因為意象集形象、情感、文化意蘊于一身,所以它成為理解詩歌、探尋詩美的關鍵所在。四年級上冊《秋晚的江上》和白居易的《暮江吟》都描繪了夕陽西下、晚霞映江的圖景。《暮江吟》中只一句“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就寫出了江中殘照的絢麗感,更傾向于靜態畫面的描繪,而《秋晚的江上》則抓住了美感生成的瞬間,將其表達出來。劉大白將斜陽描繪成被歸巢的鳥兒馱著之物,想象奇特。前一幅歸巢的鳥兒疲憊飛行的場景所體現的節奏較慢,而“雙翅一翻”作為一個轉換的節點,節奏陡然加快,斜陽將江邊蘆葦瞬間染紅的場景也就更具有視覺沖擊力了。“頭白的蘆葦”變為“一瞬的紅顏”既是斜陽映照下美景的直觀呈現,同時“頭白”轉為“紅顏”所蘊含的青春復返的一瞬間更令人心動。“歸巢的鳥兒”“雙翅一翻”“頭白的蘆葦”“一瞬的紅顏”都成為體悟此詩之美的關鍵意象。
四、用仿寫:發展審美創造能力
審美感知力、想象力、理解力的培養有助于幫助學生從兒童詩的文本中獲得豐富的美感體驗,審美創造力的培養則注重在此基礎上,將諸種審美能力轉化為學生獨立自主創新的能力。小學生模仿力強,但是獨立創新能力仍需培養,因此依托兒童詩文本,從仿寫入手來發展其審美創造力是切實可行的。
(一)仿語言運用
毋庸置疑,語言是交流溝通的工具,但是文學語言和普通語言的特性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普通語言的工具性更強,它是人們在現實世界中互相交流溝通的中介,需要傳遞信息、傳達態度,因此必然遵循生活的邏輯,最終要經得起客觀生活的考驗,否則它將是無效的。比如《四季》中“雪人大肚子一挺,/他頑皮地說:‘我就是冬天。”在現實世界中,雪人活動、說話是荒謬的,但是文學的語言并不關注意義傳達的準確性和唯一性,追求的是與整個藝術世界的氛圍相統一。對低學段的學生而言,最為基礎的技能是對語言的掌握。要引導學生清楚地認識到詩歌語言的運用遵循的不是客觀現實的邏輯,而是“美的規律”,符合的是情感的邏輯。在藝術世界中小鳥嘰嘰喳喳在說話、泉水叮叮咚咚在唱歌、紅紅的花會笑、雨后的蘑菇精神抖擻……文學語言可以用來描繪世界上的一切生命。
(二)仿形式表達
兒童詩讀起來朗朗上口,這與其韻律的使用、結構的安排、節奏的呈現都密切相關。前文已對詩歌語言押韻所形成的美感做了較為詳盡的闡釋,此處不再贅述。從現代詩歌的形式來看,分行排布是其十分顯著的形式特點,它與詩情的跳躍、詩美的表達密切相關。如《繁星(一三一)》:
“大海啊!/哪一顆星沒有光?/哪一朵花沒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沒有你波濤的清響?”
全詩歌押“a”韻,光、香、響的發音交疊,仿若海水拍岸的回響。詩行的排列也仿佛波濤的涌動,別具一格。形式帶來的視覺美感與詩歌的內蘊傳達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在兒童詩的仿寫過程中應引導學生關注這兩個方面的訓練,如對《四季》的仿寫,不但要找出對應四季的物象,還要做到句式工整,詩行排布充滿美感。
(三)仿寫作技法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為技巧的藝術》中提到:“藝術的目的是使你對事物的感覺如同你所見的視象那樣,而不是如同你所認知的那樣;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復雜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既然藝術中的領悟過程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它就理應延長。”[7]藝術之所以如此重視陌生化,是因為它能夠帶來新奇感。這一點在兒童詩的寫作中,常常以比喻、擬人等技法來實現。比如《小小的船》中將月亮看作小船,月兒和小船在兩頭尖尖這個特征上得到了統一。仿寫中可以引導學生觀察什么樣的東西兩頭尖尖,仿寫出“彎彎的月兒像香蕉”。比如對《四季》的仿寫要找出四個季節中具有代表性的物象,寫成“桃花紅紅,它對蝴蝶說:‘我是春天”等。
由此可見,比喻、擬人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法,更是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影子和人形影不離,《青蛙寫詩》中小蝌蚪、水泡泡、荷葉上的一串水珠像各種標點符號,小動物會在雪地上留下各種形狀的痕跡,秋天有各種各樣的聲音……通過對具體技巧的仿寫,可以加強學生觀察生活、體悟生活的能力。朱光潛說:“美感經驗并無深文奧義,它只在人生世相中見出某一時某一境特別新鮮有趣而加以流連玩味,或者把它描寫出來。這句話中‘見字最緊要。”[8]仿寫訓練的就是“見”的能力,以美的眼光發現事物之間聯系的能力。在仿寫的過程中,既要注意學習“同”,仿語言、形式、技法的表達,逐步提高自己的審美能力,同時又要引導學生凸顯自己的“異”,從被動訓練變為主動觀察、主動發現、主動表達,形成自己的審美創造力。
五、結語
在兒童詩的美育過程中,審美感知力、想象力、理解力充分調動,能夠使人從自動化、麻木、庸常的世界中脫出,恢復對生活的新鮮感和活力。將諸種審美能力的培養落實于對生活的觀察和體悟,引領學生以美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世界,表達自我才是美育最終的旨歸。
參考文獻:
[1] 趙伶俐.大美育實驗研究[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6:60.
[2] 杜衛.美育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2014:46.
[3] [5] [6]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 [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8,8,12.
[4]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96.
[7] [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M]. 方珊,等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9:6.
[8] 朱光潛.談修養[M].北京:中華書局, 2012:152.
基金項目:蘇州科技大學校級通識教育課項目“中國美學智慧” (2021TSY-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