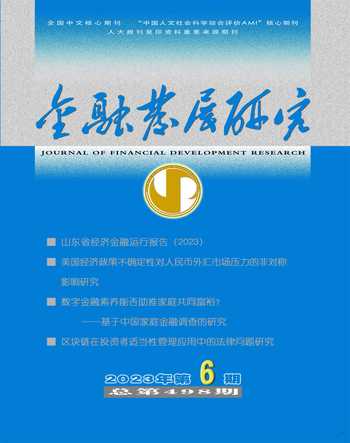地方政府專項債的功能定位與風險防范
張欽潤 王志攀
摘? ?要:地方政府專項債務迅速擴張,原因在于其經濟增長的功能定位。專項債經濟增長的功能定位導致了專項債的中央集中化、財政政策化以及杠桿化。調整專項債的功能定位,使其服務于地方事權的實現,需要把握專項債的公益性、地方性和收益性。立足于專項債的事權功能,在事權功能與增長功能之間保持合理的“張力”,是防范化解專項債務風險的現實選擇。為此,首先,專項債及其支持項目應遵循受益性原則;其次,應明確國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定位,強化中央支出責任;再次,應完善“代舉”機制,確立資金使用主體的償還責任;最后,應積極賦予地方稅權,擴大地方財政自主權。
關鍵詞:專項債;功能定位;事權;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23)06-0068-06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3.06.008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持續(xù)“高燒不退”,成為學界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地方政府債務主要有三種類型,即一般債務、專項債務和隱性債務,其成因、規(guī)模、風險、治理等呈分化之勢。一般債務“不溫不火”,隱性債務導向清零,唯獨專項債務規(guī)模迅速擴張①,逐漸成為焦點。截至2022年12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350618億元②,中央財政國債余額約為25.87萬億元。因此,2022年底,全部政府債務總額約為60萬億元③。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1210207億元。據此,政府負債率(中央政府債務與地方政府債務之和占GDP的比重)約為50%。從政府債務結構上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約占全部政府債務總額的58%,約占GDP的29%,其中,專項債務總額約占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的60%,約占全部政府債務總額的35%,約占GDP的17.4%。
從世界范圍來看,雖然我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發(fā)展時間很短,但債務規(guī)模迅速擴張,顯得非常與眾不同。美國市政債類似于我國的地方債,1812年,紐約市發(fā)行了第一只一般責任市政債券,為運河建設提供資金。經過半個世紀,到1860年美國地方政府的未償債務規(guī)模也就2億美元,1870年增長到5.16億美元(Glasser,2020)[1]。2021年,美國市政債券市場規(guī)模大約為4萬億美元④。相關數據顯示,美國2022年的GDP約為25.47萬億美元。因此,美國市政債總額占其GDP的比重約為15.7%,與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形成了鮮明對照,而且低于專項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同為發(fā)展中大國,印度的市政債券市場總額僅為約2億美元,邦一級債券債務約為4000億美元,國債規(guī)模約為1.7萬億美元,中央以下政府債務約占其GDP的15%(Glasser,2020)[1]。總的來看,與外國相比,我國政府負債率不算高,但在政府債務結構上存在巨大差異,中央政府債務與地方政府債務在GDP中所占比重存在巨大反差。截至2022財年末,美國未償國債總額達30.93萬億美元,占GDP比重高達121.5%(楊子榮,2023)[2]。印度國債占其GDP的一半以上。美國、印度的國債占據了政府債務的主要部分,特別是美國,國債總額幾乎是市政債總額的8倍。反觀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占據了政府債務的絕大部分,而國債總額不高、比重較低。
美國、印度均為聯邦制國家,特別是美國,各州具有很強的財政自主權,地方政府擁有獨立稅權和相對穩(wěn)定的收入,其市政債的規(guī)模較大、債券市場發(fā)達是正常的。按道理說,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缺乏財政自主權,舉債能力有限,并不具備地方政府債務擴張的制度條件。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地方政府債務規(guī)模的迅速擴張,進而造成了中外政府債務結構性差異?不論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還是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體系,都必須要科學回答這些問題。鑒于專項債在地方政府債務結構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突出,專項債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債務治理與風險防范的重心和關鍵,而且,專項債與一般債、隱性債的底層邏輯也不一樣,有相對的特殊性。因此,本文將專項債作為考察對象,探討其規(guī)模擴張的根源。本文認為,專項債規(guī)模擴張的根源在于其功能被定位于促進經濟增長。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應逐步將專項債的功能定位于服務地方政府事權。在此基礎上,本文從事權視角出發(fā),就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提出了若干具體的建議。
二、地方政府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
2014年8月,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以下簡稱《預算法》)第三十五條賦予了省級政府適度的舉債權,但只能通過發(fā)行地方政府債券的方式舉借債務。緊接著,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fā)〔2014〕43號)(以下簡稱國發(fā)〔2014〕43號文),規(guī)定了地方政府債券的兩種方式,即一般債券與專項債券,前者形成一般債務,后者形成專項債務。2015—2017年,在新增發(fā)行規(guī)模上,一般債均高于專項債,前者占比最高達83.3%(2015年)。2018年開始,專項債新增發(fā)行占比逐年提高,2018年為61.9%,2022年攀升至83.5%,2023年預計為84.1%(楊志錦,2023)[3]。
專項債重返歷史舞臺并且快速擴張,根源在于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定位。一方面,地方債乃至專項債是擔負著促進經濟增長的使命重返歷史舞臺的。客觀地說,地方債能夠“破冰”,存在一定的偶然性。1994年《預算法》明確規(guī)定“地方政府不得發(fā)行地方政府債券”,但是2008年爆發(fā)全球金融危機,面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為緩解地方政府的資金配套壓力,財政部安排代發(fā)地方債2000億元,并代為還本付息。《2009年地方政府債券預算管理辦法》第一條明確了“代發(fā)代還”地方債券的目的,即“為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強地方安排配套資金和擴大政府投資的能力”。由此可見,地方債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促進經濟增長的使命。另一方面,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日益明確和不斷強化,是專項債急劇擴張的根源。專項債發(fā)行的前幾年,資金主要投向土地儲備、安居工程、收費公路等領域。這些投資領域的地域性較強,投資具有顯著的地方受益性,因此,地方政府發(fā)行專項債的積極性較高,自主專項債資金投向的愿望強烈,導致中央政府難以通過專項債實現其經濟調控目標。于是,中央政府通過限額管理,不斷強化項目控制,引導專項債的資金投向,意圖實現結構調整、經濟增長的政策目標。2017年3月,財政部發(fā)布了《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分配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將“中央確定的重大項目支出”作為新增限額分配的重要考慮因素。自此開始,中央政府開始積極控制專項債的資金投向,專項債資金投向與經濟增長的政策目標逐步深度捆綁。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于做好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fā)行及項目配套融資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配套融資通知》)明確提出:“更好發(fā)揮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重要作用,著力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huán)節(jié)的支持力度,增加有效投資、優(yōu)化經濟結構、穩(wěn)定總需求,保持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經濟下行壓力日益凸顯,經濟增長面臨多重沖擊,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被再度強化,投向領域不斷擴大,逐漸形成了交通基礎設施、能源、農林水利等九大支持領域。2022年5月,《國務院關于印發(fā)扎實穩(wěn)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國發(fā)〔2022〕12號),將新型基礎設施、新能源項目等納入專項債的支持范圍,最終形成了“9+2”的專項債支持領域框架。
明確并不斷強化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定位,是專項債在債務風險“警報”聲中一路“高歌猛進”的主要原因。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定位,導致了專項債的中央集中化、財政政策化以及杠桿化。
首先,專項債本質上是地方債務,地方政府應承擔“自發(fā)自還”的主體責任,因而專項債應是地方財政自主權的重要體現,但是,本來具有財政分權屬性的專項債卻呈現出中央集中化的特點。對專項債規(guī)模實行限額管理,是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重要制度保障,基于此,國務院財政管理部門對地方政府債務行使財政監(jiān)管的權力(王茂慶和鞏岱賢,2022)[4],但這不必然導致專項債的中央集中化,因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限額內自主舉借、使用和償還專項債務。然而,由于專項債的還款期限長,官員任期制下資金使用與償還責任分離,更高的債務限額成為地方政府積極爭取的“資源”。地方政府為獲取更高的限額支持,在項目的論證、立項、入庫上積極配合中央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目標導向。中央與地方之間“博弈”的結果就是,專項債的地方屬性在弱化,中央集中化的特點在增強。
其次,為發(fā)展地方公益事業(yè),地方政府發(fā)行專項債券籌集資金,因此,專項債本質上屬于地方籌集資金的途徑和方式,但是,由于突出和強化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專項債呈現出財政政策化的特點。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并將專項債定性為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準財政政策工具。具體表現為,擴大地方專項債的發(fā)行規(guī)模,優(yōu)化組合赤字、專項債、貼息等工具以保持必要的財政支出強度,加強專項債與政策性金融工具的配合,專項債限額空間的使用,以及適當擴大專項債券資金投向領域和用作資本金范圍等(牛犁,2023)[5]。專項債的財政政策化表明,專項債對整個經濟調控政策實現了深度“嵌入”,形成了與產業(yè)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其他財政政策協同配合的調控格局。通過項目控制引導資金投向符合產業(yè)政策要求的領域,“資金跟著項目走”,從而與產業(yè)政策相結合;通過控制專項債規(guī)模、專項債的限額空間,從而與貨幣政策目標相連接;通過控制專項債發(fā)行規(guī)模,從而與財政赤字率等財政政策相配合。
最后,強化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定位,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專項債的杠桿化。近年來,地方政府投資的項目資本金來源急劇萎縮,而且到位難,配套資金不足。根據《配套融資通知》,從2019年開始,“允許將專項債券作為符合條件的重大項目資本金”,而且在逐步擴大用作項目資本金的范圍,2020年7月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2020年開始,部分專項債可用于補充中小銀行資本金。2020—2022年新增5500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專項用于補充中小銀行資本金⑤。將債務性質的專項債資金用作項目資本金,改變了專項債資金的性質,專項債資金成為其他投資的“安全墊”,有利于發(fā)揮專項債投資“四兩撥千斤”的撬動作用,從而吸引其他資金投資,放大專項債支持重大項目的功能。專項債資金用作項目資本金,集中體現了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定位,但在地方政府債務高企的背景下,其引發(fā)的債務風險是不容回避的。
三、地方政府專項債的事權功能定位
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定位打開了專項債規(guī)模迅速擴張的“閘門”,導致地方政府債務擴張和風險累積,對“中央不救助原則”的落實構成了挑戰(zhàn)。根據財政分權理論,中央政府在宏觀經濟穩(wěn)定政策中發(fā)揮主導作用,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公共物品應主要限于他們自己的選民來消費,如果地方公共物品具有跨轄區(qū)的溢出效應,那么,中央政府應當給予地方政府適當的補貼(Oates,2005)[6]。在專項債所支持的“9+2”領域框架內,交通基礎設施、能源、國家重大戰(zhàn)略項目、新型基礎設施、新能源項目顯然不屬于市政類的公益性項目⑥,其主要目的在于調整結構、擴大投資、促進增長。因此,地方政府落實中央政府的經濟調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角色,這顯然不利于落實“中央不救助原則”。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必須從學理上闡明專項債的本質和內涵,明確專項債功能的制度定位。我們認為,應當正本清源,回歸《預算法》和國發(fā)〔2014〕43號文。《預算法》將地方“必需的建設投資的部分資金”作為發(fā)行地方政府債券的條件,并且規(guī)定舉借的債務“只能用于公益性資本支出”。國發(fā)〔2014〕43號文將“公益性事業(yè)發(fā)展”作為發(fā)行地方債券的條件,并把“公益性事業(yè)發(fā)展”分為“沒有收益的”和“有一定收益的”。如果確需舉借債務,前者發(fā)行一般債券,后者發(fā)行專項債券。在此基礎上,《地方政府債券發(fā)行管理辦法》明確了專項債券的內涵,即“專項債券是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項目發(fā)行,以公益性項目對應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專項收入作為還本付息資金來源的政府債券”。由此可見,《預算法》、國發(fā)〔2014〕43號文等均將專項債的功能定位于地方性公益事業(yè)發(fā)展,而不是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2017年6月,財政部印發(fā)的《關于試點發(fā)展項目收益與融資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品種的通知》明確提出,“打造立足我國國情、從我國實際出發(fā)的地方政府‘市政項目收益?zhèn)保瑧撜f,“市政項目收益?zhèn)迸c“公益性事業(yè)發(fā)展”的功能定位是一致的。因此,要正確理解專項債的內涵,關鍵是把握其公益性的本質。
首先,地方政府發(fā)行專項債券應當服務于公益事業(yè)發(fā)展,用于支持公益性項目,因此,專項債具有公益性。何謂公益事業(y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yè)捐贈法》第三條明確了公益事業(yè)的非營利性,并列舉了公益事業(yè)的具體事項。基于法體系的統(tǒng)一性,財政法、稅法等法律部門對公益事業(yè)的界定應該與捐贈法保持一致。那么,什么是公益性項目?一般認為,公益性項目指為社會發(fā)展服務、不以營利為目的、難以從直接收益中回收投資的建設項目,包括科技、教育、文化、衛(wèi)生、體育、氣象、城市市政設施、環(huán)境保護項目,公、檢、法、司等政權機關建設項目,以及黨政機關辦公設施、國防事業(yè)建設項目(趙林如,2019)[7]。因此,公益性項目是實現公益事業(yè)發(fā)展的途徑和方式。
其次,專項債的公益性應該具有地方性。雖然《預算法》、國發(fā)〔2014〕43號文等規(guī)范性文件沒有明確公益事業(yè)、公益性項目的地方性,但是,專項債的地方公益性應是自明之理。地方政府之所以通過發(fā)行專項債券舉借債務,源于地方政府落實支出責任。從法理上講,地方政府存在支出責任的法定義務,而又缺乏充足的收入來源時,才需要進行債務融資。因此,專項債應該是地方政府落實支出責任的邏輯延伸和客觀需要。按照財政分權理論,地方政府支出責任取決于地方事權,而發(fā)展地方公益事業(yè)當然屬于地方事權。
最后,專項債服務于地方公益事業(yè)發(fā)展,用于支持具有一定收益的地方公益性項目,因此,專項債具有一定的收益性。公益性、地方性是地方債的共同特性,而一定的收益性將專項債與一般債區(qū)別開來。例如,城市道路、城市照明、城市廣場、城市綠化等公益性項目不具有收益性,可由一般債提供資金支持;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館、福利院、醫(yī)院、學校等公益性項目則具有一定的收益性,可由專項債提供資金支持。
2016年8月,國務院發(fā)布的《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國發(fā)〔2016〕49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作為建立科學規(guī)范的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要舉措,為明確專項債的功能定位奠定了制度基礎。《指導意見》明確規(guī)定,對地方政府履行財政事權、落實支出責任存在的收支缺口,資本性支出可以通過依法發(fā)行政府性債券的方式來解決。那么,如何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指導意見》以基本公共服務受益范圍即受益性原則作為劃分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的標準。因此,專項債券的發(fā)行、投向、償還應當以保障地方事權為目標,以落實支出責任為標準,并最終體現受益性原則。確立專項債的事權功能意味著,積極發(fā)行專項債券用于支持地方公益事業(yè)發(fā)展,不斷強化專項債對地方公益性項目的資金支持;發(fā)行專項債券用于支持基礎性項目投資,應將專項債資金投向地方性的基礎性項目。
四、事權視角下地方專項債的風險防范
明確專項債的事權功能定位,有利于壓實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真正貫徹“中央不救助原則”,對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至關重要。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背景下,專項債投資拉動也要加力,但是,不論基于債務風險防范,還是財政分權理論,利用專項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只是權宜之計。因此,我們認為,立足于專項債的事權功能,在事權功能與增長功能之間保持合理的“張力”,是防范化解專項債務風險的現實選擇。
首先,專項債及其支持項目應遵循受益性原則。《指導意見》確立了受益性原則,不僅直接規(guī)范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改革,而且為政府間的其他事權、財權的劃分改革指明了方向。舉債權作為財權的重要內容,政府間的舉債權劃分當然應堅持受益性原則。簡言之,專項債的舉借、使用、收益、償還應當具有內在一致性,應當服務于地方事權和地方支出責任。因此,從性質上看專項債應用于滿足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給,專項債項目應限定為地方性的公益性項目和基礎性項目。但是,公益性項目的社會效益高于經濟效益,基礎性項目長遠收益高于短期收益,因此,實現項目收益與融資自求平衡比較困難,所謂“好項目少”“專項債不好用”有一定的必然性。專項債項目自求平衡的能力偏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后期地方財政的還本付息壓力(馮俏彬和宋恒,2022)[8],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正常的。對于理性的地方政府來說,防范化解債務風險,避免陷入債務危機,必然要做好項目平衡測算,拒絕盲目發(fā)債。因此,受益性原則能夠使專項債成為真正的地方債,本身就有抑制專項債規(guī)模盲目擴張、防范地方債務風險的內在功能。
其次,明確國債的經濟增長功能定位,強化中央支出責任。推行保投資、調結構、穩(wěn)增長的積極財政政策屬于中央事權范圍,相對于專項債乃至地方債,國債在促進經濟增長中應居于主體地位。相對來說,我國國債在政府債務總量乃至GDP中的比重明顯偏低,國債在推行積極財政政策方面具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因此,應當積極發(fā)行國債,不斷強化其經濟增長功能。由此可以舒緩專項債落實財政政策的壓力,有利于控制專項債規(guī)模,消除專項債風險。具體來說,就是要優(yōu)化央地支出責任,擴大中央通過國債支持基礎性項目、公益性項目的力度。有學者指出,應該提高一般公共預算尤其是中央一般公共預算在基礎設施投融資中的比例,在債務層面,就是要提高政府顯性債務尤其是國債對基建的直接支持(徐奇淵和盛中明,2023)[9]。當然,在現階段,推進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專項債規(guī)模擴張有一定的現實基礎,也要適度發(fā)揮其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功能,但這應該是權宜之計而不是長久之策。
再次,完善“代舉”機制,確立資金使用主體的償還責任。一般情況下,“借債還錢”是極為正常的,因為舉借主體通常就是使用主體。然而,在專項債情形下,資金使用主體除了作為舉借主體的省級政府外,還包括作為非舉借主體的基層政府、公用企業(yè)、國有企業(yè)、學校、醫(yī)院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預算法》未將舉債資格賦予基層政府等使用主體,而是確立了省級政府“代為舉借”的融資機制。“代”“舉”的二維制度架構,在資金流上隔離了專項債券的融與用,設定真正的債務人是市縣級政府,而直接的責任主體是省級政府(熊偉和許戀天,2022)[10]。事實上,“借”與“用”的分離導致使用主體在法律上不需要承擔償還責任,極易引發(fā)使用主體的道德風險。因此,在“代舉”機制下,應該強化“用債還錢”,明確使用主體的償付責任。為此,可以借鑒美國的管道收入債券(Conduit revenue bonds)制度。管道收入債券是由市政當局或其代理機構、職能機構代表第三方發(fā)行的債券,還本付息義務人不是發(fā)行人而是其所代表的管道借款人(張子學,2014)[11]。發(fā)行管道收入債券的情形通常包括,代表私人實體的產業(yè)發(fā)展債券,以及為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借款人提供融資,如醫(yī)院、高等院校、電力和能源公司、資源回收設施、多戶住宅項目、酒店、體育場館等(U.S.SEC,2012)[12]。在我國,如果省級政府僅作為發(fā)行人,不再是還款義務人,而是由使用主體承擔還款義務,這樣不僅可以降低使用主體的道德風險,提升資金使用效率,而且能夠減輕地方政府償債壓力,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但是,根據《預算法》第三十五條,借鑒管道收入債券制度尚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礙。
最后,積極賦予地方稅權,擴大地方財政自主權。在“中央不救助原則”下,地方政府的舉債水平和風險防范能力應當取決于其穩(wěn)定、充足的自主財力。從實際情況看,在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占主導地位,共享稅的收入分成也高于地方稅的收入。因此,可以說地方政府缺乏自主、充分、穩(wěn)定的財力。為此,建議建立適合作為地方稅的稅種,具體包括:將部分品目消費稅征收環(huán)節(jié)后移至零售環(huán)節(jié)征收,由中央稅改為地方稅;企業(yè)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繼續(xù)作為中央地方共享稅種(樓繼偉,2023)[13]。確立地方稅權是完善地方稅體系的前提和基礎。因此,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乃至構建發(fā)達的政府債券市場,從根本上看,需要擴大以地方稅權為主的地方財政自主權。
五、結語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需要調整專項債的功能定位,舒緩其經濟增長功能,明確其地方事權功能。從短期來看,這有利于強化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真正落實“中央不救助原則”;從長遠來看,這有利于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體系,培育健康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我們認為,防范債務風險不能局限于緩一時之急,而應當立足長遠,目標是形成發(fā)達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這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涉及財政體制、監(jiān)管機制、法治環(huán)境等多個方面,專項債的功能定位問題只是其中一個制度節(jié)點。從財政體制上看,應當繼續(xù)推進中央與地方、省級與省級以下政府之間的財政體制改革,應當明確地方稅權,賦予省級以下政府適度的舉債權。從監(jiān)管機制來看,應當構建市場監(jiān)管制度,完善債券信息披露,加強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不僅影響到投資者利益的實現,而且涉及作為納稅人的地方居民的合法利益。從根本上看,應當不斷完善法治環(huán)境,實現納稅人與債權人雙方利益的制度平衡。
注:
①根據財政部網站信息,2021年1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260208億元。其中,一般債務129495億元,專項債務130713億元。截至2023年1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357018億元。其中,一般債務145344億元,專項債務211674億元。
②數據來源:財政部網站《2022年12月地方政府債券發(fā)行和債務余額情況》。
③需要明確的是,如果將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計算在內,政府負債率、地方政府債務比例會大幅上升。有學者指出,與政府關聯密切的地方城投有息債務余額也有近60萬億元,按照IMF的估算比例(將2/3的城投債務視為政府隱性債務),其中有40萬億元可視為政府隱性債務(徐奇淵和盛中明,2023)[9]。
④數據來源:Investor Bulletin: The Municipal Securities Market, https://www.investor.gov/introduction-investing/general-resources/news-alerts/alerts-bulletins/investor-bulletins-36。
⑤數據來源:《2022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zhí)行報告》。
⑥按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使用方向和不同投資主體的主要活動范圍,將投資大體劃分為競爭性項目投資、基礎性項目投資、公益性項目投資三大領域。參見桂世鏞:《中國計劃體制改革》,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頁。
參考文獻:
[1]Matt Glasser. 2020. Municipal Bonds in Three Countries: India,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Urban Law and Policy,(4).
[2]楊子榮.美國再陷債務上限僵局 [N].人民日報,2023-02-03.
[3]楊志錦.一般債額度占地方債比重再創(chuàng)新低,地方債結構如何調整? [N].21世紀經濟報道,2023-03-08.
[4]王茂慶,鞏岱賢.地方政府債務監(jiān)管路徑的反思與超越 [J].金融發(fā)展研究,2022,(11).
[5]牛犁.政策加力形成合力,經濟運行整體好轉——2023年經濟形勢展望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解讀[J].時事報告,2023,(01).
[6]Wallace E Oates. 2005. Toward A Second-Generation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 [J].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ume 12.
[7]趙林如主編.中國市場經濟學大辭典 [Z].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9年.
[8]馮俏彬,宋恒.地方政府專項債:問題與對策 [J].中國經濟評論,2022,(11).
[9]徐奇淵,盛中明.準確認識財政領域的四大問題 [J].財經,2023,(05).
[10]熊偉,許戀天.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制度困境與路徑選擇 [J].上海經濟研究,2022,(04).
[11]張子學.美國市政債券監(jiān)管執(zhí)法的狀況與借鑒 [J].證券法苑,2014,(13).
[12]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2012. Report on the Municipal Securities Market [R].https://www.sec.gov/news/studies/2012/munireport073112.pdf.
[13]樓繼偉.新時代中國財政體系改革和未來展望[J].比較,20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