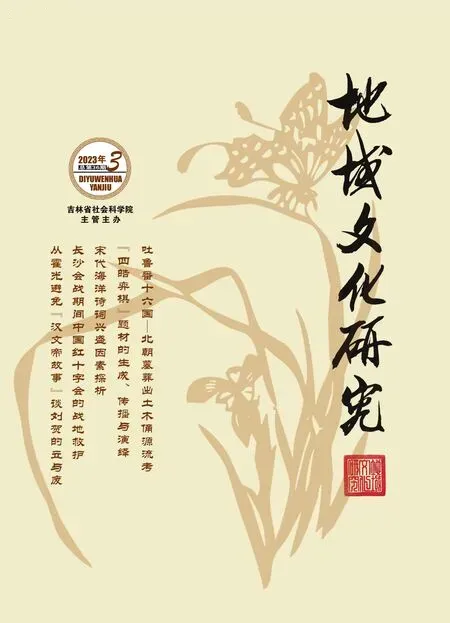吐魯番出土長行馬文書相關問題研究
李學東
長行馬作為唐代前期西域地區的重要交通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西域各地之間的聯系與溝通,有效保證了政令的上通下達,對于唐朝經略西域意義重大,不容忽視。學界關于長行馬的研究,積淀深厚,成果眾多。日本學者藤枝晃最早利用京都有鄰館所藏唐代文書對長行馬及長行坊展開研究①藤枝晃:《〈長行馬〉文書》,《東洋史研究》第10卷第3號,1948年,第213-217頁;藤枝晃:《長行馬》,《墨美》第60號,1956年。,成為探討這一課題的先行者。孔祥星較為全面地探察了長行坊的任務、性質、組織與制度,并對藤枝晃的部分觀點提出商榷,進而揭示了長行坊的設置對于唐朝強化對西域地區管理的重要意義。②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區的交通組織長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書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1年第3期。王冀青對唐代長行馬的管理方式作了考察,并揭橥了傷、病、亡馬匹的處理程序;此外,以專文討論了唐代驛馬、傳馬與長行馬之問題,認為西域的長行馬即為傳馬。③王冀青:《唐交通通訊用馬的管理》,《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2期;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區用于交通的驛馬、傳馬和長行馬——敦煌、吐魯番發現的館驛文書考察之二》,《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2期。荒川正晴則認為長行坊與傳馬坊并不相同,長行坊乃是驛傳制之外的制度,并與常駐鎮守軍體制相適應,至8世紀初河西傳馬坊被長行坊所取代的趨向日益凸顯。④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の伝馬坊と長行坊》,《東洋學報》第70卷第3·4號,1989年,第165-199頁。孫曉林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吐魯番文書,對唐代西州長行坊問題做了較為細致、詳盡的思索。①孫曉林:《試探唐代前期西州長行坊制度》,載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69-241頁。郭平梁指出長行坊具有雙重功用,其不僅發揮著運送行人的職能,還作為運輸機構,起著運送貨物的作用。②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書考釋——唐代西域陸路交通運輸初探》,《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1期。
日本學者中村裕一、荒川正晴相繼對長行馬問題做了探究。③[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日]荒川正晴:《長行馬文書考——大英圖書館所藏文書を中心として》,池田溫編:《日中律令制の諸相》,東京:東方書店,2002年,第379-405頁。乜小紅聚焦于吐魯番出土的唐代畜牧業文書,對長行坊與長運坊的牲畜牧養與管理調度作了較為系統的探討,揭示了其在政治軍事和交通運輸領域發揮的重要作用;④乜小紅:《吐魯番所出唐代文書中的官營畜牧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同時利用相關文書,探察了馬匹在唐代絲路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⑤乜小紅:《試論唐代馬匹在絲路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論叢》第9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52-170頁。。關于唐代西域地區長行死馬皮肉的處理,相關學者亦曾撰文討論。⑥參見王啟濤《絲綢之路上的飲食文化研究之二:肉——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四川旅游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趙貞《杏雨書屋藏羽34〈群牧見行籍〉研究》,《中國經濟與社會史評論》2016 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20頁;趙晶《論唐〈廄牧令〉有關死畜的處理之法——以長行馬文書為證》,《敦煌學輯刊》2018年第1期。針對文書中存在的釋錄問題,王啟濤專門加以歸納并嘗試提出解決之法。⑦王啟濤:《吐魯番文獻釋錄中的幾個問題》,《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圍繞長行馬相關問題,前賢時彥業已作了較為充分的探究,但余義尚存,相關細節仍有進一步厘清的必要。今擬在前輩學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吐魯番所出唐神龍元年(705)長行馬文書再作探討,以期深化對長行馬相關問題的認識。
一、“金婆”還是“金娑”:唐代西域地名之辨析
西州作為唐朝經略西域的前沿陣地,成為東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孔道,戰略位置十分重要。以西州為中心,輻射四周的交通干道無疑為加強各地區之間的聯系提供了便利,同時也有利于唐廷對西域地區的管轄。貞觀十四年(640),唐軍平定高昌后,以其地置西州,并于交河城置安西都護府,派兵駐守。⑧《資治通鑒》卷195,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九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269頁。其后隨著唐軍經略西域進程的推進,安西都護府的統治也逐漸深入。《資治通鑒》載:“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于龜茲,以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⑨《資治通鑒》卷200,唐高宗顯慶三年五月癸未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423頁。安西都護府的治所徙于龜茲后,并非固定不變;由于吐蕃與西突厥時常聯兵入寇,西域局勢動蕩不安,安西都護府(龜茲)亦幾經廢棄,被迫遷回西州。直至長壽元年(692),王孝杰克復四鎮,安西都護府得以復置于龜茲,唐廷發兵鎮守;⑩《舊唐書》卷196上《吐蕃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225頁。安西都護府駐所龜茲的安全得以保障,唐軍在西域的經略漸趨穩固。此外,武后又于長安二年(702)置北庭都護府于庭州[11]《資治通鑒》卷207,則天后長安二年十二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677頁。,由此形成了安西都護府與北庭都護府分治天山南北的格局。盡管隨著安西都護府的西遷,西州復置都督府,但其在唐朝經營西域過程中的重要性并未降低,從吐魯番所出長行馬文書可見一斑,以長行馬為交通工具,從西州出發至周邊地區的頻繁往來足以證明西州作為交通樞紐的重要地位。西州與庭州的往來又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文書中不乏對其交通路線的加載。《唐神龍元年(705)交河縣為長行官馬致死上西州兵曹狀》載:
1 任將狀上鎮,任為公驗者,馬既不在鎮死,錄石舍狀,牒縣任為
2 公驗者,丞判長行官馬送使北庭,回至金娑,便稱致死,
3 懸信鎮牒未可依從,以狀錄申聽裁者,謹依狀申①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114頁。
文書系年為唐神龍元年(705),狀文記載長行官馬送使北庭,北庭蓋指北庭都護府治所庭州。當長行馬在完成送使北庭的任務之后,在返回西州的過程中,變故陡生,長行馬在金娑致死。從文書所記長行馬的返程來看,金娑應當是位于西州與庭州之間的必經之地。《元和郡縣圖志》載:
(西州)北自金婆嶺至北庭都護府五百里。②(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40《隴右道下·西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031頁。
《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從西州至北庭都護府需經“金婆嶺”,此書乃是李吉甫于唐憲宗元和年間所撰,其時西州已不復唐有,河西亦被吐蕃占領多年,道路不通,往來困難,或許在撰述之時會對西域地區的記載出現錯漏。文書為當地官吏在長行馬致死之后所書狀文,屬于當時人記當時事,文書中出現的“金娑”自然出自當地官吏之手,其真實性似乎毋庸置疑。“金婆”與“金娑”字形相近,兩者所指是否為同一地方?《新唐書》載:
交河,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護府城。③《新唐書》卷40《地理志四·隴右道》西州交河縣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46-1047頁。
《新唐書》詳細記錄了自交河縣至北庭都護府的交通路線,交河縣隸屬于西州④《元和郡縣圖志》卷40《隴右道下·西州》載:“(西州)管縣五:前庭,柳中,交河,天山,蒲昌。”第1031頁。,換言之,這條線路也可以說是西州至庭州的路徑。值得注意的是,發向北庭都護府需要取道“金沙嶺”,此地上揭所述之“金婆”是否有所關聯。嚴耕望先生通過考證指出金沙嶺、金婆嶺當為一嶺,沙婆之一可能為形訛,又簡稱金嶺。⑤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卷2《河隴磧西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95-596頁。此外,松田壽男認為金沙嶺、金婆嶺、金嶺為同一嶺,乃是博格達山的一部分。參見[日]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第400頁。馮承鈞進一步指出金娑嶺亦指博克達山。參見馮承鈞撰,鄔國義編校《馮承鈞學術著作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3頁。既然金娑嶺、金沙嶺、金嶺系指同地,即博克達山,那么在時人的認知中,此山之名稱究竟為何,需要進一步厘清。《西域考古錄》載:
金山在鎮西,府西北,亦曰金娑嶺,唐置戍守處曰金嶺城。永徽二年西突厥寇庭州,陷金嶺城;顯慶二年蘇定方討西突厥,至金山北,先擊破其處木昆部是也;開元中,以西州為金山都督府,亦以山名,亦曰金娑山。⑥(清)俞浩:《西域考古錄》卷7《鎮西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93-394頁。
通過《西域考古錄》的記載,我們對金娑嶺的沿革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此書雖是清人俞浩所撰,距唐時久遠;但其在撰述過程中,對史料進行批判地利用,并十分注重經過實地踏勘的時人著述⑦司艷華:《〈西域考古錄〉的史料來源與運用》,《吐魯番學研究》2016年第2期。。因此其對金娑嶺的記述是值得采信的,而“金婆嶺”“金嶺”等其他稱謂應該是在傳抄過程中出現的。
在唐朝經略西域的過程中,長行馬在促進兩地間的溝通與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位于天山南北的西州與庭州是唐朝在西域的兩個邊防重鎮,兩地間的往來自然也非常頻繁。當長行馬完成送使庭州的任務之后,在返回西州途中于金娑致死。金娑應是西州與庭州之間的一處必經之地,文書記載其名稱為“金娑”,然而在傳世文獻中則稱之為“金婆嶺”“金沙嶺”等,是乃同一嶺,即博克達山。通過《西域考古錄》對此山歷史沿革的詳細梳理,可以發現金娑嶺應是此山的原本名稱,其他稱謂應該在諸書傳抄、流衍過程中的訛誤所致。
二、獸醫勘驗與逐級上報——長行死馬之處理
長行馬作為西域地區傳遞政令與官員往來的重要交通工具,時常長途奔馳于兩地之間,致使其死亡率較高。鑒于長行馬在國家政治、軍事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域地區又會對長行死馬履行何種處理程序?《唐神龍元年(705)交河縣為長行官馬致死上西州兵曹狀》載:
7 元是不病之馬,送使豈得稱
8 殂,只應馬子奔馳,所以得茲①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114頁。
狀文明確指出長行馬原本是“不病之馬”,應該是由專門的醫者為其勘驗,才能使相關官吏如此篤定此馬從前并非帶病,并在長行馬死后斷定是由奔馳致死。文書反映長行馬患病與否的記載十分普遍,《唐神龍元年(705)天山縣為長行馬致死上西州兵曹狀》載:
11 銀山鎮狀,得馬子令狐弘寶辭,稱從州逐上件馬,送使人往烏耆,今
12 回至此鎮西卅里頭,前件馬遂即急黃致死,既是官馬不敢緘默②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116頁。
可以發現,在這件文書中,長行馬同樣承擔了送使的任務,在返程途中卻急黃致死,據《肘后備急方》載:“馬急黃、黑汗,右割取上斷訖,取陳久靴爪頭水漬汁灌口。”③(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卷8《治牛馬六畜水榖疫癘諸病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子部五醫家類,第345頁。顯而易見,“急黃”乃是馬匹常見的一種病癥。狀文中雖然沒有對于醫家的明確記載,但是卻對長行馬致死之由知之甚詳,對其病癥了如指掌。由此觀之,其中必有精通醫理的人參與長行死馬的鑒定。此類情況并非個例,在長行馬送使返程的途中時常發生,《唐神龍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長行死馬案卷(A)》云:
9 既是長行,請乞檢驗者。右奉判,馬既致死,宜差典孫
10 俊、高慶等就檢其馬,不有他故,以不狀言者,其上件馬
11 行至鎮南五里,急黃致死有實,亦無他故者,其馬致死檢④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118頁。
這份案卷所記長行馬致死原因亦為“急黃”,可見此病乃是西域地區長途奔馳的長行馬易患之癥。長行馬作為西域地區的重要交通工具,卻極易罹患此病,那么長行坊理應配備專門的獸醫為長行馬定期診斷,以保障其健康狀況。所幸在此件文書的末尾記錄當時的獸醫名字,其文曰:
41 獸醫 曹智隆
獸醫的出現說明長行死馬的勘驗是由專業的醫家來負責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長行馬在西域地區的重要性,倘若是扮演著可有可無的角色,那么亦無須耗費資財來請專門的獸醫來鑒定其死因。此外,在《唐開元十年(722)西州長行坊馬驢發付領到簿》亦有關于“獸醫”的相關記載,茲引述如下:
17 以前使,閏五月□日,發付使,各自領
18 獸醫,目波斯乘驢一頭,○一頭青黃父,八歲①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98頁。
在長行坊領到馬驢之時,會有獸醫對牲畜進行專門的檢查。由此可見,長行坊接納長行馬時即有專人驗看其體征狀況,在其死亡后又有獸醫對其死因進行復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長行馬致死之因并非只有“急黃”之癥,其負重太多亦會導致其死亡。《唐神龍元年(705)西州典魏及牒》載:
3 ]廿一日,送張嘉義往北庭
4 ]脊破,依問馬子董德德
5 ]張嘉義往北庭,其駱馬
6 ]□升麥飯,三升忩草
7 ]□被貸一,更馱醬胡
8 ]為此馱極重,馬死者
9 ]馬死及脊破,即都護②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124頁。
這件文書同樣展示的是長行馬送使致死的事件,所不同的是,長行馬乃是因為馱載醬胡過度,以致負重太多,造成脊破馬死的結果。從文書內容來看,長行馬不但承擔了運送張嘉義前往北庭的任務,而且馱負醬胡等貨物;由此可見,此番長行馬不僅充當了交通工具,還發揮了其運輸的職能。正是因為負載過重,致使脊破,成為致死的重要原因。不難發現,長行馬死亡并非“急黃”病癥一種因素所致,馱載物資過多也往往導致其發生意外,而此時專業獸醫的存在就顯得很有必要,對其死因的鑒別成為相關機構對責任者判罰與處理的重要依據。
此外,翻檢文書,可以發現對長行死馬案件的處理并不是直接由長行馬死亡地的相關機構直接處理,而是逐級上報,最終由西州都督府兵曹來判決。《唐神龍元年(705)交河縣為長行官馬致死上西州兵曹狀》載:
1 任將狀上鎮,任為公驗者,馬既不在鎮死,錄石舍狀,牒縣任為
2 公驗者,丞判長行官馬送使北庭,回至金娑,便稱致死,
3 懸信鎮牒未可依從,以狀錄申聽裁者,謹依狀申③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114頁。
4 令在州 丞 元楷
5 兵曹件狀如前謹錄依申請裁 謹上
文書首行寫道“馬既不在鎮死,錄石舍狀”,其中“鎮”之所指應該是下文所提到的“懸信鎮”;孫曉林推斷新唐書地理志中的“石會漢戍”存在訛誤,石會應該是石舍之誤,認為石舍館應是西州交河縣最北邊的一個館①孫曉林:《關于唐前期西州設“館”的考察》,《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1 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 年,第251-262頁。。《唐天寶十四載(公元七五五年)交河郡長行坊申十三載郡坊帖馬侵食交河等館九至十二月馬料賬》即有“石舍館”的記載,其文云:
4 合郡坊帖馬,從九月廿一日以后,至十二月卅日以前,侵食
5 交河等館馬料斛斗,總壹阡陸拾捌碩,叁斗陸勝
6 叁伯肆拾碩,先支給訖
7 壹伯碩交河館
8 壹伯碩柳谷館
9 捌拾碩石舍館②《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第10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26-227頁。
馬料賬所展現的乃是郡坊帖馬侵食交河等館馬料的情況,館中儲存了飼喂馬匹的馬料,交河、柳谷、石舍等館皆是此類,為長行馬補充馬料之所。那么文書中所見之“館”在唐代一般都設在何處?《通典》記載:“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③(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33《職官十五·鄉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24頁。由此可見,“館”的性質類似于“驛”,只是其設置之地并非通途大路,石舍館既位于西州交河縣之北,地處西域邊陲,交通狀況應無法比擬中原之地,在此處設館對于保障交通往來意義重大。
石舍館之狀既已錄,那么應該“任將狀上鎮”,其中“鎮”蓋指第三行所示之“懸信鎮”。張廣達先生指出懸信鎮位于交河城西北越金娑嶺至庭州之他地道上④張廣達:《唐滅高昌國后的西州形勢》,原載《東洋文化》第六十八號,1988年;此據氏著:《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3-173頁。;陳國燦先生依據判文提出金娑館屬于北庭懸信鎮防區,并進一步闡明他地道的走向以及館驛⑤陳國燦:《唐西州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論叢》第9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37-151頁。。盡管懸信鎮已對長行死馬調查取證,然而卻未可依從,西州都督府仍需派專人對此事進行核實,并著重勘驗長行馬之確切死因。節級上報復檢的做法一方面體現了長行馬在西域地區的重要地位,使得各級部門對其死因給予了足夠重視;另一方面則表明盡管地處邊疆,從基層組織至西州都督府行政之審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唐朝法令在此地得到較為切實的貫徹與實施。《新唐書》載:“凡傳驛馬驢,每歲上其死損、肥瘠之數。”⑥《新唐書》卷46《百官志一·尚書省》兵部駕部郎中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98頁。傳驛之馬驢死損情況既然每年需呈報朝廷備案,那么西州都督府兵曹參軍對基層所上報之長行死馬情況再次核驗也就易于理解了,其目的在于核實長行死馬的真實情形,并將之詳細記錄在案,以備向兵部申報。
三、從武周新字的消亡看唐洛陽至西州的行程
武則天稱帝之時,宗秦客曾作武周新字,頒行于天下。《資治通鑒》載:“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①《資治通鑒》卷204,則天后永昌元年十一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577頁。武則天掌權之時,武周新字在官府文書中行用,吐魯番出土的唐神龍元年長行馬文書即是明證。《唐神龍元年(705)交河縣為長行官馬致死上西州兵曹狀》載:
15 三匚出(月)九○~日錄事 ?受②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114頁。
神龍元年(705)正月,張柬之等一眾大臣發動政變,迫武則天退位,擁太子李顯即位,唐室得以復興。唐中宗即位后,便下詔恢復此前李唐在政治與社會文化方面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資治通鑒》載: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③《資治通鑒》卷208,唐中宗神龍元年二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700頁。唐中宗下詔文字一仍其舊,那么武周新字自然會退出歷史舞臺。西州地處邊陲,官府文書中的武周新字究竟于何時才真正棄之不用?唐神龍元年(705)長行馬文書為我們了解此事提供了契機,為便于論述,現列表如下:

唐神龍元年長行馬文書所見武周新字消亡表
唐中宗于神龍元年(705)二月甲寅下詔廢除武周新字,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當時朝廷尚未還都長安,洛陽仍為國家政治中心;④據《資治通鑒》卷208,唐中宗神龍二年十月條載:“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724頁。唐中宗于神龍二年還都長安,可見神龍元年二月之時,洛陽依然是朝廷政務機關所在,為全國政治中心。西州地處邊陲,距離內地懸遠,朝廷詔令自洛陽發出后,并不能朝發夕至,西域地區的各級機構因而無法及時收悉中樞政令,反映在官府文書中,武周新字依然會持續使用。那么發于洛陽的詔令究竟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到達西州?嚴耕望先生指出長安西至安西行程約七千里,急行一月可達。①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卷2《河隴磧西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1頁。然而唐中宗下詔之時正值冬季,天地嚴凝,河西及西域氣候條件惡劣,驛路難行,或許在實際行進途中無法一月送達。《唐會要》載:“中宗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諱顯。……神龍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即位于通天宮端扆殿。年五十。二月五日,國號依舊稱大唐。”②(宋)王溥:《唐會要》卷1《帝號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頁。唐中宗復唐國號在神龍元年(705)二月五日,上揭提到中宗恢復國號是在神龍元年(705)二月甲寅,那么二月甲寅應該是指二月五日,廢除武周新字,恢復舊字的詔令應于神龍元年(705)二月五日從洛陽發出。從上表來看,神龍元年(705)三月二十四日西州都督府依然在行用武周新字,至三月二十九日文書中的武周新字消失,復用舊字,表明西州應已收到朝廷詔令,因而在文書行政之中停用武周新字。據此,我們可以對當時唐朝從洛陽至西州的行程做一個粗略的估算,從神龍元年(705)二月五日至同年三月二十九日,歷時54天;換言之,從洛陽至西州實際上約需54天方可到達。
結 語
金娑嶺是位于西州至庭州的交通要道,但因史籍記載不一,其名稱較為混亂,齟齬之處頗多。長行馬文書有關“金娑”的記載乃是出于時人對此地最為直接的認知,可信度較高;此外,《西域考古錄》較為詳細地記載了金娑嶺的歷史沿革,為我們了解其本來面目提供了線索。其他史籍對“金娑”的記載應該是在傳抄過程中出現了訛誤,以致名稱出現偏差。作為時常奔馳于兩地之間的長行馬,在傳遞政令、加強地區聯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地官府因而給予了足夠的重視。
長行馬致死之后,會有專門的獸醫檢覆其死因,蓋因其致死之因并非僅僅局限于“急黃”之癥,負載過重亦可導致脊破馬死的結果。因此,由專業的醫者對長行死馬的再鑒定就顯得很有必要,其死亡原因成為官府處理長行死馬案件的重要依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長行馬在傳驛途中意外死亡,死亡地驛傳組織的調查取證并不能作為案件判決的最終憑據,還需層層上報,最終由西州都督府兵曹參軍派專人進行復檢。此種做法乃是西州都督府出于了解長行馬死因真相所做出的調查,事畢還須將其記錄在案,以備上報兵部,亦從側面反映出長行馬在西域地區的重要作用。
神龍元年(705)作為武周與唐朝政權交替的一個年份,在王朝鼎革之際,政策措施發生了較大變化,體現在文書行政上便是武周新字的逐漸消亡。神龍元年(705)二月五日,唐中宗下詔文字一仍其舊,顯然是意欲廢除武周新字,當時尚未還都長安,洛陽依然為唐朝的政治中心,因此詔令從洛陽發出,下達全國各地官府。西州因地處邊陲,與中原內地相去甚遠,無法及時收悉朝廷詔令,因此在官府文書中仍然繼續使用武周新字,至同年三月二十九日方才恢復使用舊字。從朝廷下發詔令,到西州最終改用舊字,歷時約五十四日,這段時間正是詔令從洛陽送往西州的行程所花費的時間,那么我們可以據此推斷當時洛陽至西州之間的實際路程約需54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