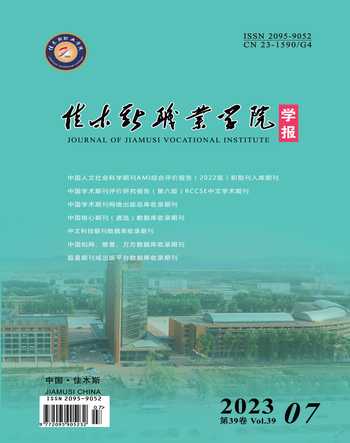夢得池塘生春草
肖肖
摘 ?要:吳福輝對海派文學概念的界定具有劃時代的學術價值,他先劃定了海派作家的范疇,區分了舊派文人與海派作家;進而梳理了海派文學的審美范疇,把都市文化中的文化因子凸顯出來,賦予海派文學現代審美質素;他還糾正了海派文學的評價導向,將之視為重要的現代文學流派之一,既不夸大其成就,也不蔑視其審美。
關鍵詞:吳福輝;海派文學;概念界定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052(2023)07-00-03
吳福輝老師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87初版)中就涉及了海派中的“新感覺派”以及徐訏和無名氏兩位作家,冠名為“洋場小說”(第二十三章);1998年該書改動修訂,直截了當打出“海派小說”的概念(第十四章),這是綜合文學史中第一次出現明確的“海派文學”概念。《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是很多高校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也是許多高校指定的考研必備書,在高校的使用和學界的引用都是文學史中的佼佼者。所以吳老師的“海派文學”概念也隨著此書的廣泛傳播更為學界廣為了解和接受。
一、確定“海派文學”作家范疇
海派文學這一概念自“京海論戰”,指向并不明確;基本成員劃分標準不統一,沈從文在《論“海派”》《上海作家》等系列文章中論述海派,他所謂的海派作家系列既包括生活在上海的作家,也包括其他城市作家中寫作風格具有匠風氣的作家。因此,沈從文對海派的概念認定中接受了既定海派文人群體,其中包括當時的鴛鴦蝴蝶派,又進一步把海派作家范圍擴展到左翼和民族主義作家中。當時在上海文人的心目中,海派即是“鴛鴦蝴蝶派”[1],施蟄存也認同當時的海派就是指“鴛鴦蝴蝶派作家如周瘦鵑、張恨水、鄭逸梅之流”。
吳老師的海派文學概念規定了海派作家身份標準。他對海派文學范疇有自己的認識,他認為鴛鴦蝴蝶派等洋場氣質文學處于“中國的現代都會尚未成型時期……不能稱為海派”,海派作家的特征是從上海市民階層的視角看待上海這座東方魔都。吳先生又試著:“給海派文學做一界定,把隸屬于舊文學的鴛鴦蝴蝶派和三四十年代可歸入新文學一翼的海派區別開來(二者自然也有割不斷的聯系),認定并勾勒了海派小說的大致輪廓。筆者認為海派雖無明顯的結社行為,卻是一種廣泛的、有豐富內涵的流派現象,它反映了現代文明在中國緩慢伸延的不平衡性,在由東南沿海局部的前工商社會,向大陸中西部的后農業社會,向西北殘余的游牧社會逐步擴展的過程中,海派的畸形以及它遭遇到的誤會,顯示了中國人文歷史的曲折與斑斕。”[2]
吳老師界定的海派作家范疇鉤沉打撈了一些已經被遺忘的海派作家或者無處劃分的作家如黑嬰、東方蝃蝀等等,學界對這些作家進行了新的研究,左懷建《評東方蝃蝀的〈紳士仕女圖〉》便明確提出是根據吳先生發掘的資料對作家進行進一步研究的,根據著名現代文學史專家吳福輝先生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附錄:海派小說家傳略與主要書目——東方蝃蝀的內容[3]進行了對這一長期被主流文學遮蔽的海派作家文學的重新發現和認識。
二、梳理海派文學的美學范疇
吳老師審視海派文學時,主要以市民眼光和都市描寫這兩個維度進行判定。在以“鴛蝴派”為代表的洋場小說中,這兩個維度同時存在。關于海派文學的審美范式,吳老師將舊文學中的市民喜好、城市描寫與海派文學中的市民眼光和新都市文化進行了細致的辨析。
吳老師認為海派文學的第一品格應為是否具有現代性,“鴛蝴派”不應是屬于海派的范疇,就是因為這一流派文學盛行時期,十里洋場的新都會文化并未呈現。而洋場文學“中國傳統的才子佳人章回小說的橫移,只是更加媚俗,更加投合中國老市民的趣味而已。”把鴛鴦蝴蝶派的審美旨趣與海派區分開來,輕描淡寫地解決了學界對海派附著鄙俗氣息的批評。這個切割十分必要,也十分科學。
起初,海派文學被批判為低級趣味的消費文學。沈從文曾撰寫過《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一文,這里首次提出文學中的“海派”與“新海派”時候就帶有此種傾向性,他指出禮拜六派(“鴛蝴派”)之所以說是海派,就是它具有十里洋場一切的趣味。所謂的“趣味”就是指向:市民趣和商業味。顯然,市民又指的是老市民,他們的審美情趣是惡俗的封建文化的遺留,風花雪月、才子佳人等情節廣受歡迎,以此套路做文,即便是十里洋場的生活,也只是穿著新衣的老故事。他又說“承繼‘禮拜六,能制禮拜六派死命的……是如像《良友》一流的人物。這種人分類應當在新海派”。他對海派的概括是:“過去的‘海派與‘禮拜六派不能分開。那是一樣東西的兩種稱呼。‘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對于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這里他又提出了“商業”一詞,再次以傳統文人“經國大業”的高高在上姿態嘲諷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海派創作。沈從文的評價抓住了禮拜六派寫作的特征,也說清楚了其對市場的依賴,客觀地說,這是海派文學不可回避的特點,但是沈從文對文學的追求和個人的審美傾向不允許他對市場低頭。1928年1月初,沈從文到達上海,抱有重造人心改造社會的文學態度,20年代末30年代初,《紅黑》雜志、《人間》月刊創刊發行,編者為沈從文、胡也頻、丁玲。三人堅持純文學立場,不愿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商品競賣之中[1],無奈上海的實際情形與沈從文他們的文化理想相距甚遠。在上海那種純粹的商業文化環境中,這樣的刊物很快就夭折。《人間》和《紅黑》月刊均出版了幾期便宣告失敗。這段經歷可看出沈從文審美追求上他向往純美的文學意境,理想讀者追求上,他定位于純樸人性的國民。因此,他與市民的鄙俗和市場的逐利格格不入。
可見,沈從文對上海大都市的消費文化十分抵觸,由此對海派文學產生了負面情緒;但沈從文并不認為居于上海的作家都屬于海派,甚至指出北方作家也具有海派習氣。也就是說,沈從文是從文學審美趣味上去審視海派文學的,他用消費文學視角關照海派文學,認為海派文學偏重市場逐利,審美旨趣與純文學大相徑庭。因此,他又因審美趣味而將魯迅、茅盾等居于上海的作家也排斥于海派之外,重點批判海派文學家賣文為生的商業氣息。海派重要的理論家之一韓侍桁撰寫了《論海派文學家》一文,此文也將海派限定為某些上海作家,并且是帶點兒下流甚至墮落的作家,魯迅在《“京派”與“海派”》一文中更明確界定海派為“則是商的幫忙而已”。大家對海派的商業性關注頗多,認為商業行為偏離了文學本質,不具備審美性。
關于海派文學被批評的媚俗化、商業化的聲浪日熾,海派作家們也不得不出面辯解,蘇汶的文章《文人在上海》中,概述了上海大不易居的現狀,他指出上海經濟發達,居住其中的文人往往生活困難,難以悠然自得地進行文學創作,只能為追求金錢而賣文生活,既然生活所迫,文章略有粗疏也在所難免。對此,左翼文人森堡深以為然:“是的,上海(應該說是中國吧)的文人誠然要錢,而且,我也跟蘇汶先生一樣地,‘并不覺得這是可恥的事情”。曹聚仁卻有不同認知,撰文指出,“海派”是“摩登女郎”“是社會的,和社會相接觸的”。以社會性為觀照視角,曹認為海派更貼近社會,換言之海派文學并非閉門造車。沿用此觀點的還有楊晦,上海《文匯報》的周刊《新文藝》在1947年3月份兩期連載他的文章《京派與海派》,也認為“海派是進步的”盡管有限,但總是比京派的沒落故步自封要進步。但是這些辯駁觀點并未能扭轉海派的聲名狼藉,包括這些辯駁者自身的文章也一再承認了海派被批評的商業性和低俗化。
眾說紛紜中,吳老師給海派文學下定義時,他摒棄了海派文學作為舊的批判對象的認知,他指出了海派的商業性被批判對象,但是其中有著重要的“現代質素”,海派的文化符號應該是現代都市。海派文學的核心是表現現代都市生活。其中的研究重點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沖突,中西文化之間的對立,現實與理想等糾纏矛盾統一關系。但筆者認為吳老沒有完全摒棄傳統對海派的認知,他某種程度上依然是把都市作為人物活動背景來展示的,無論是在穆時英筆下的燈紅酒綠還是張愛玲筆下的都市情愛,上海作為“東方魔都”它的租界背景與生活在其中的市民,他們天然的具有現代性。他把都市性當作海派文學審美的向度之一,都市與鄉土的二元對立中,都市的現代性被凸顯,海派致力于新的生活理念、哲學意蘊的挖掘,把燈紅酒綠的現代都市生活作為人活動的場景,用新的人生感受來描寫人的離合聚散、主體性的分裂與重聚。
三、校正海派文學的評價導向
對海派文學的評價向例不佳,它從誕生起就受到來自文學界內外的雙重攻擊,現代文學的許多作家對海派鄙夷溢于言表。沈從文明確批評了海派作家的“白相文學態度”。曹聚仁也說:“海派文人百無一是,固矣。”姚雪垠認為:“海派有江湖氣、流氓氣、娼妓氣”。蘇汶是海派文人的代表他也認同:“新文學界中的‘海派文人這個名詞,其惡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劇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義方面極多,大概的講,是有著愛錢,商業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這種種意味”[1]。批評之聲并未隨著時代變化而斷絕,由于作家個體興趣、知識領域和文化場域的差異,海派文學一直處于被批評的風口浪尖,魯迅更一針見血指出“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海派文學從誕生之日起便危機重重,鑒于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地位,海派文學面臨著十分尷尬的危機。吳福輝先生科學評價海派顯得十分必要。
新中國成立后至80年代,這段時間國內學界要么對海派不再論及,要么以負面批評一語帶過[4],海外夏志清、李歐梵等學者已經開始了對海派文學的研究和新認識。國內直到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也只是初步提及“新感覺派”這一海派文學的分支,1990年趙凌河的《中國現代派文學引論》是最早的一部研究新感覺派文學的專著。楊義在文中對海派做了評價“上海現代派注重都市風的機械文明。”包括一些名家的文學史如朱棟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13》,王澤龍、劉克寬的《中國現代文學》,劉勇、鄒紅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均只提到“新感覺派”這一海派的分支。學界對海派文學的重要性嚴重低估,與海派作家們的貢獻不對等。
長期或被鄙夷,或被無視的海派文學在吳先生的梳理下得以有了清晰的概念,不僅把握了海派的特質,而且將海派文學的地域文化淵源進行了開拓,從海派文學擴大到對海派文化的探討,對海派文學進行了正名,引導了學界對海派文學的新評價導向。吳先生從1970年開始涉足海派作家初期研讀施蟄存,80年代初吳福輝老師發表在《十月》上的文章《中國心理小說向現實主義的歸依———兼評施蟄存的〈春陽〉》[4],贊譽施蟄存先生的作品。在周遭都對海派緘默不語時,他以科學的實事求是態度,對海派作家進行了仔細梳理,給予其相應的文學價值。接著陸續撰寫了《對西方心理分析小說的向往》《崩壞都市中生長的“惡之華”》《中國新感覺派的沉浮和日本文學》。已經初步涉及海派文學,1989年8月5日《文藝報》與1989年《上海文學》第10期接連發表《為海派文學正名》和《大陸文學的京海沖突構造》,直至1994年的《老中國土地上的新興神話》確立了海派文學的概念,厘清了地緣關系、時間跨度、代表作家和階段性特征。海派文學終于從無視到深耕,從荒蕪到繁榮,在吳老師理論架構和細讀分析支撐下,海派文學的概念越來越豐滿。于1997年出版了《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最早為“海派”正名,成為海派研究第一人[5]。一系列研究奠定了吳先生在海派研究中的學術地位。正如陳子善老師所言:“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老吳的海派文學研究在海內外現代文學研究界處于領先地位,也是他的現代文學史研究必要的準備、補充和深化。”[6]海派文學的概念成型后,圍繞著一眾作家的作品和項目如雨后春筍般紛紛而出,海派文學終于不再是一個被忽略、輕視甚至被詆毀的地位,而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顯學之一。
在吳老師的引導下,對海派文學的評價,由三四十年代的批判商業和媚俗,轉變為對其現代性和日常性的探討。周小儀的《比爾茲利、海派頹廢文學與30年代的商品文化》、黃建生的《重看海派文學的商業性》、曹超《文化市場下的海派作家及其寫作》等文章從不同角度分析了海派文學的商業性行為,在客觀抓住實質的同時,強調了海派文學商業性對都市文學發展的特殊貢獻是“20世紀新文學與市場結合的先聲”,張馥潔的《現代性視野下的海派文學》,林朝霞的《霓虹燈下的叛逆———論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學的現代性尋求》以及許道明的《海派文學的現代性》等文章則重點探討了海派文學的現代性,達成一致的認知是海派文學不僅學習西方的現代主義理論,而且還將其運用到創作實踐中。2000年李今的《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張鴻聲撰寫的《都市大眾文化與海派文學》都重在研究現代都市文化與海派文學二者間的關系,將海派文學確認為“適應上海新興市民階層大眾文化的新興都市文學”。
四、結語
吳福輝海派文學的概念,具有明確的現代特色,不僅寫作技法上同步于世界文學洪流,而且審美上凸顯了都市文化,海派作家的界定不應以作家居住地為標準,而要以作品特色為依據。他給予了海派文學客觀的評價,批評了其過渡面向市場的商業氣息,也肯定了對現代都市品格的塑形意義。吳福輝先生第一個界定了海派文學的概念,是所有海派文學研究者繞不開的界碑。其對作家范疇的確認、對美學范疇的確立,并且直接影響了對海派文學的研究導向,引發了對海派文學現代性、日常性、文化性、地域性的研究[5],加深了學界對海派文學這一長期被主流文學史和研究排斥在外的流派的重新審視和理解,促使海派文學成為今日研究之顯學。吳老師的這些影響和成就擔得起學界一致認同的“文學史專家”“海派文學研究開拓者”“海派文學研究專家”的稱號。
參考文獻:
[1]黃德志.對立與沖突的公開化——重讀20世紀30年代京派與海派的論爭[J].魯迅研究月刊,2005(6):4-12.
[2]吳福輝.老中國土地上的新興神話──海派小說都市主題研究[J].文學評論,1994(1):13.
[3]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
[4]楊迎平.海派文學研究綜述[J].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37-42.
[5]錢理群.這一代人中的一位遠行了——送別老吳[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4):133-147.
[6]李楠.飽滿的生命和學術:吳福輝先生及其海派文學研究[J].現代中文學刊,2021(2):23-29.
(責任編輯:張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