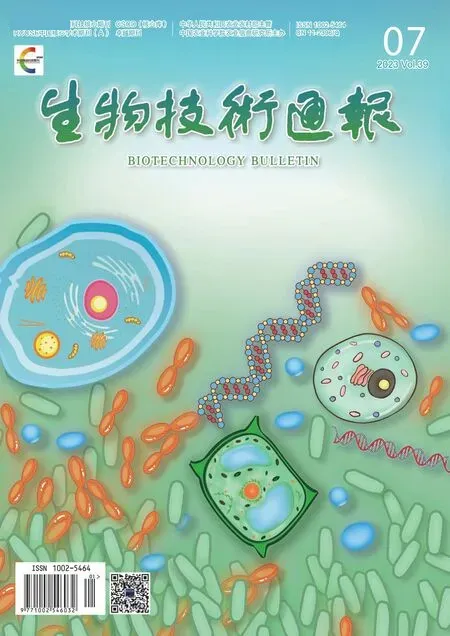早期抽薹對當歸根際土壤微環境的影響
謝田朋 張佳寧 董永駿 張建 景明
(1.甘肅中醫藥大學,蘭州 730000;2.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護中心,張掖 734000)
當歸[Angelica sinensis(Olive.)Diels]為傘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干燥根作為補血活血、調經止痛、潤腸通便的藥物在我國已有上千年的用藥歷史[1-2]。當歸在我國甘肅、貴州、山西、青海、四川、云南等地廣泛種植[3],其中,甘肅岷縣所產岷歸因品質好、產量高素有“岷歸甲中華”之美稱[4]。當歸中含有超過370種化學物質,包括苯酞類、單萜和倍半萜類、芳香類化合物、脂肪烴及其衍生物、多糖及有機酸等[5],其中當歸多糖、阿魏酸等化學物質具有抗炎、抗腫瘤、抗抑郁、增強心腦血管功能、免疫調節等多種藥理活性[5-7]。
隨著當歸廣譜藥效的研究和相關藥物的開發,其需求量逐年增加,每年栽培面積超過43 500 hm2[8],但當歸在種植中存在的連作障礙[9]、根腐病[10]和早期抽薹[11]等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在目前的種植生產中,當歸種子于第一年初夏播種,秋季收集發芽幼苗于室內越冬,第二年春季越冬幼苗繼續營養生長,同年秋季采收其非木質化根,或者在田間保存到第三年收獲新種[11]。然而,二年生當歸中有超過40%的個體發生早期抽薹現象,這會讓當歸根部木質化并失去藥用價值[11-12]。當歸早期抽薹是一個復雜的植物生化過程,幼苗年齡、幼苗重量和品種等內源因素,以及溫度、光照、施肥和海拔等外部因素均會導致該現象的發生[12-15]。但是,在實際種植過程中發現,在相同的內源和外源因素控制下,部分當歸仍會發生早期抽薹現象,這表明當歸早期抽薹可能受到一些尚未完全了解的因素影響。
前期研究表明,當歸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會隨著生長階段的不同而發生改變,并且抽薹期當歸根際土壤中部分微生物的相對豐度與其他生長階段存在顯著變化[16],這說明早期抽薹與根際土壤微生物可能存在聯系。根際土壤是植物生長、繁殖和代謝活動的最關鍵區域,植物根系可以通過分泌各種代謝物來影響其微生物群,有助于驅動根際微生物群落的組成[17]。同時,根際土壤微生物群也可能影響宿主植物的代謝,研究表明,擬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根系分泌物會影響根際微生物的群落組成,而微生物可以通過將色氨酸轉化為植物激素吲哚乙酸(IAA)來下調植物中開花有關基因,從而延緩開花,并且微生物還可以通過硝化作用增加和延長氮的生物可利用性,刺激植物進一步營養生長[18]。因此,研究根系微生物及代謝物對植物表型可塑性的影響對增加經濟作物產量上具有重要意義[19]。
目前,關于當歸早期抽薹現象與根際土壤細菌群落及土壤代謝的相關研究鮮有報道。因此,本研究通過控制試驗,利用16S rDNA擴增高通量測序和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方法(GC-MC),觀測抽薹與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細菌群落及代謝組變化,并尋找當歸根際土壤性質、細菌群落及代謝物之間在當歸抽薹現象中的關聯性,通過研究當歸早期抽薹對根際土壤微環境的影響,嘗試為解決當歸抽薹問題提供新的思路。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供試當歸為‘岷歸1號’,購自定西市農業科學研究院。為避免內源因素對當歸抽薹的影響,根據文獻記載[11],試驗中選用百苗重約100 g和直徑約0.55 cm的二齡幼苗作為供試材料。由于當歸為“低溫長日照”型植物[11],為避免光照等外源因素對當歸抽薹的影響,試驗在遮陰度25%的小型遮陰棚中開展,當歸幼苗移栽在盆口直徑16 cm、高20 cm的黑色塑料育苗盆中,1株/盆,共100盆。
1.2 方法
1.2.1 試驗地概況 試驗地位于甘肅中醫藥大學杏林百草園種植基地(103°95'E,35°97'N),當地海拔1 750 m,年平均氣溫15.5℃,年平均降雨量900 mm,無霜期290 d。供試土壤類型為黃土,實驗前土壤pH 7.77(土水比1∶2.5)、鹽分7.53 mg/kg、有機質3.77 g/kg,全氮1.38 g/kg、全磷3.32 g/kg、全鉀3.45g/kg、硝態氮39.32 mg/kg、氨態氮20.11 mg/kg、有效磷37.24 mg/kg、有效鉀172.47 mg/kg。
1.2.2 試驗設計 試驗用肥為(NH4)2HPO4復合肥料,3 g/盆,在移栽的同時拌施于土壤中,后期不再追肥。試驗過程中,每20 d對花盆進行一次隨機位置調整,避免環境差異對個體的影響,并根據天氣情況,定期對花盆進行澆灌,用水量為500 mL/盆。3個月后當歸生長進入早期抽薹期,觀察發現試驗中20%的當歸發生了早期抽薹現象。
1.2.3 樣品采集 當歸根際土壤于2021年7月19日采集。隨機選取抽薹和未抽薹當歸各18盆,用剪刀剪開花盆后取出當歸,將根部土壤抖落后用無菌毛刷將附著于根部的土壤輕輕刷落,每3株當歸的根際土壤混合在一起后分成兩份,一份裝于無菌凍存管中并迅速置于干冰中暫時存放,用于土壤細菌和代謝物的檢測,另一份放入自封袋內,用于土壤理化性質測定。抽薹和未抽薹組各設置6次重復。
1.2.4 土壤理化指標測定 密封于自封袋中的土壤風干后過60目細篩,采用pH計測定pH值、TDS計測定鹽分、有機質采用重鉻酸鉀氧化-外加熱法、全氮采用凱氏定氮法、銨態氮采用氯化鉀浸提-靛酚藍比色法、硝態氮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計法、全磷采用酸溶-鉬銻抗比色法、有效磷采用鉬銻抗比色法、全鉀采用氫氧化鈉熔融-火焰光度法、有效鉀采用乙酸銨浸提-火焰光度法測定[20]。
1.2.5 土壤細菌群落DNA提取及測序 土壤DNA提取采用土壤總DNA提取試劑盒DNeasy PowerSoil Kit(QIAGEN,德國)提取。使用前端343F引物5'-TACGGRAGGCAGCAG-3'和后端798R引物5'-AGGGTATCTAATCCT-3'對16S rDNA基因的V3-V4區進行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擴增,每個樣品在30 μL體系中擴增,該反應第一輪體系包括15 μL 2×Gflex PCR 緩沖液,0.6 μL Tks Gflex DNA 聚合酶(1.25 U/μL),1 μL模板,5 pmol/μL正反引物各1 μL。在94℃進行5 min初始變性后,將目標區域在94℃進行30 s,56℃進行30 s,72℃進行20 s的26個循環下擴增,最終72℃下進行5 min。用1%瓊脂凝膠電泳驗證PCR結果,若陰性未出帶,則用AMPure XP試劑盒(BECKMAN COULTER,美國)進行磁珠純化,純化后稀釋至50 μg/μL作為PCR模板進行第二輪擴增,在與第一輪PCR相同條件下將DNA樣品擴增7個循環。取5 μL純化過的二輪產物進行1%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檢測是否有條帶和條帶是否單一,取1 μL純化過的二輪產物在Nanodrop進行濃度檢測。樣品質檢合格后則交由測序公司利用Illumina HiSeq PE250測序平臺進行16S rDNA擴增測序(歐易生物,上海)。
1.2.6 土壤代謝組提取及分析條件
1.2.6.1 土壤代謝物提取 將20 μL內標(L-2-氯-苯丙氨酸,0.06 mg/mL,甲醇配置)和1 mL甲醇-水(V∶V=1∶1)加入500 mg土壤中,樣品在-20℃放置2 min預冷后放入組織研磨機中研磨2 min。研磨樣品以7 700 r/min低溫離心10 min(4℃),冷凍干燥后溶于200 μL甲醇-水(V∶V=1∶1)復溶,溶解后的樣品在12 000 r/min低溫離心10 min(4℃),取150 μL上清液裝入玻璃衍生瓶中。將所有樣本的提取液等體積混合制備質控樣本。所有樣品和質控樣本經冷凍干燥后,加入80 μL的甲氧胺鹽酸鹽吡啶溶液(15 mg/mL),渦旋振蕩2 min后,在37℃振蕩培養箱中肟化反應90 min。所有樣品加入50 μL BSTFA(含1% TMCS)衍生化試劑、20 μL的正己烷、10 μL混合內標溶液(C8/C9/C10/C12/C14/C16,0.16 mg/mL,C18/C20/C22/C24,0.08 mg/mL,均為氯仿配置),混合樣品在70℃下反應60 min后進行氣象色譜-質譜(GC-MS)代謝組學分析,每個處理進行6個獨立生物學重復。
1.2.6.2 GC-MS分析條件 土壤代謝物采用安捷倫7890B氣相色譜系統和安捷倫5977A MSD系統耦合分析。色譜條件:采用DB-5MS毛細管柱(30 m×0.25 mm×0.25 μm)分離,載氣為高純氦氣,流速為1.0 mL/min。進樣口的溫度為260℃,進樣量1 μL。柱溫箱的初始溫度為60℃,保持0.5 min,然后以8℃/min的速度增加到210℃,再以15℃/min的速度增加到270℃,最后以20℃/min的速度增加到305℃,并保持5 min。質譜條件:MS四極子和離子源(電子沖擊)的溫度分別為150℃和230℃,碰撞能量為70 eV,采用全掃描模式(SCAN,m/z50-500)獲取大量數據。
1.2.6.3 質譜數據的定性和相對定量 GC-MS定性采用鹿明生物自主研發的LUG數據庫(Untargetdatabase of GC-MS from Lumingbio),該數據庫中包含2 543種能夠采用GC-MS檢測的代謝物,其質荷比(m/z)范圍為85-650。對樣本的所有峰值信號強度(峰值面積)進行篩選并分段歸一化(閾值:內標RSD<0.3),對歸一化數據進行去冗余和峰合并,得到最終代謝產物。
1.2.7 數據分析
1.2.7.1 細菌群落測序數據分析 原始測序序列為FASTQ格式,使用Trimmomatic軟件進行去雜質控,過濾reads尾部質量值20以下的堿基。去雜后的雙端序列使用FLASH軟件進行拼接,將成對reads拼接成1條序列,同時利用UCHIME檢測并去除序列中的嵌合體序列。采用Vsearch 軟件,將序列相似性大于或等于97%的歸為一個OTU單元,最終得到多個 OTU。使用 QIIME軟件包挑選出各個OTU的代表序列,并使用RDP classifier軟件將所有代表序列與Greengenes或者Silva(version123)數據庫進行比對注釋,并保留置信區間大于0.7的注釋結果。
Alpha多樣性分析采用QIIME和R包vegan 2.5-6 實現,主要進行了Chao1指數、Shannon指數、Simpson指數計算,主成分分析(PCA)采用https://cloud.oebiotech.cn/task/平臺運算繪圖,采用SPSS20.0軟件(SPSS Inc., Chicago, IL)對不同微生物類群豐度進行顯著性差異分析,采用方差分析(ANOVA)和最小顯著性差異(LSD)進行事后比較檢驗(顯著性水平P<0.05),柱狀圖在Origin2022中繪制。線性判別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effect size(LefSe)]采用https://www.omicstu dio.cn/tool/60平臺運算繪圖,將LDA值>3.5作為豐度顯著差異的判定值。
1.2.7.2 根際土壤代謝物數據分析 采用SPSS20.0軟件(SPSS Inc., Chicago, IL)對代謝物進行顯著性差異分析,采用方差分析(ANOVA)和最小顯著性差異(LSD)進行事后比較檢驗(顯著性水平P<0.05)。PCA、差異代謝物火山圖、組間差異熱圖及通路富集氣泡圖用https://www.metaboanalyst.ca/平臺分析繪制。
1.2.7.3 土壤性質、差異微生物及差異代謝組互作分析 采用冗余分析/典范應對分析(RDA/CCA)分析土壤性質、差異微生物、差異代謝物之間的兩兩關系。RDA/CCA分析采用https://www.omicshare.com/index.php平臺分析進行。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對篩選出的土壤元素、差異微生物與富集在關鍵通路上的差異代謝物進行關聯分析。
2 結果
2.1 根際土壤理化性質
硝態氮(P=0.040)含量在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顯著升高,而其他理化指標均在抽薹和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間無顯著差異(P>0.05)(表1)。

表1 抽薹與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的理化性質Table 1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rhizosphere soils of bolting and unbolting Angelica sinensis
2.2 根際土壤細菌群落結構
本試驗在抽薹和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共檢測到5 554個細菌OTUs。與根際土壤理化性質結果相似,所有 Alpha多樣性指數均在抽薹和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間無顯著差異(P>0.05)(表2)。如主成分分析(PCA)所示(圖1),其中PC1解釋了變量的60.1%,PC2解釋了變量的25.88%,可以看到,抽薹與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細菌群落不能沿橫縱坐標軸發生明顯分離。結果表明,抽薹和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細菌群落并沒有發生明顯的豐富度和均勻度變化,群落結構是相似的。

圖1 抽薹(BO)與未抽薹(UB)當歸根際土壤細菌群落主成分分析Fig.1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lots of the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the rhizosphere soils of bolting(BO)and unbolting(UB)A.sinensis

表2 抽薹與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細菌群落的阿爾法多樣性Table 2 The alpha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rhizosphere soil of bolting and unbolting A.sinensis
抽薹和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細菌群落在門水平和屬水平上的優勢菌群組成一致,分析表明,菌群相對豐度在組間無顯著差異(P> 0.05)(表3)。在相對豐度前15的細菌門中,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ota)、擬桿菌門(Bacteroidota)、芽單胞菌門(Gemmatimonadota)、厚壁菌門(Firmicutes)、黏球菌門(Myxococcota)的平均占比達97%以上,是當歸根際土壤中最主要的優勢菌門。當歸根際土壤中相對豐度前15的優勢細菌屬為鞘氨醇單胞菌屬(Sphingomonas)、鏈霉菌屬(Streptomyces)、假黃單胞菌屬(Pseudoxanthomonas)、原小單孢菌屬(Promicromonospora)、MND1、溶桿菌屬(Lysobacter)、Allorhizobium-Neorhizobium-Pararhizobium-Rhizobium屬、Muribaculaceae屬、Nocardioides屬、Ellin6067、大腸桿菌志賀菌屬(Escherichia-Shigella)、纖維弧菌屬(Cellvibrio)、假單胞菌屬(Pseudomonas)、Sphingopyxis、0319-7L14,占總相對豐度的27%以上(表3)。這些結果進一步說明,抽薹與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優勢菌群的結構是相似的。
線性判別分析(LefSe)結果(圖2)顯示,將LDA 值>3.5 定義為微生物在數量上差異顯著,這部分微生物叫作響應微生物(responder),代表這部分微生物數量對抽薹現象響應顯著。由圖2可知,有3個科和10個屬的非優勢菌群在抽薹和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存在明顯的差異。在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倫黑墨氏菌屬(Rheinheimera)的相對豐度顯著高于未抽薹當歸(P= 0.037);而珊瑚狀放線菌屬(Actinocorallia)(P= 0.025)、腸桿菌屬(Enterorhabdus)(P= 0.024)、Phaselicystis屬(P= 0.010)、柄桿菌屬(Caulobacter)(P= 0.010)、Agaricicola屬(P= 0.007)、Rubellimicrobium屬(P= 0.010)、纖毛菌屬(Leptothrix)(P= 0.025)、亞硝酸菌屬(Nitrosomonas)(P= 0.025)、不動桿菌屬(Acinetobacter)(P= 0.010)的相對豐度則顯著低于未抽薹當歸,其中,Agaricicola屬和亞硝酸菌屬在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幾乎或完全消失。
2.3 根際土壤代謝物變化
采用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方法(GC-MS)在所有土壤樣本中共檢測并鑒定到了包括有機酸、有機氧化合物、脂類、苯類、有機雜環化合物等301個代謝物。在這些化合物中,有機酸和有機氧化合物的數量最多,分別占代謝物總數的20.2%和20.2%,其次是脂類(14.9%)、苯類(8.9%)、有機雜環化合物(7.9%)(圖3-A)。PCA分析表明,抽薹當歸和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的代謝物存在明顯差異,并沿著縱坐標軸分離(圖3-B)。

圖3 抽薹(BO)與未抽薹(UB)當歸根際土壤代謝物類型(A)和主成分分析(B)Fig.3 Metabolite type distribution(A)and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lots(B)of the rhizosphere soils metabolites of bolting(BO)and unbolting(UB)A.sinensis
301種代謝物中,有66種的含量在組間差異顯著(P<0.05, VIP>1),抽薹當歸組中有52種代謝物顯著上調,14種代謝物顯著下調(圖4-A),上調的代謝產物主要屬于有機酸及其衍生物、苯類化合物,下調的代謝產物主要屬于脂質和類脂分子(圖4-B)。其中,上調最多的5種代謝物是N-甲基-L-丙氨酸(N-methy-L-alanine)、松三糖(melezitose)、氫化肉桂酸(hydrocinnamic acid)、L-半胱氨酸甘氨酸(L-cysteine-glycin)、N-氨基甲酰谷氨酸(N-carbamylglutamate);下調最明顯的是紅四氟呋喃糖(erythrotetrofuranose)、四糖酸(tetracosanoci acid)、丁內酰胺(butyrolactam)、莽草酸(shikimic acid)、甲基β-d-吡喃葡萄糖苷(methyl beta-dglucopyranoside)(圖4-C)。通路富集分析可用以闡明根際土壤代謝過程的具體變化,富集通路分析(圖4-D)表明,抽薹當歸組有13條通路在P<0.05水平上發生改變,其中7條在P<0.01水平上發生改變。這7條通路主要涉及氨基酸代謝、異種生物降解和代謝、脂質代謝,其中氨基酸代謝包括苯丙氨酸代謝(phenylalanine metabolism; ko00360)、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生物合成(phenylalanine,tyrosine and tryptophan biosynthesis; ko00400)、酪氨酸代謝(tyrosine metabolism; ko00350)、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謝(arginine and proline metabolism; ko00330)4條通路;異種生物降解和代謝包括氨基苯甲酸酯降解(aminobenzoate degradation ko00627)和苯乙烯降解(styrene degradation; ko00643)2條通路;脂質代謝包括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biosynthesis of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ko01040)通路。

圖4 抽薹(BO)vs未抽薹(UB)當歸根際土壤代謝物變化Fig.4 Changes of metabolites in the rhizosphere soils between bolting(BO)and unbolting(UB)A.sinensis
2.4 根際土壤理化性質、差異細菌屬、差異代謝物的相關性分析
為揭示土壤理化性質、差異細菌屬及差異代謝物之間的相關性,對三者進行兩兩RDA/CCA分析(冗余分析/典范應對分析)。首先進行除趨勢對應分析(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DCA),結果顯示4個軸中的特征值最大均小于3.0,故選擇線性RDA模型進行后續分析。在土壤理化指標與差異細菌屬的RDA模型中(圖5-A),RDA1和RDA2軸特征值的貢獻率分別為40.31%和25.68%,總貢獻率為65.99%。分析表明,10個土壤指標對抽薹與未抽薹當歸的差異細菌屬構成均無顯著影響(P>0.05),其中,硝態氮的P值為0.061,是所有指標的P值最小值,它與抽薹當歸差異細菌屬存在正相關趨勢,與未抽薹當歸存在負相關趨勢。

圖5 抽薹(BO)與未抽薹(UB)當歸根際土壤理化指標與差異細菌屬(A)、土壤理化性質與差異代謝物(B)、差異細菌屬與差異代謝物(C)的冗余分析Fig.5 RDA analysis of soil properties and different bacterial genus(A), soil properties and different metabolites(B),different bacterial genus and metabolites(C)between bolting(BO)and unbolting(UB)A.sinensis
在土壤理化指標與差異代謝物的RDA模型中(圖5-B),RDA1和RDA2軸特征值的貢獻率分別為56.70%和10.12%,總貢獻率為66.82%。結果表明,只有硝態氮(P=0.049)對抽薹與未抽薹當歸的差異代謝物構成有顯著影響,如圖所示,硝態氮與抽薹當歸差異代謝物含量正相關,與未抽薹當歸負相關。
在土壤差異細菌屬與差異代謝物的RDA模型中(圖5-C),RDA1和RDA2軸特征值的貢獻率分別為66.48%和9.83%,總貢獻率為76.31%。結果表明,Phaselicystis屬(P=0.007)、Rubellimicrobium屬(P=0.036)對抽薹與未抽薹當歸的差異代謝物構成有顯著影響,如圖所示,二者均與未抽薹當歸差異代謝物含量變化正相關,與抽薹當歸負相關。
為進一步揭示因當歸抽薹引起的7條主要代謝通路中的差異代謝物與硝態氮、Phaselicystis屬、Rubellimicrobium屬的關系,進行了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表4)表明,Phaselicystis屬與氨基苯甲酸酯降解、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謝通路中的差異代謝物普遍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性(P<0.05),Rubellimicrobium屬與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謝通路中的差異代謝物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性(P<0.05)。結合代謝物在各個通路上表達量的變化可以得知,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Phaselicystis屬、Rubellimicrobium屬相對豐度的下降與氨基苯甲酸酯降解、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謝通路上差異代謝物的上調有較大的關聯。而硝態氮含量則與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通路中的差異代謝物密切負相關。

表4 主要代謝通路中差異代謝物與Phaselicystis、Rubellimicrobium、硝態氮含量的相關性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ial metabolites in main metabolic pathways and Phaselicystis, Rubellimicrobium and nitrate nitrogen
3 討論
本實驗主要研究了抽薹與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性質、細菌群落和代謝物的變化。研究結果證明,抽薹與未抽薹當歸的根際土壤中硝態氮含量、非優勢細菌屬和代謝物存在顯著差異,且彼此間存在一定的聯系。這一發現對進一步理解當歸抽薹現象的發生尤為重要。
3.1 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硝態氮含量上升
本研究發現,硝態氮含量在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顯著增加,這一現象的發生有兩種可能。一方面,當歸在早期抽薹期間減少了對硝態氮的吸收,從而增加了根際土壤中硝態氮的含量,這可能與植物在特定生長時期的營養偏好有關[21]。另一方面,硝態氮含量升高能夠促進當歸早期抽薹的發生,這是因為氮素是植物開花和花序發育所必需的營養元素。有研究表明,在氮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植物成花率會隨著NO3-/NH4+的增大而升高[22]。硝態氮不僅是植物生長發育所必需的重要營養元素,也是重要的信號分子[23],例如在有關茶樹的研究中發現,一種抑制開花的基因miR156在NO3-含量增加后被抑制,從而起到促進開花的作用[24]。當歸早期抽薹與根際土壤硝態氮含量升高間的因果關系還需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明確。
3.2 根際土壤非優勢細菌屬相對豐度顯著變化
抽薹與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細菌群落結構和組成是相似的,其優勢細菌門和優勢細菌屬組成與前期研究結果基本一致[16]。可見,當歸根際土壤細菌群落并不會隨植物的生長周期發生顯著變化,菌群維持平衡狀態對植株保持健康生長可能具有重要意義。雖然當歸根際土壤細菌群落不會發生較大的變化,但一些非優勢菌屬卻在組間發生改變,目前已有研究證實非優勢菌屬在影響植物生長發育中發揮著作用[25]。雖然RDA分析中硝態氮含量對差異細菌屬相對豐度影響并不顯著,但其與抽薹和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差異細菌的相關性仍是所有土壤性質指標中最明顯的,這說明硝態氮仍是非優勢菌屬豐度變化中最值得考慮的因素。土壤的NH4+可以通過硝化細菌的硝化作用轉變為NO3-,進而參與植物的生長發育過程,而NO3-亦會被反硝化細菌還原為N2[26]。目前沒有證據證明在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豐度上升的Rheinheimera屬為硝化細菌,同時豐度下降的9個細菌屬中,只有Nitrosomonas屬被證明是反硝化細菌[27],而在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Nitrosomonas屬完全消失。因此,猜測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硝態氮含量的增加可能與Nitrosomonas屬的缺失有關。
3.3 根際土壤代謝物含量顯著變化
本研究表明,當歸抽薹可引起根際土壤代謝物的明顯變化。植物根際土壤中的代謝物來源于植物根系分泌、微生物代謝及植物、微生物和土壤有機質的分解[28],本研究發現,抽薹與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中的有機質含量及細菌群落多樣性和優勢菌群并未產生顯著差異,因此,根際土壤中的差異代謝物主要源于根系分泌物的可能性較大。Song等[29]通過對辣椒的研究也發現根際土壤代謝物的主要來源為根系分泌物。代謝物作為直接反應植物生理狀態的物質,直觀地反應在植物的表型特征上。研究表明,根系分泌物可引起土壤菌群組成及功能的變化[30],本研究中,當歸抽薹過程使氨基酸代謝、異種生物降解和代謝及脂質代謝的相關通路上發生代謝物質含量變化,這些代謝物通過根系分泌到土壤中后引起根際土壤非優勢菌群的變化,其中Phaselicystis屬和Rubellimicrobium屬與代謝物的變化密切相關(P<0.05),且主要與氨基苯甲酸酯降解、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謝通路中差異代謝物顯著負相關。據報道,Phaselicystis屬具有溶菌和非纖維素分解能力,還能產生多不飽和脂肪酸ω-6花生四烯酸[31],而Rubellimicrobium屬則具有降解大分子有機物的能力[32],但目前并不清楚Phaselicystis屬和Rubellimicrobium屬在當歸抽薹中是否發揮具體作用。盡管硝態氮含量與抽薹當歸差異代謝物間有顯著的關聯性(P<0.05),但與Phaselicystis屬和Rubellimicrobium屬不同,其主要與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通路上的差異代謝物顯著負相關。由此可見,雖然菌屬和營養元素都會與差異代謝物產生負相關性,但作用的代謝通路并不相同,其相關機制也必然不相同。
3.4 當歸抽薹與硝態氮、非優勢細菌和代謝物變化的關聯
當歸根際土壤NO3-含量上升與當歸早期抽薹現象存在聯系,但彼此間的因果關系仍需進一步研究驗證。當歸抽薹后引起體內代謝水平變化,并以根際分泌物的形式進入根際土壤,進而導致根際土壤非優勢菌群的豐度變化,其中Phaselicystis屬和Rubellimicrobium屬的豐度下降與氨基苯甲酸酯降解、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謝通路中差異代謝物上調的聯系最為緊密,但并無證據表明其在當歸早期抽薹中發揮可能的作用。而根際土壤中NO3-含量上升與Nitrosomonas屬的變化可能存在聯系,但仍需進一步研究論證(圖6)。

圖6 當歸早期抽薹對根際土壤微環境的影響Fig.6 Effects of premature bolting on the rhizosphere soil microenvironment of A.sinensis
4 結論
本文對抽薹與未抽薹當歸根際土壤進行了土壤理化性質、細菌群落和代謝物變化研究。二者在根際土壤硝態氮含量、代謝物含量和非優勢菌群的相對豐度間均存在顯著差異。本研究從當歸早期抽薹引起的根際土壤微環境變化角度為切入點,嘗試為解決當歸早期抽薹問題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