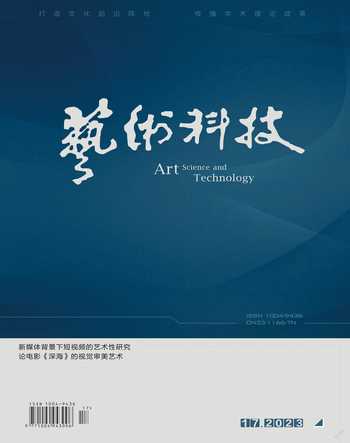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適度設計研究
周知行 楊衛華
摘要:當今,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是社會熱點話題。實現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的活化設計是設計師們展示能力的絕好機會,但是部分設計師為了聚焦城市的繁榮興盛、表達個性十足的設計審美等,某些設計逐漸成了為了設計而設計。比如,運河沿線地區建筑拆舊仿舊,全無古意,這樣的運河文化遺產設計脆弱且無力,失去了其如運河般源遠流長的生命力。近年來,常州對運河文化遺產的活化設計就像抽木條游戲一般,抽掉原本堅實的根基,卻往頂部增加負重,某種平衡一步步被打破,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岌岌可危。因此,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需要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設計師應該增強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注重歷史文化內涵的挖掘和傳承。同時,設計應該在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加強創新,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審美相結合的同時適度設計。文章對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的適度設計進行研究。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在適度的前提下實現文化遺產的活化設計,讓它們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支撐。
關鍵詞:適度設計;常州;運河文化;文化遺產
中圖分類號:K878.4;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17-0-03
1 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的“是”與“非”
2014年,大運河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17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做出重要批示,“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周邊城市文化遺產豐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高,但是也存在文化遺產的利用質量不高、生態問題亟須解決、宣傳力度不到位等突出問題。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指出,以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為引領,統籌大運河沿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探索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
江南地區素有“水鄉澤國”之名,也是大運河的起點。大運河常州城區段,由連江橋而起,止于東方大橋,全長接近23千米,是世界遺產大運河27段河道之一。2013年常州市政府印發了《常州市大運河遺產保護辦法》,由此可見,常州市政府很早就開始重視運河文化遺產保護,但也由于政府對文化遺產傳承與更新活用力度過大,因此容易出現過度設計。
1.1 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的“過度作為”
20世紀的常州可以見到小橋流水的南方景色,但隨著政府大手一揮,拆建并行,這些景色也“付之一炬”。拆時居民無計可施,建時有識者扼腕嘆息,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就像靜靜流淌的運河一樣無力。
“運河慢村”安基村地處常州市鐘樓區,坐落于運河河畔。當地有一座廟,可以追溯到數百年之前,名為安基,村莊也因此得名。村中有一棵巨大的銀杏樹,樹齡達300年之久,側面佐證了村莊的歷史悠久。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因此安基村自然成為運河文化遺產活化的先鋒軍。但適度設計理念的不成熟,使得當地建筑更新力度過大。花市燈如晝,運河水潺潺,游人密如織,這是當地規劃的發展愿景。然而過度設計之后,燈光污染、建筑風格雜亂。
1.2 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的“不作為”
運河旁的小村莊魏村地處長江之濱、德勝河口,村莊由來上溯宋朝。時間飛逝,城市更新,這個偏僻的老村莊被人們漸漸遺忘。也正是由于這種遺忘,因此老建筑雖然看不到當年的繁華場景,但是建筑深巷原貌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下來,留存了老村莊原有的人文脈絡。魏村有條老街,街道與村莊依運河而建,花崗巖鋪滿整條街道。每在村莊看到一處老建筑,都會發現令人驚嘆的歷史街萃。
老村莊從宋代延續到當今,是筆者在常州新北區域內見到的建筑受人為干擾程度最小、保存最完整的古村之一。村莊街道上的建筑多為晚清至民國時期建造,少有更古老的建筑,建筑形式多為“上宅下鋪”和“前店后坊”。村莊建筑結構多以兩層樓房和單層平房為主,大門是一種裝飾性的半矮門,詢問當地老人得知這是當時常州的建筑特色,極富江南小鎮的古典韻味。目前,魏村還是保存比較完整的古村落,但是依照現有狀況,政府如果不作為或者仿照青果巷翻新手法,村莊就難免淪為商業的附庸。
2 適度設計與過度設計
2.1 適度設計與過度設計的定義
解釋適度設計時要先清楚認識“度”。華夏文明上下5000年,對“度”的解釋不勝枚舉。《漢書·律歷志(上)》[1]:“度者,分、寸、尺、丈、引也。”其意思是丈量某些物體在空間中的長寬。度也有抽象意義上的概念,《論語》中提及“中庸之道”,這種理念與本文所倡導的適度設計有異曲同工之妙。
適度設計以“適”字為中心。“適”,有切合、復合之意。適度設計相對于過度設計而言,是在有限的空間環境內,用合適的材料來滿足受眾群體的需求,同時不會鋪張浪費或影響項目所在地的生態環境。適度設計是一種整體性的設計,而不是就某一方面進行深入設計,不會顧此失彼。適度設計是現在設計的大趨勢,如今人們提倡的“微改造設計理論”[2]“針灸改造城市理論”[3]等或多或少和適度設計有所聯系。
與“中庸之道”相反的便是過度設計。《呂氏春秋·博志》[4]:“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簡單來說,其意思就是物極必反。一件事情做得過火反而不會有很好的效果。這也體現了我國古代先人的辯證思想,如果想要項目取得最大效益,就不要過分投入,重點在于掌握效率曲線的制高點。“過猶不及”也是一個類似的成語,意思是如果一件事情做得比較過分,就不如最初沒有做的狀態,因為這樣不會造成某些方面的浪費。例如,在有限的空間內使用繁雜、高價的材料,使之造價過于高昂;或者設計師為了提高聲望,故意采用不合適的手法吸引大眾注意,博得大眾眼球,導致人力、物力的浪費。
2.2 適度設計現有研究的思考
部分學者把適度設計作為一種標榜來反對過度設計或者快設計。如任志芳在《生態構筑在于“慢”設計——多維度重新審視設計的生態文化內涵》[5]一文中提出過度設計是發展中國家設計的一種過渡現象,設計還是應該朝著適度設計和慢設計方向發展。筆者十分贊同這種觀點,由于我國設計發展的時間較短,因此必然經歷各種階段,逐漸進步。同時,部分學者認為適度設計應該作為現代設計的基本原則。如李賢在《城市名人文化景區的“過度設計與適度設計”探究》[6]一文中提出應該以“適度”為標準來審視項目進行的各個階段,從項目的實際出發。另外,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適度設計是一個設計師最基本的素養。如帥湘在《適度設計》[7]一文中指出,適度設計是設計師責任、能力、素養的體現。
基于古代先賢的各種理論及現代學者的研究,可知適度設計無論是在實踐還是理論方面,都有足夠的支撐。
3 適度設計——活化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加之受西方文化影響,各種設計手法層出不窮,如何設計及設計到何種程度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中國的土地似乎成了諸多設計大師的試驗地,各式各樣的風格、各種各樣的流派涌現在華夏大地上。在世界范圍內,設計永遠在不斷循環往復,由表現人本身到向往神、表現神,再到強調人、表現人;由功能到裝飾,再到功能。歐洲的文藝復興以及歐美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都是設計回環的實證。
3.1 常州段大運河物質文化遺產的適度設計
運河文化遺產的適度設計并不是簡單廉價的設計,是綜合考慮遺產活化保護、資金投入與社會效益的系統性設計。活化過程中的適度設計有利于讓參觀人員更容易接受設計者所傳達的理念,在運河文化環境中刺激參觀人員的感受神經,引起游客與空間文化的共鳴。例如,常州青果巷的建筑是典型的物質性運河文化遺產。經過實際調研可知,原有的建筑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被拆除,少有的幾棟也被圍欄擋住,至今未見采取措施進行修繕。有的建筑仿造原有建筑特色,經過20世紀90年代拆除之后再次拆除新建。2021年12月17日,筆者再次前去調研,部分深巷還在施工,圍擋幕布上“明磚清瓦”幾個大字令人寒心。所以,物質文化遺產活化設計一定要適度,過度設計、設計力度不足乃至不作為都不能引起游客共鳴,甚至還會讓游客心生違和感。
物質性運河文化遺產適度設計可以協調“人”與“物”之間的平衡,達到最佳保護、活化的目的。不以適度性為原則的運河文化遺產活化設計極易走偏,變成過度設計,每一次建筑動工、每一片瓦片落地、每一塊磚塊開裂都將導致文化的消亡。過度設計不僅是對游客、居民、環境的不負責,更是對常州歷史人文、文化脈絡的不負責。
3.2 常州段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適度設計
運河文化遺產活化設計時的“適度性”不能僅局限于物質文化遺產的適度設計,還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適度設計,倡導在活化設計中將過度物質性的設計轉向非物質性的設計。
非物質性的運河文化遺產活化設計,歸根結底應以展示設計為主線,以常州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為輔助,結合高新數字技術,使遺產活化設計更加完善,更適應時代的發展。非物質性的運河文化遺產活化設計是在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下,了解游客想要的文化傳承方式與文化傳承方向,于無形中使人們樹立保護運河文化遺產的意識,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
調研發現,常州本地人對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的認知和了解不深。因此,常州市政府應加大保護運河文化遺產的宣傳力度,而不是單方面地自建,陷入參與人員熟悉、普通民眾不知的困境中。就青果巷來說,拆除改建反反復復之后才有了現在的狀態,但是知者甚少,人力、財力的投入沒有獲得相應的社會效益,隨之而來的就是更多的投入及更低的社會效益。常州亟須走出這種循環往復的困境。
3.3 活化常州大運河文化遺產的適度設計思辨
運河文化遺產的活化設計與保護在本質上不同于現代或者后現代主義的建筑與公共藝術設計。從建筑設計來說,考察環境、了解文化、設計草案、建筑施工等一系列操作并不會對項目所在地的文化產生根本性的負面影響,但是運河文化遺產不同,其非常脆弱、無力。現在常州對運河文化遺產的活化設計就像抽木條游戲一般,抽掉原本堅實的根基,卻往頂部增加負重,一步步打破平衡,最終結果可想而知。所以筆者認為,運河文化遺產活化設計最科學的原則就是適度設計,不是往上增加負重,而是從底部開始,一點點打牢根基,只有這樣才會有更高的上限以供探索。
4 結語
如今,很多運河文化遺產活化設計和民眾生活沒有交集,很難產生共鳴,只是設計樣式的強力復制,雖然場地內設計感十足,但是已經看不出場地的原貌,這是一種不尊重原址人文風貌的設計泛濫。隨著一代代人逐漸老去,以前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便被深深地埋在地下,不會再有人記得。雖然社會發展的某些階段難以跨越,但是可以盡自身所能度過某個階段,而不是一直被囿于其中。希望當代設計師能真切關注人的需求,創造出反映人們的真實所感所想的設計作品。
參考文獻:
[1] 丘光明.度量衡的經典著作《漢書·律歷志》[J].品牌與標準化,2020(1):62-65.
[2] 蔡云楠,楊宵節,李冬凌.城市老舊小區“微改造”的內容與對策研究[J].城市發展研究,2017,24(4):29-34.
[3] 鄭鑫,徐秋霞,洪世銘.基于“城市針灸”理論的騎樓街歷史文化街區傳統業態保護探索:以石獅八卦街為例[C]//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成都市人民政府.面向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治理:2021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
(09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北京:中國建筑出版社,2021:10.
[4] 俞林波.中國古代《呂氏春秋》出版簡史[J].天中學刊,2021,36(4):135-140.
[5] 任志芳.生態構筑在于“慢”設計:多維度重新審視設計的生態文化內涵[J].設計,2017(3):72-73.
[6] 李賢.當代城市名人文化景區的“野趣”設計思考[J].文學界(理論版),2012(9):408-409.
[7] 帥湘.適度設計[J].中外建筑,2020(1):1.
作者簡介:周知行(1996—),男,江蘇常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公共藝術設計。
楊衛華(1973—),女,江蘇徐州人,碩士,教授,系本文通訊作者,研究方向:公共藝術、美術史、設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