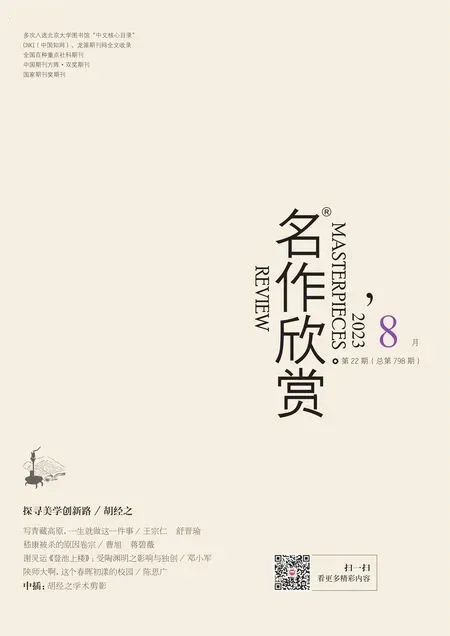紀念王富仁先生:從生命體驗出發
四川|李怡 王藝臻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于2022 年12 月隆重推出了由劉勇、李春雨兩位教授合作的專著——《思想型的作家與思想型的學者——王富仁和他的魯迅研究》一書,這是國內第一本系統闡述并研究王富仁先生學術貢獻的著作。這本書的出版引人注目,同時也引發了諸多思考,如在國內學術不斷向前發展的當今為什么要重提并紀念王富仁先生?這本書出版的深層又包含著怎樣的意義?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不斷回溯與思索,這里我們以《思想型的作家與思想型的學者——王富仁和他的魯迅研究》一書的出版為引子,就王富仁先生的思想與治學展開深入探討。在訪談中請李怡教授闡述今天紀念王富仁先生的意義。
王藝臻(以下簡稱“王”):圍繞《思想型的作家與思想型的學者——王富仁和他的魯迅研究》一書,關于如何更好地理解王富仁老師的學術與思想路徑,我有幾個問題想向您請教。
李怡(以下簡稱“李”):好的。這本書的出版非常有意義,我們也可以借此再一次回顧王富仁老師不斷前進的學術事業。
王:孫郁老師認為王富仁老師是“魯迅思想的護法者”,姜飛老師則采用了“戰士”一詞對王老師的個人形象進行了抽象塑造。王老師的“護法者”形象無須多言,熟悉王老師論述的讀者應該都深有體會。關于“戰士”形象,當然對王老師一生所堅持的研究對象魯迅而言,這樣的評價已經是深入人心了,這不僅是評價帶來的定型,而且是魯迅本人作品與相關評價的交相呼應。而以王老師的著述與思考為關鍵,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回溯、理解與學習王老師身上的“戰士”精神與意志?
李: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我們在對王富仁老師的理解上如何體會到其中的“戰士”精神呢?“戰士”形象意味著什么?這些我覺得對我們今天思考為什么要重新討論和紀念王老師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我看來,所謂的“戰士”就是說學者不是為了做學術而做學術,不是在書齋里面進行一種知識的延續和雕刻,而是用相關知識直接介入現實的社會生活中,讓知識成為社會思想的一個有力組成部分。因而當一些觀點認為王老師作為“戰士”的形象是在捍衛魯迅或者捍衛其他什么的時候,我覺得這個還不盡準確,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所謂“戰士”就是不把學問當作知識本身,而是把學問當作為了人生的一個有力武器,這就是“戰士”。在今天,隨著學院派文化的日益強化和成熟,越來越多的學者不自覺地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帶到了一種自我封閉的狀態,這就使得相關的學術活動越來越脫離了我們豐富的人生,自然也脫離了如魯迅那一代的現代文學家們所追求的方式。王老師以自己的學術研究路徑重新提醒我們這樣一種“學術戰士”風格的重要意義,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今天要重新紀念王老師的一個意義所在。
王:目前學者們基本上統一形成了對王富仁老師評價魯迅為“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的認可,這一句評價也成為開啟魯迅研究新境界的一股春風。而這也提醒我們作為“執鏡人”的諸如王老師在內的一批學者同樣至關重要,畢竟是其決定了“鏡子”以何種角度反射出何樣的光彩,從而激起社會生活中別樣的漣漪。從政治魯迅到思想魯迅再到當下對政治魯迅的再度重提,視野的開闊早遠遠超出了前輩學者的觀照。作為開啟轉折的關鍵學者,在您看來王老師的治學之要在何處?
李:王老師治學的關鍵之處也與你所談到的“戰士”品格相關。王老師的治學從來不是追隨某一種潮流,也不是對所謂某一時代主流的反主流,他所堅持不懈的正是對學術的不斷創新,從而使他每個思想的提出都具有強烈的針對性。關于王老師評價魯迅的“鏡子”之語,其實我的解讀略有不同。在我看來,理解的重點不在于“鏡子”一詞,這樣的說法更多是為了適應當時的文學評論語境,是技術性的手段,今天我們對“鏡子”這個詞的緊抓表明還是沒有跳出反映論的思維,這就偏離了對王老師學術活動真正意義的理解。王老師的評價重點在于他借此想要告訴我們魯迅小說創作中的思想內涵不是純粹過去的政治活動能夠完全概括的,從中他所觀察到的是魯迅關于中國社會、中國人生命的思考,這樣的治學方式所表現出的核心正在于提出了一種具有自己獨立思考意義的理解模式。
王:王富仁老師的博士畢業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吸收并超越了前一輩研究者,開啟了新的研究視野的同時,仍需要我們注意其中從創作主體獨特的生命體驗出發而向研究對象靠攏的路徑乃是對前一輩學者的批判性繼承,這樣的學術傳統建構不知道您如何評價?
李:我曾提出王老師的學術研究并沒有像部分人所想象的那樣完全否定包括陳涌先生在內的前人思考,這個話有著特殊的所指,我指的是陳涌先生也好,王老師也好,他們都是看中了魯迅研究當中與社會現實人生相連接的那一部分,他們不是在做抽象的學問,而是緊抓對現實社會人生的關注,從這樣一個意義上來理解王老師的學術承襲也就更為順暢,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王老師的思想與陳涌先生的思想畫上等號。在共同關注社會現實人生這一點上,他們之間是有前后承接關系的,而這種師承關系又與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許多試圖脫離開這種連接來進行單純的語言修辭研究的學術有所區別,我所指的正是這樣一層含義。而在承接過程中,王老師自身所展現的突破性和獨創性自然是無須多言了。所以說要談王老師思想與前輩學者的相通和相異之處,我們需要明確一個前提,那就是所提出的問題主要強調了什么,是從什么意義上切入。
王:您曾經撰文論述過“痛感”對魯迅現代思想的激活,魯迅敏感地捕捉著周遭環境、人事帶來的精神苦痛,并將這些內化后通過文字來希圖療救國民。不過在閱讀過程中,我注意到王老師的部分文字里所傳達出的更多是平淡,他接受了來自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磨礪,內化為了靠近魯迅精神的自我生命體驗,但是這樣的沖淡心態好像又與進入研究對象的路徑產生了絲絲裂隙?您如何看待這樣的反差表征?
李:你認為王老師的部分研究文字中包含著沖淡,我覺得這個感覺不一定準確,你應該再去體會一下王老師的文字,里面最大的特點我覺得從來不是沖淡,而是一種思想的邏輯,而且這個邏輯是飽含激情的,是有力量的,這樣的嚴密邏輯之下的激情才應該為大家所重視和感受。最早一篇評論王老師的文章由聊城大學的宋益喬老師所寫,他于1986年在《文學評論》第6 期上發表了《思想與激情——談王富仁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文,其中主標題所總結的思想與激情兩個關鍵詞就用得很好。王老師思想性的特色就在于既邏輯嚴密,又飽含著作為研究者的激情。所以仔細體會王老師的文字,我覺得沖淡的部分就顯得尤為次要。不用講現代文學,就是在古典文學領域,他發表在《名作欣賞》上后又被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古老的回聲》一書,談論的核心是古典詩歌的欣賞與闡釋,這樣的文本是如何誕生的?表面看好像很平靜,其實王老師提到過,是有一天中午午休起來后忽然聽到隔壁或北師大校園里什么地方悠悠傳來拉胡琴的聲音,這樣的聲音立刻讓他從心底感受到了來自人生的悲涼,而又因為這樣一個傳統樂器,他覺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中國古典詩詞所營造的境界當中,于是在這樣的機緣巧合之下他開始嘗試重新解讀中國古典詩歌,因而這樣一位能從悲涼的撫琴聲中激活思考的學者,理解他的關鍵絕對不是沖淡。當然這里也存在著一個客觀現實,那就是你與王老師已經是隔了一代的人,從中也隔著截然不同的人生體驗,那么如何更好地進行跨越代際的溝通和理解,這也再次強化了今天我們重新提出紀念王老師的必要意義。
王:思想,作為烙刻在王富仁老師身上的關鍵詞,為學術界帶來了新的風氣。雖然王老師的一些文字不免帶有特定時代的印記,但其中的堅韌思索卻從未過時。作為將治學與生命體驗融為一體的學者,其實王老師對文化發展的長期關注就顯得不足為奇了。從多篇論文對文化生態各方面的論述再到提出“新國學”研究,王老師研究思路的前瞻性不言自明。而其關于新國學體系的構建與當下所倡導的文化自信以及國學復興的事實都緊密勾連、共通同調,甚至部分內容實屬當下的文化政策也無法全然囊括,但是在“新國學”研究的提倡過程中,思考的高瞻遠矚與實際的發展并未能走向一致,因而使得“新國學”研究的建設暫時陷入困難,在您看來,這樣的不同步意味著什么?有哪些需要謹慎的地方?
李:你發現王老師“新國學”的倡導和當下社會現實的某些發展并不完全一致這個情況,我覺得這個感受是有價值的,同樣正是這種不完全同步的表現恰恰也體現出王老師獨立思考的意義。王老師站在一個更為深刻的角度試圖捍衛我們現代文化的理想,他為什么提出“新國學”?其實重心不在國學,而在于“新”。那么何為“新”?就是強調現代文化和現代思想已經構成了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當屬國學。在當下的國學熱中,國學往往被非常褊狹地理解為一些傳統文化中的現象,而把現代文化、現代思想直接排除了出去,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其實倡導國學也好,復興傳統文化也好,最終旨歸是為了現代人的發展,這樣的努力不是為了回到古代,而是為了解決現代人自己的問題,所以說任何國學的倡導必須具備強烈的當下性。而今天某些弘揚傳統文化的趨勢恰恰是忽略了當下,所以王老師提出的“新國學”主要側重于“新”字,其實就是要重新給我們確立現代思想、現代文化在整個中國文化傳統當中的重要地位。這就與一些褊狹的國學倡導全然不同了,也突出體現了王老師思考的價值。正是因為今天國學的倡導與傳統文化復興的建設還有很多亟待改進和完善的地方,所以王老師的思想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和深刻理解。
王:在王老師的文化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集中可見其對知識分子身份的堅守,以及對知識分子品格的發揚,其中明顯可以感受到王老師立于旁觀的角度進行著審視、社會觀察與分析,同時比起對知識分子身份的追索,王老師更是以知識分子的立場規范自身的行動,展現出樸素的精神追求。在王老師身上,更可以看到中國傳統中“士”的精神傳承,不知道您是否同意這樣的看法?
李:旁觀和知識分子“士”的傳統的表述我只能同意一半。王老師的身上顯然有傳統知識分子“士”的精神,我覺得這也是中國文化里面最為寶貴的精神。一個民族只要一直存續,那么它的發展無論經過了多少年,其間遭遇了什么,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東西毫無疑問都會代代相傳。但是,這個“士”的精神我覺得恰恰不是一種簡單的旁觀,你的表述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士”怎么是旁觀?“士”是擔當,是主動的介入,如果沒有主動的擔當和介入,沒有像杜甫等一般民胞物與的精神,沒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那就談不上“士”的精神。所以“士”的精神恰恰是不旁觀,擁有主動介入的精神。你忽略了王老師思考背后的堅守和實踐。
王:在王老師的研究生涯中,明顯可以看見他對于新方法使用的審慎。以其專長的魯迅研究而言,文字中所傳達的更多的不是方法論,而是堅持以研究者的自主意識強調個體生命的真實體驗來達到對研究對象的關懷與理解,并通過這樣樸素的路徑通往對研究者透徹認識的彼岸。但是在王老師發表的多篇古詩詞賞析的文章中,新方法的進入為理解注入了不斷闡釋的活力,當然背后包含有一些老師的個人選擇,但是其中對于方法的使用不僅締結了舊詩新解的碩果,同樣成為王老師研究領域中新的閃耀之處。那么從整體概觀,王老師研究經歷所呈現的差異性以及如此研究的對照關系,您是如何理解的?
李:王老師對新的學術研究方法的使用,在我看來與之前的研究并沒有什么矛盾,因為他對“新”和“舊”的理解有著與一般人的根本性不同。通常,特別是今天的一些研究生看來,“新”好像就是從外邊兒引入新的方法,這樣的方法是我們本土的學術研究未曾特別指出過的。因為引入了這個新方法,所以我們眼前看到的世界跟過去產生了差異,大家就能從中不斷發現新問題,產生新的思考。其實根本上來看并不是這樣,真正的“新”應該落腳于自我感受的不同,是從自己的真實感受當中生發的一些獨特發現,這從根本上追溯其實來自于人生洞見的更新,而不是簡單地對一些新方法的運用。其實王老師對古典詩歌的解釋雖然常有評論者以新批評的方法作為說明,但也并非完全是西方意義上的新批評,只需仔細閱讀就能感受到其中與英美新批評的很大不同。王老師對古典詩歌的再次闡釋,其中所包孕的獨特感受主要還是來自于人生體驗。就如前面所提到的,王老師在一天的午睡之后被傳來的悲涼胡琴聲所打動,所以他產生了闡釋相關詩歌的研究沖動,這背后最為關鍵的是那一瞬間王老師對人生滄桑的深刻感受被激活,而不是簡單地認為他閱讀了解了英美新批評的這些理論著作后就“拿來主義”式地開始重新闡釋中國古典詩歌,這樣的兩個路徑有著根本性的不同。所以說對于一個真正的學者而言,對于一個有自己獨立思想、獨立觀察的學者而言,他的“新”和“舊”都屬于他自己,“舊”是一種堅守,“新”是不斷翻涌的關于人生的深刻洞見,不存在把別處的“新”拿來改善自己的“舊”的問題。
王:王富仁老師在電影、電視藝術發展的早期就有相關論述出現,雖然不多,但讀來仍舊令人欣喜。部分學者將這些成果視為王老師研究的一次小小轉向,不過結合老師對曹禺的關注以及對話劇藝術的熱愛,這樣的小范圍跨界研究的轉向似乎又成為王老師研究進程中順理成章的結果,不知道您是怎樣評價王老師這一部分研究的突破的?
李:其實我覺得這些廣泛的、向外擴展的研究都是王老師自己思想邏輯推進的結果。就像魯迅一樣,魯迅一生中所謂多次轉向轉折,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后來的研究者加上去的,更多的時候其實他保持了自己思想的穩定性,那么作為魯迅研究者的王老師,我覺得也是這樣。至于你說研究一些電影、戲劇而出現小小的轉向,以我對王老師的密切觀察而言,這種轉向更大程度上是評論家們的誤讀。其實王老師的思想一直在向四面八方擴展,同時也在不斷地回應時代所提出的問題,他所研究的任何一個領域都是他思想自我磅礴運動的結果。在我看來,他的思想的內在的邏輯性和統一性遠遠大于隨波逐流的變化和發展。
王:了解王富仁老師的學術推進之路后,還可以明顯感受到研究者通過相關學術活動所獲得的滋養,從文學啟蒙再到文化啟蒙,從魯迅的文本再到對社會思想的撫觸,王老師將他的觀察和體驗融合,從基底處更新著社會思想的變化發展,最后則通過教育的手段不斷向外傳播,這樣的發展走向您在研究與教育事業中也有堅定的傳承與貫徹。當一位文學研究者進入教育領域,尤其是中小學教育這一板塊,以王老師與您的實際參與經驗為參考,其中作為文學研究者最為突出的優勢應當落在何處?
李:我認為王老師走進教育事業與他的人生經歷息息相關。在進入研究生學習階段前,他就長時間從事著中學語文的基礎教育工作,這個過程當中便凝結了他很深刻的人生體驗。這就像我們每個人都是從中學階段走過來,所從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又與基礎教育保持了密切關聯,所以我們的一生一方面在不斷地往前發展,另一方面則是要不斷地回顧過去。這樣的回顧也正在向未來的發展不斷提供一種力量和思想上的啟迪。以我自己的感受為參照,我非常能夠理解王老師。與其說他介入中學語文教育是所謂思想啟蒙向教育領域的擴展,還不如說他自始至終就沒有離開過教育本身,而在這一點上,教育本身其實也是啟蒙文化的應有之義。當關注王老師在教育領域的獨特成果時,我認為應該將這些成果放到王老師整個思想構成的結構中來觀照。至于他獨特的優勢是什么?那就在于他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與真實的人生體驗更多地結合在了一起,而不是從一種抽象的、已有的教育理論中推導教育的進程。其中文學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王老師的教育理念包含著他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對于生命、對于人性、對于人的自我發展的一系列獨特的見解,是真正以人為本的教育思索,而不是為了完成某種抽象的教育原則、實踐某種別人的教育理論而總結提出的一些干枯的結論,這就是王老師教育思想的真正活力所在。
最后我還要補充一句,那就是今天我們重新提出如何紀念王富仁老師的問題,起因是北京師范大學的劉勇、李春雨教授合著出版了《思想型的作家與思想型的學者——王富仁和他的魯迅研究》一書,這是目前國內第一本紀念王老師、研究王老師的著作,我覺得它的出版恰逢其時。在我看來,王富仁先生這一代人基本上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但是他們所留下的豐富精神遺產還沒有完全被更年輕的一代所理解、所接受,在更年輕的一代青年人思考中國現實、思考自己人生使命的時候,還應該進一步從王富仁先生他們這一代人中不斷汲取思想的力量,汲取前進的勇氣,這就是我們今天來讀這本著作、來重新紀念王富仁先生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