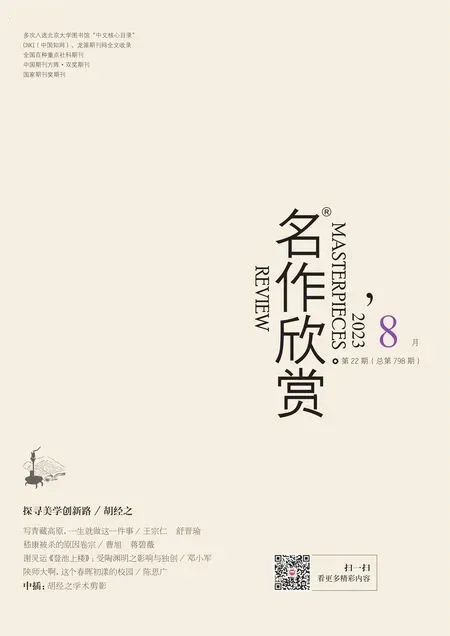思想如何進入文學
——王富仁作為“思想型學者”的幾個側面
北京|李春雨
大多數人在閱讀王富仁著述的時候,往往都會有這樣一個感覺:無論他的長篇系列文章還是短篇隨筆,讀起來都并不輕松。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富仁在字里行間傾注的那種沉重的、痛苦的,甚至有些壓得人透不過氣的思考。思想是王富仁研究的起點,也是歸宿,思想不僅是王富仁研究的結論,更是過程。王富仁最有價值的地方不是告訴我們一個東西“是什么”,而是深入討論這個東西“為什么”如此。始終以思想的方式進入文學、觀照文學,是王富仁學術研究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征。
以思想的方式進入文學,以文學的世界反觀現實,從一開始就是王富仁研究的重要特點。縱觀王富仁的學術軌跡,他在不同階段關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但不變的是他始終將目光投向當下的生活,投向對當代國人精神文化的關注,這也是王富仁學術研究能夠不斷煥發生機的主要原因。
20 世紀80 年代常常被稱為第二個“五四”,中外文化的碰撞、啟蒙思想的復蘇、“人的價值”的重申,一時成為那一時代的重要關鍵詞。在這種思潮背景下,怎么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怎么對待外來文化,怎么調整自己的文化心態,成為當時很多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王富仁連續撰寫了“魯迅與中外文化論綱”三篇系列文章:《對古老文化傳統的價值重估》《對西方文化的主動拿來》《從“興業”到“立人”》,這三篇文章加上收入《靈魂的掙扎》一書的《兩個平衡、三類心態,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文化不斷運演的動態過程》一文,都是對這些問題的回應。進入世界文化體系之后,近現代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系是什么?在這個關系中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如何借鑒西方文化,怎么應對慕外崇新的心態?……王富仁在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展開的脈絡中傾注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20 世紀90 年代,中國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對思想文化界所產生的巨大沖擊,使王富仁開始關注當前中國社會文化的危機。在《文化危機與精神生產過剩》一文中,王富仁從整個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冷靜審視了當代文化面臨的危機,并認為如同經濟發展一樣,文化也有其復蘇、發展、繁榮、蕭條等不同的演進階段,不同階段也有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發揮作用,而知識分子真正能做到的,并不是維持文化的持續繁榮,任何時代,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長盛不衰,懷揣追求永恒的文化繁榮這一想法,無異于尋覓一個精神上的“烏托邦”,那么,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追求應該如何構建?王富仁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追求應該建立在自己全部人生體驗中最強烈、最難舍棄的社會愿景和精神訴求上,即使條件再艱困,環境再惡劣,也要咬緊牙關挺住并堅持下去,努力采用一切人類歷史文化成果來充實、豐富和發展它(王富仁:《文化危機與精神生產過剩》,《文學世界》1993 年第6 期、1994 年第1 期)。
王富仁也的確用這樣的標準要求自己,無論面對何種社會環境和文化局面,他始終保有一種可貴的清醒,在復雜的文化幻象中抽絲剝繭,并提供一種深厚的、富有創見的思考。步入新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界曾有人提出“21 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王富仁認為這樣的說法具有“文化沙文主義”的性質,即過分宣揚中國文化的優長。他認為,21 世紀并非中國文化的世紀,任何一個世紀所產生的優秀的文化成果和精神遺產都是全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各個國家、民族共同創建的,因此并不存在誰是世界老大的問題。面對21 世紀世界范圍內多元豐富的文化樣態,王富仁開始思考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系,這一思考集中體現在《影響21 世紀中國文化的幾個現實因素》一文中。王富仁在文中從世界文化格局的嬗變中展望了中國文化的未來,并提出了自己的預想,他所關注的研究生制度、中國社會的社會化、宗教意識、影視文化的發展以及獨子文化、多余人文化這五個影響21 世紀中國文化的現實因素,鮮明地體現著他對于現實問題的獨特思考。
從我跟隨王富仁老師學習開始,到王老師去世,前后有十七八年的時間,至今,王老師留在我腦海中的印象都是很深的,而且一直非常鮮活。王老師作為思想型學者,他的這個“思想型”的特點體現在哪里?下面我想談一些我作為學生的觀察和理解,有些和別人看到的不太一樣。
第一是王富仁的講話。除了正式講課和做報告以外,王老師大部分時候都是比較沉默的,很少夸夸其談,講話都比較平靜,但是在我們學生的面前就不是這樣了。作為學生,有的時候,我們在學校,有的時候到他家,整個一天基本都是聽王老師講,甚至中午吃完飯,下午他接著講。真是滔滔不絕!從一個問題講到另外一個問題,思維始終處在高度活躍和興奮中。王老師的講話雖然滔滔不絕,但是邏輯性卻極強,記錄下來的話,就是一篇文章。所以王老師雖然是注重思想這一類型的學者,其實他也傾訴,他也放飛自我地講述。王老師說的時候是那樣的專注,那樣的執著,那樣的毫無顧忌,這是我們作為王老師的學生所享受到的一份獨特的精神大餐。我想,大概王老師的那種思考方式,那些來自心底的深層次的東西,也需要一個訴說的渠道,而我們這些學生,就是他特別放松和舒服的說話對象。我記憶最深的就是做博士論文期間,王老師在汕頭,通過打電話跟我談論文。那時候還是座機,每次一打都是一兩個小時,通常也都是王老師說,我聽和記,對我論文的相關問題,王老師談得縱橫捭闔,思考又極其深入、細致,讓我的內心充滿了感激之情!
第二是王富仁的看人。這里的看人不是指他看人準不準這個看人,而是他在別人說話的時候,他靜靜盯住別人的那個眼神、那個神情。我們這次會議海報選取的王老師的照片,就是我記憶中他聽別人講話時專注看人、思考的樣子。不管講話的這個人是他的長輩、他的同輩,還是一個本科生,只要人家發言,他就非常執著地關注,甚至整個臉側過來盯著人家看,眼睛一動不動地思考式地盯著人家,仿佛一定得從人家的這個講話中扣出一個他希望聽到的東西。我有時候想,學生的發言,有什么必要這樣執著、重視呢?但王老師毫無例外地重視!他聽人講話,就像他自己傾訴時一樣。對一個人來說,說和聽是內在統一的,往往自己說得好,聽別人說話也聽得好,聽別人聽得好,自己也說得好,因為無論是說還是聽,都是以思考作為基礎的,所以王老師的“看人”,是我腦海里他作為思想型學者的一個永不磨滅的形象。
第三是王富仁的沉思。沉思占據了王老師大部分的神情、動作和言談舉止。他的沉思一般都伴隨著抽煙。大家都覺得王老師抽煙厲害,一天幾包煙,其實王老師的抽煙據我觀察,并不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而是一支接一支地點,讓煙一直在他的指縫間燃燒著,讓煙霧一直向上升騰著。我們讀博士的時候,談學習的事,去王老師望京的家里最多,一般都是從我們到他家開始,大家一落座,王老師就點起一支煙,直到晚上我們離開,這煙都沒有熄滅過。一整天,他一直跟我們談話,他在煙霧升騰中思考、講話。我想,那個煙其實是王老師思考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道具,一個發動機。如果不拿著一支煙,他的思考似乎就會中斷!王老師舉例子的時候,也經常拿香煙、火柴、火柴盒這些做例子。王老師告別式那天,師母特別深情地講過,王老師一生兩個東西不能沒有,一個是書,一個是煙。我覺得,書是他的精神來源,煙則是他思考時的親密伙伴,是他思考的獨特方式。
第四,在大多數人眼中,王富仁是一個平和、謙和的人,但作為他的學生,我們也經常能看到他的喜怒哀樂,他經常真情流露。在學術方面,對一件事情、一種觀點,甚至對某個人,他不高興,他會發自內心地生氣,極其不滿,極其憤怒,甚至咆哮。有的時候高興,他就非常高興,笑得眼睛都瞇起來,像個孩子一樣!生活中也一樣。在我的記憶里,有一次王老師大發脾氣。2001 年夏天,王老師要從北師大家屬區搬到望京的新房,我和幾個師姐去他師大的家里,想看看還有什么需要幫忙的事。我們到王老師家的時候,他和師母正在等收廢品的人,說是一件舊家具看怎么收,大概能給多少錢。等了很長時間,收廢品的人終于來了,看完家具,人家說這個不收,賣不了什么錢,你實在不要了,他可以免費幫忙抬下樓。王老師聽后立刻就生氣了,非常憤怒地連說了好幾遍“不收你來干什么”,好像最終家具也沒扔,還是搬到了望京的家里。我們很少看到王老師動那么大的氣!王老師那代人生活上非常節儉,對“收廢品”行業的不懂行和過高期待,顯然是因為這個已經超出了他的思考范圍。其實,王老師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底線的人。不論是學術上還是生活中,你不能觸碰他的底線,只不過什么是他的底線,需要跟他有深入的交往才能摸透,不是誰都知道他的底線在哪里。在我看來,有很強的底線,這也是王老師作為思想型學者的一大特點。
最后,我還想講一件事。我博士畢業工作后,第一年的元旦,意外地收到了王老師從汕頭寄來的賀年卡。說“意外”,是因為我還沒有給王老師寄賀卡,卻收到了王老師先寄來的賀卡。一打開,心里更是一震,上面只寫著一句話:“學術研究不能停,一停就是一輩子!”這張賀卡我至今都珍藏著。說實話,當年并沒有真正理解王老師話中的深意。這么多年來,特別是王老師去世后,寫作這本研究王老師的書的過程中,我更深切地體會到,這句話分量太重了!而這句話其實也是王老師一生的寫照,他一生都在不停地看書,不停地研究,不停地思考,所以他讓我們也不能停,因為一停就是一輩子!我后來得知,王老師也給其他同學寫有這樣的賀卡,我覺得這句話是王老師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精神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