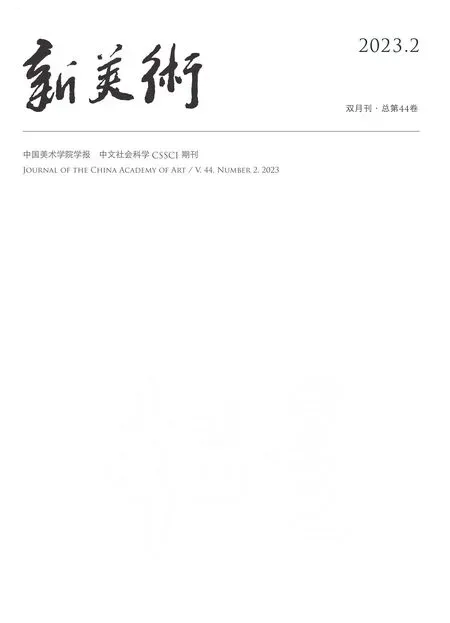作為開端的基礎
佟 飚
所謂基礎,是開端之學。
七百五十多年前,當來自河南的畫師舉起筆來在永樂宮的墻壁上落下第一筆時,這一舉動的歷史性隨即彌漫開來。而我們今日游歷在永樂宮的大殿之中,絕非只看到了那些五彩斑斕的色彩,蒼勁如游龍一般的線條或者端莊典雅的形象。對它們的這些描述都體現著審美的高度。而充盈在其中的核心力量,則是來自于歷史。當然,歷史并不能決定我們今天能看到的那種具體性——不是指那些躍入眼簾的具體的形態:灰塵、經年累月的風化或者氧化后的滄桑之感。就此來說,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正是它所開啟的而非它所決定的。歷史并不向我們保證某種確定的結果,例如上面所提到的諸如灰塵或其他的具體樣態。但是,歷史向我們敞開并綿延而來。故而,凡開端都是具有歷史性的,開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比方說我們所以能夠討論和言說一些事物,那是因為這些事物已經是歷史性的了。即:凡我們所談論的,其必然已是歷史的。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討論藝術的基礎時,我們所討論的,自然是已經置身于歷史的。那么,藝術的開端之處應是我們要關注的核心所在。
藝術的實踐向來是人類重要的行為活動之一。從人類降生以來,藝術即是伴隨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創造生活的重要活動。在中國,它被包含在對“道”的建構之中,所以為“形而上”者,而所謂“形而下”者則為“器”;在西方,它與哲學、宗教并列,為第一層級,其下才是技術,或者后來所謂科學。因此,藝術就其本身而言,它就是上層建筑,是意識形態本身。這一點應當被理解為藝術的開端。那么,我們如何得以回到這一開端之處呢?首先要能進入到“藝術”之中。要想進入到藝術之中,則需要向偉大的經典藝術學習。這些經典,連同創造它們的藝術家,構建起人類的“藝術世界”。他們就是藝術本身——是世界的世界。回到開端之處,即是回到對傳統的藝術的學習之中,也就是對審美的確認。并且,對現實的感知與把握也被包含在這一學習的過程之中。通過這樣的學習實踐,我們得以進入到“藝術”的創造性之中。這樣說,未免會有人擔心保守或者墨守成規。假如我們只是討論或者摹寫那些被創造出來的樣式和風格,那么這個擔心的確是成立的。但如果我們討論或者學習的切入點,是偉大藝術經典與世界的直接性關聯是如何被實現的,是作為意識形態的藝術本身是如何被創造的,那么,對傳統的學習就不會淪為對風格或者樣式的簡單疊加和挪用,而是真正具有基礎意義的活動了。比方說,一個孩子要想進入到世界之中,必須要學會說話,否則,世界并非世界。而孩子學說話則是要學聽得到的話——那些言語穿越時空,歷久彌堅。學說話不是要只學習說話的樣式或者語調,而是要學會說話本身。說話是對世界的描述,也是展開想象與創造,發動思想的前提。
今天的高等藝術院校就是這一學習活動得以充分展開的重要平臺。如果說四年的本科教育是對藝術的開啟,那么,基礎部為期一年的基礎教學,即是對開啟這一活動的“開啟”。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回到藝術的初心”之舉。它的一端是對歷史的感悟和學習,另一端則是對未來的想象和思考。在這個意義上,每個藝術家都將朝向開端的行為變成自己的終身實踐。
例如,在今天的高等藝術教育體系中,素描是一門核心的基礎課程。作為基礎課程,被描述為是對造型能力的訓練。
什么是造型能力?為什么要有造型能力?
就人來說,我們面對的世界毫無疑問是抽象的。我們很難通過某一種描述把這些事物精準地描述出來。因此,眼中的某一事物總是被種種的描述建構起來:物理學家看到的是物質,數學家看到的是完美的公式,諸如此類。它們從人類的共有經驗出發,構建起我們的知識體系,我們自然可以依賴對這些知識的學習來完善或者突破我們的認知。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經驗,它們穿越時間而不斷疊加。這些經驗因此又形成了我們對此事物的共同認識。我們面對這一事物而產生的情感,以及心中的深刻感受也是抽象的。把一塊太湖石說成是石灰巖,或者是碳酸鈣都是正確的,但這樣的描述只是知識。我們喜愛太湖石并不是因為上述的那些知識,而是因為太湖石的美,這種美是被想象出來的。這樣的活動,是藝術的。藝術正是通過想象力實現了抽象的存在向具象的轉換。具象,是最直接的認知。并同時將引發我們感動的內容以形象的形式保存了下來。太湖石是我們對生活世界的想象,而寫生是面向事物本身的想象,因此,在素描課程中,寫生成為訓練的核心手段。這是因為寫生的原則為“是其所是”。第一個“是”是動詞,表明我們的行動。第二個“是”是那個我們面對的事物本身,它表明這個事物本來的樣子。寫生訓練作為素描訓練的基本方式,也是訓練我們想象力的根本方式。而造型能力即是將想象力予以呈現的能力。以這樣的方式,我們把面對的那個事物,以線條和明暗組織出具體的形象并進而表達出這一事物的形式。寫生絕非是對事物的還原,更不是對事物的描摹,而是事物本身的獨特性的呈現,是對由那個事物引發出來的感動和體驗的表現和保存。因而,寫生還意味著拆解與重構。它通過觀察、歸納和想象,演繹造物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這一想象力的轉化同樣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創造力的表達。所謂造型能力的訓練或者素描寫生的意義正在于此。
因為這一要義,素描成了高等美術院校的核心課程。不可否認,作為對一種技藝的訓練與傳承,素描的確以解剖學、透視學作為基本語法結構,從技術上形成了關于客觀事物的表現模式。它包含了對外形和內部結構的精準把握以及深入刻畫的表現能力。因此,它的確是以眼、腦、手的相互合作訓練著造型能力。這一訓練模式清晰地指向著藝術,它以觀察、概括和捕捉等手段達到表現的實現,并由此構建起通往世界深處的路徑。
從藝術史來看,素描是藝術家自我成長的第一步。它需要我們從日常經驗出發,經由上手的實踐和思想的錘煉,來實現創造。
除了素描以外,還有關于色彩的訓練。我們所以能感受到“色彩”,是因為視網膜接受了不同波長的可見光的刺激。因而,色彩可以被表述為一種光的現象。事物呈現出不同的色彩,是光照的自然結果。我們據此而建立了關于“色彩”的如下認識:它有三個重要的特性,即色相,飽和度和明度。而在色彩課的教學中,我們會把紅、黃、藍合稱為三原色。通過對三者關系的不同把握,經由調和白色和黑色的方法,我們還獲得“色調”這樣一種色彩的表達式。比如,冷色調,暖色調,或者亮調等。
看上去這些概念都是可以被觀察到的。相比于素描的“空間”“體積”“明暗關系”這些概念,關于色彩的概念似乎更為直觀,更容易被把握。在“模仿”或“再現”的原則下,色彩賦予了作品更為完整的形式或意義。因為這樣的原因,作品更接近眼睛中所看到的外部世界。故而,藝術教育中的色彩課程就是按照這個要求來組織開展的。但在今天有了新的變化,發達的數字技術似乎使我們對上述原則的學習和掌握,變得更為容易了。例如板繪和AI 繪畫,通過強悍的軟件程序,我們對經典作品的學習仿佛輕而易舉。無論是色彩的強度還是色調的形成,只要熟悉了軟件的操作程序,用壓感筆的壓強感應能力取代了直接的手感,選擇合適的命令,一幅符合色彩要求的作品就能出現。
這樣看來,無論是板繪還是風頭正勁的AI 繪畫,似乎都在“擴展”著藝術的表達。但無論是板繪還是AI 繪畫,實現最后輸出的前提條件是把過往相關的藝術作品以數字的方式建立成數據庫,計算機讀取這些數據根據命令進行分類處置,依靠算法進行虛擬仿造并形成結果。本質上實現的是對過往藝術作品風格以及技術特點的“模擬仿造”。一件以這樣的方式生成出來的作品是如何被定義為作品的?是人憑借對過往藝術的實踐經驗。比如當相機內的取景框對準某一處的場景時,“構圖”的法則就來了。而“構圖”法則又是從哪里來的?先是歷代的藝術家用作品實踐出來的,然后又有人來專門研究它,最終我們都擁有了這樣的經驗體系。所以,當攝影的“構圖”出現時,它們憑借的正是來自繪畫的經驗。而板繪和AI 繪畫本質上都是在強大的算法支持下,對過往所有藝術風格的技術性復制。因為這樣的技術手段,使得我們與世界的關系越來越間接了,夕陽不再是可以細細體會的,而只是一幅充滿細節的靚麗圖像而已。所有的細節都是被平均處理的,因而缺少遺憾。這圖像,光潔華美,但缺少溫度和質感。在這里,藝術家的生動性被平均性取代,創造性被圖像的差異性取代。
問題到這一層就比較清晰了。無論是計算機的模擬行為,還是被置換為數據的藝術作品,當我們把覆蓋在上面的技術性手段去除,就會發現,構成作品的核心力量依然來自人本身。來自數千年以來人類對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審查與體驗。
我們身處的世界之所以是五彩斑斕的,是因為眼睛對可見光的接受和轉化。這是人的生理本能,也是對于世界的直接感受。此外,色彩在歷史的長河中還塑造出了我們的心理感受。比如紅色指向的熱烈激昂。藝術的創造性正是從這一點發端并生長出無數的藝術巨匠和星辰般的藝術作品。以寫生直面世界的方式,目的正在于此。它使我們從技術的藩籬中重新獲得對世界萬象的直觀感受,并進而獲得身心發動的動力。這是藝術的要求而非只是色彩課程的要求。
中國古代的“謝赫六法”中對色彩的要求是“隨類賦彩”,西班牙藝術家洛佩斯則說:“世界是如此豐富,我只要是能畫出來其中一部分就很好了。”因此,色彩訓練的目的并非只是指向“色相”“飽和度”或“調性”的達成,而是要求我們通過直接的手段回應世界的召喚。在這個過程中,身體向世界敞開,一頭接續著偉大的藝術傳統,另一頭則是我們的世界。而創造性的生長也必然地被包含在這樣的行為過程之中。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在這行詩里,不僅有作者對世界與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也飽含著濃郁蒼茫的色彩。它不來自技術,更不是技術控制下的技術性思維,它的力量來自人與世界本身。素描也好,色彩也好,都需要我們經由自身的磨煉去打通那前往世界的路徑。以此為方法的訓練,在于以直接性的手段去實現與世界的關系。自古以來,那些杰出的藝術家們無不以此為方法,建構起我們已然身處其中的“藝術世界”,而這一世界,當然也就是世界本身。
維特根斯坦說:“真正神秘,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
回到本文的開頭并由此而言之,對于藝術來說,它的基礎教學并非是簡單的教同學們畫一些畫,以素描、色彩等命名的課程,或者做一些學科內的先導教學。這個意思是說,不能只是擺一些模特或者物品,或者是到戶外畫一個風景,也不是按照一些專業的特點,去對應的設計一些專業內容進行教學,尤其是不能把過于專業的技術前置到基礎教學里。而是要認真思考教授什么樣的內容才能使同學們進入到藝術的世界之中,并從而建立課程之間內在的邏輯關聯。
基礎的核心在于開啟、開端,這一開啟始自于歷史的深處,朝向著未來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