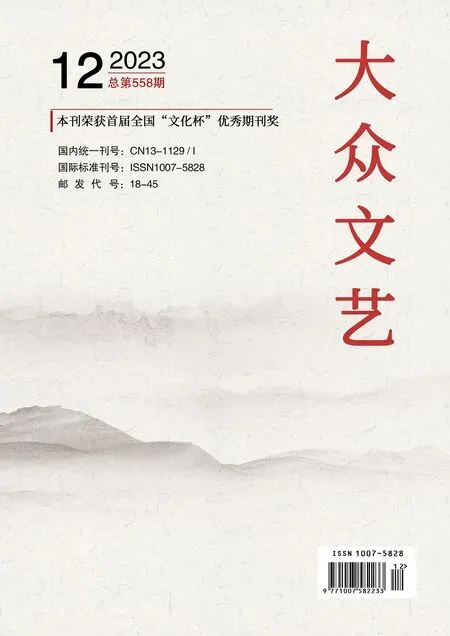理性如何實現正義?
——《米歇爾?科爾哈斯》中對理性的思考
席田越
(南開大學,天津 300071)
《米歇爾?科爾哈斯》這部小說描述了寫科爾哈斯追求正義的經歷。從表層來看,小說在探討如何實現正義這一問題,甚或是,當法律不能實現正義,應如何實現正義?科爾哈斯首先訴諸法律手段,一旦法律難以維護正義之時,他便走向了法律的對立面,一為從外部打破法律制度,建立“私人化的法”的暴力手段,另一為從法律內部,挑戰法律理論架構的神學力量。然從更深一層去看,小說是在探討理性是否能實現正義。法律本應是群體理性的代表,用以維護群體中每個人的權益,但是在實際運用中,無論是從立法權還是解釋權,法律作為統治者的工具,不能顧全普通人的權利。故科爾哈斯借以個體理性來反對集權理性,暴力便是科爾哈斯實現其個人的理性的途徑,即以“‘暴力秩序’剝奪法律的‘文字秩序’”[1]。他通過暴力來撼動象征群體理性的法律,建立起個人法律,即“法的私人化”,以彰顯個人理性。然而,無論是集權理性還是個體理性,當其膨脹之時,都會以犧牲他人權利作為其建立的代價,那么二者均不是實現正義的恰當途徑。故事中,真正使科爾哈斯獲得正義的是一張偶然獲得的“神秘紙條”,它以認知理性徹底打敗了法律的集權理性,觸發法律自身的自反性,從而消解了法律的理性意義,令法律走向理性的另一端。認知理性獲取正義的高明之處在于它是從內部推倒了法律架構之中的第一個多米諾骨牌,然而這一偶然機制,卻觸發整個法律體制的崩塌。
下面,結合文本,對這三種方式進行一一分析。
一、法律——集權理性
齊澤克曾說:“這個故事講述了一個不了解確定法律運用的不成文法則的‘固守法則的人’過分追求正義,最終以犯罪結束。”[2]他認為,科爾哈斯不了解法律運用的不成文法則,即“雖然沒有人明確地陳述過這些規則,但是,不遵循這些規則的話,便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后果”[2]馬克思解釋這種“不成文的法則”為“現實抽象”力量,是社會中約定俗成的具有服從意味的共識,其目的是維護統治特權。意識形態存在的作用之一便是遮蔽社會現實中盛行的“現實抽象”。在《米歇爾?科爾哈斯》中,“不成文的法則”是法律的天平自覺地傾向集權統治者,無論是馬丁路德、律師還是司令官,對此心知肚明,然科爾哈斯對這一“現實抽象”力量發出挑戰。
首先,科爾哈斯認為任何人必須按照法律行事。容克私設關卡,收取過路費斂財;擅自規定“沒有國君的許可證,任何人不得帶著馬匹越過邊境。”[3],限制通行;又非法扣留私人財產,并虐待科爾哈斯的兩匹黑馬,留下來照看馬匹的馬夫赫爾塞也傷痕累累。這便“從一開始的扣留馬匹,升級為對私人財產的損害以及對馬夫赫爾塞的人身傷害。”[4]這是容克對科爾哈斯所行的三件不法之事。科爾哈斯“熟悉國君有關他這個行業的一切法規”,故他深知容克違背法律規定,便要求容克賠償他的所有損失。事實上,科爾哈斯忽視了容克享有的法律特權,所謂“不成文的法則”便是容克可以濫用私權。法律固然沒有表明容克有權利用路障斂財,但是作為統治階層的一員,容克可以違反法度,或者篡改法度,因為立法權及法律的解釋權掌握在集權統治者手中。
其次,科爾哈斯堅信統治者可以維護法律的公平正義。他將希望寄托于執政者:“國君本人,我知道的是公正的;只要我能過他周圍臣仆的關,向他面呈此事,那我毫不懷疑正義會得以伸張。”所以,面對不公,他不斷求助于地位更高的執法者。一開始,當堡長要求出示“國君的特許證”,克爾哈斯主動要求面見容克,可還是留下黑馬抵押;之后科爾哈斯向德雷斯頓法院提出訴訟,最終被撤訴;之后他托人將申訴書呈送到薩克森選帝侯手中,但處理此事的首相置之不理;最后他的妻子以身犯險將申訴書送到柏林國君手中,卻慘遭殺害。容克、法院、選帝侯……科爾哈斯寄希望于更公正的執法者,實際上,沒有容克的默許與縱容,堡長不敢提出非分的要求并虐待黑馬與馬夫;因為容克與上層親近的人際關系,科爾哈斯才被剝奪訴訟權;為了國君安全,平白犧牲了妻子的生命。背后的種種原因都在證明,統治者非但無法維護科爾哈斯的正義,而且不斷侵犯著科爾哈斯的合法權利甚至傷及無辜。科爾哈斯沒有意識到的是,整個司法體系出了問題,法律的實施過程中缺乏制度的維護,“他認為公正的執法者是實現正義的保證,沒有認識到執法者作為個人,需要有制度來約束他的弱點,從而保證其不徇私情、不偏不倚。”[4]
從西方律法的傳統看,法律本應是“理性的宣言”[8],作者克萊斯特“察覺到了個體意志與法律形式的沖突,并開始質疑法律的有效性。”[1]需要明確的是,造成法律失效,并非“成文法本身的不公正”[5],而是“當權者忽視法律這一事實”[5]。所以,批判的出發點其實是法律背后的運行機制。而這完全是集權統治的機制,其正當性反應于集權理性。所以作為被統治階級,科爾哈斯利用象征集權理性的法律來為自我正義張本,從根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甚或是,在集權統治運行的機制下,法律不能實現真正的正義。
二、暴力——個體理性
“面對縱橫交錯的人性的弱點和欲望時,對于一個絕對的、由國家保障的公平的假設分崩離析”[6]科爾哈斯并非一直蒙蔽在法律的幻境中,妻子的死亡讓他明白:合法途徑不能使他實現正義。他便走到了法的對立面,用暴力來捍衛公平與正義。
科爾哈斯的暴力反抗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且主要來自他對法律的失望。首先,轉向暴力反抗的原因是因為法律手段的失敗。“速到特龍肯堡將馬匹領回,不得上訴,否則便予以監禁,以示儆戒”。選帝侯的批復使科爾哈斯對法律制度徹底失望。其次,他的遭遇在許多民眾中具有代表性,如“這幾個人平素都對容克不滿,對戰利品也有覬覦之心,很想投到他的麾下效命”所以在廣泛的群眾基礎之上,他建立武裝軍隊,開始暴力反抗。還有,如小說開篇介紹“他樂善好施,仗義執言”,而且他富有責任感,他為同胞們所受的欺辱感到憤恨。無論是他自身超乎常人的美德,還是為廣大民眾打抱不平,還是對現有制度的失望,都促使科爾哈斯走上了暴力反抗之路。
然而,科爾哈斯的暴力更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無論是為自己還是為他人,他對正義的理想化追求使得他個人理性極度膨脹,“在他的價值體系中只存在著清晰的非此即彼,在他的思維中善與惡截然對立”[6],這種絕對化、單一化的思維方式,令他逐漸偏離了理性的軌道。
當個人的理性膨脹,便會走向非理性的極端,科爾哈斯選擇暴力手段維護自我理性,即把自己當作視為世界的中心,以自我為目的,以他人為手段。在小說中,科爾哈斯將自己從現存的社會關系中剝離,并宣稱自己是一位“僅服從于上帝的帝國及其邊界的自由民”他驕傲地將自己的駐扎地稱為“世界臨時世俗政府所在地”他號召百姓加入自己,“為了建立更好的秩序”,并且將自己打造為復仇天使米歇爾的地方執行官,以上帝之命進行懲罰。他無限抬高自己的身份,為了建立自己的秩序,那就需要打破原有的體制,既然要成為“父”,那就要替代原有的“父”。如此,“科爾哈斯由一個正義的尋求者變成了獨斷專行的正義的制定者,他體現出具有超凡魅力的合法革命者之態,威脅著要剝奪傳統意義上合法統治者的生存基礎”[5]
科爾哈斯曾經作為集權體制的犧牲品而被剝奪自身的主體性,他現在以剝奪他人主體性的方式來建立自我的主體性,這一邏輯和集權統治的邏輯并無二致。他的初衷是維護自我與他人的正義,為民除害,但是在實行中,他通過縱火行為制造群體恐慌,借此將個人仇恨上升為社會仇恨,他敕令道:“如不將容克交出,將玉石俱焚,使城池化為一片廢墟,使我無須隔墻便能將容克擒拿歸案。”對于民眾來說,縱火威脅著他們的人身安全,只有將容克趕出城外,才能重新獲得穩定與安全,所以他們將容克視為“吸血鬼、害群之馬”。這種強化意識認同,馴化思想,建立統治的模式與集權統治的運行機制極度類似。
科爾哈斯的暴力維權看似走到了集權法律的對立面,究其根本,科爾哈斯的暴力來源于他對法律的過分認同。齊澤克分析說:“一旦他(科爾哈斯)開始相信現存的法律結構的腐敗,無法遵守其自己的法則,他便朝著一個幾乎偏執狂的方向送出象征性信號,宣稱他打算建立一個‘新的政府’”[2]法律作為一種“文字秩序”,通過制定明確的規則與懲罰來制約人的行為,科爾哈斯通過暴力,形成對人的恐嚇與威脅,進而通過壓迫來使人順從,他用“暴力秩序”取代法律的“文字秩序”,完成“法的私人化”。科爾哈斯的行為也就從一個“有法律保護的暴力”變成了“制定法律的暴力”[2]。本質上,科爾哈斯建立一種新的集權統治,這種集權與他曾經背棄的政治形式如出一轍,而最初所追求的正義也在暴力的行為中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
利德爾對科爾哈斯評價道:“科爾哈斯通過部分革命的方式追求一種非革命的狀態。他頭腦中也沒有那種法國大革命期間與廣泛自由理想相聯系的對全新開始的狂熱情緒。科爾哈斯將賦予暴力以拯救和純潔功能的千禧年革命的觀念給世俗化了。對義人的拯救應該通過建立一個新的耶路撒冷來實現;對社會的純潔應該通過清除雜草來實現。”[7]由此可以得知,科爾哈斯自身保守性導致他選擇暴力反抗的方式就是錯誤的,他的暴力行為無疑是失敗的。如上文分析到,他的暴力是自我理性膨脹情況下,以自我意志對對社會秩序的再構,這一定會危害到群眾的利益,既然如此,他一開始想要守衛的正義也無處談起。所以,個人的暴行和集權的法律一樣,都不能維護正義,甚至會損害正義。
三、神秘的紙條——認知理性
小說的張力在于,如果科爾哈斯因其在討伐容克過程中所做的暴行而被判處國家安全罪,那么“法律無法實現其正義”這一事實便是他犯罪的誘因,這便變相地承認了國家的過失,顯然不合適,然而,如果科爾哈斯沒有因為其暴力受到懲罰,那么國家就沒有履行對其他在這場暴亂中無辜受害者的保護義務,那么如何處理科爾哈斯,科爾哈斯的正義又該如何實現,是矛盾的癥結所在。
因此,作者引入具有神學色彩的“神秘紙條”改變了故事的走向。吉卜賽女王交給科爾哈斯記載著選帝侯命運的紙條。自此,薩克森選帝侯陷入了深深的不安當中。他企圖撤回對科爾哈斯的訴訟,故先后致函給德意志皇帝和勃蘭登選帝侯,希望科爾哈斯免于死刑。最終,薩克森選帝侯利用法律手段來延緩科爾哈斯刑期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在臨刑前,科爾哈斯徑直吞下“神秘紙條”,薩克森選帝侯永遠無法得知預示的真相,身心受到極大打擊。對于選帝侯而言,“神秘紙條”完全超出其認知秩序。這張神秘的紙條使薩克森選帝侯徹底淪為現代的坦塔羅斯。在“神秘紙條”的作用下,薩克森選帝侯和科爾哈斯在法律領域和認知領域中建立起附屬與支配地位完全不同的對立關系。在法律秩序中,薩克森選帝侯以法的命運剝奪了科爾哈斯的生命與自由,在認知領域中,科爾哈斯憑借神秘紙條獲得了選帝侯精神世界的絕對控制權。無法獲得的預言秘密就像是永遠得不到的食物與懸在空中頭頂的巨石,使他無時無刻不在受著精神的折磨,為了從認知領域的困境中解脫,薩克森選帝侯不得不在法律領域中推翻對科爾哈斯的處決,保留科爾哈斯的生命以保證“預言”的存在。這時的神秘紙條已經不僅僅是預示意義的能指,更是一種特權意義的能指。“神秘紙條”的對法律的顛覆性在于選帝侯通過法律手段懲罰科爾哈斯轉向利用法律手段來拯救科爾哈斯,然而,科爾哈斯通過法律手段的無效性達到了折磨選帝侯的目的,最終真正實現正義。
“科爾哈斯以‘神秘紙條’的認知權利完成對選帝侯法律權利的支配與奴役……象征著法律秩序中的選帝侯最終沉浮于認知秩序中的至權者(科爾哈斯)。”[1]也就是說,科爾哈斯通過認知領域中的理性顛覆了法律秩序,達到了真正的正義。需要明確的是,認知理性并非個人理性,而是一種理性標準,它憑借精神力量對抗法律代表的集權理性。對抗的方式便是激發法律的自反性,即利用法律內部規則使法律制定者深陷困境,從而消解法律自身的權威性,將其推向非理性的邊緣,背后則是對法律制定者和集權理性的一種不滿與質疑。
小結
本文探究在實現正義的途徑背后所反映的理性問題。那么為何要談這部作品對理性的闡釋,這與作者克萊斯特本人不無關系。
作者設置“神秘紙條”來干預法律機器的運行,用一種帶有神秘性的因素顛覆了理性的法律機制,透露作者出對理性的質疑與思考。這與作者克萊斯特思想上出現的“康德危機”有關。他曾不止一次在其書信中說過在思想上遭遇了“康德危機”。康德提出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而且理性的膨脹導致人偏離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而淪向工具理性與物質理性。對于在“求真觀念中包含一種非此即彼的偏執”[1]的克萊斯特,這一觀點改變了他對人理性的認知,并開始反思人過度依賴理性的后果。“理性的自我控制以及對主體的重視導致了主體的絕對化,而且帶來了這樣的后果:純粹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認知模式處于轉變狀態,然后解體。”[9]他意識到理性導致主體絕對化,即人夸大自己的作用與地位,以自我為目的而將他者當作手段,不僅認為本身有突破自身界限的能力,而且還企圖利用知識獲得支配外在世界的能力。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何在《米歇爾?科爾哈斯》中探討理性與正義的關系問題了。換句話說,不僅僅是理性能否實現正義的問題,更值得反思的是,濫用理性才是引起非正義事件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