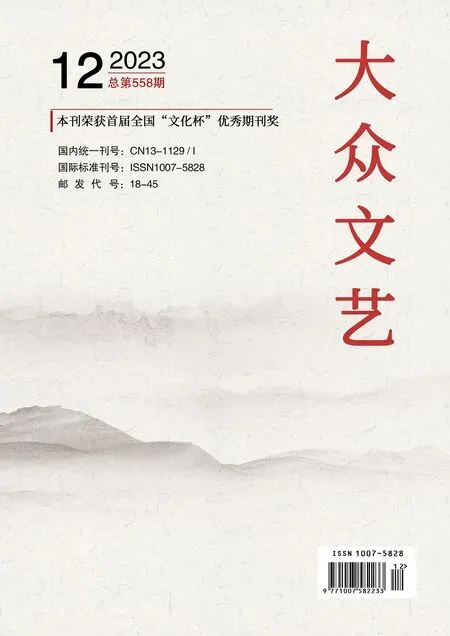生命的向度:廢墟美學于鄉村重建的意義探究
楊子鯤 夏 冬 趙 月
(西南林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云南昆明 650224)
一、廢墟美學本身
廢墟美學作為一門尚不成體系的美學理論,國內國外相關研究甚少。截至2023年1月,知網收錄的廢墟美學文獻僅有70篇。廢墟文學研究的稀缺,一是因為廢墟美學的出處誕生于悲劇文學領域,二是因為廢墟美學區別于主流意識的審美。近些年來,由于我國開始重視工業廢墟及民居廢墟的再建造與利用,廢墟美學這一名詞逐漸進入大眾視野。
1.廢墟美學的定義
廢墟一詞在辭海中的釋義為:“城市,村莊遭受破壞或災害后變成的荒涼地方”,而美學的釋義為:“研究人與現實的審美關系的科學。研究對象包括:審美對象,審美感受,藝術等。”廢墟美學即是通過廢墟這一物質載體,對廢墟中存在的美學價值進行審美及分析,廢墟美學旨在要求人們對于世俗生產意義上認為的“無用之物”作出審美反映。作為建筑形體,廢墟是無用的:作為上一個時代所留存下來的建筑痕跡,如果不加以修葺,它將是一個占用土地資源的無用形體;但作為藝術的附加造物,當以一種美學思維——廢墟美學來看待廢棄建筑,它能在滿足人們審美需求的同時,提供精神及哲學上的思索,雖然殘缺,但確是本質上的完整。它作為一種剛被人認知到的新興美學,甚至能引發大眾對生命的思考,這是廢墟美學的魅力所在。
2.廢墟美學的來源探究
在諸多探討廢墟美學的論文中,均秉承一個觀點,那就是廢墟美學理論出自德國文學家,思想家,美學評論家:本雅明。他被視為20世紀前半期德國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被譽為“歐洲最后一位知識分子”。著作包括《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等。本雅明曾說過:“只有對一切塵世存在的悲慘,無意義的徹底確信,才有可能透視出一種從廢墟中升起的通向拯救王國的遠景”[1]。對于廢墟美學本身而言,本雅明探討的不是一種純粹的悲苦沉溺,而是在廢墟之上重建新的理想王國,這便是他的救贖美學。
(1)光韻
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2]中闡述過關于“光韻”的概念,它認為自然光韻(Aura)是一種發生在自然原初世界的現象,光韻誕生于人與自然的交融,與生命息息相關,是一種“源于自然的生命之光”,他認為在古典藝術時代,當人們還采用傳統手工業生產制造時,光韻便體現在當時的藝術作品中。古典時期的人們,不論是最初的古希臘悲劇,抑或是巴洛克時期的宮廷油畫,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與自然產生聯結:它們的靈感來源于萬事萬物的本初世界,繼而與人類社會產生關聯與思考。如尼采的《悲劇的誕生》[3],古希臘悲劇藝術誕生自日神藝術與薩提爾歌隊所代表的酒神藝術的交融。在古典藝術時期,由于宗教信仰與對自然的初步認識,文學藝術作品中常出現與自然交融及人類起源的哲思。而本雅明認為這種人與自然的交融下所產生的藝術作品,都是帶有“光韻”的,只要生命的活動與自然的交往,就有“光韻”的存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生產力得到大力發展,人們可以利用機械地重復制造獲得產物,引發了大眾對于藝術作品本質定義的思考,即機械復制的藝術可否稱之為真正藝術。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4]里,本雅明闡述了如此的擔憂:他認為在機械復制時代下,藝術作品不再帶有光韻,在冰冷機械的介入下,這樣的產物失去了與自然的聯結,失去了“生命的本真交流”。
(2)生命向度
“在人被機械的再現中,人的自我異化經歷了一種高級的創造性運用。”本雅明認為光韻所創造了那種生命與自然的交流,具有“即時即地性”,他稱之為藝術的“本真性”。而現代藝術中的所謂光韻的產生,但是以生命為本質和機械載體,以新的意識形態和結晶存在于所謂“真正的藝術中”。當我們欣賞藝術作品時,情思便與作者所處的時空產生交流,所對作品做的欣賞及評價,與原作者的心流共同創造了當下時空即時即地歷史性的生命與文化的交流。在本雅明的美學思維中,這是一種“生命的向度”。而廢墟美學式的建筑自誕生之初起,自被以一磚一瓦建造之初起,經由自然的“改造”腐蝕風化,由不同時空的“讀者”發生欣賞與感受上的時空交流,隨之產生當下歷史性的即時構成。無論在何種時空下,只要形體存在,廢墟建筑始終都能產生人與自然之間生命的聯結。通過廢墟美學式審美,我們能夠體驗廢墟建筑中蘊含的時空關聯,去思考想象補充建筑誕生之日人們的生活習慣,審美樂趣,繼而引發對生命的思考。這種廢墟美學中所包含的生命向度,雖由看似毀滅死亡的物質形態表現出來,而其內核本身確是一種對新生的向往。廢墟美學的生命向度,所帶來的共情感和審美體驗,如同永恒不滅的薪火,經由生命這一載體,不斷向下延續。
(3)廢墟美學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屬性
本雅明本人作為德意志的思想家、美學評論家之外,也是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的共產主義思想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得以體現,馬克思的“藝術生產”理論在本雅明思想內生根發芽,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物質生產關系影響著藝術的理論,他闡述了生產力及生產關系于藝術領域以及藝術生產于現代技術衍生而來的消費影響,開辟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藝術生產理論,即開辟了從生產力發展角度研究文藝活動的新途徑與新視域。在本雅明《作為生產者的藝術家》中,本雅明引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討論藝術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他討論了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限制,以及突破這種限制的可能性。他將藝術制造看作成一種生產勞動,而不是單純的精神勞動,即是兩種屬性的結合。藝術生產中機械的介入,除了改變藝術本身的物質屬性,人與機器關系也發生了改變。對于生產技術,本雅明不是全盤否定的,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中,他開始探索技術與藝術相結合誕生的更多可能性,人如何與機器達成合作,并在不斷協調中進行藝術創作,他以一種歷史唯物辯證主義去看待客觀事物本身。而廢墟美學及其所展現的建筑形體中,大眾所欣賞的并非廢墟誕生時舊有的榮光,而是一種辯證性的前進力量,有助于我們形成對未來的審美及展望。“不以好的舊事物為起點,而以差的新事物為起點。”這來源于本雅明的日記。事物是螺旋發展上升的,正是廢墟美學中蘊含的歷史唯物主義特性,讓我們得以產生對過去舊有事物的一瞥,人的審美體驗及經驗才能不斷得以上升。在廢墟之上,我們得以重建新的“王國”。
3.廢墟美學的審美價值
(1)情感體驗
在環境心理學理論關于環境行為關系闡述中,環境給予人的心理刺激,將會導致人處于一種被喚醒的興奮狀態,表現為情緒變化和體力活動的增加,這便是喚醒理論。[5]當人處于被自然風蝕、戰爭損毀、被遺棄的廢墟前,感受的是無與倫比的情感體驗:“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6]從形體上,大多數廢墟由于建筑特性尺度高大,受眾感受到心理上的威壓;而其損毀所帶來的殘破性,則會讓人思考廢墟“淪為”廢墟的緣由。在廢墟建筑前,我們將體驗到與歷史的聯結,如同藝術的本真性,我們當下對廢墟產生的欣賞與感受,與建筑本身產生交流產生美的即時構成。廢墟美學幫助我們從凝聚的時間中切身感受藝術形式的更替,藝術與歷史不可分割,廢墟就是歷史藝術交替的實體形成。廢墟美學的精神屬性與悲劇同根同源,在面對無法復原的逝去之物即廢墟建筑時,我們從中得到悲愴的情感體驗,會引發我們的憐憫,困惑,感嘆之情。[7]“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這種面對強大歷史所帶來的不可抗力面前,我們感嘆時空的流逝,我們驚嘆作為人類的渺小,在被劇烈的情感沖擊過后,我們會趨于平靜,在感嘆之余,最后收獲對生命的哲思。
(2)精神力量
從人類最初誕生之時,見到的第一個“圓”便是母親的子宮,圓及其意象在人類社會中充當重要的角色。[8]而中國古人殘缺事物進行審美的行為自古有之,例如陰陽中“虛”的探討。“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殘缺事物也具有審美價值,哪怕這種審美體驗帶來的是憂郁。廢墟美學能給予人們精神力量,作家普魯斯特強調追憶乃人之本性。我們通過追憶過去,通過廢墟建筑當中儲存的精神力量,來體驗逝去時光中的生命之光,這便是精神力量的體現。在對廢墟進行審美及再利用中,充斥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物理世界尚且存在難以圓滿的事物,而精神對此的寄喻則是圓滿的。
(3)審美活動空間
當大眾對物理意義上存在的殘缺廢墟進行審美時,通常會將它所缺失的另一部分進行想象,這樣的虛與實在審美過程中加以結合,便是給予觀者審美活動空間的行為。[9]人們在聯想再創造的過程中,獲得創造的愉悅,而想象背后所帶來的無實體的延伸,神秘和富有魅力。例如斷臂的維納斯,正是因為其殘缺的部分,致使其充滿了其他圓滿雕塑所無可比擬的魅力。廢墟美學的審美對象在物理意義上是無生命的建筑材料,但與人思想中主觀的審美聯想加以聯合,整個審美對象便充滿了生命的光韻,是被賦予了生命向度的物體。
本雅明對于古典巴洛克藝術及巴洛克悲劇本身之于現在,持有一種悲傷的思考,他認為巴洛克悲劇本身就是廢墟的體現,在廢墟這一意象中,在諸多悲苦的寄喻中,我們得以窺見舊日的榮光,那最初自然與人類相融時創造的光韻藝術,承載在廢墟中。廢墟這一寄喻并不是破損或是無用的體現,恰恰是通向救贖的道路,我們從中思考,我們繼續前進,我們在廢墟之上重建新的文明。
二、廢墟美學于鄉村重建
在中國,鄉村的問題即是整個國家及社會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利用較為合理的,可行性高的發展,改造,活化策略來重新激活鄉村地區是亟待行動的任務。
1.由廢墟美學所注入的生命活力
新時代的鄉村需要文化自信為其注入生命活力,每個鄉村中的老舊民居不僅象征著時代建筑的物理留存,更是保留了當地獨特的地域特征,民俗風情所凝結成的文化脈絡,這是一種凝結在物質載體中的精神場作用力。而將廢墟美學觀念應用于鄉村重建,有助于幫助鄉村保留其獨特的文化內核。通過廢墟美學中的“生命向度”,有計劃有節制的重建鄉村建筑,保留鄉村建筑在歲月中與人自然交互而產生的“生命力”。而本地居民在回遷至原址時,能夠自然而然的融入其中,繼續原有的生活;外來游客在進入當地旅游時,也能體會建筑與人產生的光韻生命向度,而不是接受單一的商業化消費主義。
2.保留廢墟建筑,延續傳統意象
傳統意象在傳統鄉村中的重要性,相當于寄喻之于古希臘悲劇,意象作為傳統文化脈絡的延伸,能夠將抽象的情感體驗轉化為實際的腦內圖像。需要重建的鄉村中的破敗景象如廢棄民居,老舊祠堂,泥濘小路等,其實都是能給予大眾情感體驗的意象,這種經由自然風化所表現出的人造廢墟景象,恰恰能喚起大眾內心對傳統鄉土生活的“鄉愁”之情。鄉愁這一抽象的情緒體驗經由廢墟建筑物理載體,所滿足的是個體的鄉土情懷,文化及歷史的精神需求。而經由廢墟美學,將一部分鄉村廢墟加以保留,將延續鄉村的傳統意象,喚起鄉愁體驗。[10]
3.保護鄉村生態,拓展鄉村價值
廢墟建筑在人類視角看來僅僅只是物理形體,是毫無價值的“死物”,而從自然層面來說,它是當地生態的一部分。很多廢墟被人類遺棄后,便成了當地植物,動物的寄居之所。而廢墟之上爬滿的植物,也成了廢墟美學審美的一部分,那便是“死物”與“活物”相互交融的和諧生態。鄉村作為遠離都市的區域,理應是生機勃勃的。基于廢墟美學所進行的鄉村重建,將大力保護鄉村生態,為鄉村拓展其環保學意義上的價值。[11]
總結
廢墟美學作為獨特的審美觀念,不是對廢墟進行傷春悲秋或悲苦沉溺,而是感受其中所傳遞的生命向度。這種螺旋遞進式的自然與精神式的光韻結合,寄喻著生命之光。我們在廢墟之上不斷前進重建新的家園,從中感悟對于精神世界完滿的哲思。這種薪火相傳的黃金精神不僅帶給我們審美上的全新體驗,更對我們思考與自然的關系,思考歷史時空與自我的相融起到指導作用。隨著文化精神的不斷發展,廢墟美學將會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加以應用,我們會在“廢墟”之上,建立新的“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