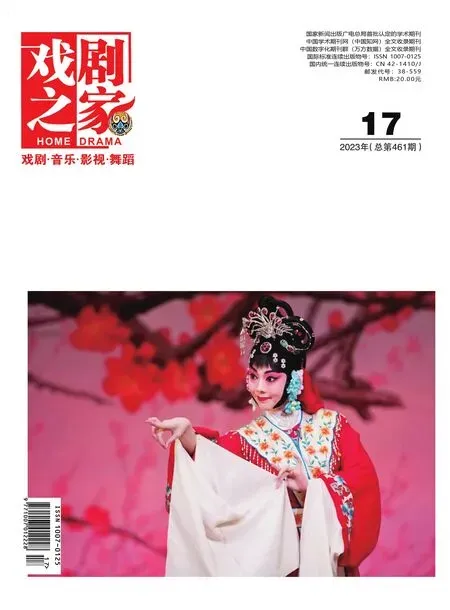對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的探討
——以《哈姆雷特》為例
許寧玲
(長江大學 人文與新媒體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電影《夜宴》上映于2006 年,是由馮小剛導演基于莎士比亞經典著作《哈姆雷特》改編而來的一部宮廷悲劇電影作品。《哈姆雷特》描寫的是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為父報仇的故事,在混亂顛倒的時代背景下,故事反映出的悲劇精神囊括了人的精神、對既定命運的抗爭、使命感與個人情感之間的對抗以及對人文精神的深入思考。《哈姆雷特》成為經典的內核是其對時代背景的深刻反思以及其中蘊含的人文主義關懷,這些思考與探索都具備了跨越時代的現實意義,也使其悲劇精神具有了超越文字載體的情感張力,將文字的價值體現得淋漓盡致。目前已經有很多影視工作者進行了大膽嘗試,如電影《夜宴》在改編過程中保留了原著《哈姆雷特》中王子復仇的故事結構。通常情況下,經典文學著作的影像化呈現應該是有質量保證的,但觀眾對于《夜宴》褒貶不一。為探究外國經典文學作品在本土影像化改編過程中的呈現路徑,本文將對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價值內核、影像化呈現以及本土影像化進行分析,希望能為外國經典文學的本土化傳播提供有效路徑。
一、對《夜宴》的翻拍分析
電影《夜宴》以莎士比亞經典文學作品《哈姆雷特》為基礎進行翻拍,其劇情走向與《哈姆雷特》的故事線基本一致,是對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本土影像化的一次大膽嘗試。在影視化改編過程中,《夜宴》團隊基本沿用了莎士比亞原作的大致人物設定,但在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部分,將原著的中世紀丹麥宮廷替換為中國“五代十國”這一歷史時期,并在影像呈現風格、燈光調度及色彩運用方面注入了濃厚的東方美學色彩,尤其是導演在攝影風格上采用了中國傳統繪畫作品中的扁平透視手法,在視覺藝術風格上極具特色,因此影片并不存在突兀感。
“公元907 年之后,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這是一個相當混亂的時期,國與國之間連年戰爭,皇帝與大臣血腥角力,甚至各個皇室內部、父子、兄弟間彼此殺戮’。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亂世’是導致一切矛盾沖突的根源所在。”[1]與《哈姆雷特》一樣,《夜宴》繼承了“王子復仇”的故事模式,在改編的過程中也有意識地挖掘和繼承了原著的人文主義精神。
但電影《夜宴》并不能算作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視化的成功模板。首先是觀眾反響。時隔多年,每當將這部電影作為分析案例時都繞不開該片極具風格的視覺呈現,服裝、化妝、道具以及演員表演都稱得上精美的一部影片,但收獲的評價褒貶不一,直到今天,大眾對這部影片除了視聽體驗之外也鮮有好評。雖然影片的成功與否不能用當下的票房和口碑作為唯一的評判標準,但影視作品終究是大眾傳媒的一部分,受眾群體的接受度可以直接作為外國文學作品本土影視化探索的風向標。其次,一部電影的核心立足點在于故事本身,經得起推敲的故事搭配渾然一體的藝術風格必然是上乘之作。經典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根本原因還是文學作品本身傳遞的價值導向和情感張力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夜宴》口碑的兩極分化再次反映出受眾敏銳的洞察力,該片的本土化改編最成功之處在于其視聽風格,觀眾也給予了正面反饋,但對于故事性的爭議比較大。《哈姆雷特》在外國經典文學中具有較高地位并不單單是因為“王子復仇”的故事模式,原作背后的時代和文化背景是其故事性和敘事邏輯的重要支撐,文藝復興對于人欲的重視、宗教地位的演變、基于人文主義精神的思考,這些無一不成為原著中人物復雜內心的組成部分。最后,《夜宴》在長線敘事中將原著的悲劇內核外化,結合觀感體驗將悲劇的氛圍進行鋪墊渲染,從中能夠看出影片制作團隊對于原著倫理綱常部分的挖掘與本土化的巧思,但并沒有抓住原著具有普遍性的人文內核。其實,在本土化過程中無論是視聽感受還是故事本身,《夜宴》并沒有生硬之感,但是基于原著的文學性及歷史地位,如何讓受眾順利接納一個已經知道結局的故事并從中感受到經典文學作品的深刻內涵,這也是一段漫長的探索之路。
總體來講,《夜宴》在影像風格上屬于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化的精品,市場反饋和受眾口碑雖表現平平,但這一勇敢嘗試和堪稱經典的藝術風格也為華語電影對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本土影視化探索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困境
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面臨著許多困境,主要體現在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創作時代背景與本土實際情況不同,其中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都會對受眾的接納程度和本土化過程中的改編幅度造成影響。這也對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應該結合當下時代背景及發展水平去感受原著的創作過程,對其核心價值要有清晰、深刻的理解,拒絕“換皮”式的改編和翻拍。
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本土化更不能為了外化戲劇內核而使原著的文學價值核心流于表面。以悲劇作品為例,文學作品中往往體現的是人性之悲,這種情緒的感染力不會隨時代而褪去,而在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的過程中很容易出現為了服務影片敘事邏輯而將人性之悲外化為人的悲劇,由人的共性變成了劇中角色的個人悲劇,無論是立意、角度還是普遍性都存在局限性。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平衡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終極目標與角色內驅力的關系。一方面是影像化過程中要考慮到受眾的觀感,但過多的人物背景及內心活動交代會導致敘事節奏拖沓,進而使作品影像化后角色的行為模式和思維邏輯不能被本土受眾很好地理解和接納。這就要求導演將角色相關的具體事件與抉擇轉變為對價值內核的回歸,在理清原著核心價值導向的基礎上梳理出為其服務的人物設定,找準發揮起承轉合作用的故事發展節點有助于在本土化過程中找到合理替換故事背景或符合時代性的新的處理方式,從而在不破壞原有框架的基礎之上講述具有本土特色的經典故事,并以本土視角對外國文學經典作出全新影像化闡釋。
另外一個關鍵問題在于文學作品的世界性與影像呈現時的本土落差。以迪士尼著名影片《獅子王》舉例,同樣是改編自莎士比亞文學名著《哈姆雷特》,其選取童話視角,借助動畫電影的視覺呈現方式講述了同樣的“王子復仇”故事,在世界范圍內贏得了良好的口碑,根本原因并不是其視覺呈現方式,而是劇作團隊在改編過程中抓住了原著的內核,符合動畫電影受眾群體的接受邏輯,因此文化背景的不同并沒有影響影片核心價值的體現。本土落差的存在是由于外國文學本土影視化的目的是要讓本土受眾能夠接受其價值導向輸出,并且能夠感受到原著具有世界性的情感張力,但影片在本土化過程中經常會走入“只求形似”的誤區。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世界性一定不體現在其人物角色的金發碧眼上,同樣,本土化也不只是將劇中人物以本土影像呈現在熒幕上這么簡單。比如著名文學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保爾,我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炙熱,這無關角色的外在形象,而是作家筆下所展現出的人物內在力量。我們在討論影像重現經典時也不是一味地重現文字,在抓住角色和故事內核時進行合乎邏輯的二次藝術創作是值得鼓勵的,也是必要的。
“經典文學作品的閱讀,往往需要讀者進行反復多次的細讀,或參照他人的批注詳解或心得,才能領會到作者的良苦用心。而電影一來針對的是盡可能廣的普羅大眾;二來其欣賞過程是有限的,電影主創需要在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內將故事敘述完畢,并且合理安排故事在不同時段發展、高潮與結束;第三,電影的欣賞是線性的、不可逆的,過于晦澀或與主題關系不大的描寫和次要線索往往會被導演刪去,或是轉化為直觀的鏡頭,將作者細膩的用心直接呈現給觀眾,避免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產生困惑。”[2]所以,在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視化的過程中,創作者還是要重視基于不同價值取向的受眾差異,尊重歷史和社會背景的客觀差異,并且正確認識本土化和視覺呈現本土風格的區別,以直觀的鏡頭展現原著的核心價值,突顯經典文學角色的核心魅力,在本土語境下講好世界故事,體現出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視化對文學推廣和培養受眾多元接受水平的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三、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的對策與建議
文學作品的影像化一直都是一個難點,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更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不僅和一般的文學作品改編一樣存在選材的問題,更牽扯到改編環節中對于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等的理解和接納問題。因此,在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的過程中,我們要基于現實,立足本土視角,全面看待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面對的問題,并提出探索方向的可能性。
首先,要抓住改編作品的文學內核。經典文學之所以成為經典,不僅因其優秀的文筆和細膩的人物刻畫,更因其中蘊含著跨越時代和國界的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內核。“英美經典文學作品歷來是英文電影的創作基礎,為電影改編提供了情節素材和人物對白,同時也使其自身通過電影再現從靜態的意義符號轉換成動態的視覺影像,擴展并深化了文學經典的傳播及影響。”[3]可以說,文學作品為影視創作提供了不盡的創作源泉,影視也成為文學作品傳播的重要推手。影視化的過程簡化了文學作品的閱讀入門,同時加速了文學作品面向更廣大受眾的推廣,抓住經典文學作品的核心價值有利于得到受眾的積極反饋。
其次,要學會善用元素。在影視化的改編中,要清晰地認識到本土元素和本土化的區別,本土元素是在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改編過程中加入本土風格的鏡頭、配樂、化妝及道具,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夠快速地使受眾建立起對于視覺呈現的美學接受,但是這樣的本土元素堆疊的缺點就是當視聽呈現與原著文學的核心價值出現沖突時就會加強這種突兀感,對受眾的信息接受造成干擾,從而使其對影片故事的邏輯性產生疑惑。要想克服這一點,我們就需要在本土化時善于挖掘文化和經驗的相通或相似之處,通過巧思使故事的可信度提升,在不影響原著小說核心構架的情況下進行替換和修正,讓故事合乎情理地發生于本土。
另外,還要意識到優秀文學作品影像化的現實價值。“不管是影視對文學的侵蝕還是文學對影視的漸趨認同,都會使文學與影視的獨立性面臨挑戰,而打破這一困境的出路是影視劇本具備更高的文學品格,以滿足觀眾對其更高的人文精神的需求。而文學家的堅守,尤其是大量優秀文學作品的產生才是影視作品達到更高水平的中流砥柱,在今天這個消費社會更需要文學經典提供有深度的價值理想和人文精神,來遏制影視往物欲和快感的無限度淪落。”[4]
最后,可以在劇作環節將故事背景、關鍵情節和驅動人物抉擇的內驅力進行本土化。在不對主線框架進行破壞性重構的情況下,合理利用承上啟下的、使故事發展和人物行為邏輯合理化的支線敘事,在不破壞故事原有敘事結構的情況下,通過“節外生枝”的安排交代背景并且使長線敘事合理化、本土化,還要考慮到當下受眾的文化背景,通過本土化的過程推動本土受眾對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審美觀念和接納能力的提升。
四、結語
綜上所述,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的路程注定是曲折的,抱著批判的態度回望固然是一種鞭策,但是我們更應該鼓勵勇于嘗試的前人,成功可以被當成經驗,但不能作為模板。文學的復雜與多樣性注定了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影像化的過程不能僅僅參照成功案例進行模仿,每部文學作品在人類文明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的點不盡相同,在摸索中總結出本土化的新路徑,重視每部文學作品獨特又寶貴的核心價值,才能更好助力外國經典文學傳播的大眾化,才能制作出更多優質的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本土改編電影,才能更好地推廣中國文化,在世界影壇上發出中國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