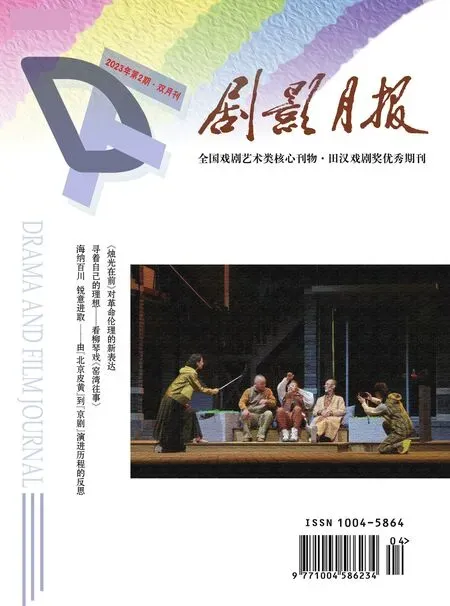愛恨情仇里的靈魂重量
——川劇《金子》賞析
■朱悅
《金子》改編自曹禺先生三幕戲《原野》,原作講述的是一個復仇的命運悲劇故事,經改編后搬上戲劇舞臺的《金子》,以金子的愛恨情仇作為故事主線,將原先的“復仇戲”改編成一部“情感戲”,圍繞金子、仇虎、焦大星三人相互交纏的命運,將故事中的每一個主人公都置于矛盾旋渦的中心點,在一連串的戲劇沖突中,刻畫人性的善與惡,描摹出金子背倚黑暗、心向光明的復雜獨特的靈魂。川劇《金子》作為一部戲劇改編作品,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提煉出濃郁的個人特色和地方特色,對于原著編劇有著自身獨特的想法和思考,在最終的舞臺呈現上完成了表現形式、主角人物和故事基調的完美嬗變,無論是文學性或是舞臺效果,都是優秀之作。
一、形式的轉變——從話劇到戲曲
一部作品的改編成功與否,當與它是否忠實或升華原著藝術精神、是否生動再現藝術形象、是否突出改編形式的藝術特色不可分割。從這個角度講,川劇《金子》完成了對于原作的再創造和與川劇藝術形式的完美融合,完成了從話劇舞臺到戲曲舞臺的轉變。鑒于戲曲舞臺篇幅的限制,相較于原著,編劇用極簡化的劇情設置,去不斷制造戲劇沖突,增加戲劇特色。川劇《金子》在題材規模和立意格局上都有所縮小,但這并不意味著人物形象的弱化;相反,在精簡了相對次要的枝節信息后,主要人物形象和主要矛盾更加突出。本劇的序幕以一場婚禮開始,伴隨著“老屋舊了,老屋朽了”的伴唱,一根紅綢猶如刑繩,將沒有愛情的金子與大星捆綁在一起,將除仇虎外的所有人物亮相于舞臺之上。金子看向身邊懦弱的焦大星向遠方疾呼“虎子哥”,而強行被牽在一處的焦大星也向著另一頭叫一聲“媽”,一下子將人物與矛盾沖突交代給觀眾,讓觀眾更容易進入戲劇的氛圍中。而后隨著仇虎一聲“我回來了”的宣言,一場“復仇”大幕在觀眾眼前徐徐展開,焦母的誘勸、焦大星的哀求、金子的勸阻,都在以愛為名的基礎上,將每一個人物逼上選擇的絕境,走向悲劇的結局。《金子》省去了細枝末節的交代,而用密集的劇情走向和戲劇沖突引發觀眾的共情,進而展現作者的立意。
川劇《金子》作為一部改編作品,在舞臺呈現上實現了與劇種的較好融合。作者在其中加入大量的民謠、童謠、俗語、川劇戲劇絕活兒,來體現地方特色、豐富劇情,完成了從話劇到戲曲,尤其是地方戲的完美轉變。值得借鑒的是,這些地域元素不是生硬地堆砌,而是巧妙地融入各個劇情發展和人物細節中。“郎是山中黃桷樹,妹是樹上常青藤,樹死藤生生纏死,樹生藤死死纏生”,表達了金子和仇虎的情真意切和悲劇命運,三人“扮家家”時的童謠,“真感情要命,假感情要錢”等俚語,都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而川劇的“變臉”“藏刀”又巧妙地嵌合在劇情發展之中,增加了戲劇的觀賞性。劇情以外,本劇在舞臺藝術上的二度創作,也為其最終的藝術呈現增添了亮色。除了劇情上的文學設計,《金子》的燈光設計和劇情巧妙地結合起來,使得舞臺效果豐富多元,給觀眾以強烈震撼。《金子》整體舞臺色調灰暗,除桌椅外的舞臺空間似乎都陷入無盡的黑暗。這時,燈光的“形象塑造”作用就顯現了出來。整部劇有兩處燈光變換給人強烈的印象。其一在第二場,焦母以巫術咒金子早死,燈光切換為詭異的綠光,配合焦母唱詞,集中表現焦母狠毒的人物形象;其二在第四場,三人喝酒憶童年,氣氛濃郁時,一束慘白的燈光打在焦大星變為焦閻王的臉上,一下子將溫馨的氣氛打回現實,舞臺上的人物情緒變化也因此變得飽滿。
二、主角的轉變——由仇虎到金子
川劇《金子》以女性人物命名,將重心人物由仇虎向金子轉變,作為一種創造性的改編。人物關系的改變使全劇的戲劇情節與矛盾沖突也隨之發生改變,弱化了仇虎“復仇”的人性扭曲,轉而放大了金子在對封建勢力反抗的“野蠻”里保持對“美”的向往,以仇虎“復仇”這個點,附著于金子的人生軌跡,組成叩擊她生命歷程的高潮。中心人物的轉移沒有弱化原著本身的藝術思想,仍然具有原作中展現出的強烈沉郁的悲劇色彩,將目光從原始野性的仇虎轉向反叛卻善良的金子。
《金子》作為一部女性的命運悲歌,在塑造金子人物形象和命運的悲劇性上,編劇利用幕間戲的設置以及人物的臺詞安排,運用一些預言式的表達方法,既讓劇情發展得更為流暢,也給劇中人物金子的結局抹上了一層宿命式的色彩。劇中大部分預言式臺詞都在幕間戲中,借由傻子這個局外人的嘴說出來,“虎來了”“虎拿了一把花”“要出事,要出禍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都是對未來劇情鋪展的預言式表達。另一處則體現在仇虎報仇的劇情中,“我要把你搶走”“一把火燒了了事”“我總是走不出這黑林子”“生個娃娃替我活”這樣的預言式表達,同樣加重了人物的悲劇色彩。其二是將“抉擇”的兩難轉移到了主人公金子身上。原作中,仇虎的兩難抉擇體現在復仇以及復仇之后的矛盾,從而展現仇虎在當時傳統倫理道德約束下受到的制約,體現其強悍的性格特質。而本劇將左右為難的境地設置在了女主人公金子身上,面對情感的糾葛,金子在丈夫與情人、愛情與責任中糾結輾轉,直到最終與仇虎走向“黃金鋪路”的地方,走向她的悲劇結局。劇情將人物一步一步推至絕境,在此亦難彼亦難的選擇里展現靈魂的重量,不斷加劇的戲劇沖突吸引著觀眾逐漸與人物共情,關注人物的最終選擇和命運歸屬,留給觀眾以思考。
三、基調的轉變——由野性到柔美
以仇虎為第一視角的《原野》誕生于廣袤荒涼的平原,充滿原始的張揚與野性,展現一種赤裸的生命力量。川劇《金子》在變化了中心人物后,戲劇基調也由男性的剛毅轉向女性的柔美。這首先體現在金子這個人物的塑造上。原作中的金子質樸熱烈,帶有幾分潑辣與艷麗,川劇中的金子則在保留了原作的剛烈之余,多了一點女性嬌柔的氣質。在與仇虎久別重逢時,金子的一聲問詢、一個擁抱就表現出一個熱烈坦率的女性形象,而在表現二人親熱時,金子調情的身段又將其嬌憨的氣質展露無遺。她明快爽利卻也端莊持重,她自信熱情卻又嬌憨柔媚。其次,它體現在作品整體風格的呈現上。川劇《金子》采用女性視角,強調了戲曲的寫意性表達。作者突破了原作對故事情節的重點刻畫,轉而以情節為依托,重點展示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和情感。金子的善、仇虎的險、焦母的狠、大星的懦,都融合在唱詞里、動作里、語言里,借由情節抒發出來。如金子、仇虎初遇時快活的音樂,金子受婆婆虐待、對生活無望時蓮花落的相融合,金子阻攔仇虎報仇時堅定有力的反抗,以及結局時金子守在將死的仇虎身邊悲涼的唱詞等,角色用“唱”來表達出自己的內心。尤其是在第四場中,焦母、大星、仇虎、金子,四個人集中在一處,將所有的矛盾沖突放在一處,四個人被命運推到了邊緣,唱詞也是一人一句、一句一減字,整個節奏加快,讓觀眾也隨著劇情漸入高潮而心跳加速,最后凝練到“殺留揪走”四個字上,也讓每個人不同的人物形象得到展現。基調的轉變還體現在《金子》的主題旋律上。相比于《原野》對命運的不屈抗爭,川劇《金子》則將目光對焦在情愛的纏綿里,勾畫了一幅具有煙火氣息的生活圖景,將原本人性和命運抗爭的吶喊變成愛恨情仇里凸顯出的善惡有別,以愛情作為故事基調,不僅中和了原作濃郁的“復仇”蠻性,且與現代觀眾的喜怒哀樂更為契合,在藝術表達上更接近當下觀眾的審美。
總體來說,川劇《金子》在現下的藝術舞臺上塑造出一個美麗而獨特的女性形象,從文學意義上,金子的“野”和“善”,她在面對愛恨情仇時的選擇,在絕境中閃耀出的人性光芒,在當今社會依然可以帶給觀眾以思考,給人性以啟迪;從戲曲樣式上,川劇《金子》的改編完成了從話劇到戲曲的完美嬗變,在改編作品中,如何完成對原作的理解與拓展、如何塑造人物的核心性格特征,如何加入濃郁的地方元素等,都可以在這部戲中找尋一些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