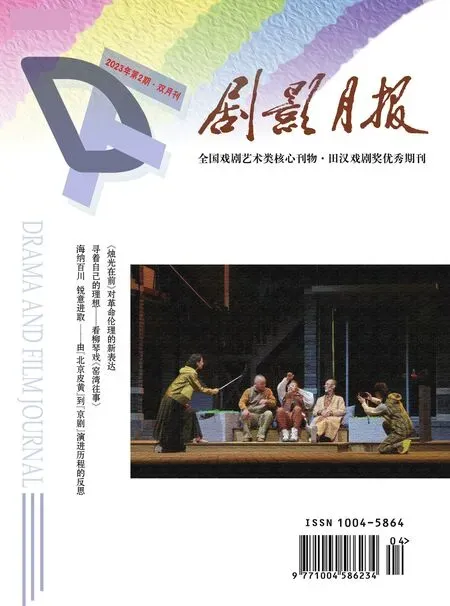從《網(wǎng)絡(luò)迷蹤》看桌面電影觀影之變
■陳樂(lè)
電影是現(xiàn)實(shí)、幻想、夢(mèng)境的三重奏:影像所呈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銀幕所構(gòu)筑的幻想、最終將觀眾帶入想象的王國(guó),為其打造一場(chǎng)又一場(chǎng)的白日夢(mèng)。然而桌面電影的出現(xiàn)打破了傳統(tǒng)的銀幕電影所建構(gòu)的想象王國(guó),將觀眾再度拉回象征界,麥克盧漢曾做過(guò)一個(gè)比喻:媒介的內(nèi)容好比一片滋味鮮美的肉,破門而入的竊賊用它來(lái)分散看門狗的注意力。只留意到“肉”而放過(guò)了“竊賊”的人,是懷著“技術(shù)白癡的麻木態(tài)度”。在對(duì)待傳統(tǒng)媒介時(shí),我們常常將如何使用媒介以及媒介所呈現(xiàn)的內(nèi)容視為至關(guān)重要的,卻忽略了媒介本身所蘊(yùn)含的豐富信息。僅僅留意到“肉”而放過(guò)了真正的“竊賊”是我們對(duì)待傳統(tǒng)媒介時(shí)所采取的錯(cuò)誤做法,這個(gè)生動(dòng)的比喻警示我們應(yīng)當(dāng)將目光從單一的媒介內(nèi)容轉(zhuǎn)移到媒介本身。在桌面電影的研究當(dāng)中,我們不容忽視的是“桌面”這種全新的形式所帶給受眾的全新體驗(yàn)感。
一、觀影情境:從銀幕到屏幕
吉爾·德勒茲在其著作《電影1:運(yùn)動(dòng)—影像》中提道:電影的力量在于電影過(guò)程與知覺(jué)思想之間的緊密結(jié)盟,電影不僅把運(yùn)動(dòng)置入影像之中,也把運(yùn)動(dòng)置入人腦之中。傳統(tǒng)的銀幕電影,將觀眾安置在電影院的座椅上,他們成為與嬰兒無(wú)二的視覺(jué)能力早熟但行動(dòng)能力并未完全獲得的個(gè)體,被電影院的座椅所牢牢捆綁,影院之中僅有的亮光投射在銀幕之上形成的圖像便成為觀眾的感官匯聚之處,受眾將自己代入其中,將銀幕上完滿的人物形象以及其所經(jīng)歷的奇特人生設(shè)想為自我,繼發(fā)過(guò)程和現(xiàn)實(shí)原則在這里讓位于初始過(guò)程和快樂(lè)原則。當(dāng)影院之中燈光驟暗,影像投射于銀幕之上時(shí),這一場(chǎng)的“白日夢(mèng)之旅”便開始了,所有的現(xiàn)實(shí)煩惱均被拋之腦后,影像此刻被深深地注入人腦之中,“想象的能指”所實(shí)現(xiàn)的觀影者虛幻的完滿感,主宰力和認(rèn)同性,是其他媒介難以企及的。
屏幕的概念在當(dāng)下主要指涉的是一些用于呈現(xiàn)彩色圖像的電器,在手機(jī)、個(gè)人電腦等屏幕上觀影,情境與銀幕有著很大的差別。首先從外部環(huán)境來(lái)看,不同于觀眾在影院時(shí)被座位所牢牢固定,在屏幕上觀看影片時(shí),沒(méi)有固定的區(qū)域,區(qū)域是自由且隨意的,觀眾可以隨處選擇自己的觀影場(chǎng)景,且存在諸多的干擾因素?zé)o法使其如同“銀幕前的嬰兒”任其擺布。其次就時(shí)間來(lái)說(shuō),在電影院觀眾必須遵守約定的電影開場(chǎng)時(shí)間進(jìn)場(chǎng)、退場(chǎng),而在屏幕上,觀眾可以自如地掌控影片的播放時(shí)間,暫停或者切換。再次,影院在“鑰匙孔的情境”之下,銀幕成為唯一的光源所在地,觀眾的感官全部聚集于銀幕,銀幕界面的唯一和確定性與屏幕的多界面信息呈現(xiàn)形成了差異。從觀眾自身出發(fā),時(shí)空的可選擇、可切換,屏幕界面的不唯一性,觀眾成了屏幕的掌控者,其從銀幕下被座椅捆綁的觀眾成了屏幕前主宰的智者,不再一味地沉浸于銀幕世界所提供的幻想。他們已經(jīng)從“具身化”感官化的被動(dòng)觀者變?yōu)椤叭ド砘敝切缘闹鲃?dòng)觀者。從銀幕到屏幕的轉(zhuǎn)變,使得受眾的認(rèn)知情境產(chǎn)生了巨大的變化。桌面電影以電腦屏幕作為鏡頭的拍攝對(duì)象,以桌面屏幕呈現(xiàn)的信息變化來(lái)完成敘事。在《網(wǎng)絡(luò)迷蹤》中,所有的故事都在桌面屏幕上展開,通過(guò)屏幕中諸多媒介呈現(xiàn)相關(guān)信息,幫助父親找到了女兒并將事件的發(fā)展經(jīng)過(guò)完整地呈現(xiàn)給觀眾。由于影片的敘事全部在電腦屏幕上展開,因此在電腦屏幕前觀看成了最佳選擇,影片在開始后的第一個(gè)鏡頭便是觀眾所熟悉的Windows系統(tǒng)的山水屏保,不少觀眾第一眼將其看成自己的電腦屏幕,而后出現(xiàn)的諸如待機(jī)畫面暗示著危機(jī)的來(lái)臨,無(wú)數(shù)跳出的彈窗,使得不少觀眾將其誤認(rèn)為自己的電腦屏幕,因此觀眾即便是在外部環(huán)境隨意多變的情況之下,還得以輕松地進(jìn)入“入片狀態(tài)”。反觀《網(wǎng)絡(luò)迷蹤》等桌面電影在院線上映時(shí),不少觀眾第一感覺(jué)即是突兀,巨大的電腦屏幕投射在銀幕之上,不同于以往熟知的視覺(jué)效果使得觀眾容易跳戲。桌面電影在屏幕前觀看相較于傳統(tǒng)的銀幕下觀看,受眾的注意力被最大限度地吸引,同時(shí)其“視覺(jué)體驗(yàn)”也得到了滿足。
二、感知方式:從白日夢(mèng)的旅行者到文本的解碼者
愛(ài)森斯坦在《蒙太奇論》中曾說(shuō)道:在所有這些鏡頭之間相互作用、吸引、排斥中,為觀眾的眼睛尋找最佳路線,把這種大量的間隙精簡(jiǎn)為一種簡(jiǎn)單的視覺(jué)平衡,一種最完善的傳遞影片基本主題的方式。在愛(ài)森斯坦的理論之中,蒙太奇作為電影藝術(shù)的基礎(chǔ),被暴力地傳遞給了觀眾,當(dāng)觀眾在影院坐下之時(shí),能夠最大限度地吸引觀眾注意力的方式早已被設(shè)計(jì),不論自愿與否,觀眾都將踏上這一趟“白日夢(mèng)之旅”,成為想象王國(guó)的旅行者。傳統(tǒng)銀幕無(wú)論是觀影情境抑或是影片文本本身都早已被設(shè)計(jì)好,觀眾在購(gòu)買電影票的同時(shí)也獲得“想象王國(guó)”的入場(chǎng)券。反觀桌面電影,在觀影情境發(fā)生巨大變化之時(shí),受眾在感知方式上將會(huì)產(chǎn)生何種變化呢?
(一)心智游戲的參與感
影片《網(wǎng)絡(luò)迷蹤》的故事主軸簡(jiǎn)單且明確,即父親尋找女兒的過(guò)程,然而通過(guò)多重懸念和反轉(zhuǎn)的設(shè)置,這樣一次極為尋常的女兒失蹤的故事逐漸發(fā)展成扣人心弦的懸疑故事。《解除好友1》中故事開始于尋常的網(wǎng)絡(luò)社交,即視頻電話之中,然而由于神秘人“勞拉”的加入,事態(tài)逐漸地失去控制,參與者相繼在“勞拉”的操控之下丟失性命。在影片之中,某些至關(guān)重要的信息被隱瞞或者模糊地呈現(xiàn),觀眾成了游戲的參與者。不難發(fā)現(xiàn),無(wú)論是在《解除好友》系列或是《網(wǎng)絡(luò)迷蹤》之中,桌面電影的建構(gòu)均呈現(xiàn)出了某些“心智游戲電影”的特征。游戲化文本的建構(gòu),使得觀眾全身心地參與其中,獲得類似于游戲的快感,這便是桌面電影在感知方式上給受眾所帶來(lái)的最直觀的感受,即心智游戲的參與感。分析《網(wǎng)絡(luò)迷蹤》的敘事結(jié)構(gòu),不難發(fā)現(xiàn)其與游戲時(shí)的闖關(guān)模式存在類似之處,即玩家獲得信息開始行動(dòng)、難度逐漸升級(jí)、玩家信息更新再行動(dòng)的模式。托馬斯·愛(ài)爾塞澤爾認(rèn)為心智游戲電影的一個(gè)重要特征即是迷惑觀眾的樂(lè)趣,且總體上觀眾不介意被玩弄。相反,他們樂(lè)于接受挑戰(zhàn),解決難題。在游戲闖關(guān)式的敘事模式建構(gòu)之下,觀眾不自知地便成為玩家,參與到影片設(shè)置的難題之中,尋找影片中被模糊化的關(guān)鍵信息。與傳統(tǒng)銀幕所建構(gòu)的一系列心智游戲電影相比較,諸如《黑客帝國(guó)》《香草天空》等影片主要是讓角色在多重空間之中來(lái)回穿梭,打破觀眾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固有認(rèn)知,亦不同于《記憶碎片》《搏擊俱樂(lè)部》中所建構(gòu)的精神失常的人物形象使得銀幕呈現(xiàn)其幻覺(jué)或是錯(cuò)覺(jué)。桌面電影立足于現(xiàn)實(shí)空間,建構(gòu)精神正常的角色,“游戲”體驗(yàn)的獲得以屏幕世界內(nèi)多樣化的信息媒介為渠道,輔之以多次反轉(zhuǎn)的敘事,同時(shí)屏幕前觀看的形式為受眾提供了暫停、反復(fù)觀看推敲的機(jī)會(huì),受眾在這種模式之中成了游戲的參與者。且由于“網(wǎng)生代”獨(dú)特的桌面屏幕經(jīng)歷,他們得以飛快地適應(yīng)這種“體系背后的迷宮通道和導(dǎo)航原則”,積極地參與到影片所設(shè)定的游戲之中,獲得影片文本的信息,成為文本的解碼者。
(二)一屏之隔的沉浸式體驗(yàn)
傳統(tǒng)的銀幕電影從生活之中提煉精彩片段,加之與現(xiàn)實(shí)本身無(wú)限的接近性使得觀眾沉浸于其中,因此再現(xiàn)現(xiàn)實(shí)成了影片拍攝時(shí)的首要目標(biāo),為此電影人進(jìn)行了不斷的探索,燈光、攝影、場(chǎng)景、剪輯、聲音等多個(gè)方面,形成了一套又一套的“縫合系統(tǒng)”,將觀眾縫合于其中。然而桌面電影在視聽表現(xiàn)上與之大相徑庭,其所營(yíng)造的不再是一套又一套的“縫合系統(tǒng)”,觀眾的感知體驗(yàn)不再依賴于獨(dú)特的光影以及縫合鏡頭所構(gòu)建的真實(shí)可信的世界,不再通過(guò)架構(gòu)還原時(shí)空的橋梁。通過(guò)屏幕,影片以一種鏡面反射式的呈現(xiàn)方式以及主觀視角直接讓觀眾產(chǎn)生與角色僅一屏之隔相互對(duì)話交流的體驗(yàn),觀眾形成了與角色宛如面對(duì)面的交流感。在這種鏡像觀看所形成的交流感以及屏幕所營(yíng)造的一系列類似于“我看”“我想”的主觀鏡頭,使觀眾獲得了沉浸式的體驗(yàn),這與傳統(tǒng)的銀幕電影所帶給觀眾的體驗(yàn)形成了巨大差異。
1.鏡像交流
鏡面反射式表演是創(chuàng)作者在場(chǎng),通過(guò)移動(dòng)終端諸如手機(jī)、電腦等,進(jìn)行自我拍攝的一種創(chuàng)作方法,觀眾在桌面電影中觀看到的大部分的呈現(xiàn)方式都是鏡面反射式的,主要有自拍和視頻聊天兩種方式。人類的感性認(rèn)識(shí)方式是隨著人類群體的整個(gè)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改變的,隨著移動(dòng)網(wǎng)絡(luò)的發(fā)展,媒介及屏幕充當(dāng)了人的視知覺(jué)以及神經(jīng)系統(tǒng),將其延伸,視覺(jué)和神經(jīng)系統(tǒng)啟動(dòng)了“接線程序”,看著屏幕之中的“他者”,觀眾與鏡中的“他者”形成了一種鏡像觀看模式。當(dāng)“他者”面對(duì)屏幕說(shuō)話時(shí),交流感也就此建立,這樣,觀眾得以與“他者”產(chǎn)生情感上的共鳴,對(duì)“他者”所呈現(xiàn)的事物產(chǎn)生情緒。諸如在《網(wǎng)絡(luò)迷蹤》中通過(guò)Margot的社交平臺(tái)所呈現(xiàn)的一系列其自拍視頻,觀眾得以知道小女孩真實(shí)的心理感受和社交狀態(tài),同時(shí)也為觀眾參與到影片當(dāng)中觀察影片所透露的細(xì)節(jié)和疑點(diǎn)提供了情境。通過(guò)鏡面反射式的表演,“縫合系統(tǒng)”已無(wú)處遁形,角色之間的對(duì)話、信息的傳遞不再通過(guò)正反打鏡頭進(jìn)行表現(xiàn),屏幕之上“缺席者”已然消失,這是桌面電影鏡面反射式表演所帶來(lái)的全新變革,正是在這種鏡像觀看當(dāng)中,觀眾與角色之間得以建立強(qiáng)大的溝通橋梁,給觀眾營(yíng)造了一種“交流”的假象。
2.情感傳達(dá)
傳統(tǒng)的銀幕電影在其拍攝的進(jìn)程之中,攝影、表演等多方面都必須以一個(gè)“缺席的在場(chǎng)”即將來(lái)觀眾的觀看為前提,同時(shí)又務(wù)必充分地實(shí)踐一個(gè)假定,并沒(méi)有人在看,是故事在自行涌現(xiàn),故事的自行涌現(xiàn)依賴于影片所構(gòu)建的是時(shí)空、鏡頭之間的無(wú)縫組合,同時(shí)在人物視角上采用第三人稱來(lái)講述故事,或者虛擬一個(gè)人物講述他的主觀視角。這樣的人物在影片之中是斷然不可能出現(xiàn)的,因?yàn)樗某霈F(xiàn)將會(huì)導(dǎo)致角色與觀眾的直接對(duì)視,觀眾將會(huì)瞬間從“想象王國(guó)”之中跌落。觀眾得以沉迷于影片之中,與影片建立情感溝通的橋梁均源于這些暗藏影片之中的“縫合系統(tǒng)”,然而桌面電影的情感傳達(dá)完全有別于銀幕電影,由于不在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之中展開故事,因此它無(wú)須顧及時(shí)空的連貫性,角色開始直視攝像頭,同時(shí)角色本身在影片之中又再度出現(xiàn)在屏幕上,在這一系列“破壞縫合系統(tǒng)”的操作之中,桌面電影的信息乃至人物的情感又是如何傳達(dá)給觀眾的呢?這得益于桌面電影所提供的屏幕,以及屏幕之上呈現(xiàn)的諸如自拍、攝像頭、視頻等視角模擬人物的主觀鏡頭,角色的內(nèi)心狀態(tài)、心理活動(dòng)通過(guò)屏幕完美地呈現(xiàn)出來(lái),完成了情感的傳達(dá)。《網(wǎng)絡(luò)迷蹤》中,6分30秒處父女二人的聊天對(duì)話框呈現(xiàn)之初,伴隨著大特寫,Kim詢問(wèn)Margot是否忘記了什么,在6分40秒時(shí)轉(zhuǎn)換成中景,屏幕的輕微抖動(dòng)和起伏模擬角色的頭部運(yùn)動(dòng),在6分50秒之時(shí),Kim等不到滿意的答復(fù),于是刪掉了對(duì)話框想給予Margot提示的想法,立刻發(fā)起了視頻。在這短暫的20秒鐘之內(nèi),觀眾不再需要通過(guò)演員的自白或者時(shí)不時(shí)插入的旁白來(lái)了解角色的內(nèi)心狀態(tài),而是通過(guò)景別的變化,以及屏幕界面信息的呈現(xiàn),角色的內(nèi)心狀態(tài)被完美地表現(xiàn)出來(lái)。影片的結(jié)尾段落與開頭形成對(duì)稱一般,父親的主觀視角再次呈現(xiàn),94分鐘30秒呈現(xiàn)大特寫,而這次不再是怒氣沖沖的父親想找女兒算賬,而是詢問(wèn)女兒的鋼琴課是否有消息。94分45秒時(shí)轉(zhuǎn)換成為中景,變成了女兒的主觀鏡頭,通過(guò)景別的切換,桌面電影利用屏幕界面之間的相同性輕松地實(shí)現(xiàn)了主觀視角的切換。鋼琴課的重新申請(qǐng),正視母親的離世,父女二人的隔閡就此打破。通過(guò)開頭結(jié)尾兩次對(duì)稱性的主觀鏡頭的呈現(xiàn),觀眾得以清晰地感知到父女二人之間的情感變化,以及角色們的心理狀況,移情作用得以產(chǎn)生。
桌面電影通過(guò)構(gòu)建一種游戲化的敘事,輔之以獨(dú)特的影像,諸如鏡面反射式表演和主觀化的視角呈現(xiàn),使得觀眾在遠(yuǎn)離電影院,擺脫一場(chǎng)白日夢(mèng)之旅時(shí),同樣也產(chǎn)生移情作用的機(jī)制,從“旅行者”成為影片的“參與者”,參與到了這一場(chǎng)桌面游戲當(dāng)中,成為文本的“解碼者”。
三、信息傳遞:從現(xiàn)實(shí)世界到“賽博空間”
電影本身作為技術(shù)和工業(yè)資本現(xiàn)代化的一部分,在影像內(nèi)容的建構(gòu)上又無(wú)限趨近于現(xiàn)實(shí)——“電影媒體即是現(xiàn)實(shí)本身”,同時(shí)在影院內(nèi)部真實(shí)的物理空間之中又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鑰匙孔情境,傳統(tǒng)銀幕電影無(wú)論是從其產(chǎn)生條件、建構(gòu)的機(jī)制還是影像本身都發(fā)生在現(xiàn)實(shí)世界當(dāng)中。觀眾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之中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受到電影機(jī)構(gòu)的影響,作為外部機(jī)器的電影工業(yè),內(nèi)部機(jī)器的觀眾心理學(xué)以及第三機(jī)器的電影批評(píng)、觀念等,電影機(jī)構(gòu)所創(chuàng)建的一種讓觀眾自愿來(lái)影院的機(jī)制,均被部署在了真實(shí)的時(shí)間與空間之中。因此觀眾在傳統(tǒng)影院之中銀幕上呈現(xiàn)的內(nèi)容來(lái)自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觀眾觀影感的產(chǎn)生依賴于影院所提供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影像呈現(xiàn)給觀眾的所有信息都依賴于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空。然而桌面電影與銀幕電影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讓觀眾從現(xiàn)實(shí)世界來(lái)到了“賽博空間”,屏幕影像表現(xiàn)的是“賽博空間”,觀眾的信息接收途徑是個(gè)人電腦屏幕,觀眾對(duì)于影像的認(rèn)識(shí)不再基于現(xiàn)實(shí)世界和銀幕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而是通過(guò)虛擬世界和屏幕二者之間的連接。
建構(gòu)“賽博空間”這一概念最開始由小說(shuō)家威廉·吉布森提出,其小說(shuō)《神經(jīng)浪游者》之中他提到一種存在高度交融性的信息媒介,這種媒介的產(chǎn)生來(lái)自個(gè)人計(jì)算機(jī)和計(jì)算機(jī)互聯(lián)網(wǎng)的建立,他將通過(guò)這種媒介所建構(gòu)的虛擬現(xiàn)實(shí)世界稱為“賽博空間”。在“賽博空間”中呈現(xiàn)出許多完全不同于現(xiàn)實(shí)空間的特征,影像的建構(gòu)不再依賴于光、影、聲等現(xiàn)實(shí)因素,信息的傳遞不再僅限于傳統(tǒng)的媒介。那么觀眾在“賽博空間”中又是如何獲取信息的呢?當(dāng)影像的呈現(xiàn)不再依靠于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時(shí),信息又是如何在浩瀚的網(wǎng)絡(luò)世界之中傳遞的?
(一)“賽博空間”的暢游
在傳統(tǒng)電影的創(chuàng)作之中,大多表現(xiàn)的是同一時(shí)間、同一空間之下涌現(xiàn)的故事,時(shí)空的同一性為敘事的真實(shí)可靠性以及觀眾與影片之間產(chǎn)生共鳴提供了前提和基礎(chǔ)。然而在桌面電影之中超越了時(shí)空的局限性,在二維顯示屏之中通過(guò)多空間同一時(shí)間的組合彌補(bǔ)了二維平面所缺失的空間感。這種超時(shí)空的實(shí)現(xiàn)得益于“賽博空間”作為一種特殊的媒介,不同于其他的“自然媒介”,接收者必須使用視覺(jué)和聽覺(jué)等感官系統(tǒng)來(lái)接收并且解碼這些信息,這也解釋了為何傳統(tǒng)的銀幕電影必須保證時(shí)空的同一性,只有在時(shí)空同一性的條件之下,接收者才可以通過(guò)視聽等感官系統(tǒng)接收信息。其超越了“自然媒介”所帶來(lái)的時(shí)空局限性,在“賽博空間”之中,聲音、圖像等信息可以被編碼以及儲(chǔ)存,不再需要通過(guò)“自然媒介”來(lái)進(jìn)行傳播,接收者可以隨時(shí)徜徉在“賽博空間”中。“賽博空間”之中不排斥任何個(gè)體加入,為觀眾的暢游提供了條件,同時(shí)其裹挾著巨大的信息量將觀眾包裹,在《網(wǎng)絡(luò)迷蹤》中,通過(guò)被儲(chǔ)存的聲音、圖像、視頻等一系列包含巨大信息量的媒介,我們可以快速且清晰地了解到Margot一家曾經(jīng)的情況,以及母親去世后父女二人目前的生活狀況。在短短的10分鐘之內(nèi)跨越了10年之久的時(shí)間同時(shí)給觀眾呈現(xiàn)出了巨大的信息量,桌面電影在擺脫時(shí)空束縛的同時(shí)給予了觀眾直觀可視的信息,使得故事的講述更為可靠。而父親也通過(guò)這個(gè)儲(chǔ)存巨大信息量的“空間”,找到女兒Margot所儲(chǔ)存的直播視頻,帶領(lǐng)著觀眾一步步破解謎團(tuán)。受眾被巨大的信息所包裹,同時(shí)在自身的意愿之下暢游于“賽博空間”之中。
(二)信息傳遞——虛擬主體
康德割裂了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黑格爾將主客體辯證統(tǒng)一起來(lái),而在阿爾都塞的筆下,主體更是成為國(guó)家機(jī)器的馴服臣民。主體的概念歷經(jīng)了多年的演變到當(dāng)下被認(rèn)為“主體是社會(huì)存在和心理存在的統(tǒng)一體”。而虛擬主體的概念則可以理解為在由互聯(lián)網(wǎng)所建構(gòu)起來(lái)的虛擬空間之中進(jìn)行“隱身交往”的主體。桌面電影之中角色身為“虛擬主體”,其實(shí)身體隱藏在文字、表情等符號(hào)之后,即便是在視頻聊天之中,所呈現(xiàn)的身體,也不過(guò)是一種數(shù)字信息匯合。虛擬主體消解了恒定的主體,以符號(hào)來(lái)建構(gòu)自身。譬如在《解除好友2:暗網(wǎng)》中,主角撿到了電腦,電腦的用戶名是一個(gè)問(wèn)號(hào)而密碼也是,這一符號(hào)被主人公所破解,而真正的這臺(tái)電腦的主人,一直戴著黑色的頭罩在威脅傷害主角一伙人。被符號(hào)所代替的用戶名,蒙面的威脅者,象征著在“賽博空間”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威脅,沒(méi)有特定的指控對(duì)象,觀眾在觀看此類影片時(shí)會(huì)不自覺(jué)地感受到來(lái)自這一虛擬空間的危害。與傳統(tǒng)的銀幕電影相比較,雖然觀眾在面對(duì)二者之時(shí),都知道故事是虛構(gòu)的,但是在銀幕之上所發(fā)生的離奇的、玄幻的故事,難以甚至無(wú)法找到在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之中的對(duì)應(yīng)體。反觀桌面電影,故事是虛構(gòu)的,但是這些被演繹的故事在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之中完全存在發(fā)生的可能性。《網(wǎng)絡(luò)迷蹤》中通過(guò)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尋找女兒的父親,《解除好友1》中受到網(wǎng)絡(luò)暴力的青少年們,《解除好友2:暗網(wǎng)》中不幸卷入暗網(wǎng)的人們以及維持并進(jìn)行黑色交易的地下網(wǎng)絡(luò)市場(chǎng),這些都切實(shí)地在我們的實(shí)際生活之中存在著,即便故事發(fā)生在虛擬的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之中,接收這些信息的人不得不引起警覺(jué)。
通過(guò)對(duì)于桌面電影的考察,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桌面電影已經(jīng)在審美機(jī)制、視聽美學(xué)上產(chǎn)生了顛覆性的變革,電影的誕生使我們超越了機(jī)械論,轉(zhuǎn)入發(fā)展和有機(jī)聯(lián)系的世界,而桌面電影所帶來(lái)的變革使得我們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聯(lián)系再次發(fā)生了轉(zhuǎn)向,桌面電影將觸角延伸至無(wú)限寬廣的“賽博空間”,為影像的建構(gòu)提供了嶄新的美學(xué)形式,但是桌面電影的拍攝也表達(dá)了人類對(duì)于屏幕媒介的一種反思,當(dāng)今絕大多數(shù)人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對(duì)于媒介影響潛意識(shí)的溫順的接受,使媒介成為可能囚禁其使用者的無(wú)墻的監(jiān)獄,如果真如同布萊克所言,技術(shù)將人分割,成為人體器官的一種自我截除,人本身內(nèi)在的東西得以外延、延伸,人終將會(huì)成為其外延物的傀儡。那么分析桌面電影之后,媒介本身作為一種信息,所反饋的社會(huì)現(xiàn)狀和焦慮更是我們應(yīng)當(dāng)警惕的,媒介本身對(duì)于人的催眠能夠使人淪為傀儡,是桌面電影帶給每個(gè)人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