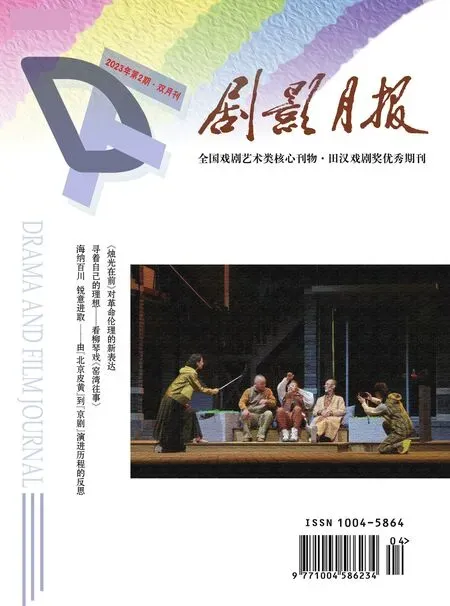結構主義神話學視域下《犬之力》的二元論分析
■韋璐
新西蘭導演簡·坎皮恩的新作《犬之力》,又譯名《犬山記》,是根據作家托馬斯·薩維奇1967年出版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影片背景設置在1920年的美國西北部蒙大拿州,粗獷的西部風光與片中細膩壓抑的情感交織,流暢的鏡頭語言與精準的場面調度搭配,讓簡·坎皮恩不僅摘得威尼斯銀獅獎、美國金球獎,也將第94 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收入囊中。《犬之力》中的二元論理念與結構主義神話學思想不謀而合,列維施特勞斯神話學思想為電影的意義闡釋提供了學理支撐。電影作為現代世俗神話,背后蘊含著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把握其整體結構有利于闡釋其背后的深層意義。
一、結構主義神話學
結構主義理論作為電影敘事學理論的重要分支,在電影理論及批評實踐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雖然結構主義來自索緒爾在語言學上的開創性研究,但列維施特勞斯大膽地將索緒爾的方法運用在人類學上,“他將人類關系看作某種適用于語音學問題分析的語言,從而使得把結構語言學邏輯擴展至所有社會的、思想的、藝術的現象與結構中成為可能。”列維施特勞斯作為“結構主義之父”,通過對古希臘神話傳說的語言表象研究,挖掘無意識的深層結構,整合出一個共同的意義內核,并將二元對立的模式以及中間調解者為核心的神話結構作為理論的分析方法,將二元論的理念擴展成為一般人類文化體制的組織原則。他認為,神話的構成要素像語言的構成要素一樣,只有在和其他要素的關系中,才能獲得意義,只有在建構對立的基礎上,才是可以理解的。
二、《犬之力》中蘊含的二元對立關系
(一)主體與客體的對抗
影片開篇借菲爾之口,以古羅馬建城、母狼育嬰的神話傳說來預示兄弟二人的結局。神話傳說中,特洛伊首領的后代羅慕路斯和雷穆斯尚在襁褓之中,被篡權者丟棄在臺伯河邊,后經母狼哺育、牧羊人收養,成長為羅馬的奠基人。電影中菲爾將布朗柯·亨利比作“母狼”,以示對他和弟弟的“哺育”之恩,亨利教他們騎馬、經營牧場。菲爾將亨利視作自己精神上的哺育者,由此對他產生了超越性別的感情,這種感情中有“父子”之間的舐犢之愛,也有戀人之間的情意綿綿。菲爾壓抑的情感源于母親對兄弟二人的管束,母親在他們有性意識時,將牧場里的所有女孩趕走。從弗洛伊德的觀點來看,“對于青年男子來說,在青少年時期完全禁欲,并非最好的選擇”。如果正常的性欲望得不到滿足,將會加大同性戀的概率。“由于成年時期原欲的主要流向受阻,被迫另辟蹊徑”。另外“禁欲只能產生一些順從的弱者,他們不免泯然眾人,被迫接受強者的擺布”。禁欲的弊端顯現出來,兄弟二人中,哥哥菲爾最終將欲望指向男性,變成同性戀者,而弟弟喬治的欲望對象雖然是女性,但是由于長期的禁欲和哥哥的打壓,喬治變成了順從的弱者,難以完成大學學業,孤獨并且渴望親密關系,只能被迫接受強者菲爾的擺布。兄弟之間由此構成一種二元對立關系,菲爾作為主體,利用諷刺、挖苦等手段,使弟弟處在客體、他者的位置,力圖把他壓制到奴役狀態來達到自我完善。這種主奴關系一旦確立,自我意識就成為自在自為的存在,在主奴關系中,“承認”是其關鍵詞。根據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主體具有獨立的意識,是一種自在自為的存在,主體需要他者的承認來完成自我。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他者的客體也感到自身是本質,而主體變成非本質。
影片中兄弟二人的辯證關系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喬治結識蘿絲之前,他逆來順受,聽從哥哥擺布。他們成年已久,卻共用一個房間,說明哥哥作為一個主體,表面囂張跋扈,但是內心依賴弟弟,需要弟弟的承認。而弟弟雖然厭倦了這種生活,卻不敢提出公開的要求,說明弟弟性格軟弱,恰好滿足了主體對客體的控制欲望。二是喬治結識蘿絲后,他開始反抗哥哥的控制,菲爾的主體地位開始動搖。兄弟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隨著喬治結婚而瓦解。喬治之所以迅速和蘿絲完婚,一方面是為了擺脫哥哥的掌控;另一方面,喬治在蘿絲那里得到了“承認”,獲得了愛與尊嚴,“愛和承認相關,愛可以對主奴這種永恒的二元政治結構進行反思性的批判”。影片中蘿絲在山岡上教喬治跳舞,由于多年的壓迫,喬治已經形成慣性的自我否定——“我做不到”,蘿絲一直鼓勵、支持喬治,所以那一刻喬治淚流滿面。他不再孤單,他終于作為獨立的價值獲得認可,由之前“奴性”的壓抑變為“人性”的滿足。
影片中菲爾是耶魯畢業的高才生,喬治是大學未讀完的“爛仔”,從知識層面來看,菲爾是文明的,喬治是野蠻的。但從社會角度看,菲爾的行為充滿了原始性,在泥潭里洗澡,閹牛不戴手套,學過古典文學,但經常口吐芬芳,脾氣暴躁,人際關系緊張,他從不壓抑自己的動物性,盡可能地展現人的本能。喬治則西裝革履、生活精致、善于社交,體現出了良好的教養,并且積極擁抱現代文明。這種“二元對立”模式不僅體現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兄弟二人的牧場經營理念也存在分歧,菲爾固守傳統,25 年來一直遵循著布朗柯·亨利的管理原則,并奉為圭臬。喬治則主張現代化經營,積極開展合作。回到開篇母狼育嬰的神話傳說,羅慕路斯和雷穆斯長大后,在母狼喂養他們的臺伯河畔大興土木,建立新城。但在新城的冠名權上,兄弟二人發生爭執,最后羅慕路斯將雷穆斯殺死,以“羅慕路”命名新城,盡管古典作家對羅馬建城的細節有所爭議,但雷穆斯之死是兄弟二人爭奪統治權的結果這一點無可置疑。影片借助神話來隱喻兄弟二人的命運,菲爾的死雖然不是喬治直接造成的,但是也與喬治相關,并且在菲爾的葬禮上,喬治表現出的冷漠似乎是一種解脫,也是漠視血緣關系的表現。兄弟二人中,一個固守傳統,一個擁抱未來,可想而知菲爾死后,喬治接管牧場,會以全新的方式經營。影片中多次出現火車穿過牧場的畫面,預示著現代工業文明對粗放式牧場經營的沖擊,以及美國中西部牧場社區必將消亡的事實。
(二)男性與女性的較量
“神話”中充滿了“二元對立”,反映著“二元對立”,也試圖調和與解決這種“二元對立”的沖突。在研究方法上,施特勞斯運用了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method of dialectics)來分析“神話”。他認為,“神話”經常通過“第三因素”的引入來解決二元對立的沖突,通過尋找一個適當的“中間調解者”來完成對對立的兩者的揚棄,以便在更高的層面進行綜合。電影中蘿絲的出現彌補了喬治心理上“承認”的缺位,消解了兄弟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作為中間調解者,她與菲爾構成新的二元對立關系,即男性與女性的對立,抑或說父權社會中家長制家庭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蘿絲作為女性只能被動承受。
傳統的父權制觀點認為,這個世界總是屬于男性的,男性始終處于主導地位,他們是女性的主宰,是社會的主宰。女人只是權力的媒介,而不是權力的掌控者,從封建社會至今,女人的命運始終與私有制密切相關。蘿絲在未和喬治結婚之前,自己操持著飯館,要面對醉酒難纏的客人,日子艱苦而拮據,但是在自由勞動中,她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起到了經濟和社會的作用,此時的蘿絲作為寡婦,有著與男人同樣的權利。和喬治結婚之后,她搬進了牧場,過上了寄生的生活。對蘿絲來說,結婚是最體面的生涯,她依仗婚姻進入高于她的階層,這個奇跡是她工作一輩子也不能帶來的。但是凡是利益背面總有負擔,如果負擔太重,利益就無異于束縛。蘿絲進入喬治家后,處處受到菲爾的針對,蘿絲只能以順從來補償她的無所事事,經濟不獨立,女性勢必受到男方的壓制。從于父權制視角來看,男性與女性的婚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男性結婚不需要離開原生家庭,而女性則要離開原生家庭,入住男方家里。“在血統形態變動的后面,入住夫家的常規表明了人類社會特點的兩性不對等的基本關系。”這種不對等關系是因為婚姻制度將女性作為附屬品,從屬于丈夫。從夫居制是男權社會的產物,女人被無情地犧牲給私有制,丈夫掌握的財產越多,對女人的奴役就越嚴格,男人在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越是強大,他便越有權威,越起著家長的作用。女人由此處于他者地位,服務于男性的經濟利益。
電影中蘿絲受到的壓迫并非來自丈夫喬治,而是來自“大家長”菲爾。菲爾作為牧場主,家境殷實,聰明能干,受人尊敬,影片中菲爾出場時閑庭信步地進入畫框中,展現出他的自信以及掌控一切的態度,隱喻著父權制象征秩序的要求。喬治結識蘿絲后,開始反抗哥哥的控制,代表著一種“失序”。在菲爾眼里,蘿絲是一個精明且偽善的女人,和弟弟結婚是看中了家中的財產。面對逐漸失控的一切,他要予以回擊。當菲爾與蘿絲兩人出現在畫面中時,菲爾始終處于高位,蘿絲在一樓彈琴,菲爾在二樓利用班卓琴干擾;蘿絲在雜貨堆里找酒喝,菲爾在二樓吹口哨調侃。畫面中菲爾處于被仰視的地位,并且占據了極大的畫面空間。畫面空間可以作為家庭空間的延伸,說明菲爾在這個家里具有極大的話語權,并且受人仰視。而蘿絲則處于低位,并且在和菲爾的對抗中始終占據畫面左下角或右下角逼仄的位置,給人一種壓抑和窒息的感覺。導演通過這種位置的高低不對等,暗示著男女關系得不對等以及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冷暴力。蘿絲沒進入牧場之前,喬治為了和她約會不顧哥哥的反對開著車揚長而去,菲爾只能用抽馬來發泄憤怒。蘿絲進入牧場以后,正是從夫居的婚姻制度,給菲爾提供了報復的條件。作為家長制家庭中的掌權者,“懲罰”是在極其狹隘的空間里發展起來的,它是強權者、家長的反映,是菲爾因為自己的命令和禁令遭到蔑視而表達出來的憤怒。蘿絲為了迎接州長和公婆,努力練琴,菲爾卻輕松彈奏出蘿絲的練習曲目,家庭晚宴上,面對菲爾的嘲諷,蘿絲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
從蘿絲的角度來看,她作為女人,在公婆面前小心謹慎,和傭人們打成一片,只不過是想融入這個家庭。面對強權者菲爾的精神折磨,懦弱成性的喬治并不能為妻子遮風擋雨,蘿絲酗酒、焦慮、神情恍惚,都是男權社會對女性壓迫的表現。面對菲爾的高壓,蘿絲做出的最后反抗就是將牧場里的牛皮賣給了印第安人換得一副手套,蘿絲拿著手套在夕陽下哭泣,有反抗的喜悅,也有解脫的釋然。在影片中,“手套”是一種隱喻,也是一種保護機制,是蘿絲保護自己的象征,即使躺在病床上也不能摘下它,因為這是她安全感的來源。與蘿絲形成對比的是,菲爾為了凸顯自己菲勒斯主義者的特質,勞動時從來不戴手套,他的手粗糙而布滿傷口,而這也為菲爾的死埋下了禍根。在父權制社會里,女性始終處于被壓制和排斥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要求,她的一切應有的權利都被壓抑或剝奪了,她被迫保持沉默。在性別的二元對立較量中,菲爾以其強大的霸權地位壓制住蘿絲,贏得了勝利,維護了男權的中心地位與話語權。
(三)陽剛與陰柔的廝殺
“父親去世后,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母親能幸福,如果我不去救她,如果我不去幫助母親,我還算什么男人”,這是影片開頭的旁白,隨著劇情的展開,觀眾知道旁白來自蘿絲的兒子——彼得。影片中彼得對母親的感情很微妙,承諾讓母親住新居并且不為生活操勞,有時會以曖昧的態度直呼母親的名字,說明彼得具有強烈的俄狄浦斯情結,并且極度重視親情。在菲爾與蘿絲的性別二元對立關系中,蘿絲受盡了精神折磨。為了保護母親,彼得作為“第三因素”開始接近菲爾。彼得的出現消解了菲爾與蘿絲的二元對立關系,作為“中間調解者”,他與菲爾形成新的二元對立關系,即從男性氣質來講,陽剛與陰柔的對立。在這場博弈中,具有閹割氣質的彼得,將充滿男性霸權氣質的菲爾反殺,完成了“弒父”的過程,最終成長為男人。
如果說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是顯性的,那么對男性的壓迫則是隱性的。“男性是一個享受父權制特權,并通過壓迫女性他者和壓抑自身女性氣質進行自我定義的特權集團..”男性因為是父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會忽略父權制度對男性性別角色的傷害與束縛。男性在成長過程中,要忍受孤獨、痛苦才能獲得男子氣概,而一旦展現出一點女性氣質或者同性戀傾向,就會處于邊緣化的位置,受到排斥;男子成年后,要承擔家庭責任,獨自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不能輕易表露情感,“男兒有淚不輕彈”背后蘊含的社會建構與權力話語關系,都是對男性隱形的壓抑,而所謂的“男性氣質”,不過是父權文化把男性身份作為權力的運作對象,為了維護男性特權而建立的意識形態。
影片中亨利去世后,菲爾以暴戾和邋遢的形象來展示自己的男性氣質,以隱藏自己的男同身份。父權社會的規訓讓菲爾對自己的身份焦慮不已,只能不斷對著遠山和亨利留下的馬鞍顧影自憐。菲爾表面上為人刻薄,要控制、馴服一切,但內心卻敏感、細膩且脆弱,在意周圍人的看法。阿蘭·德波頓在其著作《身份的焦慮》中寫道:“人類對自身的價值判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的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完全受制于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評價。”面對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菲爾陷入男性性別角色焦慮之中,“厭女”特質,隱匿山中小木屋里的裸男雜志,獨自在河邊用絲巾懷念亨利,這些都是他懼怕世俗眼光的表現。菲爾只有不斷地壓抑情感和訴諸暴力,以“陽剛”氣質來塑造男性力量,緩解男性性別角色的危機。相對于菲爾的隱藏,彼得從不壓抑自我,反而直面自己男性性別中的“陰柔”氣質。剪紙花、轉呼啦圈、用梳子緩解壓力,進入牧場后面對牛仔們的嘲諷,他依舊保持自我。彼得看似柔弱纖細,充滿了女性氣質,但實則陰狠涼薄,內心充滿力量。“知子莫若父”,彼得的父親擔心他太過冷漠不夠善良,而菲爾卻被彼得外表的“陰柔”氣質欺騙,覺得他單純善良,有點“娘娘腔”,需要調教才能成長為男人。對于菲爾來說,從彼得認出了犬形山影那一刻,他似乎找到了那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另一半,從而拉近了兩人之間的心理距離。菲爾教彼得騎馬,完成了一個身份的轉變,他將對亨利的感情投射到彼得身上,是“父”與“子”的傳承,而彼得接近菲爾的背后卻暗藏殺機。
影片中菲爾外表“陽剛”、內心“陰柔”,彼得外表“陰柔”、內心“陽剛”,他們身上都兼具男女兩性的性格特質,而這也是遠古神話原型“雌雄同體”的折射和映象。“從遙遠而無法記憶的時代起,人類就在自己的神話中表達過這樣一種思想——男人和女人是共存于同一軀體中的,這樣一種心理直覺往往以神圣的對稱形式,或以創造者身上具有雌雄同體這一觀念形式外射出來”。柏拉圖《會飲篇》中,阿里斯托芬講述了關于“陰陽人”的神話就是最好的例證。弗洛伊德則從解剖學角度闡釋了一定程度的雌雄同體本身就是正常的,一個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不可能是完全的男性或女性,更像是兼具兩性的混合體。導演通過“雌雄同體”的形象建構,打破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俗套刻板化印象,而審查所謂的男性陽剛氣質與女性陰柔氣質的同時,說明性別身份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和文化共同作用下的建構物,性別身份的實質是一種裝扮和表演,作為同性戀的菲爾可以通過陽剛氣質來冒充直男,而“娘娘腔”彼得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女性氣質扮演同性戀誤導菲爾。“雌雄同體”作為一種區別于傳統社會性別認同機制的觀點和角度,擁贊了性別身份上模棱兩可的形象,在影片中既消解了父權社會中性別的二元對立,也緩解了男性性別角色危機,打破“男性必須陽剛”的傳統觀點,同時鼓勵男性氣質的多元化。影片結尾,菲爾感染炭疽病毒而死,彼得也完成了保護母親的承諾,與片頭呼應。在父權體制框架下,縱觀影片中所有二元對立關系,沒有人是贏家,都是被壓迫的對象。菲爾的死消解了他和彼得的二元對立關系,在這場陽剛與陰柔的對壘中,與其說彼得戰勝了菲爾,不如說菲爾輸給了對愛的渴求。
三、結語
《犬之力》作為西部片,脫離了傳統西部片的內核,借助西部片的外殼來探討人物之間的關系,表達的是父權社會的規訓與自我天性的矛盾。電影通過其深層結構所承載的二元對立以及在敘事過程中二元對立的消解,如性別的對立,自我身份的認同,男性氣質的一元化與多元化問題,來呈現和轉移現代西方社會的社會意識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