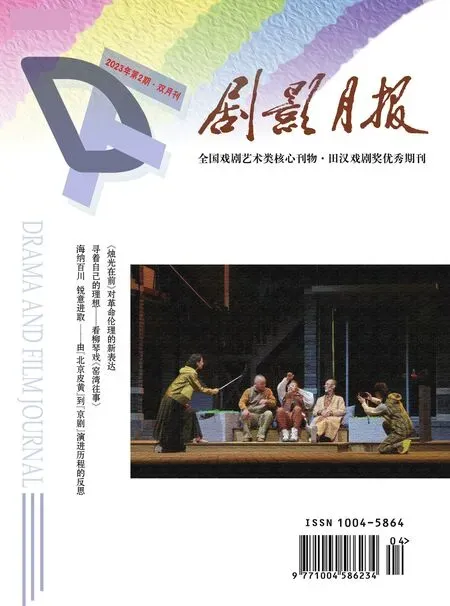現(xiàn)實主義力作《人世間》的禪意
■趙偉偉
《人世間》由著名導演李路執(zhí)導,著名編劇王海翎改編自著名作家梁曉聲曾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同名小說。這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題材作品,以東北某市一個非常傳統(tǒng)普通的工人家庭為切入點,講述了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半個多世紀以來普通中國人在時代變遷中的奮斗、努力、沉浮、無奈,寫盡時代浪潮中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與無可奈何,凡夫俗子的苦痛磨難和掙扎奮斗,以及那些隱藏在日常瑣碎中微塵一般的希望,那些拼盡全力的抗爭,那些令人心碎的幻滅,那些螢火一般的溫暖,直擊人心,透露出一種若隱若現(xiàn)的禪意,那是創(chuàng)作團隊透過雞毛蒜皮的人間煙火而發(fā)出的對人類終極意義的思考與追問,也是一種哲學思想在影視作品中的呈現(xiàn),這種文學性和哲學性在中國多年快餐式的電視劇作品中極為少見,是一種令人驚喜的存在。《人世間》這部劇,寫了周家及其派生出的幾個小家庭的悲喜故事,刻畫的人物大多鮮活生動,令人難忘。但令人玩味的是,具有濃重中國傳統(tǒng)意味的周家,幾個頂梁柱式的重要男人,最后的歸宿都充滿深深的禪意,十分耐人尋味。
先說周秉義,這是一個近似“神”的高尚男人。他的身上幾乎有著中國人潛意識中所欣賞和向往的一切優(yōu)點:品行好,長得帥,有擔當,有才干,肯付出。他出身平民卻通過自身努力躋身權(quán)貴階層,既能不卑不亢借助岳家勢力,又能一步一個腳印在官場步步升遷。更重要的是,他并非踩著別人的肩膀和幸福往上爬,官越做越大、越是清正廉潔、愛民如子,最難得的是,不因官場得意拋棄不能生育的發(fā)妻,甚至寧愿自黑也要在眾人面前保護妻子,這與現(xiàn)實中那些靠婚姻升遷,功成名就后又拋棄糟糠之妻的“鳳凰男”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周秉義是一個完全符合中國傳統(tǒng)價值的理想主義人物,暗合了觀眾對官、男性、階層的種種期許:于公,他是個好官,是所有平民百姓對強權(quán)的一種期許;于私,他是個好男人,是所有女性對男性的期許;于父母,他是個好兒子,是所有父母對孩子的期許。
再說周秉昆,他是周秉義的弟弟,劇中的男一號。這是一個非常質(zhì)樸而接地氣的人物,不完美卻真實可愛,是存在于萬千大眾中的普通勞動者,是千千萬萬個你我他的化身。周秉昆是家里的小三子,不愛讀書,初中只上了一年,相當于小學畢業(yè)。他一輩子最大的夢想就是證明自己也很優(yōu)秀,不比北大畢業(yè)的哥哥姐姐差。于是他努力工作,終于從一個工人混到出版社,并最終獲得事業(yè)編制,這在當時是相當不容易的。然后他努力掙錢買了一幢大房子,讓父母和全家離開了貧民窟“光字片”,過上寬敞舒適的日子,至此,無論是事業(yè)還是家庭,他的人生都達到他所能達到的頂峰。但是,命運無常,無論他多么努力向前,仿佛永遠都無法逃脫“無能”的宿命,他的幸福和輝煌在各種磨難中被無可奈何地消解殆盡:先是房子沒了,一家人只能從寬敞的別墅搬回逼仄擁擠的老屋;接著他因過失殺人吃了官司,身陷囹圄,又被單位開除,令人羨慕的身份沒了;出獄后,他曾試圖重新站起來,他還有深愛的妻兒、當干部的哥哥和當大學教授的姐姐,他完全有條件重新開始。但是,他并沒有如愿,作者并沒有讓他童話般地獲得世俗的成功,而是很現(xiàn)實地讓他成為被后輩接濟的“老人”,這是殘酷的,也是真實的。周秉昆是真實的,是無數(shù)個最平凡的人中的一個。他先天不足,因此有些自卑;他不愿屈服,因此非常倔強;他對未來并未失去希望,因此一直努力往上,但他卻被命運一次一次拋入谷底,最終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融入無數(shù)個漸行漸遠的背影中……劇終時,周秉昆和鄭娟共打一把傘,從一生的坎坷風雨中走來,又在風雨中牽手走向遠方,祈愿來世還能在一起。
周楠,是周家第三代長男,這個因孽緣本不該出生的孩子,卻成了劇中最完美、最充滿希望的新生一代。他不僅聰明、刻苦、重情重義,還擁有別人無法企及的一切:有愛、有錢、有資源。他有溫馨和諧的原生家庭,有青梅竹馬的初戀情人,有官運亨通的大伯,又憑空冒出一個家財萬貫的親爹。他有著與父輩完全不同的條件和機遇,也因此成為很早就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幸運兒。但是,這樣一個前途無量、寄托著所有人愛與希望的完美男孩,在他還沒有真正成年、真正走向人生的時候,卻突然死了!他和世界上許多美好事物一樣脆弱,他充滿生機的年輕生命在流氓的槍彈下瞬間毀滅,化為塵煙,飄散在異國的土地上。周楠的死,是對“完美”的第二次毀滅和祭奠,深深刺痛觀眾的神經(jīng)。
周家還有一個重要男人,就是馮化成,他是二女兒周榕的丈夫。在劇中他的戲份兒并不很重,因為現(xiàn)實世界里的失意和愛情生活中的失德,他并不是一個令人喜愛的角色,但不可或缺。馮化成的名字大概是出于《易傳》中的一句話:“剛?cè)峤诲e,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指陰陽迭運、剛?cè)峤诲e的自然變化過程與法則,而“人文”是指人類制作的禮樂典章制度及其對人的行為的規(guī)范教化作用。馮化成這個人物,是理想與現(xiàn)實碰撞擠壓的矛盾統(tǒng)一體,是跟周秉昆所代表的塵世生活相平行的另一個精神世界的最真實存在,寄托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諸多辛酸與無奈。馮化成成名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詩寫作。詩,是最純粹浪漫、超凡脫俗也最需要靈性的創(chuàng)作,他詩情橫溢,吸引了年輕漂亮、才華橫溢的周楠背叛家庭,從遙遠的東北跑到大西南當“反革命分子”家屬,心甘情愿跟著他過那種看似浪漫卻艱苦無比的生活;他本應(yīng)以詩“化成天下”,卻因?qū)懺姳徊叮瑢е略滥赋蔀橹参锶耍黄椒春蠡氐匠鞘校⑽茨茉凇耙栽娀恕钡穆飞侠^續(xù)下去,卻面臨現(xiàn)實的窘迫與尷尬,被困于物質(zhì)不能自拔:分不到房,升不了職,甚至無法把女兒接回家,最大的“成就”是成為不折不扣的家庭“煮夫”。他依然寫詩,這是他內(nèi)心的需要,他才情依舊,寫的詩依然能吸引那些不諳世事、尚未被柴米油鹽摧殘的年輕女性,而他,也只有從這些年輕女性崇拜的目光中找到自己的價值,于是,他出軌了,為了維護一絲尚存的尊嚴,他成了拋妻棄女的負心人,被觀眾所唾棄。但是,即使背負著這樣的罵名,遠走高飛離開這片土地,即使去到那個以浪漫著稱的國度,他依然水土不服,依然無法成為世俗社會的“勝者”。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體,他注定是個悲劇人物。馮化成最終的結(jié)局是皈依佛門,躲進深山古剎苦度余生,以求得內(nèi)心的安寧,這樣的安排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
說到宗教,不得不提到劇中另一個人物:鄭光明。這個從未見到一天光明的盲孩,卻取名為“光明”,真是別具韻味。也許他看不見這個世界,內(nèi)心卻有一片來自天國的澄澈的光明世界?鄭光明出現(xiàn)得并不多,卻是全劇禪意體現(xiàn)最集中的人物。他是一個不知道父母是誰的棄兒,從小跟著養(yǎng)母和姐姐過著缺衣少食、備受歧視的生活,在姐姐鄭娟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他用小小的肩膀成為她的精神支柱,當姐姐的生活走上正軌,他卻出家為僧,走上自己的人生之路。平心而論,鄭光明這個角色,無論是人物刻畫還是演員表演,都似乎乏善可陳,以至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幾乎被觀眾忘卻。但這個人物存在的用意卻是明顯的,在鄭娟后來人生中遇到的每一個坎坷中,都有他的開解和引領(lǐng),他以亦僧亦俗的形象出現(xiàn),寄托了普通人對宗教既親近又隔膜、既敬畏又向往的態(tài)度。這個并不常出現(xiàn)卻貫穿始終的人物,其實是全劇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滾滾紅塵,眾生皆苦,他代表了一種隱約的希望,給苦難人生帶來一絲心靈寄托。
當劇中主人公周秉義、周秉昆、馮化成、周楠們最終都化為虛無,當他們代表的真善美都歸于沉寂后,鄭光明所攜帶的那一縷佛光,是留給人們的一線難得的光明。但是,宗教是人類真正的靈魂歸屬嗎?它真的能帶給凡塵俗世以希望和新生嗎?這是一個永恒的懸念,并非一部電視劇所能回答。無論如何,電視劇《人世間》試圖在蕓蕓眾生的掙扎與奮斗中,在苦難與幸福的交替中,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紅塵欲念中,給觀眾留出一絲思考的縫隙,相比于那些毫無精神營養(yǎng)的文化快餐,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