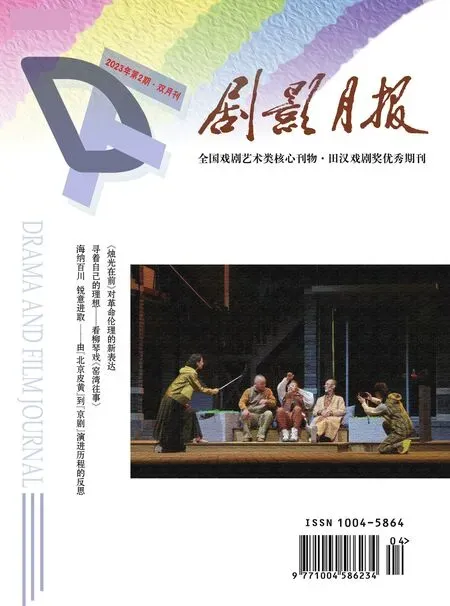《金龍與蜉蝣》中對蜉蝣的創作反思及表演技巧初探
■徐崢崢
由羅懷臻編劇創作、上海淮劇團首演于1993 年的淮劇《金龍與蜉蝣》,不僅被認為是淮劇,甚至是中國戲曲的里程碑之作,更是被譽為“十幾年探索性戲曲走向成熟的標志”。當年《金龍與蜉蝣》的出現,興起了“都市新淮劇”的概念。《金龍與蜉蝣》對中國戲劇界的影響是深遠的,使其找到了生存下去的價值,使之與現代都市文化接軌,使得觀眾感受到中國戲劇可以與西方經典戲劇媲美的深刻崇高的悲劇感。
劇里寫了四代人——老王、金龍、蜉蝣、孑孓,他們一個個都和王位、權欲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之間有一條隱蔽的但又是可以窺見的血親的鏈,在四代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同樣的“權欲”基因,都是惡的化身。
被刺死于王座上的老王,權欲充滿了血腥。老王的幽靈時不時就會出現,提醒著金龍,顯示著權力的傳統性和繼承性,激勵著金龍去追求至高無上的王權,在金龍心中樹立起王權的至高無上。
金龍的人性泯滅,為了爭奪王位,拋妻棄子,拼死廝殺,奪取王位;為了保住王位,復仇后殺死功臣,在必要時可以“大義滅親”,斬草除根,翦除牛牯后代,最終閹子霸媳;為了交接王位,不惜殺害兒子蜉蝣,留住孫子孑孓;為了代傳王位,被孫子孑孓洞穿也在所不惜……一個活脫脫悲劇的締造者和傳承者。
蜉蝣的人性被扭曲。他原來是善良的、純樸的、稚氣的;但在被閹割以后,處在暴君的寵幸和監護下,身心兩殘的蜉蝣變得令人難以識別。面對金龍,蜉蝣阿諛奉承;背對金龍,蜉蝣恨之入骨。為了報仇,蜉蝣可以不擇手段。因為被閹割了,他失去了爭奪王位的條件,但是他卻以另外的方式來滿足他的欲望。當知道金龍是自己的生父以后,他走向回歸,他情愿放舟天涯,放棄帝王霸業,放棄留在宮廷,只想攜子歸于自然,人性此時在他身上得到了復歸。然而權欲生活與普通生活之間的矛盾達到頂端,蜉蝣依然不能復歸而抱劍自刎,悲劇再次升騰。
孑孓——一個孩子,也和金龍、蜉蝣一樣,站在權欲的頂峰——王位上。他是王位唯一繼承人,厭倦了血腥王位的父親極力想帶他走,去過平常的生活。從小就明白了這種權欲斗爭的殘酷性,目睹了滿足權欲的最高手段是自相殘殺,于是他繼承了這一手段,最后也親手殺死了自己的祖父。一代新王誕生,在父母尸體、在祖父鮮血中誕生的新王,讓悲劇沖上高潮……
越劇舞臺的化妝,跟生活化妝是有不一樣的。由于它是舞臺化妝,在臉部用的化妝品也是結合了油彩和生活化妝,色彩上來說會比生活妝要夸張。由于舞臺上的燈光,舞美設計都比較鮮艷,妝面一定要比日常化妝濃。越劇化妝跟京劇昆曲的化妝也是不太一樣的,它比較貼近于我們的生活和影視劇的一種化妝手法,但是作為一個越劇舞臺的化妝,它要注重美感輪廓,注重對于每個演員的臉型,五官的美感塑造,讓他們的臉型在舞臺上顯得更加端莊完美。陰影修容,鼻梁輪廓,都要更加強化。越劇由于是以女小生作為劇種特色,所以傳統的越劇女小生在化妝時,常會使用大刀眉的眉形,顯得人物英俊瀟灑又不失英氣。而蜉蝣這一角色由于是少年又慘遭宮刑,所以在眉形上做出了一些調整,眉形較之以往的大刀眉會稍許纖細一些。這樣既能顯得角色年齡感較小,也能使人物看上去多些陰柔之氣。
服飾是以寬松為主的素白色長袍,所以色彩是最重要的視覺元素,當角色出場亮相時,映入觀眾眼簾的首先是劇裝色彩,《刑戮》這場戲中,蜉蝣剛剛受刑還是善良的、純樸的、不諳世事的,選用白色,象征著純潔美好、純凈與光明,與之后變成閹人的變態形成強烈對比。
越劇尹派唱腔醇厚質樸跌宕起伏。講究字重腔輕、以情帶聲、吐字清晰,運用音色速度的變化表達人物情感的起伏。《刑戮》這段唱中,首先要把每段的層次、情感分好,練習時氣聲要少用,聲音要實、真假嗓結合。小腔上不能多腔。比如“把路上”練習時要做好“路”的收腔和“上”的轉腔,表達出蜉蝣出門尋父一路的艱難。
《刑戮》的身段拋開了傳統的水袖,甚至臺步,借鑒了舞蹈的一些造型來達到一種極致的扭曲,演繹出蜉蝣經過閹割之后,血脈中的變態開始覺醒。身段練習時,所有的身段動作及呼吸氣口都要放大,要將身體發揮到極致,延伸感抻滿。蜉蝣剛被閹割完,為表現出對閹割這一巨變的驚慌,運用側趕步來表達受到驚嚇膽戰心驚時的狀態及痛苦。痛感上分為身體的疼痛及心理上的痛。運用挫步、踢褶、咬褶表達出蜉蝣眼中自己受完刑被拖行的血路,跪步表達出對行刑人的乞求和受驚嚇的情緒。跪、挫練習時都要由慢變快,步子都要由大到小,通過節奏速度變化表達強烈情感。蜉蝣角色的扮演,貫穿蜉蝣人生的四個過程,著重體現其四個階段不同的心境與情感。一是替母尋夫過程中對父愛親情的“渴望”,一個充滿稚氣的英俊少年,在海邊漁村長大,并沒有經歷太多的人生磨難,舉手投足中體現的都是不諳人世、好奇的情狀,這使得他生活中缺少了高大父親的形象,而這個情狀充滿著與父相遇的“渴望”;二是剛剛被金龍閹割后的“絕望”,蜉蝣尋父入宮,誤認為親生父親牛牯慘死,而又慘遭宮刑,從此求死不忍、求生不得,思念故鄉妻兒老母,痛苦異常,無法自拔,想著復仇,而又無力回天的“絕望”;三是蜉蝣變成閹人并經歷了八年宮廷生活磨煉之后,他有些陰險和玩世不恭,甚至慫恿金龍縱欲,鼓動金龍征選美女,進而企圖利用妻子玉蕎的美色摧殘金龍,他是個玩弄兩面、不擇手段的復仇者,他用另一種方式來滿足自己的“欲望”,這種欲望充滿著復仇與變態。四是當蜉蝣得知金龍是自己親生父親后,他“不愿宮中留”“情愿天涯去放舟”,并真誠地吶喊出“帝王與我是對頭”的舞臺最強音,表現出他對帶兒子孑孓返家歸漁、過太平日子的“奢望”,最終還是在奢望中倒在了父親的劍下。
角色扮演是需要找到與劇中人物共鳴的那個點,而作為蜉蝣的扮演者,如何感受蜉蝣在宮刑后那種變態的“欲望”心理,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心路歷程。蜉蝣的唱一定是抒情而富有魅力,樂感極強,表現蜉蝣的痛苦與哀傷,及對坎坷命運的不滿。蜉蝣的唱在這個階段,一定不能有蕩氣回腸、一吐為快的痛快與順暢。蜉蝣的唱讓人感受到厭惡、可憐又沉痛。被閹割后,蜉蝣陷入痛苦,不能自拔,思緒萬分而又萬念俱灰。此時蜉蝣一唱三嘆,苦苦掙扎,充分展露出人物深刻的痛恨和無盡的悲哀,催人淚下、肝腸寸斷。把蜉蝣的心境與此時復仇不能的情感交織在一起,經歷了痛苦與哀傷,復仇與變態充斥著整個軀殼,形體上的扭曲演繹出心理扭曲,內心的仇恨與屈辱,不時地流露出來。這里的表演,體現出一個“癲”字,不規則的步履,大開大合的扭曲身段、陰森的笑聲、痛苦中顯出瘋癲,面對金龍時老成圓滑、唯唯諾諾,背后卻詛咒唾罵,無時無刻不把那種閹割后的奇恥大辱隱現出來,這種扭曲之美是通過無數次閱覽、無數次體驗和無數次預演才得以呈現的,足以讓蜉蝣這個角色躍然眼簾、沉浸于心。
角色扮演一定是情感基礎上心路歷程的演繹與升華。角色扮演即人物形象塑造,不再是簡單的正面與反面的符號,而是著力于人物內心情感的挖掘,演繹出崇高與卑鄙、善良與邪惡、勇敢與怯懦、堅定與退縮,一個個活脫脫的人物形象,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人物形象,給人以啟迪,發人深省。角色扮演一定是社會發展中民族文化的相通與相承。以民族文化和人類心理為背景,尋找現代文明與之相通相承的精神氣質,強調的是生命和蜉蝣的“奢望”情感的永恒價值,對歷史、對人生底蘊的探究。最根本的是角色的愿望激起了當代人的共鳴,是歷史的,是現代的,更是時代賦予的。
角色扮演一定是文明進程中人民大眾的價值與追求。《金龍與蜉蝣》中蜉蝣的角色扮演在挖掘、回歸藝術傳統本質特征的同時,又展示了人在本能、欲望、情感、文明之間的矛盾沖突,展現了人類在文明進程中的困惑和絕望以及在絕望中的痛苦掙扎。由蜉蝣式返家歸漁、太平過活的生活理想擴大為黎民百姓的基本生存權利,以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和價值觀念來對抗孤家寡人的根本利益和價值觀念,這是蜉蝣這個角色在歷史觀上的又一發展和開拓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