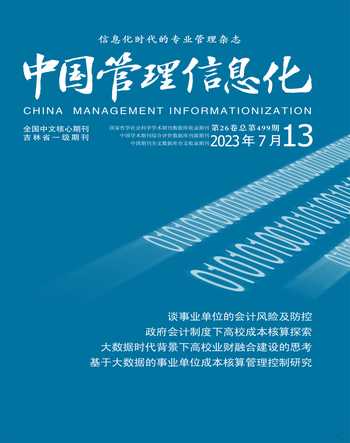粵港澳大灣區空間格局下中山市產業協同研究
蔣永宏 王玲
[摘 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全面鋪開為中山經濟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中山市如何在灣區空間格局下謀求產業協同發展是理論界關注的焦點。論文以“核心-邊緣”理論為研究基石,結合中山市在灣區中的經濟地位、產業發展現狀、產業發展制約因素等現實條件,對中山市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對中山市在灣區中的城市定位、“核心”產業和“邊緣”產業定位分別進行了研究。提出中山市應立足于大灣區全域進行產業布局;承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地區輻射和延伸,促進中山市傳統優勢產業升級;促進“邊緣”產業智造化等建議。
[關鍵詞]核心產業;邊緣產業;產業升級;產業協同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23.13.044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23)13-0152-04
0? ? ?引 言
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山市開始進入對接灣區推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機遇期。圍繞如何在灣區經濟中布局中山的產業,如何在灣區建設中謀求動態發展問題,學界提出了一些建議,但是,目前從理論層面研究上述問題還有很大空間。基于此,本文分析目前中山市的核心產業和邊緣產業定位,并結合灣區核心城市經濟輻射能力以及產業轉移的方向,找到中山市承接產業轉移的對象,向外輻射的產業選擇和區域選擇,最終實現灣區空間布局下的產業協同發展。
1? ? ?“核心—邊緣”理論的基本觀點與應用
本文是基于約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1966)的“核心—邊緣”理論展開研究的。“核心—邊緣”理論聚焦區域經濟由孤立發展到相互關聯的變化過程。弗里德曼認為:可以按經濟發展水平將區域經濟空間分布劃分為核心區和邊緣區;區域中創造能力較強的核心產業和核心區得到率先發展,而后這種發展逐步向邊緣區擴散,進而推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以來,“核心—邊緣”理論逐步應用到我國不同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制定中[1]。相關的研究主要有:李映照(2005)等人討論了資本要素在壟斷競爭、報酬遞增及交易成本條件下的移動與企業集聚形成的關系。呂康娟,付旻杰(2009)將核心—邊緣模式應用用于汽車產業,選取美、日汽車產業為例,重點研究了核心—邊緣模式自發形成和自我維持的過程。龍良富、黃英(2011)構建了珠中江三地在區域合作中的核心—邊緣空間結構,提出三地應在旅游合作中共同發展。趙金麗、張落成(2015)基于“核心—邊緣”理論,將泛長三角4省1市分成“核心—邊緣—外圍”3個圈層,發現3個圈層之間的產業轉移呈現出顯著的梯度轉移特征[2]。劉漢初、樊杰等(2020)研究認為不同類型制造業空間集疏差異促使城市群“核心—邊緣”結構進一步強化,核心城市更加專業化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而邊緣城市則承接核心城市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3]。
從以上闡述可以看出,“核心—邊緣”理論對研究中山市與灣區城市產業協同發展具有指導作用。
2? ? ?中山市在灣區協同發展中的地位
2.1? ?在灣區區域經濟中處于中等水平
近年灣區經濟運行總體情況表明灣區“9+2”城市群經濟發展呈現顯著的梯隊分布,中山市居于中等水平。
灣區內各區域經濟發展“核心—邊緣”特征明顯,在空間上呈如下分布:香港、澳門、深圳、廣州、佛山、東莞處于核心區,相對來說,中山、珠海、江門、惠州、肇慶則為邊緣區。中山市由于制造業基礎好,優勢產業競爭力強,故處于次核心地位[4]。
目前,中山市在灣區中的定位為:一是灣區的重要一極,中山與香港、深圳、廣州、佛山四個城市連接,與這四個城市的經濟關聯密切,同時與澳門、佛山、珠海和東莞四市構成灣區崛起的中堅力量;二是灣區的幾何中心,從交通區位上看,中山可以更好更快地與周邊各地互相連接與輸送資源,并成為珠江東西兩岸融合發展的支撐點①。
2.2? ?中山市與周邊城市的協同水平偏低
在港澳和珠三角九市間優化配置資源,首先要解決各城市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融合問題。目前,中山市與珠海、江門、澳門、廣州、佛山等城市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升,產業融合和經濟協同發展進展尚不盡如人意。與東莞市融合度偏低,與深圳、香港的產業合作有待深化[5]。中山亟須借助灣區建設契機加速與周邊城市的協同發展,促進生產要素流動和產業梯度轉移。
3? ? ?制約中山市產業協同發展的因素
3.1? ?傳統主導產業優勢減弱
中山的傳統主導產業是紅木家具制造業、服裝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如今普遍存在產業低端徘徊、缺少知名品牌、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不暢、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以及國家開始對東北、環渤海等區域的發展政策實施,中山專業鎮原有的區位優勢逐漸弱化,對資本和技術的吸引力有所降低。出現了吸引高端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和其他勞動要素難度增加的情況。隨著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壓力增大,部分專業鎮資本加速流出,傳統主導產業的優勢逐漸減弱[6]。
3.2? ?土地碎片化問題凸顯
中山市的土地開發強度較高,與灣區其他城市相比,僅低于深圳、東莞。諸多原因導致中山市產業發展陷入“土地碎片之困”,平均每個鎮區有1.83個產業園區,部分鎮區多達3到5個產業園區。對于產業轉移影響重大的土地成本劣勢極大地降低了中山市對大企業、大項目的吸引力。土地碎片化問題導致產業轉入空間小,嚴重影響了中山市承接深圳、廣州等大灣區核心區的產業轉移。嚴重影響了中山市打造開放包容的營商環境,限制了中山在灣區空間布局中地理優勢的發揮。
3.3? ?產業競爭力提升緩慢
中山市制造業基礎良好,但近年產業競爭力提升較慢,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環境資源壓力。改革開放后,中山的產業發展以燈具、小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一些產業迅速擴張,通過外部規模經濟獲得了較快發展,形成了較大的產業集群。但是也暴露出個別產業盲目擴大規模、片面追求高速發展,造成大量固定資產投資雷同、產品同質、產業同構,最后陷入被動的價格競爭,利潤空間不斷壓低的局面。尤其是在制造業數字化轉型趨勢下,中山的制造業競爭力提升相對緩慢。
4? ? ?中山市“核心”產業和“邊緣”產業定位
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核心”和“邊緣”產業動態變化。
4.1? ?“核心”產業定位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山市不斷調整“核心”產業。90年代,中山市經濟發展勢頭迅猛,紡織服裝、機械電氣、電子通信、金屬制品、化學制造等為核心產業。從1991年起,上述產業的產值占GDP比例在41%以上。1999年,中山市提出“工業立市”的發展戰略,核心產業的優勢進一步提高。2011年中山市確定新能源、裝備制造業、電子信息、健康醫藥、電氣機械及金屬制品、紡織服裝為六大核心產業。此后,隨著制造業的發展,中山逐步將核心產業調整為先進制造業等產業。中山市2018—2022年的核心產業定位于三大產業,即高端裝備制造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和健康醫藥產業。中山市的智能家電、高端裝備兩大產業集群產業規模已超“千億”。
4.2? ?“邊緣”產業定位
本文所指的“邊緣”產業,并非“淘汰”產業或“落后”產業,而是指按照產業轉移理論,基于“核心—邊緣”模型在區域內外進行梯度轉移的產業。
中山的產業結構中,紡織、服裝、燈飾、家具、五金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占較大比重,產品附加值低,面臨著產能過剩、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問題,亟待由“中山制造”向“中山智造”轉型。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應鼓勵企業進一步向粵東西北地區實施產業梯度轉移,將制造加工環節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區域;另一方面,產業梯度轉移過程中,提升產品品質和附加值,加快品牌培育,推動產業數字化,促進當地就業和產業發展。
5? ? ?基于灣區空間格局的中山市產業協同發展對策
5.1? ?從灣區全域視角進行產業布局
強大的集聚外溢效應是灣區經濟的突出特點,未來灣區內城市圈之間的交通會更加順暢,對于勞動力就業而言,城際界限會逐漸模糊,彼此間的產業關聯進一步加強,產業間分工和產業內分工將從城市內部擴展到灣區范圍。因此,著眼于城市自身的產業布局將會限制產業的發展,中山應從灣區整體產業布局出發確立支柱產業和重點產業。例如,坦洲鎮應充分發揮區位優勢,迅速謀劃布局與港澳合作的金融、旅游等現代服務業項目;翠亨新區是珠江西岸的前沿陣地,要抓住深中通道通車后深中一體化融合發展的歷史性機遇,有效承接深中通道開通后的經濟輻射。因此,中山市要從灣區全域出發,有針對性地對產業發展進行規劃布局[7]。
5.2? ?承接產業轉移,實現產業協同布局
灣區將發展成為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制造中心、科創中心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將來會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現代服務業產業集群,在核心區和邊緣區中形成完善的產業鏈條。灣區內有像華為、騰訊、中興、格力、大疆等領軍企業,在承接產業轉移中,東莞已經搶占了先機。中山應積極向東莞、佛山汲取產業融合的經驗,承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的產業轉移,與東莞、佛山在制造業價值鏈上聯動發展。與灣區外城市對接,推動傳統優勢產業加工制造環節轉移,激發當地經濟活力。在承接與轉移中培育競爭優勢,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8]。
5.3? ?優化人才戰略,吸引高端人才
對于實現高端裝備制造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和健康醫藥產業等“核心”產業的發展目標而言,高端人才是至關重要的高級生產要素,因此要大力引進并留住高端專業技術人才。通過優化人才發展的制度環境吸引人才,通過培育良好的產業創新體系留住人才,為優秀人才提供潛心科研和創新工作的土壤,為科研合作和成果轉化提供平臺。
5.4? ?促進“邊緣”產業“智造化”
中山要由內而外地強化“邊緣”產業的發展,利用好白色家電制造、燈具制造、紡織服裝、電器機械等產業的發展基礎,通過科學的政策引導,促進“邊緣”產業智造化、服務化。學習和借鑒東莞、蘇州等城市在制造業數字化發展方面的先進經驗,在灣區空間內合理配置資源,將原有的生產和加工環節轉向灣區內其他城市。通過龍頭企業培養計劃,讓產業政策更多地向龍頭骨干企業傾斜,讓更多的科技元素、文化元素注入到生產環節之中。同時,建設全生命周期公共技術服務平臺,促進企業降成本、提效益,推動中山傳統優勢產業加快轉型升級,推動產業結構現代化。
5.5? ?推動產業創新體系的建立
灣區內各區域產業定位和規劃難免趨同,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非合意性產業同構,這對中山市借助灣區發展機遇進行產業規劃和再造價值鏈提出了新的挑戰。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突破原有產業結構演進的路徑依賴,建立產業創新體系。如下兩個方面的措施值得進一步論證和實施:一是與灣區內高校合作建立中山產學研基地;二是鼓勵企業和研究機構建立研發和創新聯盟,開展多種形式的跨學科、跨行業合作研究。
6? ? ?結束語
中山市具備與灣區城市間產業協同發展的客觀條件,應緊緊把握建設機遇促進產業協同發展,推動建設高質量城市群。本研究以“核心—邊緣”理論的分析框架為基礎,分析了中山市的產業定位。提出中山市應從灣區全域視角做好產業布局;吸收核心區引擎的輻射作用并向邊緣區進行產業轉移;通過優化人才發展的制度環境吸引人才;促進“邊緣”產業“智造化”等對策建議。
主要參考文獻
[1]王小玉.“核心—邊緣”理論的國內外研究述評[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10):41-42.
[2]趙金麗,張落成.基于“核心—邊緣”理論的泛長三角制造業產業轉移[J].中國科學院大學學報,2015(3):317-324.
[3]劉漢初,樊杰,張海朋,等.珠三角城市群制造業集疏與產業空間格局變動[J].地理科學進展,2020(2):195-206.
[4]梁邦興,陳浩然,朱竑.區域協同發展背景下邊緣城市的空間治理與融入策略:以廣東省中山市為例[J].地理科學,2022(3):381-389.
[5]喻鋒,梁綺琪.粵港澳大灣區空間聯系與地緣關系的匹配研究[J]. 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68-78,91.
[6]鐘輝新.新時期中山市專業鎮經濟面臨的挑戰與發展對策[J].特區經濟,2010(4):40-41.
[7]張志明,林琳,李健敏.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要素稟賦優勢評估[J].城市觀察,2021(3):153-164.
[8]岳鵠,譚月彤,周子灼.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協調發展建設的現狀、問題與對策研究[J].廣東經濟,2021(9):4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