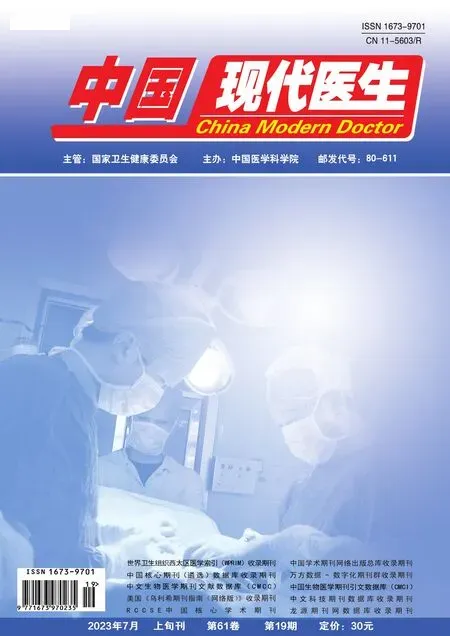中西醫結合治療冠狀動脈微循環障礙的研究進展
張輝,陳鐵龍
·綜 述·
中西醫結合治療冠狀動脈微循環障礙的研究進展
張輝1,陳鐵龍2
1.浙江中醫藥大學第三臨床醫學院,浙江杭州 310053;2.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杭州市中醫院心血管病科,浙江杭州 310007
冠狀動脈微循環障礙是由于冠狀動脈微循環結構和功能出現異常而導致心肌灌注不足的一組疾病群。隨著冠狀動脈造影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普及,越來越多的冠狀動脈微循環障礙患者被發現,針對冠狀動脈微循環障礙的研究亦越來越多,對冠狀動脈微循環障礙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入。本文從中西醫兩方面對冠狀動脈微循環的發病機制、診斷標準、微循環功能評估及治療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中西醫結合;冠心病;微循環障礙
冠狀動脈微循環障礙(coronary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CMD)是指由心臟血管中的微動脈、毛細血管及微靜脈構成的微循環系統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現的心臟血流灌注不足、冠狀動脈造影未見明顯狹窄的心血管疾病,其以勞力性心絞痛為主要表現,包括冠狀動脈慢血流現象(coronary slow flow phenomenon,CSFP)和心臟X綜合征兩種類型[1]。中醫根據其勞力性心絞痛的臨床表現,將CMD歸于“胸痹心痛”范疇,認為主要病變在心、絡脈、孫絡,涉及肝、脾、腎等,病機包括氣血痰瘀。本文就中西醫結合治療CMD的最新研究進展進行綜述,為其臨床診治提供參考依據。
1 西醫對CMD的認識
1.1 診斷標準
CMD的診斷標準:①存在心肌缺血癥狀;②冠狀動脈造影檢查未見阻塞性冠狀動脈疾病;③影像學檢查存在客觀心肌缺血證據;④存在冠狀動脈微循環功能受損證據。同時滿足上述4條則確診為CMD,同時滿足上述3條則為疑似CMD[2]。
1.2 診斷方法
CMD的診斷指標包括冠狀動脈血流儲備(coronary flow reserve,CFR)、血流儲備分數(fractional flow reserve,FFR)及微循環阻力指數(index of microcirculatory resistance,IMR)。①CFR是冠狀動脈接近最大擴張狀態時的血流和靜息血流的比值,是對心外膜冠狀動脈和微循環血流的完整測定,是評估冠狀動脈循環功能的直接參數。通常認為CFR<2.0時為血管舒張能力受損[3]。②FFR是冠狀動脈狹窄存在時最大血流與正常狀態時最大血流的比值,是冠狀動脈狹窄嚴重性的特異指標。FFR的正常值為1,當FFR<0.75時被認為存在缺血病變[4]。③IMR是冠狀動脈在最大充血狀態下,狹窄病變遠端壓力和平均傳導時間的乘積,可定量測定微血管的完整性,其特異性好,是近年來受到學者青睞的用以評估冠狀動脈微循環功能的指標之一[5]。
目前,臨床應用影像學方法對CMD進行診斷。①心臟磁共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CMR利用高空間分辨率顯示局部心肌灌注,同時結合左室形狀及功能測定,對冠狀動脈微循環功能進行評估[6]。②正電子發射體層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PET于1975年被首次應用于臨床,可用于局部心肌循環定量CFR的檢查。其缺點是對CMD缺乏敏感性和特異性,易受心外膜動脈血流狀態的影響。③心肌超聲造影(myocardial contrast echocardiography,MCE):MCE是經血管注射含有微小氣泡的超聲造影劑,心腔或心肌組織內出現云霧狀造影劑回聲,通過二維超聲或多普勒超聲技術測量造影劑回聲出現的解剖部位及時間,進而將心肌微循環顯影的一種診斷技術[7]。MCE作為一種無創檢查,更易被患者所接受,對CMD的診斷具有重大意義。
1.3 發病機制研究
目前,西醫關于CMD的發病機制主要有2種學說:①構成微循環系統的血管結構改變;②微循環系統的功能失調[8-13]。
1.3.1 血管結構改變 在高血壓、高脂血癥、糖尿病及吸煙等多種因素影響下,微循環內皮細胞腫脹損傷,動脈中膜肌纖維肥大、增生,導致微血管狹窄、重構,造成微循環阻力升高,引起微循環障礙,從而使微循環對心肌的灌注減少。此外,在多種因素作用下,血管內皮損傷后引起脂質沉積于微循環內膜下并形成斑塊,造成動脈粥樣硬化。不穩定性斑塊破裂后激活凝血系統,形成血栓造成微血管狹窄,亦是造成微循環障礙的機制之一。
1.3.2 功能失調 Egsshira等[14]利用侵襲性冠狀動脈內多普勒血流導絲測量在血管活性藥物作用下的左冠狀動脈前降支近端和遠端部分管腔直徑和血流速度的改變,結果證實CMD患者存在內皮功能障礙。在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作用下,冠狀動脈微血管內皮細胞和平滑肌細胞出現損傷和功能障礙,局部血管活性物質失衡,具有舒張作用的一氧化氮、前列環素、鳥苷酸環化酶等物質的生成減少或利用降低,而具有收縮作用的內皮素-1生成增多,微血管的擴張功能受損、收縮功能增強、舒縮功能失調。內皮損傷可啟動新的炎癥反應,釋放大量炎癥因子,促進內皮素-1生成,阻礙一氧化氮的利用,抑制內皮祖細胞增殖,無法有效修復損傷的內皮細胞,從而造成氧化應激、炎癥反應、內皮功能破壞、微血管收縮和舒張失衡的惡性循環,導致微循環障礙的發生。
1.4 治療方法
西醫治療CMD主要包括擴張血管、穩定斑塊、抗炎、改善內皮功能等,其主要治療藥物包括β受體阻滯劑、鈣離子拮抗劑、他汀類藥物和尼可地爾等。
1.4.1 β受體阻滯劑 β受體阻滯劑可改善冠狀動脈微循環功能。研究表明,給予患者nebivolol或美托洛爾治療,發現患者血漿內皮型一氧化氮、L-精氨酸水平明顯升高,提示β受體阻滯劑可改善冠狀動脈微循環內皮功能,從而改善CMD的臨床癥狀[15]。另有動物實驗證實,β受體阻滯劑可增加一氧化氮敏感性,從而促進冠狀動脈微血管擴張[16]。上述研究提示,β受體阻滯劑可通過作用于一氧化氮改善冠狀動脈微循環功能,但具體作用機制仍待進一步探究。
1.4.2 鈣離子拮抗劑 鈣離子拮抗劑是治療冠狀動脈痙攣的主要藥物,關于其是否能改善冠狀動脈微循環功能存在爭議。既往研究表明,地爾硫?僅能改善CMD的臨床癥狀,但對冠狀動脈微循環血流量無明顯改善[17]。Mehta等[18]研究發現,ranolazine能改善CMD患者的CFR及臨床癥狀;Villano等[19]研究表明,ranolazine僅能改善CMD患者的臨床癥狀,CFR無明顯改變。綜上,鈣離子拮抗劑對冠狀動脈微循環的作用需進一步研究。
1.4.3 他汀類藥物 他汀類藥物是治療冠心病的重要藥物,在降低血脂水平的同時,可降低氧化應激水平,抗炎,改善冠狀動脈微循環內皮功能。Zhang等[20]研究表明,接受他汀類藥物治療的CMD患者體內一氧化氮水平升高、內皮素水平下降,冠狀動脈微循環舒張和收縮平衡得到調節,從而改善CMD。歐洲心臟學會指南推薦CMD患者使用他汀類藥物進行治療[21]。
1.4.4 尼可地爾 尼可地爾作為一種新型三磷酸腺苷敏感的鉀離子通道激動劑,能擴張動脈并減輕炎癥反應、氧化應激,改善內皮功能。郭英[22]研究發現,尼可地爾能更好地改善CMD患者的IMR,降低血清脂聯素、超敏C反應蛋白水平。另有動物實驗研究發現,小鼠體內尼可地爾濃度與微血管內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水平相關,尼可地爾濃度越高,IL-1β、IL-6水平越低,提示尼可地爾可通過抑制炎癥反應改善微循環障礙[23]。李露[24]研究發現,尼可地爾治療的小鼠體內丙二醛濃度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增加,說明尼可地爾可減輕氧化應激反應。
2 中醫對CMD的認識
2.1 病因病機研究
CMD的主要癥狀表現為勞力性心絞痛,與中醫胸痹心痛癥狀相似,中醫認為其病因為飲食情志失調、勞倦內傷、年邁體虛等[25]。其病位在心之絡脈,涉及肝、脾、腎等多個臟腑。《靈樞·癰疽》記載:“中焦出氣如露,上注溪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認為機體臟腑功能正常運行的先決條件在于氣血運行無礙、暢達全身臟腑經絡、發揮濡養功能。《難經·二十二難》指出“氣主呴之,血主濡之”,說明氣血虧虛均可使心脈失于榮養,從而不榮則痛。《血證論·陰陽水火氣血論》言:“運血者,即是氣。”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瘀,說明血行與氣關系緊密,氣滯不能運血,血行緩滯,瘀積脈絡,不能及時充盈榮養心脈,不通則痛。《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言:“為喜怒憂思悲恐驚忤郁不行,遂聚涎飲。”說明氣滯日久,易生痰濁。《靈樞·百病始生》曰:“凝血蘊里而不散,津液澀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瘀血可助生痰濁,二者相兼為病,心脈因痰濁阻滯,血行緩滯加重,亦發為胸痛。綜上,不論是氣血虧虛,還是氣滯、痰濁、血瘀造成的氣血運行阻滯,都會使臟腑經絡失于濡養,導致不榮、不通而引發疾病[26-28]。
2.2 治則與治療措施
CMD涉及氣血痰瘀,包含不榮則痛、不通則痛。結合中醫虛則補之、實則瀉之的治療原則,對氣血虧虛、經絡失養引起的不榮則痛,應以補氣養血等補虛為主,使氣血充沛,能夠循行到絡脈,發揮濡養功能;而對氣滯、痰濁、血瘀引起的不通則痛,則應以行氣、化痰、活血等瀉實為主,從而達到通暢心脈的目的,使氣血得以運行,環形周身濡養臟腑經脈,保證臟腑功能的正常運行。
2.2.1 中醫治療CMD的研究 對氣血虧虛證患者,可使用補氣養血藥物。龍衛平等[29]研究發現,中藥湯劑益心飲能有效改善氣血虧虛證患者的胸痛癥狀。中成藥芪參益氣滴丸可改善氣虛患者冠狀動脈微循環功能,增加冠狀動脈血流量,緩解胸痛癥狀[30]。對氣滯血瘀痰濁證患者,可采用行氣活血化痰藥物。鐘正龍[31]研究發現,瓜蔞薤白半夏湯可改善血瘀痰阻證患者心絞痛癥狀,降低不良心電圖發生率。多項研究發現,成藥麝香保心丸可調節血瘀痰阻證患者微血管舒縮功能,改善心肌灌注[32-33]。研究發現,中醫治療胸痹心痛使用頻率最高的是丹參、川芎、當歸、黃芪、三七、紅花等藥物,這與中醫治療CMD補氣、行氣、活血治則不謀而合[34]。研究證實,丹參、黃芪、當歸、川芎等中藥具有抗炎、抗氧化應激、抗血栓形成、改善內皮功能、擴張血管的作用[35-37]。另外,傳統針灸、體操(如八段錦、五禽戲)、結合現代技術的電針等方法,都能夠通絡活血,緩解止痛,改善冠狀動脈血流量,緩解CMD患者的胸痛癥狀,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38-39]。
2.2.2 中藥作用靶點和信號通路 張耀杰等[40]研究發現,扶脈益心湯治療CMD主要涉及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3、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蛋白激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A等核心靶點及PI3K-Akt、VEGF等信號通路。其中,PI3K-Akt信號通路與細胞的增殖、凋亡、氧化應激等密切相關,VEGF信號通路可激活血管內皮細胞的生成,促進內皮細胞增殖、轉移,促進毛細血管網的生成[41-42]。正常情況下,兩種信號通路的激活可促使機體釋放IL-6、IL-8等炎癥因子,扶脈益心湯通過作用于上述兩種信號通路,抑制炎癥因子釋放,達到治療CMD的目標[43]。張耀杰等[44]構建“雞血藤–活性成分–作用靶點-CMD”網絡,發現63個靶點通過作用于PI3K-Akt信號通路、松弛素信號通路,發揮治療CMD的作用。與扶脈益心湯相比,二者有部分信號通路相同,而雞血藤還可通過松弛信號通路促進一氧化氮生成,拮抗兒茶酚胺、血管緊張素等的縮血管作用,改善微循環。
綜上,中醫治療CMD,無論是復方合劑還是單味中藥,都可通過相應靶點、信號通路,調節炎癥反應和血管內皮功能,改善心肌缺血癥狀。PI3K-Akt、VEGF、松弛素信號通路等為后續研究中藥作用靶點和通路提供方向。
3 總結與展望
近年來,CMD越來越受到學者關注,中醫、西醫對CMD的研究越來越多。關于CMD的發病機制、診斷及治療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CMD的診療仍不完善,藥物治療效果差異較大。未來希望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明確CMD的發病機制、診斷標準、治療方案等,為CMD的診療提供確切證據。
[1] 郭曉鵑, 何平. 幾種常見冠狀動脈微循環病變的臨床特點及機制研究進展[J]. 微循環學雜志, 2018, 28(3): 71–75.
[2] TAQUETI V R, DI CARLI M F. Coronary microvascular disease pathogenic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options: JACC state-of-the-art review[J]. J Am Coll Cardiol, 2018, 72(21): 2625–2641.
[3] KAUFMANN P A, CAMICI P G. Myocardial blood flow measurement by PET: Technical asp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J]. J Nucl Med, 2005, 46(1): 75–88.
[4] KERN M J, SAMADY H. Current concepts of integrated coronary physiology in the catheterization laboratory[J]. J Am Coll Cardiol, 2010, 55(3): 173–185.
[5] MARTíNEZ G J, YONG A S, FEARON W F, et al. The index of microcirculatory resistance in the physiologic assessment of the coronary microcirculation[J]. Coron Artery Dis, 2015, 26 Suppl 1: e15–e26.
[6] BAKIR M, WEI J, NELSON M D, et 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myocardial perfusion and diastolic function-reference control values for women[J]. Cardiovasc Diagn Ther, 2016, 6(1): 78–86.
[7] BARLETTA G, DEL BENE M R. Myocardial perfusion echocardiography and coronary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J]. World J Cardiol, 2015, 7(12): 861–874.
[8] 孫秋愿, 鄒亞男. 冠狀動脈微循環功能障礙的研究進展[J]. 心血管病學進展, 2018, 39(1): 40–44.
[9] 王保平, 孫余華. 冠狀動脈微血管功能障礙和微血管心絞痛[J]. 臨床心血管病雜志, 2018, 34(10): 957–960.
[10] 王文杰, 王志梅, 郝偉. 微血管性心絞痛中西醫發病機制研究進展[J]. 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 2018, 18(72): 123, 126.
[11] 沈偉, 王邦寧. 冠狀動脈微循環障礙診治及其研究進展[J]. 心血管病學進展, 2017, 38(5): 566–570.
[12] 陳田亮, 孔令閣. 心臟X綜合征研究進展綜述[J]. 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 2019, 19(6): 100–101, 103.
[13] 陸培培, 馬杰, 馬麗紅. 冠狀動脈微循環障礙及麝香保心丸作用機制研究進展[J]. 中西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 2016, 14(15): 1741–1743.
[14] EGASHIRA K, INOU T, HIROOKA Y, et al. Evidence of impaired endothelium-dependent coronary vasodilatation in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 and normal coronary angiograms[J]. N Engl J Med, 1993, 328(23):1659–1664.
[15] SEN N, TAVIL Y, ERDAMAR H, et al. Nebivolol therapy improves endothelial function and increases exercise tolerance in patients with cardiac syndrome X[J]. Anadolu Kardiyol Derg, 2009, 9(5): 371–379.
[16] PEARSON J T, THAMBYAH H P, WADDINGHAM M T, et al. β-Blockade prevents coronary macro- and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induced by a high salt diet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 the Goto-Kakizaki rat[J]. Clin Sci (Lond), 2021, 135(2): 327–346.
[17] SüTSCH G, OECHSLIN E, MAYER I, et al. Effect of diltiazem on coronary flow reserve in patients with microvascular angina[J]. Int J Cardiol, 1995, 52(2): 135–143.
[18] MEHTA P K, GOYKHMAN P, THOMSON L E, et al. Ranolazine improves angina in women with evidence of myocardial ischemia but no 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11, 4(5): 514–522.
[19] VILLANO A, DI FRANCO A, NERLA R, et al. Effects of ivabradine and ranolazine in patients with microvascular angina pectoris[J]. Am J Cardiol, 2013, 112(1): 8–13.
[20] ZHANG X, LI Q, ZHAO J, et al. Effects of combination of statin and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in patients with cardiac syndrome X[J]. Coron Artery Dis, 2014, 25(1): 40–44.
[21] KNUUTI J, WIJNS W, SARASTE A, et al. 2019 ESC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coronary syndromes[J]. Eur Heart J, 2020, 41(3): 407–477.
[22] 郭英. 尼可地爾在改善冠脈微循環中的療效分析[J]. 中國保健營養, 2021, 31(3): 178.
[23] 詹碧鳴. ATP-敏感性鉀通道開放劑尼可地爾改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的冠心病患者冠脈微循環的機制研究[D]. 南昌: 南昌大學, 2019.
[24] 李露. 尼可地爾減輕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損傷作用的研究[D]. 十堰: 湖北醫藥學院, 2017.
[25] 王帥, 薛強, 劉毅, 等. 大樣本冠狀動脈慢血流的相關因素分析[J]. 心臟雜志, 2017, 29(2): 180–183.
[26] 李曉雅, 吳敏, 王松子, 等. 冠狀動脈慢血流及其中醫藥診療思路[J]. 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 2021, 41(5): 616–623.
[27] 徐健鑫, 杜忠劍. 活血化瘀法治療冠心病心肌微循環障礙研究進展[J]. 大眾科技, 2021, 23(4): 108–112.
[28] 王偉平, 高紅梅, 董玉江. 冠狀動脈微血管疾病的中醫治療研究進展[J].中國中醫急癥, 2021, 30(10): 1877–1880.
[29] 龍衛平, 陳劍, 何漢康, 等. 益心飲治療冠狀動脈慢血流的臨床研究[J].環球中醫藥, 2010, 3(4): 286–287.
[30] 康利銳, 袁晶晶, 阿那日, 等. 芪參益氣滴丸對非阻塞性冠狀動脈缺血疾病患者冠狀動脈微循環功能障礙的影響[J]. 中南藥學, 2021, 19(5): 1014–1018.
[31] 鐘正龍. 瓜蔞薤白半夏湯加減治療冠脈慢血流(痰濁阻痹型)的療效觀察[D]. 成都: 成都中醫藥大學, 2015.
[32] 杜海波. 麝香保心丸治療微血管功能障礙的研究進展[J].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 2016, 16(56): 34–35.
[33] 孫慶莉. 麝香保心丸治療合并高脂血癥心臟X綜合征患者的臨床效果[J]. 中國醫藥指南, 2021, 19(6): 134–135.
[34] 龔勝蘭, 范雅雯, 牟雷, 等. 中醫藥治療冠脈微循環障礙用藥規律的數據挖掘[J]. 中藥新藥與臨床藥理, 2021, 32(11): 1731–1736.
[35] 王樂琪, 張云帆, 李莎莎, 等. 丹參治療微循環障礙作用機制的“成分–靶點–通路”多層次互作網絡模型研究[J]. 中草藥, 2020, 51(2): 439–450.
[36] 張淼, 李丹丹, 馬民, 等. 基于網絡藥理學探討丹參–黃芪–川芎配伍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作用機制[J]. 中西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 2021, 19(21): 3640–3644.
[37] 熊鹿, 劉云兵, 吳屹. 銀杏蜜環口服溶液治療心臟X綜合征的療效觀察[J]. 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 2019, 19(71): 240–241.
[38] 王勃, 那威, 韓賽男. 溫針灸聯合阿托伐他汀對女性X綜合征的影響[J]. 上海針灸雜志, 2016, 35(12): 1432–1435.
[39] 董帆, 柯志福, 陳聯發. 針灸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研究進展[J]. 按摩與康復醫學, 2020, 11(2): 15–16, 19.
[40] 張耀杰, 莫霄云. 基于網絡藥理學和動物實驗探討扶脈益心湯治療冠脈微循環疾病的作用機制[J]. 廣西醫科大學學報, 2021, 38(7): 1332–1338.
[41] 潘曄, 殷佳, 蔡雪朦, 等. 基于PI3K/Akt信號通路探討中醫藥治療冠心病的研究進展[J]. 中草藥, 2017, 48(19): 4100–4104.
[42] 馬卓. 血清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在不同類型冠心病的差異分析[D]. 唐山: 華北理工大學, 2017.
[43] 李麗君, 溫子云, 何澤淮, 等. 虎杖苷經PI3K/AKT/ FoxO1信號通路抗ApoE–/–小鼠動脈粥樣硬化損傷研究[J]. 解放軍預防醫學雜志, 2020, 38(1): 29–32.
[44] 張耀杰, 朱海波, 陳建軍, 等. 基于網絡藥理學和分子對接探討雞血藤治療冠脈微循環疾病機制[J]. 廣西醫科大學學報, 2021, 38(6): 1107–1112.
陳鐵龍,電子信箱:ctlppp@163.com
(2022–09–07)
(2023–06–11)
R543.3
A
10.3969/j.issn.1673-9701.2023.19.034